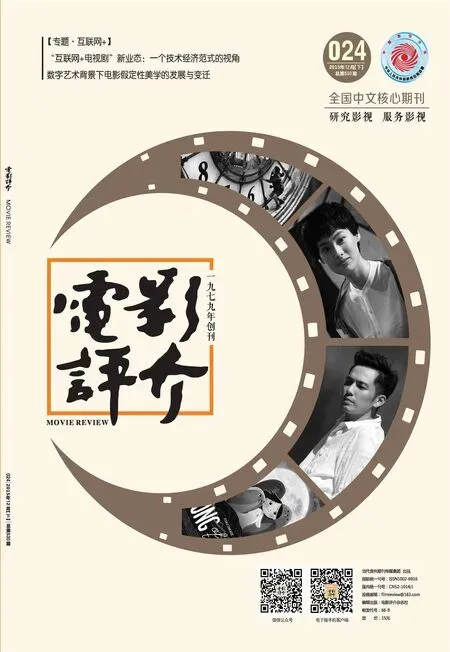藉“虚实”理论试析《吕蓓卡》由小说到电影的改编
王 静
藉“虚实”理论试析《吕蓓卡》由小说到电影的改编
王静
达芙妮·杜穆里埃因其神秘、充满悬念的小说而独树一帜。1938年出版的《吕蓓卡》是杜穆里埃的成名作,一经出版便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使杜穆里埃声名大振。小说《吕蓓卡》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手法,描写“我”与丧偶后萎靡不振的迈克西姆一见钟情。但是当“我”嫁给迈克西姆并随他回到曼陀丽庄园后,却发现自己时时刻刻生活在他的亡妻吕蓓卡的阴影当中。1940年该小说被英国著名导演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搬上大银幕。本片获得了第十三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摄影奖(黑白),全片气氛诡异迷人,是悬疑手法十分高明的心理文艺片。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集中体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独特追求。中国古典艺术普遍追求意境美的创造,以此为核心,形成民族化审美理想范式。“虚”与“实”的创构是意境艺术构成的重要内容。在艺术作品中,“实”表现为直接诉诸于人的审美感受,“虚”则诉诸人的审美想象。“实”是指具体的人、事、物的象以及由人、事、物的象所构成的艺术整体境界,常常称之为实境。“虚”是指与实境有某种必然联系的艺术想象境界,也包含蕴藉交融于实境中的特定情思,常称之为虚境。中国诗词、绘画、建筑艺术都极为讲究“虚实相生”,它是中国人独特的运思方式的鲜明体现。在具体的创作中,“虚实相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柳晓枫曾说:“虚实相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条重要原则,从虚实相生的角度研究意境很容易抓住意境的本质特征,也使得意境在各类艺术中的呈现更加具体。”[1]
一、“以实生虚,以虚促实”的魅力
在《吕蓓卡》自小说到电影的改编的过程当中,从人物层面看,吕蓓卡的“虚”以及叙述者“我”的“实”使得两个人物之间形成强烈的发差;从情境的角度出发,梦境的“虚”和现实的“实”的结合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悬念及神秘色彩愈加浓烈。由于影片不仅表现已经完成的绘画,而且还能把作画的过程作为一桩事件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就是一幅幅会动的画。因此,可以用中国绘画中蕴含的虚实相生来阐释希区柯克的改编,人物上的“虚实”和情境中的“虚实”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虚实相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人物的“虚”与“实”
小说到电影改编的基本原则是要忠实于原文,在这一方面,导演希区柯克做得很好。在小说中,作者杜穆里埃通过塑造两位女主人公的形象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一位是叙述者“我”是真实存在的;而另一位则是已经去世的吕蓓卡,她自始至终从未出现过,但是她的“虚”却不容忽略,正是由于她的“隐形”越发衬托女主人公“我”的性格特征。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情节发展,这种叙述手法类似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虚实”表现手法。
1. 吕蓓卡的“虚”
吕蓓卡是曼陀丽庄园的男主人迈克西姆的第一任妻子,在小说中虽然有很长的篇幅来描述她,但是她却从未出现过。据说她是最有魅力的女人,“我”根本无法与之相媲美。在这种情况下,就给观众留下足够的空间去想象到底吕蓓卡有多美。自从“我”来到曼陀丽庄园,无时无刻不活在吕蓓卡的阴影之下。虽然她不在了,可是无形中却仍然是庄园的女主人,控制着庄园的一切。她的“隐形”常常使作为庄园新女主人的“我”精神上备受煎熬。每次看到带有R标志的信封或者听到电话铃声,都不由得害怕起来,更不用说去触摸吕蓓卡曾经用过的东西了。例如,“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寒噤,似乎有人在我背后打开了门,引进了股冷风”。[2]此时,观众就越发地想知道吕蓓卡的音容笑貌,这样的人物设置使得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扑朔迷离,更加体现小说中神秘与悬念的主题。
此外,每当别人说起吕蓓卡时,“我”总感觉到她依然活着。一次,“我”非要弗兰克讲出对吕蓓卡的真实评价,没想到弗兰克竟然说:“她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女人。”[3]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不知所措,没想到吕蓓卡此时仍然活在每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她的忠实女仆丹弗斯太太,她的一言一行无不在强调吕蓓卡的权威。因此吕蓓卡的“虚”更加影响“我”的感受,愈发衬托出“我”的胆怯、自卑与懦弱。更为重要的是,观众心中产生一连串的悬念,到底吕蓓卡在迈克西姆的心中是什么样的位置呢?吕蓓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为何让众多的人为之神魂颠倒?当然这些问题也是“我”想要搞清楚的,显然拉近了观众与女主人公之间的心理距离。
2. 叙述者“我”的“实”
在电影中,导演希区柯克同样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电影一开头就以“我”的口吻展开叙述,让观众有种亲近感共同关注故事情节的发展。申丹提到:“第一人称叙述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以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4]因此,观众可以亲身感受到“我”的成长变化,比较容易从“我”的立场来看待问题。
与吕蓓卡不同,“我”是个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我”的形象及性格都被演员琼·芳登以其精湛的演绎呈现在观众面前。在观众眼里,“我”简单朴素,并深爱着迈克西姆,对庄园里的所有人都很友好。但是“我”极其不自信,与自信、美丽、善于交际的吕蓓卡相比,“我”怯懦、害羞、毫无交际经验。然而正是由于二人鲜明的对比恰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化妆舞会上“我”的出丑恰恰反衬出吕蓓卡的能干与精炼。这样的反差更让“我”越来越自卑。当迈克西姆首次向她求婚时,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会得到他的青睐,立马就拒绝了迈克西姆的请求。她总是怀疑别人要对她评头论足:“我想象得出客人坐车离开曼陀丽时的对话:‘亲爱的,多么平庸乏味的一个女人!她差不多没有开口说话。’接着便是我头一回从比阿特丽斯嘴里听到的那句话:‘她跟吕蓓卡多么不一样!’打那次以后,这句话老是缠着我,在每位来客的眼光和言谈中,我仿佛都看到这几个字:‘她跟吕蓓卡多么不一样。’”[5]殊不知正是由于她的朴素、天真才深深地吸引着迈克西姆。在这个庄园里她没有安全感,常常认为自己的缺点恰恰是吕蓓卡的优点,“那时的女主人无论出身和教养都同这座庄园相配,做什么事情都驾轻就熟;我每时每刻总意识到自己的缺陷正是她的长处——自信、仪态、美貌、才识、机智——啊,反正对女人说来最重要的素质全有了!想到这些,叫人丧气,真叫人灰心丧气。”[6]
总之,“我”的“实”与吕蓓卡的“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手法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化虚为实,以实生虚。虚实结合”的魅力。在电影中,希区柯克同样展现出了两个人相互映衬的效果,淋漓尽致地将两个人不同的性格呈现在观众面前。吕蓓卡的“虚”正好留给观众足够的想象空间,让大家尽情发挥想象她的美丽、精明、能干与聪慧。而“我”的“实”更能拉近角色与观众的距离,从而更加展现她与吕蓓卡的极大反差。
(二)情境的“虚”与“实”
此外,梦境与现实的结合也是该小说中一大亮点。这一结合恰恰更有助于描写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神秘气氛。在电影当中,尽管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已经删去,但是所采用的拍摄技术并不影响导演去表现神秘、悬念的气氛。梦境的“虚”恰恰反衬出现实的一些无奈与隐忍;而现实的“实”也更能衬托出“我”在梦境可以得到少许的安慰与宁静。二者的结合共同推动情节的发展,这一表现手法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虚实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梦境的“虚”
小说开头就是描述“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曼陀丽庄园:“我突然像所有的梦中人一样,不知从哪获得了超自然的神力,幽灵般飘过面前的障碍物。”[7]小说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感,同样在电影中,导演希区柯克也保留了这样神秘、恐怖的气氛。影片开头,从一片迷惘梦幻般的景色中,传来了“我”的画外音:“昨夜,我在梦中又回到了曼陀丽……”伴随着它的画面是禁闭的铁栅门,两旁杂草丛生的大道,朦胧中浮现出的府邸废墟;在这片举目凄凉之中,“我”的声音回溯着那永远不能再现的梦境。情意绵绵,无限怅惘,声音和画片情景交融,就在这平平静静的倒叙之中造成悬念与神秘感。
在影片中,有许多关于梦境的展现,尤其小说的女主人公“我”经常沉浸于梦境之中。许多年之后,她常常回忆起与迈克西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当时的心境至今记忆犹新。我仿佛还能看见那天下午挂着缕缕绒毛云的天空和卷起白浪的大海;我仿佛又感到清风拂面,听到我自己的以及他应和的笑声”。[8]出现在她梦境最多的应属曼陀丽庄园了。然而,每当从梦境中醒来,她会发现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梦境与现实的差别极大。梦境中的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虚无缥缈。当迈克西姆决定带她参观曼陀丽庄园时,她会立即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当中:“我想象自己如何在早餐后站在石阶上,眺望天色;我又想象自己挎着装满葡萄和梨子的果篮,走到门房看望一位生病的老妇人……”[9]很显然,在她的内心中已经对庄园充满了诸多幻想。可是,当她真正来到此地,一切却已物是人非:一扇扇窗凄凉地洞开着,车道显得既狭窄又荒僻,树枝倒垂下来,阻挡着去路,众多的野生植物无人修剪,又黑又丑。
此外,“我”时常会在梦境中回忆起自己过去的长相:“穿着紧身衣,一头平直的短发,幼稚而不敷脂粉的脸蛋,衣裙均不合身,汗湿的手里抓着一幅齐臂长手套,瘦小孱弱,窘态毕露,站在门槛上。”[10]很显然她对自己当初的样子并不满意。相比之下,现在的她已经成熟不少,不再像当初那样笨拙与害羞。“自信是我十分珍视的品质。我想,最终使我一扫怯懦的因素,是他毕竟依靠着我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拜托了我的自卑、胆寒和怯生的羞态,与初次乘车去曼陀丽时相比,已经判若两人。”[11]这些梦境中的回忆恰恰证明了她已经脱胎换骨。因此,梦境及回忆这一表现手法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女主人公的成长变化,与现实状况形成强烈的对比以求增加影片悬念与神秘的气氛。
2. 现实的“实”
小说的女主人公“我”经常会沉浸在梦境与回忆当中,梦中的曼陀丽庄园既宏伟又壮丽。可是她更愿意活在现实当中,尽管此时的庄园已经破败不堪,物是人非。因为她获得了比奢侈、舒服、富贵的生活更加重要的东西,比如迈克西姆对她真挚的爱以及那份珍贵的宁静。所有这些都是真实可靠的,她特别渴望过这样的日子。在曼陀丽庄园被烧毁之前,“我”常常生活在怀疑与恐惧之中,精神也因吕蓓卡的“隐形”和女仆丹弗斯的鄙视备受煎熬。但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她感到非常放松。总之,现实的“实”与梦境的“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将人物的性格变化表现的淋漓尽致,让观众与“我”一起体验这份变化。
除了精神上的放松之外,“我”与迈克西姆之间纯洁的爱情更加坚实可靠。相比之下,迈克西姆与吕蓓卡之前的爱情显得那么虚无与虚伪。在很多情况下,拥有财富并不意味着拥有真挚美好的爱情。只有当对方遭遇灾难或陷入困难及贫穷境地时,才更能彰显一方对另一方的真实情感。在现实生活中,“我”与迈克西姆两个人住在普通的房子里,没有仆人,必须自食其力,可是两个人觉得非常幸福,而且这份幸福真实可靠。“我们留下的是一生中的一个时刻,是思想和心境,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12]因此,无论现实多么残酷,可是这份简单平凡的幸福仅属于他们两个人,精神上的财富远远比物质上拥有的更加珍贵。
以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虚实”理论视之,导演希区柯克在电影中的改编手法充分体现了“虚”“实”的魅力。从意境审美的角度来看,小说与电影所体现的意境美相同。更为重要的是,原文本之“神”——即独特的神秘、悬念的主题意蕴在电影中得以完美体现。
结语
以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虚实”理论观照《吕蓓卡》由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即能看出导演希区柯克在把握原文本之“魂”时的独特才能。改编中创新固然重要,但是忠实于原文本之“魂”更为可贵。虽然小说与电影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任何文本都并非孤立存在,小说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两者互相借鉴、互相促进。以“虚实”理论视之,二者所体现的意境美相同。此外,以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虚实”理论观照《吕蓓卡》自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以期体现中国古典美学对西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论阐释意义,同时着意突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互补态势与共同促进。
[1]柳晓枫.虚实相生——意境的审美特质[J].时代文学(双月上半月),2009(6):61-62.
[2][3][5][6][7][8][9][10][11][12](英)达夫妮•杜穆里埃.蝴蝶梦[M].李永,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1-183.
[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38.
王静,女,河南开封人,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艺美学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