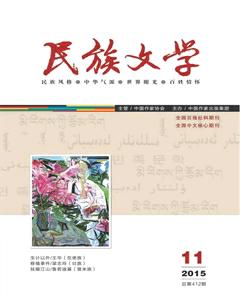如影随形
罗勇
雨一场接一场地下,雨水浸透了老屋的墙,墙就出汗一般冒出涔涔的水珠,终日不干。等我发现时,挂在墙壁正中的妈妈的遗像,已经湿透了,浆糊似的黏住相框玻璃,妈妈的面容有些模糊了,我赶忙掏出手机拍照。挂在墙壁上的妈妈,从此住进我的手机里。
如果不是连续不断的雨,如果不是老旧的墙壁抵挡不住雨水的浸淫,如果不是水渍浸湿模糊了照片,我根本不会想起拍下妈妈的遗像来保存好。妈妈的遗像依然挂在墙壁的正中间,面对空空荡荡的房间,十四年不曾挪动一寸地方。一颗铁钉和她朝夕相处,互相牵挂了十四年,钉子锈了,瘦了,妈妈在冰冷的玻璃下面,望着阒无人迹的房间,一丝不苟地慈祥了十四年。
十四年里,我们只在清明节这种特殊的日子里成群结队、浩浩荡荡赶回老屋,在妈妈的遗像下面扫干净一片足够磕头的地方,跪下僵硬的膝盖,惯常地祈求另一个世界里的妈妈保佑我们得到想要得到的一切,满足依靠我们自身力量无法实现的欲望。相框里的妈妈,抬头看她一脸慈祥,不看她也一脸慈祥,一副普度众生的慈悲模样。含辛茹苦养育了四个儿女的妈妈,一生体弱多病,早早离开了人世,因为死亡,被儿女们凭空赋予各种无所不能的神圣力量,并且必须义不容辞地庇荫后人。
磕完头,大家在妈妈的遗像前聊天吃饭喝酒,喜怒哀乐都和妈妈无关。人人手里拿着几百万像素的手机,发短信发微信,打游戏看新闻。即便想起拍照留影,镜头里,妈妈的遗像成了标志性的背景,是我们清晰的嘴脸后面模糊不清的必要点缀,向旁人昭示我们的孝心,无言地见证我们每一次热闹的到来和匆忙的离去。我们挑剔着照片里谁的脸被挡住了谁的眼睛闭上了谁的笑容不自然。没有人想起给妈妈的遗像拍一张清晰的照片,没有。
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保存着许多儿女们的照片,宠物的照片,景点的照片,甚至设了密码的美女照片,十几G的手机内存,可以容纳成千上万张照片,如此巨大的空间,唯独没有一寸属于妈妈。我好像还听谁说过,给坟墓和遗像拍照是十分不吉利的事,会折了生者的阳寿。这是谁说的呢?真有人对我说过吗?我想不清是道听途说还是我为自己的自私冷漠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想。十四年里,妈妈留给我的记忆,只剩一张挂在老屋里的遗像和一座荒草萋萋的孤坟,坟墓埋葬妈妈的身体,空寂的老屋,也仿佛一座荒凉的坟墓,埋葬了妈妈辛劳的一生和她所有的往事。
雨过天晴,我赶回老屋把妈妈的遗像小心取下来,放太阳底下晒干,相纸龟裂,断开,片片剥离,留下让我触目惊心的空白,妈妈的面容愈加模糊不清,像极了我对妈妈斑驳的记忆。那慈祥的笑容慢慢消失在玻璃板下,仿佛退回到了时间的最深处,回到妈妈的坟墓里,那亲吻过我的唇,为我流过无数次眼泪的眼睛,都已风化成泥,融入大地,寻无来处,找无归宿。
我为我拍下妈妈的遗像倍感庆幸。我把手机屏幕上女儿笑颜如花的照片隐退了,换成妈妈的遗像,每次开机,黑色的手机边框陪衬着妈妈的黑白照片,饱受诟病的山寨智能手机,顿时充满从未有过的庄重,尊贵感油然而生。
从拍下妈妈遗像那天起,手机对我有了非同凡响的意义,我改掉了胡乱把手机揣裤兜或乱扔乱放的习惯。我的手机不在手心里握着就在胸口贴身的口袋里放着。有时候不方便带身上,就找一小块干净的地方,铺上洁白的纸巾,一头垫高了,再把手机放上去——妈妈患脑出血离世的,生前常常彻夜头疼,要将枕头垫高才能缓解症状。妈妈平生爱干净,怕吵闹,爱盯着我们看……我极力在我的生活环境里营造妈妈喜欢的氛围——从把妈妈的遗像拍进手机那天起,我觉得她活过来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住进我的手机,终日陪伴着我。我晚上关机睡觉,妈妈安然入睡,清早,手机闹铃把我吵醒过来,屏幕上的妈妈,像我小时候一样不厌其烦地催我起床。
我和妈妈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我摁亮手机,带妈妈看我宽敞的办公室,她一直希望我出人头地,让她看看我坐的位子,我为之摸爬滚打许多年如今又觉得容不下我的位子,她一定会为我骄傲——她去世的时候,我还是一名边远乡镇的乡村医生,现在,我考进了公务员队伍,离开农村,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大楼上班。这在妈妈的愿望里是没有企及的,所谓出人头地在她的想象里就是不当农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已超越了她的预期很多,我还打算继续超越。我信心满满地和妈妈对视,她慈祥淡然的眼睛陡地照见了我的俗不可耐,她的目光穿越十四年的岁月尘埃,落到我脸上,温暖如初,妈妈的眼里,无论富贵贫贱,我永远是她长不大的孩子。我把妈妈的脸贴在我脸上,泪雨滂沱。俗世的累已累了我很多年,我竭尽全力追求的一切,并没有给我带来预想的幸福,而此刻,当我与妈妈对视的一瞬间,我突然如释重负,幸福从天而降。
我摁亮手机,带妈妈看我的家。妈妈的家被时光的河流带走了,我希望我的家能让她安心,放心,开心。这个家,在繁华的城市里只能算蜗居,我和妻子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同舟共济,开心,忧愁,快乐,悲伤,深情相拥或怒目相向,亲手将岁月的挂历一页一页撕下来扔回过去,再将新鲜的日子一页一页翻开展现给未来。我们在七十多平米的空间里活,也可能在这里死,未来的某一天,墙壁的正中央或许会挂上我们的遗像,这房间或许会成为一间落满灰尘、门可罗雀、人迹罕至的空房吧。
我摁亮手机,让妈妈看我的女儿,那长得极其像我的小人儿,我见证了她的生,她必将见证我的死。我为她整理襁褓,拥她入怀,用生命的体温呵护她成长。她会为我整理遗物,把我放入棺椁,连同她的眼泪和悲伤一起埋掉。妈妈和我身上发生过的一切,都将在我和女儿身上重演一遍。只是不知道,女儿的手机里,会不会为我的遗像留下一寸空间。
黑夜里,我独坐书房,关了灯,摁亮手机,默默和妈妈对视,我让她看我头上的白发,眼角细密的皱纹,逐渐后退的发际。她心中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已被岁月的手拉扯成人,和她差不多一样老了。像她当初一样,整日为生计奔忙,为女儿操心。失眠,食欲减退,血压升高,偶尔头昏眼花,还没来得及好好规划一下人生,年轻就渐行渐远,衰老已如期而至。我喃喃向妈妈倾吐,她默默静听,如同许多年前那些伏在她膝上诉说,扑进她怀里痛哭的夜晚一般,心静如水,幸福和温暖却重峦叠嶂包围着我。
我告诉手机里的妈妈,我不死,她就一直活着,温暖我的白天,照亮我的黑夜,直到我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