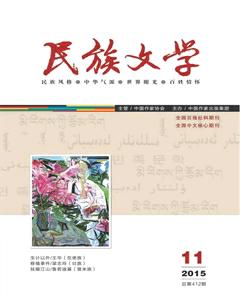1929年的那次比武
1929年的那次比武,是在后秋里。
石佛镇外的田野上,是那种五谷丰登、颗粒归仓后的空旷,鸟儿格外多,迎风展翅,上下翻飞,不知疲倦地展示着丰衣足食后快乐的形姿。鸡鸭鹅不慌不忙,拣拾着散落在田里的食粮,没有丝毫往日里你争我夺甚至为一只小虫、一粒谷物大打出手的行为。家畜们默不作声,很安心,自由从容地在田地里有滋有味地啃食着稻茬上新发的嫩芽。坐在丰收图景中的石佛镇,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你卖我买,百业兴旺,街巷里氤氲着恬静祥和的气息。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多年后还让石佛镇人津津乐道的事情——比武。按说,比武在石佛镇本不是什么让人大惊小怪的事,但从人们延续至今的言说中可以看出,1929年的那次比武非同以往,亦不同于后来。
以往的比武与后来的比武,虽在场地、用时上有时不同,但类型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双方通过交手比武:两人一搭手,一发力,一人飞出数米外,滚落在地;或两人刚一搭手发力,同时蹿了出去,便不再打了,相互报了名,拱手告辞;或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战好几个回合未见分晓而又互不言罢。比武多以拳为主,外家拳、内家拳均有。在南小街的清真寺主要是回回们,他们练的多为查拳、八极拳、形意躬身立拳;而北小街石佛寺里的僧侣多练少林拳,有时也比器械,许是怕生出事端,不让挑选剑、刀、枪等易伤人的器械比。回回们平时练基本功时,主要是跟陶阿訇练弹腿和传把,所以,清真寺里比器械时,常比大杆子:只见那人持杆一刺,这人一抵,那人身子大震,手里杆子落地,立刻抄起再刺,这人飞速退开两步,静等那人下一步。来了,又一抵,那人杆子掉了,这人的杆子擦着那人的脖颈儿压在他的肩上。结果一目了然。比武时,拳脚动作快,让人眼花缭乱;器械生风,常常惊心动魄。禁用阴狠毒辣之招以免伤人,以至比武多半在短时间里难以分出高下。在清真寺比武,偶遇斗狠逞强之人,陶阿訇会及时阻止,好言相劝,免得伤人结仇。唯有一次,一位自北去南京打擂的途经石佛镇,比武时一时图快而连下重手,危急时刻,陶阿訇接过招式,见其无收敛之意,便一个燕子抄水,扭胯发力,用挑领一式将其挑飞出丈外,而就在其将要跌落的一瞬间,陶阿訇人已赶到,轻轻一拉,止了他的摔倒。那人顿时醒悟,连忙拱手致礼。
比武自然给石佛镇人平静的生活带来了兴奋点,也留下了话题,但时日总不会很长,随着为了生计而奔波于南京、镇江、蚌埠、汉口贩卖皮张的人们带回来的新消息,随着官道上南来北往的人们带来的逸闻趣事,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就由新变旧,自然淡化消逝在苍茫的岁月里。
1929年的那次比武却不然,它一直晃动在石佛镇人的记忆里,以至于我刚记事时就听到人们对当年事件绘声绘色的描述。少年时的我更是常常缠着祖父旧话重提,他总能不厌其烦地追溯起来……
比武是在清真寺的陶阿訇与留居石佛寺的今空大师之间进行的。
陶阿訇身材高挑,面容白净瘦削,骨骼清晰利朗,手指纤细,没有一个老茧,仿佛古书里的上将军,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样,只是慈眉善目之中还有一丝似有非有的光亮,如下雨前迎风而来的一点潮气,让人心生敬畏。
今空大师身材笔挺,身形壮实,大脸盘,络腮胡,一双大脚让人称奇,大眼睛里的淡然空寂之光难以隐去敏锐犀利之神。他是山东口音,据石佛寺住持说,今空大师是在云游之中留居石佛寺的。
陶阿訇怎么都没想到,正是此前他于危急时刻那难得一露的挑领,让碰巧打此路过的今空大师顿生留居石佛寺之意,扯出了一段经久不息的话题。
比武分四场,清真寺与石佛寺各两场,均为文比。何为文比?多年后,石佛镇人还在为当年比武者之间不见刀光剑影,不见闪转腾挪,不见交手的比武啧啧称道。
第一场在石佛寺。比什么呢?按之前约定,客随主便。事先不说,陶阿訇也不知道。从南小街到北小街,路程不远,经过一条大街,过了一方古砖井,就到了石佛寺门前的小广场。
那天早晨,天高云淡,陶阿訇头戴小白帽,身着青灰布长衫,脚穿白边黑布鞋,健步向石佛寺走去,一副干净利爽的扮相。刚爬上房顶的太阳斜照出陶阿訇英武、沉稳、自信的剪影。
路上,有人提醒陶阿訇,说石佛寺里两只四眼大黑狗凶猛无比,已多次伤人。陶阿訇脸上并无明显反应。在将至石佛寺时,他弯腰从街边拾起一小片甘蔗皮,一分,两头一掐,两根尖细如针的物件便藏于指间。
见陶阿訇走来,早已候于寺门前的人们自动闪出一条通道。有人上前击打门环,门开人入。突然,两只大黑狗嗖地一闪,低吼着迎面冲了过来,人群在惊叫声中炸开。陶阿訇不动声色,等那两只四眼大黑狗扑到跟前,他一弹指,在人们毫无觉察中将细小甘蔗皮分别打进两只狗的鼻孔里,眨眼间,那两只四眼大黑狗调头打转,由低吼向呜咽急转直下,在一串串变调失声中落荒而逃。
人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不知其缘由。这时,石佛寺住持匆匆赶到,身后跟着今空大师。待住持与陶阿訇互致问候后,今空说:“陶阿訇,刚才不在比武之列吧?”陶阿訇微笑道:“当然。悉听尊便。”
陶阿訇话音刚落,今空猛地扬手向天,“陶阿訇你看。”循着今空手指的方向,只见一只瓦灰色的鸽子一头扎了下来。人们一阵惊嘘。
陶阿訇看着住持痛苦的表情,良久未动,再三思考后问今空:“我可以选别的吗?”今空说:“你可以不比。”
陶阿訇轻轻叹了一口气,随后在石佛寺院子里的一片黄土中挑了一个小坷垃,用手指在四周打磨了一下,走到住持面前,小声说了句什么,便一抖腕向天空射去,只见一只白鸽扑棱着下坠,落在了一条树枝上,少顷,又扑棱棱地向空中紧接着向院外飞去,一根漂亮的尾羽摇晃着飘落在陶阿訇与今空的面前。
石佛寺住持向陶阿訇躬身立掌,说:“输赢已有分晓。”
今空无语。他站在寺院里望着陶阿訇远去的背影,忘记了送行。
在石佛寺的第一场比武,当时并未由谁言明结果,陶阿訇与今空两个人谁也没有半点声明,甚至没有异样的表情。因而人们当场并没有明晰的判断,甚至一部分人还以为陶阿訇输了,因为他没有像今空那样将鸽子打下来。同时,出乎人们意料,第一场比武就这么结束了,时间过短,过程太简单,没有来得及给人以感观上的刺激或震撼。倒是两只四眼大黑狗变调失声落荒而逃,并且从此凶猛不再,给以后人们心目中的第一场比武平添了些许传奇。
四十年后,我第一次背起书包跨进了石佛小学的大门,那个大门还是四十年前陶阿訇与今空大师在那个秋天进行第一场比武时的石佛寺寺门,门前的石狮子刚刚被“文化革命者”砸得伤痕累累,但厚厚的门板、实实的门柱、深深的门槽、悠悠的门楼依然完好无缺,只是岁月在上面以斑驳的印迹记录下诸多历史的映象。作为一个懵懂少年,我自然不知怎么依据石佛寺住持之语去评判陶阿訇与今空大师谁输谁赢。
五十二年后,我大学毕业又回到了原为石佛寺的地方,曾经的石佛小学已为石佛高中。我早已不再纠结谁输谁赢了,因为今空大师从一开始就已经输了。我祖父曾告诉我,陶阿訇跟石佛寺住持小声说的那句话是:“取其羽,不取其命。”
第二场比武在清真寺。
第二天午后,今空大师一身素装随石佛寺住持来到清真寺大院。他目光有神,环视四周,一副揽物于胸坦然无束的样子。按客随主便的规矩,先由陶阿訇选项。但还没等陶阿訇说明,今空突然向大殿蹿去,陶阿訇脸色陡变,二话没说,飞身箭步跨上大殿前的廊台,居高正色俯视,止住了已在台阶上的今空。清真寺里的回回们一阵骚动,欲围上前,陶阿訇用手一止,人群便安静了下来。
今空仰起脸来,锐利目光与陶阿訇的正色碰出了只有他俩能够听见的声响,今空笑了,“陶阿訇,我知道贵教的规矩,我怎么能进大殿呢?我是试试这青石条承不承重。”说罢,今空向陶阿訇立单掌,随后转身下了台阶。只见第三级台阶上刚才今空脚下的青石裂开了一道清晰新鲜的曲折缝隙。
陶阿訇稍加思忖便从大殿前的廊台上走了下来,打量了一下缝隙,冲着大院中的今空道:“好脚力。要的正是这道印子。”陶阿訇迈开步子向正门走去,脚步没有一丝慌乱,小白帽与青灰布长衫在秋天的午后显得从容镇定。
陶阿訇走到大院内侧的照壁墙前,沉吟片刻,扎下马步,凝力发于单掌,单掌形如弯刀,凌空劈下,挖向照壁墙,手起掌落,照壁墙上被生生挖出个手窝。
人们络绎不绝在两边仔细看着,与第一场比武似乎戛然而止不同,在清真寺的那场比武聚集了人们的心神和气力,比中静观,比后也没有喧哗,人们看着,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在心里回味着,琢磨着,品评着。
石佛寺住持面向陶阿訇躬身立掌,说:“论武,难分伯仲;论礼,今空欠缺。”
今空大师留在大殿前台阶上的那道缝隙与陶阿訇留在照壁墙上的那个手窝保存了整整四十多年,一直到1970年春天,石佛镇清真寺毁于造反派之手。
因我家住在石佛镇南小街,与清真寺斜对面,于是我自幼便如鱼得水地在清真寺里疯玩。最初是被我祖父牵着小手来到青石上,祖父指着,讲着,那道曲折的缝隙早已陈旧,几棵小草从石缝里坚决地钻出来,站立起身子,很挺拔,被青石衬得嫩绿逼眼。无独有偶,照壁墙上那个手窝里竟还积累了些许雨水,雨水之下还能积灰成土,几株细小的草居然临风玉立。在那毫无禁忌的年代里,真切地触摸着这些仍留有温度甚或散发着体能和生命力的物件,听着已显零碎的叙说,仅是感到好玩,没有任何高度、深度,甚至没有刻度。多年后长大成人,眼见得建于康熙年间的清真寺销声匿迹,连同寺内的古井、古碑、铜壶和《查拳谱》《七字梅花剑谱》《十路弹腿要诀》,陶阿訇的手窝与今空大师的石缝一并消逝于如烟往事之中,总会情不自禁地生出一阵又一阵揪心的疼痛。
第二场比武显然调动起石佛镇人空前的兴趣,虽然更多的人并不知晓伯与仲,但“难分伯仲”之意大家是明了的,因此,人们以更大的热情与关注度期待着第三场比武的到来。
第三场比武是第三天傍晚在石佛寺里进行的。那天,落日硕大,映衬得西边天际红霞遍野,如火烧,如血洒。天空中不时有雁阵飞过,偶留有三两声辽远的鸣叫,如此景象,颇有几分壮烈与悲情。陶阿訇仍是头戴小白帽,身着青灰布长衫,脚穿白边黑布鞋。浓郁的秋天晚霞为陶阿訇,也为近在咫尺的石佛寺披上了中正肃穆的色彩。
石佛寺住持早已站在大成殿前等候。台阶下,今空大师一身青灰素衣,绑腿打得很缜密很严实。见了面,相互致礼,今空说:“陶阿訇一袭长衫,以不变应万变,大将风度。”陶阿訇应道:“承蒙夸奖,教门中人,遵圣训,守准则,交友而不树敌,即便贵教信士,能和平共处,亦当为手足兄弟。以武切磋,行为无欺,约定不爽,谈不上变与不变,更谈不上大将风度。”
今空一直看着陶阿訇,眼睛里闪着光亮点头称是。
众目睽睽之下,今空从大成殿的台阶下突然起身,向大成殿疾奔,在最高一级台阶上,双臂高高扬起,整个人竟然像只风筝飞升起来,在挑檐处,今空摘下一只正在秋风中悠然响着的风铃,旋即如一枚树叶悄然飘落。今空这一飞身高处摘风铃的动作,一气呵成,在场观看之人惊讶闭声后,不禁齐声叫好。
陶阿訇没有拾级而上,而是信步绕到大成殿的西侧,人们也尾随而至,只见陶阿訇轻轻吸了一口气,飞身向上一跃,离地面一人多高,空中转过身来,双臂展开,两手沿隙寻缝,后背贴在了大成殿的西墙面上,像只壁虎吸附在墙上,更像幅画悬挂在墙上。所有的人都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眼前这一亦真亦幻的场景。此时,残阳斜照,镇静如初的陶阿訇尽染在瑰丽的晚霞中……
无疑,第三场比武将1929年的那次比武推向了高潮。石佛镇人大开了眼界,通过对照比较,人们切身感受到了“不同”的魅力。如果说第一场比武比的是点功,求的是适逢其会,方能指哪打哪,在哪打哪,需得心开眼明手快;第二场比的是硬功,意导气,气沉丹田,气导力,力于一点;那么第三场比的就是轻功了,束身而起,起无形,藏身而落,落无迹,旁观者怎么都无法领会这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化虚的要旨。回想以往的比武场景,顿觉单调,在往后的时日里再看比武,颇感贫乏简陋,武术的内涵与风貌已难再现。
多年后,我问及祖父当时的所见所闻,祖父仍很感念:“听话听音,走路走径。高人与高人比武,看似简短,可一点都不简单。真主恩典,石佛镇的回回们有个陶阿訇。”祖父还向我讲了陶阿訇一件事,解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惑。陶阿訇手指纤细,手上无茧,看似有别于练武之人,殊不知他打小就苦练着指功,硬壳退了一层又一层,他本身就是精通医术的先生,一直坚持边练功边用中药水浸泡。一次,陶阿訇去开封探望河南贡院的同窗,恰逢他家来了位北方的客人,得知陶阿訇练功,那人便提出比武,陶阿訇谦让,那人不依不饶,陶阿訇便不经意在友人家墙上一攥,将挂物件的洋钉拔了下来,然后不往原来的钉孔上插,而是错开钉孔,手一拧,洋钉就进了砖里。看罢,那人再不提比武之事。
原来,第三场比武陶阿訇挂在大成殿西墙上,不仅是他轻功使然,亦因指功了得,硬是把指头扣在砖缝里撑住了身体!
石佛寺大成殿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还在做石佛高中的办公室,在石佛高中工作的那几年里,我经常在傍晚时分借着一分空暇与几分兴致,闲庭信步走到办公室西侧,面对余晖中的西墙,遥想五十多年前的那次比武,恍若穿越,自己竟也成了众多观者中的一员……
第四天夜晚,在清真寺院内坐北朝南的古兰书屋里,陶阿訇与今空大师要进行第四场比武了。
书屋内墙面上垂挂着古琴与箫,这本是陶阿訇在古兰书屋教授汉字、阿文、算术、自然课目之余用来教授孩子们的,此时,悬琴而生静意,室内未掌灯,屋外的月光轻轻飘来,静得能听得见一根针落地的声响。安静,安静,从清真寺弥漫而起的安静之气笼罩着月光下的石佛镇。
陶阿訇伫立窗前,一手背后,一手轻放胸前,凝望月亮出神。一阵细微声从远及近,他知道是今空来了。
古琴音起,松沉而旷远,余韵细微悠长,时如人语,可以对话,时如人心之绪缥缈多变,悠悠不已中,凡高山流水、万壑松风、水光云影、虫鸣鸟语及人性之理尽在其中。
继而,箫声绵绵,时而低沉委婉幽幽,似远在深山若入幽谷的空明;时而悠扬流畅朗朗,鸣声起落现隐,印照着盘旋顾盼的心境。
那夜,除陶阿訇与今空大师外,整个清真寺再无他人。从古琴《流水》始,接下洞箫《平沙落雁》,最后琴箫合曲《梅花三弄》终,以至余音袅袅,丝缕不绝……
后来,我祖父在为我就第四场比武事宜解难答疑时,用的是陶阿訇当年的说法:武即琴,武技如琴技,都是活物,二者相通,琴弹人,而非人弹琴,拳练人,而非人练拳。我祖父面露几丝神秘之色,“这里有嘎尔德(奥秘)。陶阿訇讲,比的是弦外之音。”原来我对第四场比武的深意远未参透,以暴虐好杀之音置人于死地的担心就此画上了句号。
真相不久即大白。
今空大师并非云游四方的出家人,而是正遭追杀的军官,途经石佛镇,恰逢有人比武,生死之间,正欲挺身而出,不料陶阿訇先他一步。挑领一式刻骨铭心,搅得他寝食难安,索性留居石佛寺,说通住持,约定后秋比武一事。
我祖父说,今空大师是山东德州人,真名叫金保,字道恒。1933年春死于喜峰口长城与日军激战中。
1929年的那次比武,以琴箫合曲后,今空大师趁月色而去,陶阿訇相送两程,再目送于夜色朦胧中而告一段落。
但由此而引发的事情及话题远未结束。
十年后,石佛镇回回中出了陶孟璜、金玉明、常侠彬等古琴名师。
十五年后,石佛镇回回中出了白云启、杨正昌等武术名家。
八十六年后,石佛镇回回中出的一个写字人,忆及家族珍传的负重回声与斑驳故迹,又念起茫然无际的未来,西望长嗟,满襟肃然,便举意写出了这桩老事。
责任编辑 石彦伟
责编手记
一阵苍茫烟尘过后必然在空气中留下些许熟稔的气息,沉落在碎石片瓦中,掩埋在老人漫漶不清的追忆里。有人将此遗忘,有人将其视作边角沉渣,不予理会,而胡亚才却把这些零碎的纪念拂去浮灰,引以为宝,即便那些青石、照壁上的历史旧迹已荡然无存,但凭着祖父的星斑讲述,凭着一份作家的敏感与担当,竟还真的写出了满满这么一篇,且又是悬念递进,妙处迭出。比武已非新鲜事,但拳脚背后更为重要的人的精神气节、情怀境界、信仰素质的比量,经久不衰,诱人深想。
胡亚才的散文,历来是挚情于中原民族杂居地带之掌故,家族文化之传习的,如若说先前篇什多讲回民内部之风尚,那么这一篇则用力于回族穆民心灵节操的外化,即对本民族以外的世界所产生的交叠、碰撞与润物之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