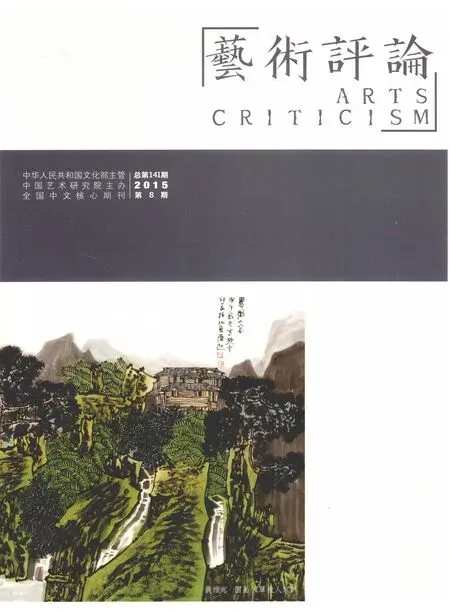当迪伦马特遇到蓝天野
——看人艺演出话剧《贵妇还乡》
彭 俐
当迪伦马特遇到蓝天野
——看人艺演出话剧《贵妇还乡》
彭 俐
知名的戏剧作家与导演在文本中神交,在舞台上相会,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而令观众格外好奇,当瑞士的迪伦马特遇到中国的蓝天野时,北京人艺的铁杆观众蜂拥而至。除了迪伦马特的粉丝、蓝天野的拥趸以外,还有主演陈小艺、濮存昕、张志和等人的戏迷,共同沉醉于《贵妇还乡》的悲喜剧色彩之中,感受首都剧场狂欢之夜的盛况。这是2015年初夏之际,该剧在时隔33年后的又一次亮相。执导这部剧的88岁高龄的蓝天野先生,无意中创造了一个中国话剧舞台导演的高龄纪录。
幸亏在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上,有一个绚丽迷人的戏剧舞台,它像UFO(不明飞行物)一样的神秘莫测,又似万花筒一般的曼妙神奇,伴随夜幕带给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以欢愉和惊喜。那些跨地域、跨国度、跨文化、跨语言的戏剧家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打破物理意义上的时空界限,在艺术层面上背靠背地联手合作而毫无障碍,做到彼此契合乃至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此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迪伦马特故去了(25年前,即1990年),他那奇葩一般的荒诞戏剧却不会在戏剧园地上荒芜,纵然欧亚两个大陆相距遥远,但两者之间戏剧移植、嫁接的种子生长繁茂,因为今日中国——蓝天辽阔,沃野千里。
剧作家迪伦马特出生于1921年,导演蓝天野出生于1927年,前者比后者年长6岁,两人堪称同时代人。除了戏剧创作以外,迪伦马特热爱美术,大学毕业后曾在苏黎世《世界周报》做过美术编辑;除了演戏、导戏以外,蓝天野喜欢绘画,曾向李苦禅、许麟庐两位先生学艺。而有关导演迪伦马特的名剧《贵妇还乡》的最初动议,还有一个趣话。当时同为少壮的蓝天野和黄永玉(1924年出生,小迪伦马特3岁,长蓝天野3岁)曾在一起聊天,竟然都对迪伦马特倍感兴趣。黄先生对蓝先生说:什么时候你能导一出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呢。——这一戏言,真就成戏。如今,我们大家不是都在饶有兴味地观看和谈论迪伦马特的这部天才戏剧作品吗?
凡是看过话剧《贵妇还乡》的人,恐怕都会惊异于迪伦马特的天纵之才。天才的戏剧作品带给人天生的好感,并让人产生追慕其辉煌足迹、愿做“青藤门下牛马走”的冲动。于是,便有了写出“闲人三部曲”——《鸟人》《鱼人》《棋人》的戏剧作家过士行。迪伦马特,是顽童式的戏剧天才,恶作剧式的哲学家,荒诞式的布道者,调侃式的神父。他的剧作善于夸张,却讲究分寸;长于渲染,而张弛有度;他能够巧妙地处理故事与人物的虚实关系,在营造喜剧氛围的同时调动悲剧因素,孕育荒谬于神圣,陶铸怪诞于庄严,酿造惨痛于欢悦,披露死讯于新生……总之,他既能让你喜极而泣,也能使你兴尽悲来,在悲喜之间坐过山车,在忧乐之中乘冲锋艇。
剧作家反映生活,各擅其能。
如果我们将剧作家比作镜子的话,那么瑞士的迪伦马特就是典型的哈哈镜(让镜中人的面相、身体、思维和情感扭曲,变形,既滑稽又可悲,既荒唐又有趣);俄国的契科夫是显微镜(让人物性格和心理纤毫毕现,显露无遗);美国的奥尼尔是穿衣镜(让每个人都能照见自己,同时窥见站在自己身边的人);德国的布莱希特是多棱镜(让人看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中国的老舍和曹禺是夜视镜(无论微光夜视镜还是红外夜视镜,都让人在黑暗中看到人性美和生活的光亮,譬如《茶馆》和《雷雨》);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莎士比亚和更早期的古希腊的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则是望远镜(让人看到人类栖息地球的广阔景象和辽远的地平线)。导演选择剧作家和剧本,口味各异。而选择剧作家和剧本就像选择终身伴侣一样,需要格外谨慎。
一个好的导演总能够凭直觉发现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伴侣”,而找到自己一生痴迷、钟情的“心上人”何其难也,因为可供选择的有分量的剧作家和作品实在不多,而原创戏剧作品又难觅佳作。鉴于话剧文本堪称标准的文学读本,因此阅读话剧剧本的快感与陶醉,若不能在观赏舞台话剧的时候有所提升的话,便是话剧导演和演员的失败和灾难。反之,则是编剧、导演、演员和观众共同参与的戏剧盛宴和夜晚狂欢。
导演本身的角色定位决定了舞台戏剧的成败。倘若角色定位有误,则后果不堪设想。导演可不能有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生猛霸道,取代编剧和演员没得商量。越俎代庖者被人耻笑,喧宾夺主者尽显粗俗,李代桃僵者表现拙劣,偷梁换柱者于心何忍。导演是乐队指挥,是球队教练,是婚礼主持,但绝不是首席小提琴,也不是主要得分手,更不是新郎或新娘。
话剧看得多了,就会发现导演与剧作家有三种勾连方式:一是肩扛;二是手挽;三是脚踩。有的导演用自己宽阔、坚实的肩膀,扛着剧作家攀登;有的导演用自己友善、热情的手臂,挽着剧作家同行;有的导演则用自己轻薄、粗糙的两脚,踩着剧作家飞升。
今天,我们眼见的情形是,迪伦马特的身材略胖一些,而蓝天野的双肩略宽一些,尽管扛起来有些沉重、费力,但是导演蓝天野还是扛着剧作家迪伦马特在北京的夜幕下行走。于是,迪伦马特的文字鲜活地站立起来,重新排列组合,有了生命的热度和体温,也有了脉搏和呼吸,眉目传情而动作潇洒……迪伦马特在不经意间走进了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现实,正如导演蓝天野所说:“迪伦马特说自己不是荒诞派。但他的创作确实很怪异,人们总能从他的戏剧里感受到今天的现实社会,引起深思和震撼。”
艺术家蓝天野导演的这部话剧《贵妇还乡》是一种还愿,是中国戏剧人向故去在20世纪、却依然“活”在21世纪的德语剧作家迪伦马特的问候和敬礼,也是蓝天野本人和他的好友黄永玉的夙愿成真。而迪伦马特理应受此礼遇,当之无愧,他在哲学层面拓展了戏剧内涵,在美学范畴丰富了戏剧文化,在社会伦理学领域提出了尖锐问题,在舞台艺术空间指明了一种可能性——悲喜剧的潜质无穷。而蓝天野的执导风格秉承了焦菊隐所创立的人艺特有的舞台风范,雍容典雅,端庄迤逦,风流蕴藉,浑然大气,以华夏民族气质和传统文化艺术为底色,格局与境界自是不同。无论是贵妇——复仇者克莱尔的出场之雾气氤氲,还是终极审判时的“罪人”伊尔的棺椁隆升,都具有中国古典艺术所推崇的写意味道,场景一出,意境迷离……一位饱经磨难的妓女仿佛从仙境中走出,而一个下地狱的亡灵在音乐伴奏下被高高托举……但见整部话剧——交响乐般的起承转合脉络清晰,剧情仿佛河水在流动中浪花迭起,演员的阵容庞大各司其职只因调度有方,每一人物处理时的表演力度分寸得当……所有这些,全都仰仗88岁耄耋导演至少六十多年舞台经验的积累和沉淀。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叹,人艺舞台导演的老黄忠不仅身体矫健,而且身手不凡。
从编剧的角度来看,迪伦马特遇到蓝天野是幸运的。后者将前者《贵妇还乡》的精神内核凸显,同时充分利用舞台的优势营造剧作家想要表达的梦幻的现实空间:居伦城是邪恶之城,瘟疫之城,鬼蜮之城,却也是一个足够娱乐、欢欣,并带有迷失与惆怅的迷宫,令人流连忘返。原来一部戏剧也可以这样好玩,有趣,痛快,开心!把人性恶推向极致的时候,极端状态的人物和事件就会层出不穷,人类在生命安全和利益保障受到威胁的极限环境下便会变得十分荒唐、荒诞与荒谬。迪伦马特与同是德语作家的布莱希特趣向相反,却又异曲同工:布莱希特劝善,迪伦马特惩恶。贵妇克莱尔,是妓女,是挥霍者,是摧残者,是霸道者,是复仇者,但是她首先是一位无辜的受害者。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玩味的戏剧,整部剧中几乎没有一个正面人物。迪伦马特无意与居伦城的全城人做对,但他把全城人都描写、塑造成了像微生物一样渺小、卑贱的存在,自私自利,虚伪至极,见风使舵,丑陋不堪。正如翻译家叶廷芳所言,迪伦马特的剧作揭示一个社会问题,令人深思:有罪的无罪者,无罪的有罪者。
彭 俐:《北京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雍文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