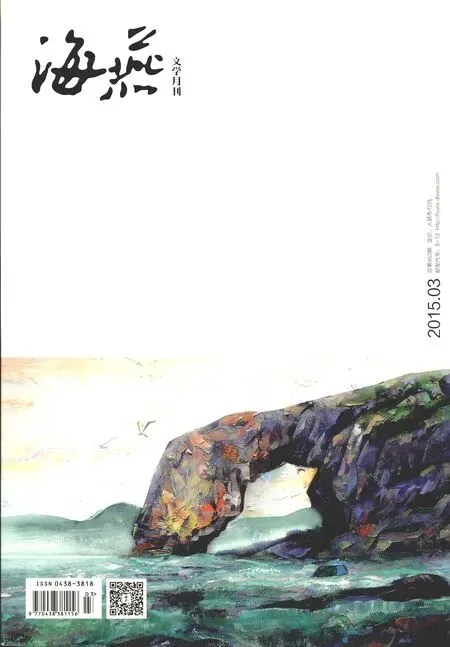小村往事
□戈三同
一只1974年的狗
慢慢我发现,狗与其他家畜的区别在于:狗围着人转,人围着家畜转。这种情景,往往从一个新鲜的早晨开始。那时,鸡窝、柴垛、炊烟依次清晰,起早的拾粪人,把清脆的咳嗽传递很远。我走在一片新翻的茬地,我要去西洼地背豆秧。西洼地很偏,紧挨一片集体林,有风吹过,人就卷入一种阴森气息里。大豆秧拔下有些时日了,经过阳光的暴晒,标本一样摊在地里,我要赶在豆荚爆裂之前,把豆秧背回来,让连枷以居高临下的姿势,迫使豆秧吐出憋了一个夏秋的豆粒。
在我前面十米左右,是每天与我形影不离的狗。十米左右,是一段合适的距离,它使我有机会应对突变,人与狗的默契,想来就是这样的,忽远忽近总也走在人的心思里。我庆幸拥有一只懂事且不惧危险的狗——四眼。狗不惧危险,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对危险洞若观火后的清醒,是清醒后靠实力的征服;一种是以天性中的鲁莽为攻击之剑,受伤后不会痛定思痛那一种。四眼属于后一种。它还小,骨架子还没定位。我利用它,正是抓住了它这个弱点。这大抵算是我的羞耻和悲哀。我怕蛇,怕一切藏在暗处的偷袭。而四眼似乎也理解,比如在草丛趟行,不时有蚂蚱乍起,还有虫类惊飞,四眼会一跃而起,在空中将猎物准确衔进嘴,其实它完全可以在草根处降服这些,没有必要如此大展身手。但我还是喜欢一睹狗在如此细微举动中,所具有的机敏和判断力,至少在那灵巧的动作中,我感知到了依靠。
说来惭愧。村里的狗,大多悠闲,在主人嗔怪多于怒骂的恫吓下,蜷着身子谦卑,或者为一星半点毫无瓜葛的动静狂吠不止,像例行公事,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很多时候,人们只当那是一团会呼吸的茸毛。是的,在一个狼狐绝踪,门户祥和的小村,狗的天然禀性得到的不是发掘,而是萎缩,是被滤去。养只狗吧,有个动静也是照应。当初队长如是说,主要是冲着我家没有院墙,没有遮挡,散放的鸡鸭、骡马常在窗下过夜,对一个有序的院落常常构成威胁。有几次,睡眼惺忪的我,从微明的窗玻璃上,看见贴窗而窥的驴脸,疑是见了鬼。从那时起,我的身边有了一只三个月大的狗,为了安生,我接纳了它。几天过去,它已经流露出对主人的忠诚,它随时龇着尖细的乳牙,舞着还很弱势的前爪。周围的一切都令它不安。可它毕竟还小,天一擦黑,就拱进柴垛,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找寻温暖,于是,这个夜晚有了狗看星星的宁静。
一段时间,那些相对文弱的畜禽,像鸡、鸭、猫,羊开始与我的家门保持距离,或绕道而过,我知道那些放浪的习惯已经得到纠正,四眼的作用已经得到发挥。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邻家老母猪,在二十几只长相一致小崽的簇拥下,很风光地进入四眼的领地。起先,四眼绝对没有恶意,它只是从老母猪的胯下钻进钻出,戏斗那些出窝不久的小崽。可能它的长相,激起猪崽的排外情绪,惊恐的骚动让一直警觉的老母猪下口极狠。四眼伤在大腿,是贯通伤。兽医来看过,说他在这个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经见的事不少,猪伤狗还是头一次见。四眼可怜兮兮,潮乎乎的鼻头专拣你敏感的地方蹭,很凉,有点像人。所以,我一直心怀愧疚,也有些许伤感。让四眼过早分担了主人的无奈,这与它小巧的身子多么不相称,这与它的天性多么相悖。另一次,对四眼的出色印象来自雪地里一只野兔。那时四眼跟我在一个叫大青沟的地方遛套。在这片雪地里,我下了几十个兔套,隔不几日,来遛一次。可我运气不好,一连几天空手而归。那一次,我站在沟帮上,看见腿伤刚好的四眼在沟底与一只鹰争抢着,鹰拼命用翅膀抵挡着,与来犯的四眼做殊死抵抗。我看见四眼穷追不舍,鹰飞了几气,弃下猎物。显然,这是鹰的战利品—— 一只有体温的野兔,除眼珠啄去外,通体完好。我把它当作自己的收获,在左邻右舍面前争回了面子。其实,这叫人尴尬,也是人的不知羞耻之处。
现在,我已经给豆秧打好捆儿,并斜倚着小憩。四眼在左右来回穿梭,不时竖起耳朵谛听,同时抬起后腿向一棵蒿草撒了泡尿,来年这里会长出一只狗尿苔;天空碧蓝,正好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划过,留下白色烟雾,久不散去;无风,近旁的树叶无力地摇晃,整个西洼地是沉寂的。就在这时,四眼发出一声少有的哀嚎,焦灼、绝望,令人不安。这叫声冲着我,回头,那条锹把粗的灰蛇从身后豆秧上挺起,正好与我照面,柔软的信子好像积攒了一生的毒素。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挣脱绳套,慌不择路落荒而逃的,我的耳朵先是短暂地失聪,后来听得见四眼的叫声忽急、忽缓、忽强、忽弱。我想,它一直近距离迟滞蛇的游进速度,它一直在与这个古怪的家伙较量,它甚至和蛇缠绕在一起。
晚上,母亲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小孩不可以单独去西洼地,你知道吗?那地方的蛇伤过牛马,还说,队长把四眼处理掉了。很长时间想起这句话我还犯疑,处理掉了是什么意思?是让蛇咬死被埋掉了,像埋掉一只死去的鸡、猫,还是迷信使然,受伤后被放逐山野或远送他乡?总之,那是个多么遥远的年代,仿佛没曾存在一样。而我,当时没有能力知道它后来的结果,因此我后来生活中必然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惊闻狗叫,心灵一颤。
乡村情怀
我站在小村一片空场上,背后是三棵傲视青天、华盖厚土的古榆。据说在小村稀稀拉拉形成之前,这树就挺拔茂盛、郁郁葱葱了。从树根到树梢,有三十多公尺,这高度是我用弹弓测出的。虽然这种测量有失精确,但适宜一个少年对高度的认知和习惯。
此时正是吃早饭的时间,在雾气的笼罩下,空气里弥漫着饭香味。看到三五一群的大猪小崽朝这边颠过来,我知道我散漫的日子已经结束。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安排,一个无书可读的少年,一个以打鸟耍狗来消磨时光的人,百无聊赖、心性高远,整日游荡在农事之外,一经有正事可做,便感念我又被这个世界拾回来了,就有了些许安慰感。有农人把猪撵来,头也不回朝田野走去;有农人将猪驱出圈外,又返身回屋拎取打磨光滑的镰和锹。他们行色匆匆,根本无暇顾及我。我知道那是丰收的缘故,我也理解他们的匆忙,这些忙忙碌碌的身影,也许就是我的未来。
在一片远离庄稼的洼地,我让猪们自由活动开了。这些大小不一毛色有别的家伙,是社员们各家的自留畜,而我的活计就是管理好这些猪。在农忙季节,社员中午地头上简单对付一口,只有太阳落山时,才拖着疲惫的身躯朝炊烟袅袅的家门走去。所以要有大块时间由人照顾猪。生产队认为我干不了地里的活,放猪的活不累,这让我感到很是满足。秋天,地里的庄稼成熟了,我就很当回事地跟在猪屁股后面。猪群向前蠕动时,我格外警觉那几头贪嘴的,只要牵制住它,其余的就随大流一古脑儿跟着走。我暗暗惊讶猪也是懂规矩的,甚至也具有服从性。当暑气渐渐消失后,天也就渐渐黑下来,我会按原路折回村。在村口,先大概清点一下猪的头数,然后就看见猪们撒欢般奔向家门。四眼已在村口迎候我了。四眼是我养的狗,已经两岁多了,一直寒来暑往地陪伴我。我和它感情很深,要不是前些天戏斗邻家的猪崽,被老母猪咬伤腿,它会始终警惕在我左右的。
现在,我坐在洼地一高处,俯瞰让野草淹没的猪。有的,露一节尾巴甩动,嘴巴却像安放了马达;有的,不时露出扇动的耳朵,像是藏不住的秘密。尔后,我把木杈弹弓放在一旁,听任猪们各自找寻喜欢的蕨类及草根,听得见咀嚼时发出的呱唧声,就像有人偷吃酥糖那种声音,既爽口又耐嚼还引人口舌生津。近旁有一堆堆翻新的泥土,好像谁在大地上落笔留下的省略号,其实那是土拨鼠听见迫近的声音惶惶弃下的。我习惯于在这个时间段仰天而躺,望着碧蓝的天空想入非非。因为我知道上午猪有足够的耐心在地里觅食,溜号只是临近晌午或无食可觅时。有一次接近中午,我莫名其妙迷糊着了,几头猪把队长家土豆地拱了。农民经营那点自留地不容易,看见他们白天在大田忙乎,夜晚就着星光在自家地里伺弄,就让我想起那些面黄肌瘦的娃娃们,心里也会多一层悲悯。每次我看见有猪朝着村庄的方向蠢蠢欲动时,就悄悄拿起弹弓,那样子就像儿童团员对付偷雷的鬼子。这办法很管用,中弹的猪缩头缩脑,发出不情愿的哼唧声,然后会眯眼躺下,享受阳光的摩挲。
而我在山上放猪时,想得最多的就是我的前任猪倌老周了,有时是一遍遍地想,也想不明白这个人。老周放猪也是生长队照顾。本来老周人高马大,干活风风火火,在一次夜间打麦时,被脱谷机吞去一只胳膊。所幸,他没有死。那以后,他常常坐在村口,用非常羡慕的眼神,看候鸟在天空飞过,看人们来来回回走动,看暑去冬来的日子融化在劳动中。让他放猪,也称得上量才使用。但老周家里实在太穷,他很计较放猪比干大田每天少去的三个工分。于是,为夺回一只残臂带来的损失,老周白天放猪,夜晚去生产队羊圈下夜。其实下夜也是很省心的,羊圈由草坯垛成,两米多高,顶部用榛柴做了防护,很坚固。圈门旁是下夜人的小屋。但后来的事情,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那是一个冬日夜晚。一只狼,也许是更多只狼,随着夜色渐深潜入羊圈,悄然撕碎了几十只羊。可以想象,日后这个焦灼的男人,小心翼翼挣着工分,规规矩矩守着本分,突然间贼一样躲闪着全村严厉的质询。他努力挺着颤抖的身子,无法说清事情的原委。关于那一夜,一直有着两种说法。一说他圈羊时,狼竟以善变的毛色,骗过他的眼睛混入羊圈,待夜深人静时才放开胆子开始了横扫。另一说是老周虽肢残,但身体健康,有着正常人的七情六欲。那夜他翻墙进入一寡妇家,擅离职守导致事情的发生。因为这些羊既有集体的也有个人的,所以他感受的压力是巨大的。看到他抱着头狼嚎般痛苦的情形,看着他哭得凌乱的头发和灰尘泪水涂抹的面部,我心里起先忿忿不平,后来也跟着难过,心生悲悯。怎么说,老周也不是故意的。再后来老周去了草地,在盐道上贩卖苦力。尽管村里有人好心相留,但老周含泪认命,走后一直没了消息。
想着,日影就偏斜了。好像生物钟在猪身上也是显灵的。当阴影一寸寸占据洼地,猪们停止了找寻,开始显得躁动不安,尔后就蠕动着形成一条黑色河流,沿着村庄的方向,缓缓地漫过沟沟坎坎。在经过一片收获后的土豆地时,猪们开始忘情起来。犁铧翻耕过的土地,垄沟齐刷刷伸向天边,仿佛顺着这方向走下去,就可以走进彩云、跌入夕阳。而捡不净的土豆,仅仅露出一点点,就金子般耀眼。听说那些贪心人,故意把土豆驱入土层,无人时再拾入自己的背筐。那些藏在土层下的土豆,瞒不过猪的鼻子。立马,我的周围响起空前的脆响。我从来不会想到的是,猪的这个举动,无疑惩罚了某些人的小伎俩,也捍卫了土地的尊严。我看见猪们带着乐而不疲的满足感冲撞着、争抢着,分享着土地恩赐的盛宴。
这时,天色向晚,沉入暮色中的小村恍若一片梦境。我希望村里人尽可能即刻走出来,眺望或一睹我给这一天带来的变化。然而我知道,此刻灶台和院落已经将他们栓死,像磨盘上的驴,周而复始重复那几个简单动作。我遗憾,但又无可抱怨什么,只能学着猪倌老周的样子,强忍一天的疲惫,扯起嗓门大声吆喝。那炊烟、狗吠和马嚼夜草的声音,在不经意间,已经把足够丰富的神性,注入我草木一样单纯的情感。
守望
我们哥仨终于没有熬过这漫长的白日,像急于入洞的獾,在村庄傍晚嘈杂的声音之外,在早秋的夜幕暖暖覆盖之前,钻入被窝。刚才,队长经过我家门口,十分友善地问询我父母的消息,现在,隐隐传来他对待牲口凶巴巴的呵斥声。我知道,他家的驴因伤了后胯误了地里营生,让忙于大秋的他肝火四起。已经二十多天了,我们就这样一直在望眼欲穿的期待中捱着无聊的日子,在恍若梦境的遐想中虚构那个幸福时刻的降临。父母走时告诉我们,最多三至五天,他们将唤来卡车,把这个尚未扎牢实根的家搬走,我们也将从这个村庄消失。想到有一天人走屋空的样子,想到会有一个陌生的人家,用搬家的速度,把家当迅速摆满这个不大的空间,我的心里会充盈着无奈和酸楚。在黑暗中,我们听到彼此的喘息,显然都大睁着眼睛。我们如此偏爱黑暗,是因为,对于想得到的一切,黑暗似乎提供了某种可能。
而夜深,我们常被一种声音惊醒,而且这些声音一次比一次夸张。我们都知道那声音来自屋角三节柜的下方,就用绳栓了一把铜锁悬在那里,一有响动就拉绳。起先还管用,用过几次之后就形同虚设了。听人说,即使是动物也能感知人间的变化,若此,那些一下子胆大起来的老鼠,该是耐不住性子来逐客的吧。我去邻家借来小猫。小猫是会意的,很快就听见猫鼠之争发出的叫声。天亮见了那一幕,我们仨还是惊骇地半天说不出话来:小猫咬住一只老鼠颈部,那老鼠的身长竟长如小猫。在屋外,小猫用了一整天时间吃净了老鼠,是扒皮吃的,剩下一具完整的鼠皮,可能嫌皮厚,也可能是故意留下作纪念。我把鼠皮用棍挑着在屋后埋掉,像埋掉黑夜最后的影子。
弟弟不止一次把耳朵贴近大地,说来听,我听见汽车马达声了。我们凑过去,撅着屁股,上面的补丁线几乎要胀开。确实听到了声音,若即若离,似有似无,就像捉到手的鸟顷刻间飞走,而小手掌留有鸟的体温。后来发现,这声音源自不远的场院,是卧式脱谷机启动时发出的不规则响动,从而迷惑了我们的视听。意识到这一点,世界一下子又静了。平常,场院里尘土飞扬,总有一些粮食颗粒随风扬到墙外。我喜欢撵着小鸡去遛食,而又不致被人指摘。如果小鸡不受惊,它们有足够的耐心替人类的粗心纠偏,我看到那些嗉子鼓胀如袋的小鸡艰难挪步,心里充溢着满足。但我不会听任小鸡自由散漫到因贪食误入场院,把憋不住的蛋一颗颗留给麦秸垛。
哥哥总是不声不响走上小圆山,山无语,人默然。这山紧傍村东头,比屋脊高不过多少。登上去,方圆十几里尽收眼底。金黄的田野被一条小路从中间分开,像给大地留了一个中分。那路的尽头,是返乡人消失和出现的地方。哥哥就一直盯着那个地方,有几次,还真出现了令人心动的移动的黑点,哥哥兴奋地叫出声,想跑下山坡去迎。其实,那不过是队里的大车,因为装载过多,远远地容易和汽车混淆。车把式老远冲我们甩个响鞭,算是打过招呼。我说,咱们去乱石窖吧,那山高,看得远。乱石窖雄踞村北,因生产石具而闻名。据说过去千里以内县衙所用条石以及农用碾子、碌碡均出自这里,站在山顶看得见60里外的县城,远远望去仍可见大山腹部的坑坑槽槽。有一次我去几十里外的骆驼场子买盐,曾听见村民们议论我,他们在柜台前交头接耳,像在议论重大的秘密,我低头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其实,嗡嗡的嘈杂声,还是漏过了他们压低的声音。我只听见了一句:他是“乱睡觉”的。后来我才明白,“乱睡觉”是乱石窖的谐音,也可能又包含了些许民风。那一刻我也明白,这个宁静的小村肯定有不为我所知的秘密。哥哥不同意,他说登一次乱石窖,恐怕天黑也回不来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主意是对的,试想费尽力气爬上去,云里雾里又能望见什么呢?
而更多的时候,我在用羡慕的眼神,偷偷看着我的同学结伴从我眼前走过,或者扛着树苗,排队去坡上栽树,他们骄傲地挺着小胸脯,他们清脆的歌声此起彼伏的,根本无视我的存在。我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一个月前就办了转学手续,害得我整日与猫与鸡为伍。哥哥是县城中学住校生,他的阅历已经不屑于我的心情;弟弟刚刚上学,还不能胜任人世间的聚散。场院里的噪音更大了,夜里悬了几盏大汽灯。队长粗鲁的呵斥声从未间断。老鼠的磨牙声夜夜纠缠我们,我们已经习惯了与老鼠同居一室,也容忍了与它分享黑夜和空气。乡里的草台班子在邻村唱戏,归来的人口中唱词不绝。早霜降下来,给屋脊和田野蒙上一层银色。
从初来到欲走,有两年的时光,青草绿过两次,麦子熟过两茬。我希望、失望、叹息,身体长久支撑着精神的渴望,像一株快要扭断脖子的向日葵。
几天后,搬家的卡车进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