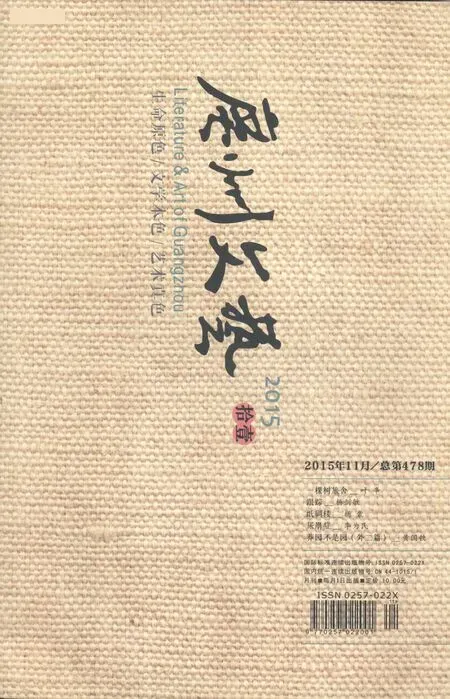几时得闲,饮茶倾偈
文春梅
几时得闲,饮茶倾偈
文春梅
十六年前初到广州时,朋友请我上茶楼饮早茶,说是为我接风。我觉得喝茶很好啊,可以清清静静地聊聊天。待上得茶楼来,才发现我的想象完全不对,茶楼上人声鼎沸、热气蒸腾,黄发垂髫熙来攘往,间或还有点心车仔,骨碌碌地推来推去。面对眼前铺开一桌的碗碟笼屉,看着一件件叫不出名的精致小点,我正犹豫何处下箸时,来了一个黑且胖的壮汉,很熟络地和朋友打招呼。原来此人正是这间茶楼的老板,人称 “肥佬”。肥佬听说我是教中文的老师,非要给我讲个 “煲冬瓜”的笑话。我不明白什么叫 “煲冬瓜”,朋友解释说,广东人说不好普通话,就笑称普通话为 “煲冬瓜”。还没等我醒过神来,肥佬已径自开讲了:“靓女啊!我吻你吻得好辛苦啊!终于被我吻到你啦!我们来亲亲啦!”说完他顾自大笑,朋友也跟着笑,我惊诧莫名,且有些被侵犯了的不快。
这便是我对粤地、粤人、粤语的初印象,或者说,这个肥佬更坐实了我之前从舞台小品里得到的广东人印象:暴发多金、粗俗无礼、说话拖腔拉调。到广东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适应,我觉得广东也很排外啊,打开电视,本港翡翠南方珠江,通通讲的是外语般的广东话,好在屏幕上有字幕,边听边看也慢慢能明白一些。最初我只看新闻时段,一则是因为新闻播报语速较慢、表达正规,容易听懂;二则是没有 《新闻联播》那么多领导开会的内容,对街坊食肆的报道让我觉得更亲切。等到半年后春节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看珠江台介绍广州人行花街,而不是年年例牌的央视春晚!
在这个鸟语花香的地方生活久了,享受四季花香的同时,也爱上了以前视作 “鸟语”的粤语。我发现粤语之所以难听懂,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留存了许多中古汉语的音韵,如 “-p”、“-k”、“-t”三个塞音韵尾,那种短促又含蓄的效果,北方方言区的人是很难领会到的;粤语还完整地保留了中古汉语 “平上去入”中的入声,独特的 “九声六调”使得粤语说起来、听上去都特别低回婉转;粤语入乐更是韵味深沉,尤其是粤调南音,无论是 《客途秋恨》抑或 《叹五更》,静静地一个人听来,仿若看到暗夜里沉沉的珠江水面,洒着两岸灯火的点点碎金。粤语词汇的古雅,更直接融入了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中:着衫、食饭、饮水、行路,是日日都要做的功课;隔篱邻舍、街坊四邻,虽不复鸡犬之声相闻,但也是朝朝照面、点头微笑互道“早晨”的。我还听到过一个阿姨抱怨她儿子的房间 “七国咁乱”,见到过何淡如的无情对 “有酒何妨邀月饮,冇钱哪得食云吞”,真叫我惊叹!谁说广东没文化?原来史、诗可以就这么轻轻松松地挂在广东人嘴边!
粤语的妙处并不止于 “古雅”一味。广东人 “识食”,尤钟意 “和味”,和味牛杂、和味龙虱、和味田螺……和味系列有个特点,就是原材料出身乡野,且带有桀骜不驯的气味,但粤地的庖厨不拘一格通通拿来,以巧妙的烹制方法去除异味,调和出异香扑鼻、口感丰富的美味。粤语亦具这样的和味,在古代,它是古雅的汉语与生猛的百越土语相互交融,到近代,又渗入了丰富活泼的外来语。古与今、土与洋就这么合为一体,毫不违和。由饮食到语言,都体现出广东 “敢于创新、善于包容”的文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广东人在近代开天辟地,在当代一马当先,饮到了改革开放的 “头啖汤”!
我也习惯了周末上肥佬的茶楼饮早茶,学会了熟练地叫出自己想要的点心,也能自如地在朋友为我斟茶时屈指叩谢并道 “唔该”。我和肥佬渐渐熟起来,知道他曾在北京开过十年餐馆,能在粤语和京片儿间无痕切换。当然,我也知道了 “吻”其实是 “搵”,寻找的意思;而“亲”实际上是倾诉、倾听的 “倾”。但是当我想要 “搵”肥佬好好 “倾倾”时,他却忙得脚不沾地,不得闲同我倾偈了。
“倾偈”大概类似于普通话的 “聊天”,但从字面上来看,“倾偈”似乎又比 “聊天”要庄重一些。一次真正意义的 “倾偈”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参加者必须是两人或两人以上,这样才能完成倾诉与倾听这两个角色的分配;第二,参加者的时间必须比较充裕,这样才能实现倾情倾心的效果。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邀约:“你几时得闲啊?一齐饮茶倾偈啦!”至于 “倾偈”的 “偈”字,有本地人告诉我说,就是“佛偈”的 “偈”,并举例说最有名的佛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作者禅宗六祖惠能,就是广东新兴人,说不定当时还是用广东腔吟诵出来的呢!我听得恍然大悟,然而又有点疑惑。我不知道古代的广东人是否都如惠能,善于舌绽莲花?就我所闻所见,当代的广东人好像并不热衷于谈玄论道,一如饮茶,广东人是不耐烦满室清静、花工夫去体验禅茶一道的文艺范儿的。在广东闹闹嚷嚷的茶楼上,在飞来传去的排骨凤爪虾饺叉烧包的间隙,茶扮演的不过是润嗓的配角,大厅统一三元一个茶位,普洱还是铁观音,无所谓。这样喧闹的市声中,倾佛偈显然是不相宜的,还是倾倾如点心一样 “顶肚”的内容更实在些。于是,现在更多的广东人把 “倾偈”写作 “倾计”,茶楼上的客人,就不独 “倾闲偈”的老人、“倾心偈”的友人,更有 “倾谋计”的生意人。普通话说 “有事好商量”,广东人话 “凡事有得倾”,倾谈的倒不一定都是商战计谋,儿女之情也需要从长计议啊,国家大计也可以倾倾嘛,只要不是 “得个‘讲’字”就行。
粤语里与 “倾佛偈”相对应的,还有一个 “讲耶稣”,但这条短语总是以否定形式出现,比如:“你唔好同我讲耶稣!”、“我唔想听你讲耶稣!”我十分好奇,在神佛满天且素来开放的广东,为何 “佛偈”都有得倾,“耶稣”却单单不能讲了呢?思来想去,问题似乎并不是出在耶稣身上,广东信耶稣的大有人在,问题出在 “讲”字上。与强调对话的 “倾”不同,“讲”是单方面的言语行为,其影响效果往往只是一厢情愿,尤其在言语最终没能落实到行动上、“得个讲字”时,广东人民是断不肯埋单的。记得第一次从珠海过深圳,蛇口港甫一登岸,劈头就见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两行大字,着实震撼!务实的广东人批评高谈阔论者 “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谦虚却不无骄傲地声称自己 “识做唔识讲”,对于外界评论广东人“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广东人很淡定:“由得渠讲啰,有乜嘢所谓啫?”
粤语动词 “讲”与 “话”都是 “说”的意思,但绝不在一个重量级别上。普通话里 “我说了算”,用粤语表达更加简洁有力——“我话事”,说话的人显然控制了主动权。“我唔话你知,等你心思思。”说话的人更是将听者把玩于掌中逗弄了。我曾亲见一场劳资纠纷,就发生在肥佬的茶楼。肥佬刚出来讲话时,激愤的员工们根本听不进去:“你讲乜嘢啫?收声啦!”肥佬处乱不惊,坚持说下去,员工们的情绪慢慢平复:“好了好了,你话乜嘢就乜嘢了!”肥佬由 “讲”变作 “话”,个中的力量,岂不就是我在书本上经常看到的 “话语权”?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广东人何以重实轻名——在 “白猫黑猫”的语境中,广东是实实在在捉到了老鼠的猫,经济上的成功让广东掌握了某种话语权,粤语成为一种强势方言。广东经验向全国推广,广货成为最好的国货,“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要跟广东人打交道做生意,当然首先要会说广东话,粤语流行金曲、TVB电视剧集,曾经是内地人学习粤语的最佳捷径。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广州街头的粤腔粤调越来越少了,邻里街坊 “倾偈”之中多了京味儿的段子,小朋友也不念粤语的童谣了,甚至听说有领导建议,粤剧要扩大影响,最好不要使用粤语……有一天,肥佬茶楼的墙上被街道办贴上了一张推普标语:“讲普通话,做文明人”,肥佬一时火滚,拍着桌子爆了粗。我理解他当时的感受,那条傲慢无礼的标语如同当年那个简单粗暴的笑话,他所受到的伤害,也一如当初我受到的侵犯。
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人际沟通,沟通时要用彼此都懂的语言,这是最基本的尊重。广州人同广州人倾偈当然讲广州白话,上海人和上海人嘎三胡自然用上海闲话,如果广州人和上海人走到一起,最方便的就是讲普通话。各地的方言与普通话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并无等级高下。强行让外地人只能说粤语,或者规定广东人必须说普通话,都是话语的霸权。
肥佬穿了件写着 “撑粤语”的T恤,在茶楼里走来走去,他也许不知道有些人在网络上发起 “粤语保卫战”,也不懂得什么叫话语权,但他坚持 “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从他那里,我听到一些 “粤语保卫者”的说法,说广东人才是最纯种的汉族,粤语是最纯正的汉语,说中原一带的人早已是胡汉混血,普通话就是胡化了的汉话。更让人惊诧的是,为了维护粤语作为汉语的纯粹性,他们宣称南粤大地上最早的土著——百越人早在唐代就已被汉人赶杀殆尽!我感受到这种声音里藏着的深深的恐惧:他们恐惧着,担心话语权被强行剥夺,但同时他们又在制造着恐惧,用一种话语去驱逐另一种话语,不变的依然是霸权主义。
这不是我所熟悉的粤语的声音,我想搵肥佬、搵那些战斗者们好好地倾下偈,但他们都太忙了,忙着上网炒股、忙着上街散步。我想知道点解本土的写作者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说没有人愿意听也听不懂吧?我想听听专家的意见,但他们似乎更愿意谈中国梦如何实现。我只有翻开书本,搵返惠能,听他初见五祖弘忍时,与弘忍所倾的一段佛偈:“人即有南北,佛性无南北。”弘忍说岭南人是 “獦獠”,惠能却不急不怒,这源自他的自信与根性,也是岭南文化最可贵的根性——包容。
我还是更钟意茶楼上小笼包与叉烧包的搭配,钟意南腔北调的喧腾。几时得闲?我们一齐坐下来饮茶倾偈?
责任编辑杨希
——粤语·女独·伴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