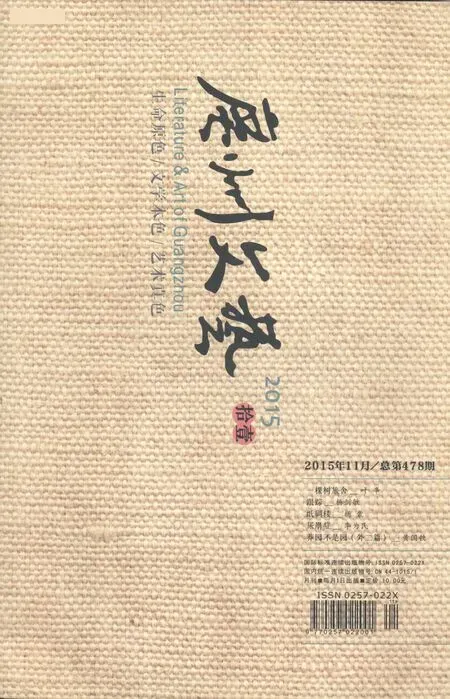莽园不是园(外二篇)
黄国钦
散文选家
莽园不是园(外二篇)
黄国钦
莽园不是园,是一个人,一个十足的文人。在古潮州这片土地上,能称得上文人的人有好多,但口齿伶俐、妙语连珠、哲理禅意、诙谐幽默、出口能迷住我的前辈呢,不过三个人。一个是我曾经日日聆听的李前忠,一个是声名远播的林墉,一个就是郭莽园。
恰切地说,莽园是一个美人。因为李前忠有语录,写文章的人是文人,画美术的人是美人,跳舞蹈的人是舞人……一个美人,能够迷倒一个写文章的人,你说,他肚子里应该装有什么样的彩墨和智慧?
很多人说莽园是一个孤傲的人,尖刻、自负。我说莽园是一个寂寞的人,尖锐、自信。现在,很多画画的人不读书,从早到晚一支笔,就知道在画案上画啊画,没有学养的滋润,没有传统的熏陶,没有思想的磨砺,没有诗文的铸就。一个学中国画的人,没有学过芥子园,没有学过古体诗,没有学过毛笔字,不知道民国乃至清代以前中国画坛的样子,你说这样的人能画出什么画?
莽园呢?是读书读书再读书,思考思考再思考。他很奇怪,现在美术学院的国画系,为什么不考古文考英文?不考白描考素描?我击掌赞赏他的两句话:真艺术没有雅俗共赏,成功者没有中西合璧。想想是这个道理啊,你不走向极致和极端,你就达不到高峰;你和稀泥,你就什么都不是!
我知道莽园不是故意在孤独,他永远在寻找知音,他一辈子都在寻找知音,但是,莽园的知音在哪里呢?一个寂寞的人,是因为他有别人没有的想法,有别人没有的追求,有别人无法理解的艺术观和价值观。
在别人眼里,莽园是一个桀骜不驯的老人,那一头蓬乱的头发,那一把须髯飘飘、从左腮连到右腮的胡子,就给人一副十足的叛逆形象。我和莽园促膝,却从来没有感到压抑和局促,都感到逸然随意和自由自在。尊重一个饱读诗书、个性鲜明、创意无穷的画坛前辈,理解一个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笔底不愿意重复自己的率真美人,他能不露出一脸天真灿烂的笑容?
看莽园画画,是一种真正的称心,他总是把一管长锋高高地提到笔端,一只手按在画案上,然后成竹在胸,从容地下笔。这完全不像现在的很多后生哥哥,开头几笔十分架势,但是画着画着,心里无底,画面芜杂,乱象丛生,又不懂得 “收杀”,无奈之下,就只好淋水,倒色,把一个画面弄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最后撕掉了事。
莽园是一个从生活的底层走出来的人,底层的苦难艰辛和穷困潦倒,底层的人情冷暖和无依无靠,深深地刺激了他独树一帜的雄心和志气。他学习西画又跳出西画,学习海派又跳出海派,一生孜孜不倦转学多师,最终成就了大写意和指书画。我屈指算来,从清光绪三十年到公元2015年,历111年,大名鼎鼎的西泠印社仅有社员300多人。但是莽园,一个西泠印社的社员,就是这样给艰难困苦的生活逼迫和造就的。
我很喜欢这个有着和马克思一样头像的潮籍美人,他那种天真烂漫的像向日葵一样开心的笑容,不是每个人都能目睹的!
王显诏
王显诏是一位画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半个中国都很有名。
我家和王家是亲戚,按辈分,我应该管他叫老舅。
老舅住在攒槐里。从同安里,到攒槐里,只有一百步,转过一个仙街头,就到了。
潮州城文气氤氲,这里的人知书达礼、温文尔雅。每年的春节,父亲就要带着我,给各位亲戚、长辈拜年。攒槐里、双忠宫巷、上西平路、曾厝巷……
老舅住的攒槐里,是一条只有六七个门楼的小巷。走进攒槐里,一个小小的石门框,两扇窄窄的栏杆门,一级高高的石台阶,进门,是一个湿湿的小天井,种着几盆铁骨铮铮的兰。
老舅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人,儿女都到外面读书了,只有老妗伴着他。
王显诏,是潮州文艺界、广东美术界的一张响亮的名牌,岭东画派一代的宗师,但是,我感觉不到,作为一个名人的喧嚣。
老舅的客厅无闪门,两把明式的太师椅,一张通雕的八仙桌,后边是通雕的长条桌;这些摆设的后边,是已经暗旧的木板壁,木板壁后面,一条黑洞洞的木楼梯,通向了我永远没有上过的二楼。
老舅很少到我家,但老妗却常常来,她和我母亲很谈得拢。很早以前,老舅的女儿王尔聪,也经常到我家,她和我的大哥黄国璋、我的堂叔黄海潮,都是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们意气风发地在一起,谈的都是新鲜的民主与科学。
后来,这个留学苏联的才女,不知怎么却失踪了。
老舅是高高的挺拔的个子,老妗却是瘦小的女人,但是,他们却是天底下最恩恩爱爱的一对。每天的早上和黄昏,在义安路的下闸门、仙街头和西马路的后巷头,都可以看到他们缓缓地散步的身影。
穿着一身灰色唐装的老舅,脖子上围着一条褐色的围巾,它一头垂在老舅的胸前,一头垂在老舅的背后。老舅一只手提着一根文明杖,一只手挽着老妗的手,人来人往的义安路,仿佛,就只有老舅和老妗两个人。五十年前,潮州城,多少人有这样的情怀呢?
“文化大革命”,老舅所有的字画都被 “抄”走了,老舅也一下子病倒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再也看不到老舅了。老舅去世了。只剩下瘦小的老妗一人了。
七十年代末,“落实政策”了,老妗又来到我家了,她请我们帮她把老舅的字画找回来。但是,老舅散失的字画,能找回来多少呢……
郭爱华
郭爱华是一位书法家。在潮州城,像这样满肚子学问、眼高手高的艺术家,已经不多见了。
我是一个恭恭敬敬地称郭爱华为郭老师的人。在潮州城,只要是真正有学问的人,我都尊称他们一声老师。
郭老师住在岳伯亭街。岳伯亭是一个石牌坊,旁边还有一个省郎坊,岳伯坊和省郎坊,都是明朝潮州进士刘斐所建造的。
小时候,我也常常到岳伯亭下玩,揣摸岳伯亭和省郎亭上的字。这两座石牌坊上的字,都是明朝潮州隐士陆竹溪所写的。陆竹溪的字瘦劲,笔笔通神。
岳伯亭一带,是潮州府城的政治中心区。往东,是孔庙、城隍庙、府衙;往西,是三达尊黄尚书府;往北,是许驸马府、卓总兵府;往南,是火神庙。浸淫在这样的氛围里,郭老师的品位和性格,就修养得高古和率真了。
郭老师是一个小个子,不高,只有一米五几、八十来斤的样子,我是一米八零的大个,但是和郭老师谈话,我常常觉得要仰视他。
郭老师只会走路,在百花台,在柳衙巷头,在开元路尾,在南濠池一带,总会看见郭老师一个人蹀躞的样子。这些地方,是潮州书店集中的地方,郭老师,就老是到这些地方来淘书。诸子百家、《说文解字》等等,就连潮州仅来了两本的 《应用训诂学》,也让他淘去了一本,另一本让学者曾楚楠淘去了。
郭老师的房子是旧房子,又是典型的潮州古民居,暗淡,不通气。郭老师是勤奋的人,夏天,在屋子里写字,就常常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这样一个斯文人,却要裸着瘦骨嶙峋的身子,挥汗如雨地写字,我不知道这种时候,郭老师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儿。但是,郭老师的字,总是笔正字正、一腔正气、豪气干云。
有一次,书协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前一段时间,他们几个人去郭老师家,看到郭老师家里还在用蜂窝煤。我不由万千感慨,郭老师文人的洁身自好、文人的傲气和骨气,真是修炼到家了。在潮州城,他的字,拿出去,一幅两三千块,家里何至于如此呢?
有缘的人,郭老师随意指点,却从不收徒课徒,不为那几个课徒的钱,束缚了自由的身和心,因为现在没有多少可堪造就的人!为艺术,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要坐得住十年八年冷板凳,时人几个有这样的操守和执著呢?
培养的是写字匠,培养的是只想弄几个钱的人,老师何须去玷污这颗纯真的心!
癸未年元宵节过后,一个星期天,郭老师到我家里闲坐。我也有一个四壁萧然的厅,坐在昏暗的客厅里,我们谈文史、谈书画、谈音乐,谈到高兴的时候,我和郭老师一起唱起来,唱的是五十多年前的歌剧 《柯山红日》:“一整夜,北风吹,北风吹柯山……”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 《柯山红日》的旋律呢?
责任编辑杨希
黄国钦Huang Guoqin广
东潮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东文学院重点扶持项目签约作家,一级作家。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