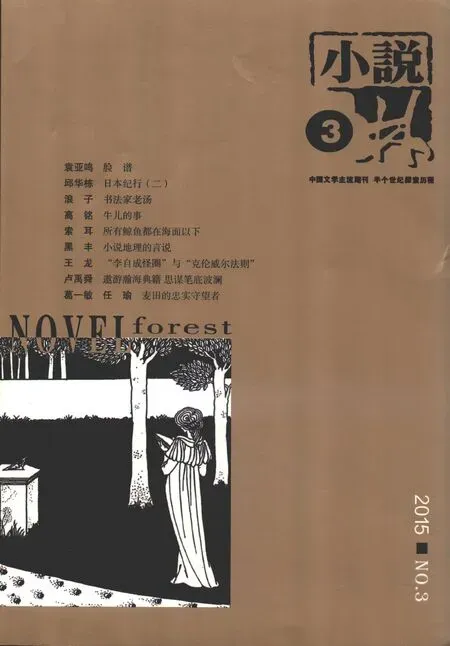商战搏杀中的人性迷失
——评袁亚鸣的中篇小说《脸谱》
商战搏杀中的人性迷失
——评袁亚鸣的中篇小说《脸谱》
袁亚鸣是商场中人,他曾经当过银行信贷部主任、基金管理公司经理、期货有限公司总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等,对当今中国商场诸多隐秘洞若观火,因此他的长篇小说如《终极破产》《生死期货》《牛市》等几乎都是围绕着期货、基金等商战题材展开,展示商战中别一种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由之透视该行业中的人性波澜。苏童曾谈及对他的小说的观感,“我觉得亚鸣的小说似乎不同于一般的财经类型小说,他一直在探索金融邪恶的诗意,并且借助于一个个‘赚大钱’故事,对欲望刨根问底,努力地挖掘人性的深度。”的确,正是对人性深度的挖掘,使得袁亚鸣的财经小说崛起为当今中国文坛风景独特的行业小说。他的中篇小说《脸谱》也聚焦于当今中国期货市场中的商战搏杀,通过几个人物的爱恨生死之悲剧,勾勒出该行业中过于炽盛的欲望主导下的人性迷失,从而折射出现实中国的阴暗一景。
小说主人公双奎和全胜成长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辛店,少年时期就一起在街区打架斗殴,后来双奎在父亲老右派的逼迫下不得不好好学习,远赴江西读财经学校,学工业会计,在学校谈过一场不成功的恋爱,毕业后先到砖瓦厂工作。正是在砖瓦厂时期,双奎结识了银行信贷员应荣富,从他那里知道如何依靠不法手段掠取金钱。等双奎想方设法调入银行工作后,应荣富便去海南岛做交易所了。全胜也紧随着双奎调入银行工作,并利用双奎挪用银行贷款做期货的内幕消息逼走了双奎。随后,双奎到赵部长的私募公司里做黄金期货,风生水起,深得赵部长的信任和器重。双奎在公司招聘会计时对彩云很感兴趣,彩云的丈夫已死,有个十岁的双腿截瘫的女儿雪莲;双奎后来与彩云结婚,但婚后生活并不和谐。一次黄金期货大涨时,双奎没有满足赵部长的要求,赵部长便把全胜调入公司,和双奎构成对峙态势。当应荣富再次以首富的身份返回辛店时,他邀请双奎、全胜联合成立了南天公司,也开始做期货,并利用会计红云窃取赵部长公司里的商业机密,结果导致赵部长的公司亏损。原来,应荣富回辛店别有目的,当年他跟着大老虎做空线材,却输给了赵部长和巨无霸,如今大老虎回到中央,应荣富就想着回来找赵部长报当年交易所的一箭之仇。在应荣富利用红云、双奎初步击败赵部长时,大老虎却被双规了,于是风云突变。会计红云被杀,正在双奎被怀疑为杀人凶手时,应荣富被烧死,全胜也被杀死,双奎却似乎逃之夭夭了,而这一切又似乎都在赵部长的掌控之中。
由于该小说学习侦探小说采用了较隐晦的限知叙事,许多情节即使到小说末尾也没有完全清晰地交代出来,像红云到底是被谁害死的,双奎如此残忍地报复了应荣富和全胜后又过着怎样隐姓埋名的潜逃生活,赵部长是否才是幕后的主使。这一切可能都得依靠读者去慢慢揣测、想象,由此也使得该小说别有一番耐咀嚼的艺术韵味。不过,即使不能确定红云到底是被谁害死的等情节,该小说对当今中国商战中被欲望扭曲的人性书写主题还是力透纸背,令人不由得悚惧有加。
而要理解该小说中人性迷失的深刻意蕴,在笔者看来,首先值得关注的还是全胜的一个梦。全胜利用双奎挪用银行贷款做期货的内幕消息逼走了双奎后,曾经想过不再对双奎下手了,但后来被赵部长调入其公司,再次和双奎共事,上班前夜他梦见自己抢了双奎的饭碗,“他看见自己一直跟在双奎后面,双奎到东他到东,双奎到西他又到了西。双奎手捧饭碗,满头是汗,赤裸着往前跑。他举着鞭子在后面追。他夺过了饭碗,但一下子就惊醒了。饭碗里,全是吃剩的骨头,还有蠕动的小半碗蚯蚓和蟑螂。那些蟑螂布满心机地看着他,触须谨慎而冷静地轻轻绕动。他听见了笑声,他看见在不远的地方,双奎正缩着脖子,交叉着双手在对着他笑。双奎不知道从哪里找了顶破旧的船形帽,笑得满脸皱纹,颧骨高耸,脸上只剩下一张露出黑洞的大嘴巴。”全胜的噩梦揭示非比寻常的人性内涵。
世俗社会中的常人总是被汹涌的欲望纠缠不休,总是被权力、金钱、美色等欲望目标牢牢地吸引、主宰着。但权力、金钱、美色等真的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其实,常人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内在的空虚,在于他们不知道生命的内在意义和真实目的,没有领悟到内在的真实自我,于是他们就模仿他人的欲望,试图攫取他人也觊觎的权力、金钱、美色等目标,从而引起他人对他的羡慕、承认和尊重,并在他人的这种眼光中来确立其自我形象。因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权力、金钱、美色等欲望目标,而是常人的自我建构模式。例如一个戴着绝美首饰的美女在街头炫耀她的美,对于她而言,并不是首饰装饰了她,而是众人的羡慕、欣赏的眼光装饰了她,让她再次在自己心中确立了美丽的自我形象;一个大权在握的人,并不是权力本身有多大的魅力使得他熠熠生辉,而是他人对权力的尊重、敬畏,使得他得以确立重要、有价值的自我形象。所以,所有被欲望主宰的常人都是缺乏真实自我的人,都是模仿他人欲望的人,也就是觊觎他人的存在的人。法国思想家勒内·基拉尔就曾指出常人的欲望模式并不是像浪漫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主体对客体的直接捕捉,而总是一个主体对其他主体的模仿,因此他把这种欲望称为模仿性欲望,主体所模仿的对象称为介体或模式。而且他认为主体之所以要模仿介体的欲望,和介体抢夺欲望客体,最关键的还是通过客体觊觎介体的存在。基拉尔曾说:“客体只不过是达到介体的一种手段,欲望觊觎的是介体的存在。普鲁斯特把这种成为他者的强烈欲望比作干渴。‘就像久旱的土地盼望甘霖,我的灵魂渴望得到一个生命的滋润,因为至今这生命的甘露我一滴都没有沾尝,所以会更加狂热地一饮而尽,一醉方休。’”
《脸谱》中的全胜就是被这种欲望所主宰的人。他做的抢夺双奎饭碗的噩梦就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一点。他在梦中发现抢来的双奎的饭碗里只是骨头、蚯蚓和蟑螂,这恰恰喻示着欲望目标其实是空虚的,他真正觊觎的乃是双奎这个生命的存在。其实,小说在这个噩梦之前,还写到全胜在双奎去读大学后的失落之情:“有了双奎这样的人在边上,他就能从双奎的一言一行里汲取营养和灵感。他觉得自己面对的世界,就像一排宽大高耸的窗户。窗户严严实实的,只有双奎在面前,他才能打碎一块玻璃,接着,双奎就会帮他打破更多块玻璃。很多块玻璃打破后,阳光照射进来,就可以让他把自己的心思,还有这个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双奎是他的明灯,没有双奎,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因此,不能把全胜不断地逼近双奎、强逼其就犯简单地理解为他要和双奎争抢金钱、职位等。真正的原因在于,全胜是个没有真实自我的人,是没有真实生命的人,就像蒲松龄在小说《画皮》中塑造的女鬼一样,因为自己没有真实的心脏就要不断吞噬活人的心脏苟延残喘,他也要吞噬双奎的生命,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像影子一样跟着双奎,甚至和双奎的妻子彩云私通的根由。
全胜的这种觊觎他人存在的欲望模式,恰恰是《脸谱》里主要人物的共享的欲望模式。例如双奎,从表面上看来,他是富有生命激情、富有真实内涵的人。但其实,他也是被这种欲望模式控制的常人。他年轻时要模仿的是电影人物扎卡,在好勇斗狠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到砖瓦厂工作后,真正引发出他的欲望是应荣富。身为银行信贷员的应荣富以不法手段攫取财富,引发了双奎不可控制的欲望。小说中这样写双奎的心理:“应荣富能够得到,为什么他就不能得到呢?双奎用农村话这样问自己的时候,于是一切在他心田里,豁然开朗起来了。”所以,就像双奎是全胜的模仿性欲望觊觎的对象一样,应荣富是双奎的模仿性欲望觊觎的对象。后来双奎也调入应荣富所在的银行,想着终于可以和他平起平坐了,谁知应荣富又要去海南岛做交易所,从而交易所就成为双奎的梦想。由此看来,双奎也是内在空虚的人,也是没有真实自我的人,也是像画皮女鬼一样试图吞噬他人生命的人。双奎生活中有两件事情不同寻常,一是他身为期货经理,操纵着巨额资金,腰缠万贯,但偏偏不碰现金,还说自己是离现钞最远的人;另一件是他虽然能够得到玫瑰、乌云、彩云、红云等美女的青睐,却偏偏是阳痿早泄患者。一边是金钱,一边是美色,双奎都能够轻易得到,却对它们没有真实的激情,这其实和全胜做梦抢到的双奎的饭碗里装满骨头、蚯蚓和蟑螂的寓意如出一辙,都显示了欲望目标的空虚本质。双奎真正觊觎的并不是金钱、美色,而是像应荣富这样的他者的存在,因为他自己没有真实的生命。
那么应荣富、赵部长呢?表面上看来他们能够呼风唤雨、谈笑风生、潇洒自如,其实他们也是被模仿性欲望模式控制的常人。不过,该小说因为是中篇篇幅,没有必要写出他们的生命景深,但从应荣富和大老虎、赵部长和巨无霸的关系中就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出他们的空虚本质。大老虎、巨无霸就像曹禺的悲剧《日出》中金八一样,虽然没有出场但又无处不在,他们无疑是对当今中国缺乏民主监督的特权体制的隐喻,正是该体制肆无忌惮地催生出最恐怖的欲望滔天、暴力横虐的阴暗现实。
理解了这种欲望模式,我们才可以更好理解该小说独特的鞭子意象。全胜自以为自己是双奎的鞭子,赵部长以为自己是双奎的鞭子,彩云也以为自己是双奎的鞭子,但最后彩云如此反思道:“到底谁是谁的鞭子?这样的问号让彩云无法入眠。每个人都会以为自己是鞭子,鞭挞别人,让别人臣服。但鞭子面前,更多人会选择不臣服,甚至奋起反抗。而一旦遇到双奎这样的‘臣服’,便会让人忘记双奎其实也是一条鞭子,他也可以,或者也会想叫人臣服。不同的是,双奎这样姿态了,他出的鞭子更狠毒,更出其不意,抽在他认准的要害,一点不手软。彩云明白过来了,其实双奎就是他自己的鞭子。他挥着鞭子,驱使自己一路向前。他不知疲倦,一直更新着目标。也许在他眼里还从没有过什么障碍,又或许正是如此,才没有了他过不去的坎儿。这样的坎儿,哪怕叫生死,一样也无法挡住他一路向前。而别人那些鞭子,在他眼前也就是做做样子罢了。”的确,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鞭子,也是他人的鞭子;最关键的是,如果人缺乏内在真实的自我,没有真实的信仰,没有内在的精神自由,那种永远觊觎他人生命、模仿他人欲望的形而上欲望才是他不变的鞭子。在这种鞭子的挞笞下,常人永远是行色匆匆、流离失所的丧家奴隶。其结局,无非是像应荣富、双奎、全胜那样的横死。
这也就是为何该小说要题《脸谱》的深意。在鞭子的暴力威逼下,没有人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展示出真实的自我,因此可以映现精神的脸蜕化为假模假式的脸谱,真实的生命蜕化为虚假的生存。小说写彩云到女儿雪莲所在的学校礼堂去看变脸,“表演变脸节目的时候,礼堂的灯暗了下来。舞台上,一阵烟火一张脸,每张脸都是一个世界,幻象丛生,妙不可言,让人瞠目结舌。”而最后在双奎祭日,彩云看到双奎的身影,追上去,“那个人转过身来,一副白聊聊的面皮,像刚刚上过了戏装一样,干净而失真。是一个脸谱,彩云轻声对自己说。”脸谱,隐喻着真实生命的缺位和退场,显示的是模仿性欲望的虚假和空洞。当脸谱四处泛滥时,人性彻底迷失了。
当然,《脸谱》还值得一提的是其带有先锋色彩的叙事技巧,限知叙事、悬念设置、意象叙事营造出迷离幽暗的艺术空间,值得反复吟味。
汪树东,1974年出生,江西上饶人,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超越的追寻: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分析》《黑土文学的人性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