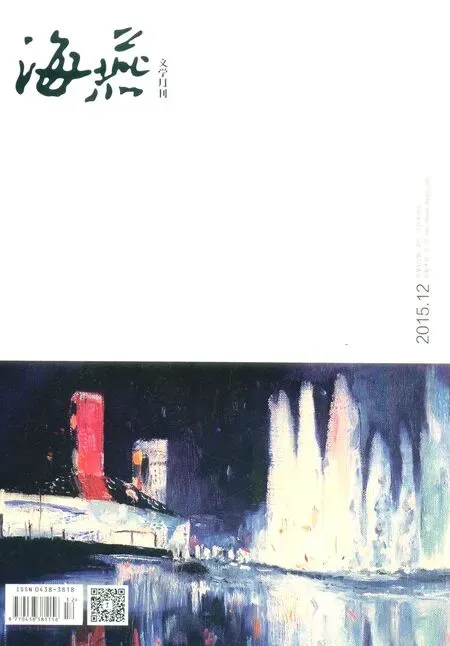小小说三章
□马英东
小小说三章
□马英东
众目睽睽
男人很是着急的样子。他绕着超市外一辆崭新的“雅鹿"牌电动车至少转了有五圈,双手不停地在裤兜里掏来摸去的,嘴里直嘟念着:“明明是放兜里,哪儿去了呢?”
男人穿了件藏青色的夹克,一条米黄色的裤子,脚上蹬着双半新不旧的欧版皮鞋,三十岁左右的光景,长得很憨厚。
天气很好,超市外人头攒动,熙来攘往的,没人在意男人的举动,人们都急着进超市里抢购打折商品,这不快过年了嘛。
“咋的了,小伙子丢什么东西了?”超市旁卖报亭的老林走出来问。老林在亭子里观察了那人五六分钟。看看小伙子的表情,就知道一准是丢了电动车钥匙。这种事在超市前的停车场里经常发生。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没心没肺,干什事都丢三落四的。
“唉!钥匙丢了。”那人一脸沮丧,他把左边裤兜掏出来,里面果然有个巨大的洞,他人苦笑着说,“裤兜破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也不知成天净想些什么。”老林一边数落着一边从报亭里拿出串钥匙,自鸣得意地说,“试试吧,兴许能打得开。上个礼拜天,有个逛超市的女同志也是在这儿丢了钥匙,让我老头子用这串钥匙给她兑开的。”
那人说:“那——试试吧。”却往后退了一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盒“红塔山”烟。
“不抽不抽。”老林头摇得似拨浪鼓。他一门心思想帮那人打开电动车后轮的“U”型锁。老林是个很热情的人。年轻时就喜欢助人为乐。
老林试遍了所有的钥匙,很遗憾,那把锁仍未能被打开。
那人不言语,眼睛瞟着周遭行人的表情,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
几个熟悉老林的人围拢过来,帮着把那串钥匙又挨个试了遍,还是没打开,倒是把大伙搞得手忙脚乱的。那人只是在旁边看着,不吱声也不帮忙捣鼓,只是一个劲地抽着烟,一副六神无主失望透顶的样子。
“给锁王打电话吧。”人群中有人提议。但很快被众人否掉了,“开这么把破锁还不够锁王打的钱呢。”这招行不通。
“小伙子,”老林说,“没招了,我看还是砸了吧,正好我家里有条链子锁,也没啥用,赶明儿,我带到报亭,有空时你过来取。”
那人又往后退了退:“那——砸了吧。”
“砸,”老林说干就干,上报亭里找了把…头几个人三下五除二,锁头被砸开了。
那人感激不尽掏出“红塔山”:“抽烟抽烟!”
没人抽。人们打着哈哈四散而去。那人骑了电动车拐进超市旁边的巷子里,转眼便没了踪影。
老林回到报亭里,他拿出大女婿孝敬他的“铁观音”沏了一大杯,打算好好地品一品,这时他听到外面人群乌央乌央的噪动声,赶忙拎了茶杯跑出去看个究竟。
就在他们刚才砸锁的地方,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披散着头发,半跪在地上,边哭边骂:“作孽啊,昨天才买的电动车……杀千刀的啊。”女人边哭边晃着手中的钥匙,“这个年可让人咋过啊……”
老林的嘴一下子张成了“O"型,手中的茶杯掉到地上摔了个稀碎……
黑道
阿牛见到那人时,着实吃了一惊:那人体重足有二百四五十斤,身高能有一米九,阔面粗膊,虎背熊腰,剃着锃亮的光头,后背上纹了一条巨大的虬龙,张牙舞爪的仿佛随时会从那人的后背上蹿下来咬他一口。那人一边紧着往身上套着猩红色的T恤,一边听阿牛介绍情况,不时地撇撇嘴,没言语。
阿牛在筒子楼里七拐八拐,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那人的出租屋。一间红砖黑瓦的小房子。屋子里满是臭脚丫子的味道。除了几件破烂不堪的家具外,再就是一张单人床,上面胡乱放了床浅绿色的军用被褥,脏兮兮的散发着难闻的汗臭味。在床边的矮脚柜上放了部老式的“诺基亚”手机,正充着电。手机旁是一本装帧精美的杂志,封面上穿着“比基尼”的妙龄女郎摆出撩人的姿势,很妩媚地笑着。床的另一边放了张用工地的三页板钉起来的简陋饭桌,一瓶“牛栏山二锅头”已经见了底儿,还有一碟油氽花生米。许是昨晚吃剩下的,有个十几粒的样子。一根咬了大半截的黄瓜直挺挺地杵在花瓷碗装着的褚红色的大酱里,碗沿上落了几匹硕大的青蝇,正撅着肥臀,旁若无人地梭巡着……
那人是阿水介绍给阿牛的。阿水说那人早年在少林寺练过功夫“金钟罩,铁布衫”什么的,三五个人根本不在话下。阿水还神秘兮兮地告诉阿牛:那人是黑道的,江湖人物嘛,自然是侠肝义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阿水免不了眉飞色舞地为阿牛列举例子若干,自然都是张三李四朱五羊六……那人帮着讨回了工钱云云。说得云苫雾罩,神乎其神,把个老实巴交的阿牛听得是激情澎湃,一夜无眠。
为了讨要八千块的工钱,阿牛可没少费心思。年关近了,湖南老家的婆娘三天两头打电话催促阿牛回去,可是没钱咋回去?阿牛忍不住把一肚子窝囊气撒在了婆娘身上:“工钱没要出来,你让我咋回去?咋回去?”
按说建筑公司的陈经理也不缺钱,偏偏为富不仁,要去克扣民工的血汗钱。看他面皮白净慈眉善目的一副学者专家的派头,其实心肠墨黑墨黑的。阿牛和工友们每次去讨要工钱,陈经理要么是推三阻四,要么干脆拿捏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最后不耐烦了,便扔下句“你们上劳动局告吧”扬长而去。
阿牛和工友们便真的去劳动局。劳动局局长亲自接待了他们。局长五十多岁,很健谈,说话也很中肯:“农民工也是人,也要过年哩,干活不给钱,天底下还没了王法不成?”局长的话立即引来阵阵掌声,阿牛努力控制才没让自己哭出来。局长再三保证年前一定让他们拿到应得的工资,"一定要让农民工兄弟过个团团圆圆的好年。”
但阿牛实在是等不及了,眼见小年就要到了,老家的婆娘更是因为工钱的缘故,着急上火,得了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保不齐还要做手术哩!阿牛本来就是个心眼窄巴的人,摊上这几档子事,免不了整天郁郁寡欢,唉声叹气的,这让同乡阿水很是瞧不起。
阿水可不是个一般人。虽然长得没有三方豆腐高,但这小子精神头足,人又活络。看他整天撇着个罗圈腿在劳务市场里踅摸,市场里但凡有点好活俏活肥活都少不得有他的份儿。这小子腿勤,能白话,胆子又大。闲暇时,他要么泡到市场周围的饭店小吃部里,跟些个漂亮风情的服务员撩骚,要么就撺掇几个狐朋狗友到居民楼里捯饬点小物件变卖。有了钱,吃喝嫖赌自然是少不了的,这不,最近又跟拉面馆的老板娘打得火热,老板娘长相不俗又风情万种,特喜欢花钱大方的男人。
阿水可不主张阿牛他们去劳动局,“六扇门是好进的吗?”阿水牙龇眼瞪跳踉着小脚说,“知道陈经理啥背景?人家是市政协委员!你们这些傻帽儿也不想想,劳动局能为你们几个臭打工的去得罪陈经理?嗤!”
“那你说咋办哩!”阿牛本来没啥好心情,被阿水劈头盖脸数落一通,顿时觉得脸上挂不住。他本来就看不惯阿水的为人:一个土包子,撇妻抛子的到城里打工,却整天不务正业,偷鸡摸狗,坑蒙拐骗。还不知羞臊,腆着个脸在人家吆三喝四耍威风。
“俺婆娘现今还在医院里打着吊针哩!劳动局没说不管,局长让俺们等,你说还能咋办?”
“真是个驴粪球子脑袋!”阿水轻蔑地白了阿牛一眼,“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啊?"说着话的工夫,一边掏出手机,一边往外走。约摸一袋烟的光景,阿水回来了,他给了阿牛一个地址,让阿牛去找那人,其间少不了向阿牛介绍一番那人的一些“感人事迹”。阿水说已经跟那人谈妥,阿牛先付1000元给那人,那人负责两天之内帮阿牛要回工钱。
“先付1000块?”阿牛皱了皱眉头,“太多了吧?”
“多啥呀!”阿水不屑一顾地说,“这可是友情价儿,我可费了半天口舌的。现今的千八百能干点啥子哩,充其量就是打打牙祭嘛。”
看着阿牛没啥反应,阿水叹了口气说:“你自己掂量着办吧,觉着行明天你就去找他,我可是看在同乡的面子上,不挣金子不挣银子还搭上电话费的,到时候别埋怨我不帮你就行。”
阿水边说边把桌子上的两包“黄山”烟揣进兜里:“这烟,我拿了抽了啊。”……
阿牛寻思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便跟房东借了三百块钱,凑够一千元。然后按着阿水提供的地址去找那人。
……
那人穿好T恤面无表情地问:“东西带来了吗?”
“带了,带了。”阿牛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米黄色的信封,信封里有一千元现金和一张欠条的复印件,那人接过信封,轻轻地掂了掂,掖进了裤兜。
“是老干部局旁边那个工地?”那人问。
“对对对!”阿牛点点头,“有个大塔吊的那家。”
“明早九点你过来。”
“行!”
第二天上午九点,阿牛如约准时来到那人居住的出租屋,他忐忑不安地敲响那扇斑斑驳驳的墨绿色防盗门,半天没人应。一丝不祥的预感立即涌入阿牛的心头。果然,一位老太太被敲门声吵得不耐烦,从旁边的楼道里探出头说:“甭敲了,屋里没人。”
“人呢?上哪儿去了?"阿牛感到两眼一片迷茫,不由得打了个趔趄,险些跌倒。
“昨晚走了,偷着走了。”老太太没怎么注意阿牛的反应,自顾自地说,“还欠着两个月的房租哩,真是没良心。”
阿牛一下子傻了……
局
星期天的上午,我照例到古玩市场里溜达。古玩市场就在我家楼下,但凡空闲的时候,我都会到古玩市场里淘弄点小物件。还别说,这几年还真没少让我“捡漏儿”,赚了好几万。我把这些钱藏在家里,没想私设“小金库”,主要是想偷着攒点钱,一旦在古玩市场里遇到好东西,不用跟老婆撒谎撂屁的要钱。你懂的,现在的老娘们可不好糊弄,跟她多要五块钱都抠根抠把的。更何况,老婆根本不支持我倒腾古玩——她偏说古玩市场里都是大骗子在骗小骗子,小骗子骗白痴,而我就属于白痴那伙的。哼!我迟早要捡个大漏儿,让这死老娘们瞧瞧!
古玩市场里人头攒动,赶大集似的。我信步走着,边走边看。我说过,我只淘弄小物件。原因很简单:小物件用不了多少本钱,赚头可一点也不少。我那几万块“私房钱”可得悉心呵护着,得让它多下崽,千万可别夭折了。一个中年妇女裹着粉红色的格子头巾,拎着个不大不小的柳条筐,筐上盖了块脏兮兮的花围裙——从我身边挤过去,一个西装革履大腹便便的男子紧随其后。男子拎了个棕色的公文包,戴着金丝眼镜,一边走一边说:“大姐,价不低啦,卖了吧。”
妇女睬都没睬他一眼,自顾自地在市场里寻了个空地,放下柳条筐,一屁股坐到地上。男子尾随过去,在妇女面前蹲下身来,他瞅瞅四周,压低声音说:“我再给你加五千。”
“不卖,不卖!”妇女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给到价儿就卖了吧,大姐。”我在一旁做了个顺水人情。中年妇女抬头瞅了瞅我,把额前的刘海儿往围巾里掖了掖:“不卖!”女人回答得很干脆。
“看看总可以吧?”说着话,我蹲到男子旁边。
“行——”女人边说边撩起柳条筐上的花围裙。筐里装了七八块形状各异的石头,我一眼就认出是品相普通的寿山石,值个三头二百的。实话实说,一下子勾走我魂魄的是中间那块鸡蛋大小通体橘黄的石头。“田黄石!"我差一点叫出声来。“一两田黄一两金”——那块石头至少有500克!我暗暗盘算了下:我的天,那块石头按市价至少值100万!
我不动声色故做镇静地说:“我当什么好东西,不就几块破石头吗?哪儿捡的?”
中年妇女白了我一眼,用围裙把柳条筐重新盖上:“可不兴不懂装懂。这东西可是祖辈传留,俺乡下人见识少,听人说这叫什么寿……寿什么石,金贵着呢!”
“寿山石。”我身旁的男子推了推眼镜,说,“没你说得那么金贵。”他暗暗用胳臂肘碰了碰我,意思让我帮他侃侃价。
“你要多少钱?”我问道。
中年妇女拎了拎篮筐,说:“就这筐里的东西,不挑不捡,5万,不讲价儿。”
“哪有卖东西的要一个是一个,还不让挑。”我旁边的眼镜男小声咕哝着。
“少一分都不卖!10年前就有人给到4万了。”妇女用眼瞟着眼镜男,哀怨地说,“要不是俺男人从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急等钱用,俺才不卖呢!看你们城里人一个个文绉绉的,买东西不实诚。”
眼镜男的电话响了,男子拎着电话离开了。放屁工夫又跑回来,一把拉起我。他把我拉到一个背人地儿,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沓人民币,气喘吁吁地说:“这是5000元,我有点急事儿,得半小时能回来。”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你只要看住那个死三八,不让她把东西卖给别人,等我回来,这5000元就是你的了。”
我一下子如坠云雾里。事情来得太突然,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眼镜男便把5000元现金塞到我手里。“一定等我回来。”说罢,急匆匆地走了。
我站在原地,独自思量了一刻钟,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大漏儿是上天赐给我的,非我莫属。我太幸运了,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正好砸到我头上,得抓紧时间!
如你所想,我如愿以偿得到了那筐石头。中年妇女坚持一手钱一手货,我只得把她领到家里,幸好老婆不在,买卖成交。不过,我不打算把那筐东西交给眼镜男——傻子才会把吃到嘴里的鲍鱼吐出来呢!100万让良心打打折也算值了。
我重新回到古玩市场,老远就见到眼镜男拎着公文包在转悠着。见到我,这家伙好像见到了救星,一把揪住我,忙不迭地问:“那个死三八哪儿去了?那筐东西呢?”
“东西卖了。”我有些无可奈何地说,“一个大老板把东西买走了。”
“我不是让你看着,等我回来吗?”眼镜男用狐疑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好像我把他的东西撬走了——我也回敬他一个无辜的眼神,好像我问心无愧似的。
“没办法!”我叹口气说,“人家张嘴给了十万,我有啥法子?”
“咳——”眼镜男长叹一声,“这就是命!那……钱?”
我是个明白人,赶紧从兜里掏出那沓钱,“5000元,一分不少,你数数。”
眼镜男把钱塞进公文包,嘴里直嚷着“命苦”,一脸沮丧地走了。
我哼着《好日子》的调子,一路小跑奔回家去。我得好好欣赏一下那块能改变我后半生命运的石头,好好在老婆面前显摆显摆。要让她知道自己的男人不是白吃饱窝囊废。省得她成天拿我跟那个瘦猴子马云比——有可比性吗?
我小心翼翼地从筐里拿出那块黄石头,觉得有点不对头:那劳什子握在手里软软的,毫无玉石那种清凉温润的感觉。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这才想起买卖成交前,我居然连摸都没摸一下这块石头,也从未有人说过这是块田黄。感觉欺骗了我,我犯了个低级错误。
果然不出所料!我那块自以为是的“田黄”竟是货真价实的“蜜蜡”!真可笑,我辛辛苦苦攒下的“私房钱”转眼打了个“水漂”……
说真的,到现在我也没闹清我是如何着了道,是贪婪?是利令智昏?反正我是吃了个哑巴亏。打那以后,我再没踏入古玩市场半步,我知道,类似我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市场里上演着。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