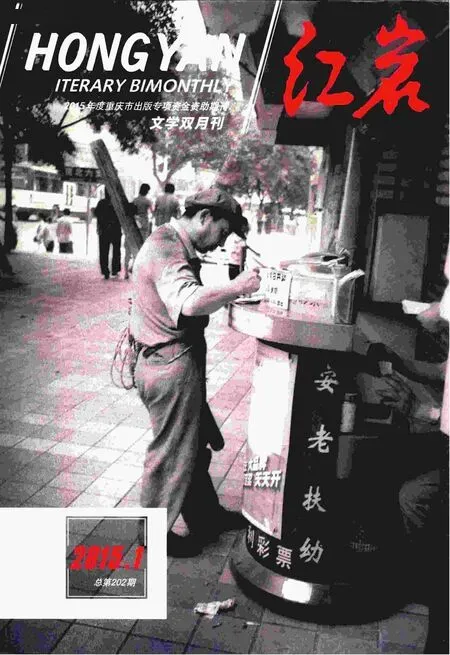变形记
祝勇
祝勇 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历史研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
已出版主要作品有:《旧宫殿》、《血朝廷》、《纸天堂》、《故宫的风花雪月》等,20卷《祝勇作品系列》正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任总撰稿和导演,代表作:《辛亥》。先后荣获中国电视星光奖、金鹰奖、十佳纪录片奖、学院奖等诸多影视奖项。
一
我们不能错过“黑船祭”—— 下田当地纪念“黑船”的节日。2014年5月16日,我们到达下田那一天,正是它开始的日子。一到酒店,我就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酒店的大堂上悬挂着许多“黑船祭”的小旗,墙上张贴着“黑船祭”的宣传画,连房间里的睡衣上,都印满了大大小小的“黑船”造型,处处提醒着“黑船”的存在,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下榻的这家酒店,名字就叫“黑船酒店”。
公元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领的四艘军舰,也就是日本人所说的“黑船”,在鸦片战争之后已经开放的门户——上海完成编队,直指日本江户湾的浦贺港的。与鸦片战争不同的是,美国舰队没有开炮,因为这个弹丸小国,实在是不经一打,也就没有必要开炮,他给日本幕府的国书傲慢地说:“你们可以选择战争,但胜利无疑属于美国。”他甚至送给幕府一面白旗,告诫他们,一旦爆发战争,他们要学会投降,简直是羞辱到家了。只是吓唬了一下,孝明天皇就天颜大失,一筹莫展了,江户城也乱成一团,“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进神社,击掌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 “落后就要挨打”,终于,这个积贫积弱的岛国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我是为中央电视台创作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之《甲午战争》,专程来日本寻访历史遗迹和史料的。除了纪录片,我还打算写一部书,通过日本遗迹和史料重看那场战争。书的名字去时就想好了,叫《隔岸的甲午》。
下田属静冈县,在伊豆半岛的南端,伊豆当然就是《伊豆的舞女》的那个伊豆。在川端康成的这篇小说里,我第一次看见下田这个地名。川端写道:“巡回演出艺人辗转伊豆、相模的温泉浴场,下田港就是她们的旅次。这个镇子,作为旅途中的故乡,它飘荡着一种令人爱恋的气氛。”
我未曾来过下田,但我在一些日本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海边小镇,有茂密的山林、起伏的公路,还有面向大海的悬崖。其实午后时分在御殿场看过富士山,我们的车子转而向南,就一头扎进了伊豆半岛茂密的山林。从东京到伊豆,我仿佛一下子从现代穿越到古朴的旧时代,从我视线尽头走来的,应当就是《伊豆的舞女》里那个“头戴高等学校的制帽,身穿藏青碎白花纹上衣和裙裤” 的20岁青年。
那青年不是三浦友和,而应当就是川端康成自己。1918年,川端康成考上第一高等学校后,就去了伊豆半岛旅行,并邂逅了他小说里的那位舞女。第二年,他在第一高等高校文艺部编辑出版的《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千代》的小说,小说中的那名舞女,就是《伊豆的舞女》里熏子的雏型。
1926年初,川端康成在《文艺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伊豆的舞女》。这篇小说后来在日本尽人皆知,还先后6次被搬上银幕,其中,田中绢代、吉永小百合先后在1933年和1963年出演过《伊豆的舞女》,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是1974年山口百惠主演的电影,那一年,山口百惠只有15岁,比川端康成记忆里的熏子还小,那是她第一次登上大银幕,也是第一次和三浦友和共同演出。她清清浅浅的笑容,从此刻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也涂抹不掉。不知那个名叫熏子的舞女,是否读过这篇小说,或者看过这些电影。在电影里,那些貌美如花的演员,都是作为她的替身出现的。不知世界上还有哪个初恋情人能够享受她的待遇。可她始终没有出现,以至于川端康成在60岁时无奈地写道:“电影、电视和广播多次映播了《伊豆的舞女》,不晓得她知道不知道?《伊豆的舞女》这篇作品也选入国语教科书里,她恐怕不知道吧。”
川端康成一生中不知去过多少次伊豆,他爱那里的自然,当然也爱那里飘荡的那种令人“爱恋的气氛”。那的确是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地方,川端康成朦朦胧胧的初恋,就应该发生在那个地方。
二
我走进“黑船酒店”的房间,窗子刚好面对着深蓝色的太平洋。隔窗一望,我笑了,因为停在岸边的,正是那艘威风凛凛的“黑船”。佩里的“黑船”早就去向不明了,但它的替身还在,赖在下田不走,成为这座城市里最重要的布景。
暮色降临时分,窗外响起了音乐声,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房间里的“黑船祭”活动册页上说,今晚有音乐会,舞台是在街边搭起的,夜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舞台的灯光刚好亮起,人们就朝着那灯光里走。音乐自舞台上倾泻下来,像一袭袭帖身的绸衣,把每个人包裹起来。海风掀动着绸衣,让每个人的身体都荡漾出节奏感,像是那舞蹈的一部分。
川端康成把下田形容为“旅途中的故乡”,只有住下来,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深意。多日忙碌之后,倒是在下田——一个面对太平洋的海边小镇,我睡了最安稳的一觉。那一晚有很大很圆的月亮,从海面上一点一点升起来,像一盏孤独的灯,照耀着幽黑的大海。在酒店泡室外温泉,我们就仰头看着那月亮,心里想着我们此时几乎是在本州岛的东端尽头,可以说是孤悬海外了。我惊叹于下田——或者说整个日本傍山面海的美,心里苦思,守着如此美丽的家园,日本人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而偏要选择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我整晚都开着窗子,也没有拉上窗帘,淡淡远远的音乐被风吹着,带着山林与海风相混合的腥甜气息,溢满整个房间。“黑船酒店”当然是一座现代化的酒店,但它的内部房间一律装修成和式。到日本的第一晚,我疲惫之极,像一只白胖的蚕虫子,躺在桑叶一般的席子上,浸泡在清风和蔺草席子的芳香里,美美地睡上一觉。
像一首古诗中写的:“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
恍惚中,我看见大片的樱花在夜空中绽放,我知道那不是梦,是“烟花祭”开始了。我坐起身向窗外看,硕大的花朵正在夜空中此起彼伏地绽放。花期如梦,烟花的花期最短,常常是刚刚绽放就消失无踪了,不肯有丝毫的逗留,因此更像是一场梦,让真实的美景变得虚幻。
我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人居然是以一份狂欢的心境度过“黑船祭”的。我以为当地设立“黑船祭”,并且仿制出一艘原大的“黑船”供人瞻仰,是为了“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毕竟,下田是日本人缔结城下之盟的耻辱之地,而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又把日本文化总结为“耻感文化”。但是,自我到达下田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自己完全错了。
三
下田的了仙寺是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下田条约》的历史性场所,因此被定为日本国家史迹。了仙寺如同日本的许多寺庙一样,依傍着青山,山色翠绿,天空湛蓝,近处有粉色和白色的花瓣一层层地绽放。我们有备而来,已经预先知道了仙寺宝物馆陈列有当年的有关公文和黑船舰队来日的画卷,并收藏有关“黑船”舰队的文物一千多件,是日本国内最大的“黑船”资料库,要想了解日本开国和对外贸易的历史,在宝物馆里可以一目了然。
我们抵达了仙寺的时候,看见门口竖着一面用来照相的画板,上面画着“黑船”,还有佩里和幕府将军的形象,只是头部是挖空的,拍照的人站在画板的背后,把头伸进那个挖空的圆洞,他自己就成了佩里或者幕府将军,每一个把脑袋伸出那个圆洞照相的日本人都开怀地笑着。寺内还上演着一出舞台剧《下田条约的签订》,剧中美国“黑船”的炮声把幕府将军的脸吓得变了形,他们对美国“黑船”的夸大让台下笑成一片。美国等列强打到了家门口,逼幕府将军们投降,这事就这么值得开心吗?还有没有民族自尊心了?
我想当时的幕府将军们是有自尊心的,不战而降,世界上有比这还丢人现眼的事吗?难道这不是对“武士道”(Bushido)的巨大反讽吗?自从12世纪末,武士首领源赖朝出任“征夷大将军”,创立镰仓幕府,统帅天下军政,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前,那些威风凛凛、武艺高强的武士一直都是日本历史的主语,历史学家坂本太郎在描述武士时说:“武士娴于弓刀,它是对人忠心耿耿的打仗机器。他们穿着一套精心设计的有效铠甲来保护自己。在宽腿马裤、宽大袖子的轻丝袍之外,他们穿着金属薄片做的一件套战袍,用绳子串起来,通过皮带子吊在身上。为活动方便,右臂没有保护,腰下的铠甲分成四片宽松的战裙。武士头上醒目地戴着向外张开的头盔,意在威吓敌人,也可避开刀砍。”
第一次来日本,我就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到过那些精美的武具。那些被展厅的射灯照亮的铠甲、头盔、刀剑几乎可以被当作艺术品看待,其中溶铸了日本人特有的细腻与精致,它们的审美品质让人几乎忽略了它们的暴力本质。幕府时代一位名叫村正的匠人,制作出一种锋利无比的刀剑,只要把他制作的刀剑放到小溪里,迎面漂来的树叶就会被刀刃一切两半。
然而,在这些光芒闪烁的武具背后,是日本漫长的、血腥的杀伐史。无休无止的统一战争,却成全了这些武士。尽管这些武士经常一无所有,穷成了赵光腚,许多下级武士甚至没钱讨老婆,只能混迹于花街柳巷,但“武士道”却让他们感到无比富有,这种不畏艰难、忠于职守、精干勇猛的信念照亮了他们穷困潦倒的生命,让他们成了“英雄”。宗泽亚先生在《清日战争》中说:“在漫长的历史变革中,武士主导了中世社会的发展,完成和构筑了近世社会的体制。长期以来,抽象的理想主义精神伦理,在全民意识形态中定格,即‘武士本分,其勇乃武士的价值,武士的价值对君主的忠义’,这种支配武士价值观的理想境界‘士道’在江户时期发扬光大。” 他们手起刀落,斩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那份潇洒,至今仍在许多影视剧和电玩游戏中不断重现。
丰臣秀吉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
如晨露之坠地,
如晨露之消失,
宏伟如大阪城堡,
亦不过梦中之梦。
在他们眼里,人生并不值得留恋,如晨露、樱花般绚烂地绽放又迅速地消失,更不失为一种凄艳的美,连女人也不例外。静御前是日本版的“花木兰”,她在12世纪在源氏将领的麾下作战,在一次战斗中,她冲向敌将,将他拉下马,一刀割去了他的首级。而大多数留守后方的女人,也需要军事训练,她们使用一种刃长两尺的刀,面对侵犯,也会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战斗力,据说她们的弯刀常常可以砍断敌军的马腿或者直接插入步战士兵的身体。对于她们来说,忠诚和荣誉同样重要。大名织田信长的妹妹,后来的浅井长政夫人,被认为是“天下最美的女人”。为了缔造联盟,她曾两次出嫁,当她的第二个丈夫受到德川家康的攻击时,她将女儿们送走,她本人却拒绝离开,以自杀表达了她对丈夫的爱和忠诚。
因此,在幕府时代耀眼的繁华背后,总是浮现着一种凶狠的表情,凶狠的武士,终于抵挡不过西方人的战船。在这里,这个封闭的岛国决定开放自己的门户,与西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包括: 1855年,日本与俄国签订《下田条约》,要求日本开放箱根、下田、长崎三港为对俄商埠。1858年,美国又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迫其开放神奈川(后改名为横滨)、长崎等五个通商口岸,降低关税,规定出口税为5%,美国货的进口税除酒类为35%以外,其他绝大多数为5%,等等。就像戴季陶所说:“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杀伐气。这都是最值得我们研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我们习惯于把这样的条约称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因为这种条约有两项重要内容,一向被我们视为耻辱——第一是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中国犯罪,中国不能审判,而要由他的领事来审判;第二是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国家可以将税率降低到5%。但是只要回看原文,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不平等条约其实是平等的,因为这些条件都是对等的,只是因为我们不到他们国家去,因此我们自己把它变成了不平等条约。
然而,日本人逐渐意识到,它们非常平等,因为它们让日本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对于开国利益的获得,日本方面比起美国方面是多了许多……如果你考虑到之后的文明开化现象,日本方面是获得大得多的利益……”伊豆半岛南端的下田,从此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开国之地,是他们融入新世界,成为世界强国的开始。所以下田这个名字,尽管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尽管它对日本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中国的近代史是和日本紧紧纠缠在一起的,因此,下田对中国来说也无比重要。
四
当“黑船”来袭的时候,日本也有林则徐式的民族英雄,抱着飞蛾扑火的决心,与西方列强以死相拼。1859年,日本的爱国志士在横滨杀死俄国军官和水兵;1860年,他们杀死了美国公使馆的秘书;1862年,几名年轻志士趁着夜色靠近品川御殿山新建的英国公使馆,神不知鬼不觉地锯断木栅栏,潜入进去,扔出自制的燃烧弹。21岁的伊藤博文参加了这次恐怖活动,那时的他,是“尊王攘夷”的积极分子……“尊王攘夷”,略近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
这一份宁折不弯的气质或许可以让武士们超凡入圣,但并不能救日本于水火,相反只能把它往火坑里堆。日本人很快明白了这个道理,情况也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公元1861年,日本幕府派遣使节前往法、英、荷、俄等国,与西方列强商讨推迟开放江户、大阪等城市的时间,使团成员中,有福地源一郎、福泽谕吉、箕作秋坪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日本的近代化转型中至关重要的人物。这是日本人第一次到西方的大城市旅游,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花花世界,立刻就让这群日本乡巴佬看傻了眼,顺带着也唤醒了日本人的强烈的自尊心。村垣范在《遣美使日记》中密密匝匝的图文,记录的不只是西方科学知识,更透露出他们对西方强国表现出的惊讶和赞叹。
面对“黑船”事件之后的国际形势,日本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说:“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与夷狄。必须严定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蓄养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吉田松阴为日本建立海军提供了一个真正目标——“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
似乎是担心他的这些在当时看来很不靠谱“远大理想”会吓坏了幕府当局,吉田松阴还提供了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案,其中包括:派遣优秀人才到国外直接学习;在日本设立近代化军事学校,在军事学校中的教学必须是按照外国书籍的原文去教授学生,如此才能直接了解并学习到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尽管在美国“黑船”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幕府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实行开国,但在他们眼里,依旧是一团狗屎,必须把它彻底打倒,再踏上亿万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维新运动是思想、体制、社会的全方位革新,大清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维新运动尽管发生在同时,却根本没有可比性,甚至连戊戌变法也只是在沙漠上泼上一盆水,只冒了一股烟儿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倒是五四运动可与维新运动有一比,但与明治维新比起来,五四运动整整晚了半个世纪。
“黑船事件”让日本人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14年后,公元1867年底,萨摩藩武士西乡隆盛与大久保利通等人发动政变,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1868年四月,在弥漫日本的樱花的芳香里,一份政治改革方案颁行全国,它就是著名的《政体书》。明治维新,自此开始。
如同我在《盛世的疼痛》一书里所写:日本人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只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血性救不了日本,还需要“理性”,对于日本来说,这个“理性”就是谁厉害就拜谁为师。眼下是英国人厉害,所以不仅不应该与英国人为敌,还应该拜英国为师。与坚守儒家精神价值的中国人不同,“在‘町人根性’影响下,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 ,谁厉害,谁就代表正义,他们没有儒家“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没有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优越感……,无论多么精深的文化,在他们眼中都会被分解为至为简单的两种:有用的和没用的,在伊藤博文眼里,西方文化是有用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已经过期作废,日本人不准备跟亚洲人玩儿了,决定与狼共舞,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叫“脱亚入欧”。
与福泽谕吉相比,就读于剑桥大学的稻垣满次郎更深谋远虑,因为在比学赶超西方列强的热潮中,他不仅有豪猪般的激情,还有鳄鱼般的冷静。当人们在福泽谕吉的煽动下把目光投向西方,稻垣满次郎则看到东方还是真正的福地。投奔西方只是出发,返回东方才能算是抵达。在甲午战争前三年出版的《东方策》一书中,他已经预言了今天的事实,那就是:世界政治的中心正在往亚太地区转移。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中取得优胜的大国注定会成为下个世纪的主导。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日本必须努力增强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为了推行他们的扩张主义,对中国有深入研究的冈田仓心又给野心膨胀的日本提供了一副更加生猛的理论药方,就是“日本的伟大特权”。这一“伟大特权”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流贯着印度、鞑靼的血,我们从这两方面汲取源泉。我们能够把亚洲的意识完整地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的与这种使命相适应的一种遗传。我们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的无与伦比的祝福,有着未曾被征服过的民族所具有的自豪,我们有着在膨胀发展中作出牺牲而坚守祖先留传下的观念和本能这样一种岛国的独立性,我们就能够使日本成为保存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而在中国,王朝的覆灭,鞑靼骑兵的侵入,疯狂的暴民的杀戮蹂躏——这一切不知有多少次席卷了全土。在中国,除了文献和废墟之外,能够使人回想起唐代帝王的荣华、宋代社会的典雅的一切标记,都不复存在了。
日本就这样被他们想象为新的“中央之国”,亚洲的一切秩序,都是围绕日本这个中心来构建的。无独有偶,德国纳粹也宣扬“种族优越论”,认为只有日耳曼人与雅利安人才是上苍赋予了“主宰权力”的“优等民族”,有消灭和奴役劣等民族的权力。美国著名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约翰·道尔在分析日本民族主义内核时认为,西方种族主义一般以一个具体鲜明的劣等“他者”来衬托,主要表现为对自我的高扬甚至崇拜。在对其他种族的贬低和偏见方面,日本人和别的民族相比也毫不逊色。 德日好像都意识到自己的特异功能,准备联手主宰世界了,只是这种不可思议的自我膨胀中,早已预埋了他们的悲剧。
五
在下田的那场酣睡无疑是我个人睡眠史上的重大事件。很多年中,睡眠都是困扰我的难题,但在下田的夜风和月色中,这一切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梦醒时,我觉得自己足足睡了一个世纪,从一个甲午年,睡到了另一个甲午年。
伊豆天亮得早,此时已是九点,阳光已升得很高,有近中午的感觉。透过窗子看大海的点点光斑,犹如无数只华璨的蝴蝶在半空中乱舞。“黑船”还固执地停在原处,没有开出去一步,仿佛历史不肯睡去的神经。
“黑船祭”的大游行预定开始的时间是上午11时。剧组分成两组,我与余乐、金颖为一组,前往游行始发地佩里公园,陈爽、曹一平、邢熠(日本新中华通信社记者)等在中途拍摄。从佩里公园通向市中心的道路很窄,游行开始前,当地民众已经沿着道路排成两队,手里挥动着小旗(日本和美国国旗),对游行翘首以待了。
11点,军歌响起,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肃穆起来,游行开始了。军歌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军歌《军舰进行曲》,这支岛山启作词、濑户口藤吉作曲的军歌,中国人并不陌生,因为它曾经作为日本“二战”时日本海军军歌,响彻“大东亚战争”的战场,被称作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政策主要工具。歌词大意是:
防守和进攻
都依赖着这黑色的钢铁城堡
漂浮在海上的师
镇守四方的皇国军舰
开火吧!
向着仇视太阳升起的国度!
煤烟摇曳着仿佛海上的巨龙
炮弹的呼啸盖过了风暴中的惊雷
开拓万里波涛,
布皇国国威于四方
然而,在2014年的日本,在下田这样静美的海边小镇听到它,还是让我觉得恍惚。下田,这个“旅途中的故乡”,这个充溢着少女微笑的地方,怎么奏响荼毒生灵的军国歌曲?在水彩画似的海湾风景中,它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尽管海上自卫队的军舰就停泊在下田的港口,近在咫尺,早上我乘坐那艘“黑船”游览下田港湾的时候,还亲眼目睹了这些军舰。但那毕竟是今天的自卫队,而不是从前的侵略军。这个曾经以“爱和平的人,请到自卫队来”为招募广告的日本自卫队,难道真的要“向着仇视太阳升起的国度开火”,让炮弹呼啸着盖过“风暴中的惊雷”?
六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支军歌是与日本侵略的恐怖记忆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在它雄壮的旋律里出现的,是天幕上落下来的黑压压的炸弹、南京屠杀的雪亮刺刀、七三一部队的活体实验、“三光政策”的变态与疯狂。日本军人无数次在这支军歌里器宇轩昂地出发,而他们行军的终点,却不是“王道乐土”,而是他们亲手制造的地狱。刽子手的形象并不那么美好,再优美的军歌也修改不了杀人者的形象。不知当年开国的幕府将军们是否会想到,他们走向世界的冲动,竟然慢慢被篡改成征服世界的野心。他们听懂了“黑船”的语言,也相信了“黑船”的哲学。他们很快有了自己的“黑船”,去兵临别国的城下。这样的“黑船”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快感,让他们欲摆不能,最终让他们陷入彻底的癫狂。
然而,对民众来说,战争中的变态与疯狂都被过滤掉了,关于战争的所有真实讯息都中途夭折了,无法跨过辽阔的日本海回到故乡。故乡的人们既听不到南京被屠杀者的哭喊,也听不到慰安妇的痛苦呻吟,当战争的消息传回日本时,剩下的只有日本军人拼死搏杀的“英勇”和“开拓万里波涛”的“豪迈”。一场战争竟是那么容易被简化,几乎简化成了军歌本身,激情,嘹亮,具有唯美的品质和鼓动人心的力量,它遮蔽了战争本身的残酷、冷血,以及被害国人民的诅咒。
走在最前面的,是驻日美军的旗手,手里举着的却是日本国旗和日本海军旗,后面是军乐队,接着,下田市长、静冈县知事、横须驾地方总监、第三区日本海上保安部长、美国第七舰队战斗部队司令官等日美官员乘坐各自的敞篷轿车接踵而来,有些官员身边还坐着妻子儿女,戴着雪白的手套,微笑着向人群频频致意,一副“军民共建”的和谐景象。紧随其后的,是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方队。日本自卫队的旗手很帅,又瘦又高,军姿挺拔,手里握着日本海军旗,呈四十五度角斜举着,他走过来时,路边的民众情不自禁地响起掌声,或者拼命地晃动着手里的小旗。臭名昭著的日本海军旗,在特定情境下的确可以给人一种力量感,在中国人心中近乎滑稽的日本海军军歌,此刻也有了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让现场的人们血脉贲张。军队的后面,是当地民众和学生的方队。在军歌中,每个人的表情都是严肃的,军歌把他们每个人都与他们的国家联系起来,让他们心中充满了庄严感。
然而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都会知道,那些英雄主义幻想不过是一场幻觉,是军国精心策划的骗局。那些经历过“大东亚战争”的老兵们曾经相信过军歌缔造的神话,但他们绝不会再信第二次了。可怕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人类的本性,年少的人们不会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他们会被那种所谓的“英雄主义”情怀煽动着,重新投向战场。
我想起爱因斯坦曾经对悲剧做出这样的定义:人们总在做着相同的事情,却总想获得不同的结果。
在下田,“黑船祭”不过是一个旅游者的狂欢节,但不知为什么,从下田的天光帆影、歌舞升平里,我却看到了和平的脆弱。清茶浅酌,花好月圆,在枪炮的面前,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创作谈
我很喜欢看作家的创作谈,无论从同行的角度,还是从读者的角度,窥知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才是一件有吸引力的事。然而,轮到自己头上,又觉得创作谈是最不好写的。因为写作太多地依赖着写作者的个人经验,是写作者个人经验的总结。就像一位高超的医生,无论有多么先进的医疗设备作辅助,手术时个人的判断与手感依旧是重要的。而这样的判断力与手感,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更难以成为普遍的经验。固然,写作连通着一个广大的公共世界,存在着某种普遍的、永恒的向度,而实现它的手段却又有很强的私密性,像暗盒里的胶卷,虽图像丰富,却不可轻易曝光。这些经验深藏于身体内部,秘密生长,蔓延成我们眼前的一部作品。这正是写作的神秘性所在。
我固然很愿意分享莫言获诺贝尔奖的经验,也想得知张嘉佳销量过二百万的秘密。但我绝不至于傻到相信仅凭一些现成的口诀就能抽中文学的彩票。当然,我也搜索不出多少有价值的经验贡献给他人。如果一定要说,我只能如实招认,真正的写作者,是一个内心很大的人,强大到可以不去计较无边的孤独、命运的捉弄、反复的失败、同行的压制、市场的冷漠,以及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磨损,这些都是写作生涯的一部分。甚至,可以功利地说,所有这些来自外部的挤压,都将极大地丰富一个写作者的内心,转化成他的写作资源,从而从相反的方向上,成全一个作家。
所以,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写作,是与他的生命同步成长的。年轻时依靠才华,但再炫目的才华也抵不上一颗宽厚、博大和丰富的内心。如果说训练,生命的沧桑就是必修课。这是老生常谈,却是永恒真理。写作者的内心不会折旧,相反,越是磨损,就越有韧性。有80后曾豪迈地宣称:“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但不必着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的沧桑都会不请自来,公平地降在每个人头上。既不会放过一个好人,也不会轻饶一个坏人。这不是咒语,只是说出了生命和写作的真相。是预言,也是期许。
今夜,在旅次中,在酒店提供的几张A4纸上匆匆写下上述自供状,有人可能听出了弦外之音。说了半天,不过是一位青春已逝的中年老男人的自我宽慰或者自我辩护。但我很陶醉于自己的当下,既没有了凭青春打天下的那一份骄狂,也没有老到写不动。我写过一些及格或不及格的文字,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有大把的时光可以用,还有机会写得更好。列夫·托尔斯泰71岁才写完《复活》,像《复活》这样的作品,也只有71岁的托尔斯泰能够写出。因为那时,他已然长成了俄罗斯土地上的一棵老树。我们无法与大师比肩,但大胡子托尔斯泰让我们感到温暖和踏实。他让我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伟大的作品,绝不可能产生于一颗轻薄、狭隘、柔弱、荒凉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