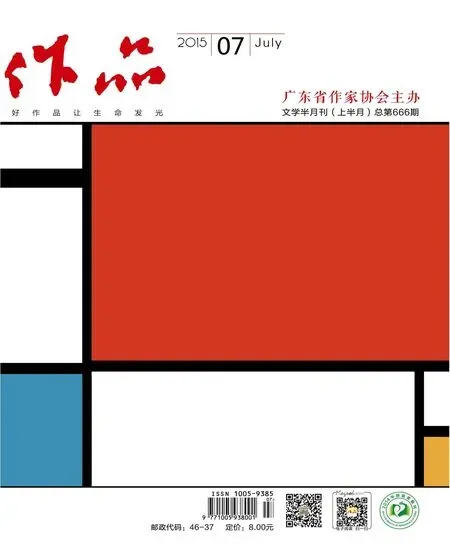晚上遇见莫小海
文/李 云
晚上遇见莫小海
文/李云
季红梅总会在密集如雨点的织布声里想起一个男人。
男人叫莫小海。两人曾经是工厂里做工的同事,他做保全工,季红梅是纺织女。纺织女简称织女。易让人联想到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那么,莫小海是“牛郎”?咱们很难见到,当中存在着一条银河——不过,见了又能怎样呢?如此,还不如不见,各过各的生活。但不会忘记。比如现在,季红梅又想起了他。
想起了这个男人的季红梅,心里就乐开了花—— 一个女人内心一旦开了花,就注定了身体里的爱意会滋生出来。
前面,季红梅的丈夫正蹲在不远处维修机器。丈夫叫黄西林。身形清瘦颀长,皮肤干净白皙,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当然,也可理解为他没有工夫打理。季红梅第一次看到他,就觉得他男生女相,俩人婚后在床上欢愉,也不止一次说过,你要是女孩儿一定很好看。手指在丈夫的眼睛、鼻子、嘴唇上画着,总觉得这样的五官比自己的长得都精致。
但长相精致的男人并不就能高贵起来。两口子这些年,一直在不停地干活,生活过得风雨兼程。有时候,季红梅看着丈夫双手油渍的摸着机器修理,有几分心疼。但仅仅是心疼。于是,接好断头,季红梅将手落在屁股上擦试着朝黄西林走了去。她的屁股很有肉感,是那种天生瘦个子也翘着一个圆臀的女人。此刻,季红梅想跟黄西林说会儿话。迫切地。如果不说,她盛开的心灵,就无法闭合了,渴望表达,也渴望聆听。谁叫夫妻俩平时话说得太少了!黄西林成天忙着修机器,接单子和送布;季红梅除开织布还要管理车间,做账,以及料理好家务。比去外面打工还不省心。最最主要的是,在织布车间说话不方便,织布机的声音太大了,说轻了听不见,得喊着说。可是,有些话一旦喊出来,感觉就没了,温情也没了,像吼。
季红梅斜靠在车间的柱子上,只觉得喉咙里像有一把青草在骚扰着。她也不想过问“好加布了,喷嘴没有了”之类的工作用语。双手落在屁股上摸着,摸了一屁股的燥热。想想,季红梅问黄西林道:嗨,你说我这也不闲啊,每天十二小时对班调,咋就不瘦掉点呢!你看这屁股,还是那么大!
季红梅说着就扭着腰肢转了一圈。
黄西林没有听见她说话,他的眼里仿佛就只有机器!季红梅落了个一脸悲凉。嘀咕道:就懂得修修!机器的病你能看,咋看不懂人的呢?黄西林曾经的一手好技术,此刻变得一分不值了。然后,季红梅就看着黄西林的手走神了,想到他曾经上班的工厂老板娘为了留他这双手可是下足了功夫。这个很有钱却瘦得像一直在饥饿着的老女人,为了留住黄西林的这双手,还拿着粉嘟嘟的毛巾帮着擦油腻腻的手。呸呸,真恶心!外面的女人再老也是新鲜的橙,远远地站着,都有一股鲜亮的气息跑来。害得黄西林对毛巾上的香气经久不散:你晓得吧那条毛巾洒了香水!不知道用了什么香水能这么香!季红梅笑着问:比桂花还香?男人连连点头,季红梅又问:喜欢吗?男人嘻嘻笑着拉季红梅的手,试图亲热,季红梅推开他,叫他老实回答。黄西林点头说:好闻。季红梅啐一口痰到地上:那好,咱们也开厂,只要有钱了,我也会香喷喷的。有钱谁不会花啊!黄西林退缩了,开厂要钱的,你有钱啊。季红梅有种被逼上梁山的感觉,一愣,流泪道:我会织布,你会修机器,咱怎么老帮别人修呢?
想到这个女人就会牵扯起创业史,季红梅便扭着屁股将头也扭开了,兀自陷入在一种沉思中。是的,季红梅的身体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她看着黄西林一双手在油腻腻的齿轮间摸来摸去,穿越了山山水水,沟壑和丘陵。身心一动,突然感觉到这双修长的手指是落在女人身体上的,每一个指关节都很熟悉女人的身体部位,深具把握度,那么迷恋手艺和迷恋手掌相差有多远呢?
于是,莫小海又出来了。同时,得以证明的是工厂男女间的情事谁不知道呢,你想啊众多男女聚在一起,一个修机器,一个机器坏了需要被修,说白了,修好的可不单单是机器,还有身心上的跃跃欲试。天长日久处下来,总归有几个是对上了眼的。真好也有,为了产量也有。工厂里的收入都是多劳多得,还有个人呵护着自己的身体,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每有搬运工来,将布匹扛上肩膀,都会嘀咕上几句:这布怎么腥得嘞!谁织的,骚味重得嘞!
当然,莫小海与季红梅还没有到更深的那一步。这种感觉很奇妙,当时不觉得,可是,一旦他离开,却从此念念不忘了。仿佛每一个女人都善于藏一个男人在心里,让这个男人在自己每一个无助的时刻站出来,让无聊的日子散发出一些光辉来。为此,季红梅一度里,是渴望着能够跟莫小海相遇的,再发生点什么的,比如说亲吻,到墙角的布堆里去打个滚。
这跟爱情无关,也跟莫小海长得风流倜傥无关。季红梅总觉得不甘,人生不能就这么成为机器的一份子啊。总得发生点什么,开心一下吧,你说要怎么才能平复好身体深处荡漾着的热度与旖旎呢,还有喉咙里的酥痒感?于是,莫小海的出现是必要的,季红梅便愈发迷恋他身上的男人味,那沧桑历尽,但又深得人信赖和依靠的长相多么具有力量感啊。还有,他喜欢自己,也曾暗示过。他每次走到季红梅身边,季红梅的脸就会红起来。但最终季红梅只被他摸了几把屁股,在机器的喊叫声中做了一个浅尝辄止的性行为的暗示。但是,他的手掌仿佛就一直留在身体之上了。
两人后来没有“好”下去,是莫小海离开工厂自己做老板去了,他购买了织布机带着老婆发家致富去了。在江城,人人都在想发家致富,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百分之八十的人从事的是纺织行业,随便在路上遇见一个人都会对着一块布说得头头是道。自然,纺织厂遍地。莫小海的离开,让季红梅思念了一阵子,幡然醒悟了,也开始琢磨起要么也开个小厂做做?所谓的小厂,就是买上一组喷水织机由自己来打理,可以给大厂加工,也可以自产自销。对于季红梅这种没有关系网的、初出茅庐辈最安全的方式是给大厂加工——只是这样一种梦想实现又在好几年后,这时候,那个叫莫小海的男人已经暴发了。民间四处流传着他的暴发史,听来玄乎神奇,却又是合情合理的,这个男人脑子灵活啊,他最终还是靠自己精湛的维修技术与众多老板搭上了关系。关系网建立好了,发达就是很快的事。季红梅就想,黄西林也懂技术,只可惜黄西林不能跟莫小海比。
现在,季红梅家的工厂,资产为织布机24台和一个租赁来的车间。只可惜,生不逢时,此时市场开始走下坡路,纺织业时好时坏。最现实的问题是,季红梅当初根本没有资金去开厂,她手头的钱远远不足她这样异想天开。这一会租赁厂房,一会购买织布机,还要买各种维修配件,以及一大批不可预计的开支,需要花钱的地方多如蚂蚁。好在季红梅开厂的决心大,坚持了下来。亲自去找了黄西林姐夫帮忙。黄西林的姐夫是搞建筑的包工头,早靠着纺织业行情好赚了个金钵银钵。可姐夫会赚钱,也会花钱,不仅会花钱,他还会花女人。一会儿大姑娘,一会儿小媳妇,起初还藏着掖着,背着姐姐在外面搞搞算了,可后来就有女人跑到家里来挑衅。不知是现在的女人胆子大了,还是姐夫没有将姐姐放在眼里?姐姐不仅要赔钱给那些女人,还要受气,没有想头了,就哭丧着脸朝娘家跑——悲痛欲绝地滚在凳子上哭诉这日子没法过了!黄西林便被父母怂恿着去帮姐姐出头,可去了几次,只得放弃了,因为姐夫早已是一个圆滑之人,处事周正,不是一般人能摆平的。见妻弟来,不管你脸上有多少怒火,他都只客气地散烟、泡茶,之后再不温不火道:不就是为个女人么,我又没对你姐不好!你就别担心了!如此,去也是白去,黄西林只好回来劝姐姐说要过就忍着,不过就离婚。你离婚他巴不得呢,他这样十八岁的小姑娘都会主动送上门!所以,季红梅跟姐夫借钱的事是瞒着黄西林做的。这次借贷的过程自然也给她带来莫大的耻辱,但是不跟他借贷又能跟谁借贷呢?虽然季红梅想过要么去找莫小海去借点,可拿什么原因去找他呢?
季红梅暗自叹道:如果没有那一摸,大家看在同事过的面子上倒好开口,可他那一摸就将关系摸结束了。
黄西林终于修好了机器,他站起来试机的时候,看见季红梅失魂落魄的样子,便用胳膊肘拐了下季红梅的肩膀,说,发什么愣啊,机器都停光了。他的这一拐却错误地拐在季红梅的乳房上,有点疼,季红梅冷不丁就有点火大,你就不能好好说句人话么!
前一秒的春风拂面早已荡然无存。季红梅转身离开,大约走了三五步,她又转身,笑吟吟道:我先去擦下身子,机器你照看着点。
属于季红梅的车间大门口上挂着一块长方形的蓝牌子:B02车间。这个车间就是季红梅嘴巴里所说的工厂。车间是租赁来的,季红梅第一次站在B02车间门口,竟热泪盈眶。
在B02车间的角落里,有一间用铝合金隔起来的小房间。房间约十六七个平方。是两口子的卧室。除了摆着一张小床,和一张抽屉桌。后来还硬塞进一个小衣柜和一只洗脸盆架子。抽屉桌上码着一摞摞出布的码单,季红梅临睡前都会坐在桌前拿着计算机照着码单加减乘除一番。如此,这里也是工厂的办公室。季红梅打好一盆热水放在门背后,墙壁上挂着她擦身用的毛巾。毛巾是阴干的,有点硬,也有股馊味。季红梅就想去浴室洗澡。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很快她就蹲下去擦身了。有关背后的床,两口子平日里也是鲜有机会一起躺在上面舒舒服服睡觉。至于夫妻间的事,也得看时机。有时候白天劳累了一天,体力不支,不想了;有时候想呢,又会遇见一些不配合的状况。比如那个贵州籍的织女,就很调皮,每次都会在关键时候敲门,一口一个老板叫着说机器坏了。机器坏了就得起来维修,不修好就出不了布。可多数时间黄西林发现都被这名女工耍了,女工只是一个人在车间里害怕,她说窗外黑黢黢的,老觉得有人在偷看,说着,她还指着黑窗口,叫黄西林看。黄西林哭笑不得,回去了还得回答季红梅的询问:哪里坏了?要紧吗?机器可不能停啊!这个勤快的女人,今天的心里可不平静,身体也不平静了。想到这里,她看到黄西林摇晃着身体跟了进来,嘴角就泛了一个温柔的笑意,然后,跟着织布机“哐啷哐啷”地哼上了。
墙角里,放着一瓶用过的洁尔阴。黄西林握住季红梅的手时问道:咋又痒了?
季红梅无声地摇头。说了一句很好哇。身体就被黄西林压在了床边上。但她很快感到下身不舒服。下身湿热,这个老毛病,一旦身体疲乏,天气不好了,就会发出来。跟感冒伤风一样,一年总有那么一两次,不是大病,却让人纠结。特别在阴冷的冬季,发生的频率就会高点。据说这都是跟车间常年潮湿有关。
但这都没有关系,厂开好了,自己就是真正的老板娘了,享福的日子在后面呢!季红梅忍受着屁股硌在床沿上的疼痛应付着黄西林。突然,她就想到了一件事,这件事令她身体一热,同时她又无比的懊恼自己以前怎么没有想到一个人呢?于是,季红梅仿佛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一把推开黄西林问道:你说是谁介绍你认识莫老板的啊?哪个莫老板啊,我认识不?
莫老板就是黄西林托原来的老板娘介绍的大老板,他跟黄西林签了三年的加工合同。为此,在行情如此衰弱的情况下,黄西林和季红梅的工厂仍旧可以热火朝天地干着。突然地,季红梅就一跃而起,扑倒在黄西林身上,她喘着粗气说:等我们的厂开大了,咱们就好好地干一场,我们还出去旅游!隔一会儿,她又关照道:你明天送账单过去,要么请老板去吃顿饭吧。现在做生意,哪有不请客的!再说又到年底了,正是送礼的时候。
季红梅决定见见这位“莫老板”。
黄西林睡意朦胧,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嗯嗯地应道: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季红梅躺在床上独自听了一会儿热火朝天的织布机响声,准备起床了。这之前,必须得承认一件事,刚才在某个瞬间,她是将黄西林想象成了莫小海的。于是,她冲动了,可是,她一冲动,黄西林却不行了,翻身下去说睡觉了。季红梅看一眼酣睡中的黄西林,一时竟很心酸,有点看不起他,恍惚了一阵子,又摸了一下他的发顶,下床了。
季红梅对黄西林还是有点恼的——你看你,没用的家伙!
这天晚上不用落布,也不用换经轴,将经轴上的丝织完也可以放年假了。快凌晨的时候,睡意袭来。季红梅去泡了一个热水袋抱在怀里,准备坐到墙角去打瞌睡。从窗户边走过,她的身影映射在窗户玻璃上。夜色成为一道忠诚的背景,土不拉几的季红梅被映射出来——这是自己吗?季红梅麻利地捋着头发扎了一遍,再看,眉头越皱越紧。
看门老头的脸突然挂在玻璃上。季红梅问老头不好好去睡觉,跑出来干嘛?老头听不见,豁着牙齿在窗外呵呵地笑。他在喊什么呢?季红梅没有跟老头开门,她明白老头估计喝了酒,发酒疯了。季红梅就在窗户里跟老头比划,让他早点回去睡觉。可老头根本听不见,手握拳头敲着玻璃窗要进来。一定要进来。季红梅懒得去理他了。老头是季红梅请来看门的,他的儿子欠高利贷跑掉了。对于这个传言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他们夫妻早被债主杀死了,也有人说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他敢回来吗,欠了那么多的钱,他有几条命偿?可惜老头辛苦一辈子建造的房子也被债主霸占了——还是被霸占的好,那红彤彤的“还钱”两个字像两把刀架在门楣上,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怎么能安生呢!季红梅跟老头一个浜里住着,看着老头无家可归,就跟其他两个车间的小老板商量,同意老头住到门卫上看门。可哪知老头中年丧妻,白天睡足觉,晚上就不好好睡了,裹着棉衣缩在床上喝酒,又哭又笑。他一喝醉,看女人的眼神就直了。有女工反映,他还借着酒意常常后半夜溜达到厕所门口去瞄女人的屁股。有次还将生殖器甩出来给女工看。
作孽啊!
季红梅见老头不依不饶的样子,只得又起身赶他回去,季红梅说道:都这把年纪了,不作兴做这种事啊。老头不知道怎么就发脾气了,捡起地上的石子敲打着玻璃。玻璃破碎的声音,将季红梅吓了一跳。受了惊吓的季红梅反而知道如何对付老头了,她捡起一块碎玻璃,在老头的脸颊上比划着:你到底滚不滚,你不滚我就将你的脸划破!我杀了你!
老头最终被亮晃晃的玻璃碎片赶走了。可是被老头砸破的玻璃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豁然炸开。季红梅对着这个黑洞伤心地哭了。她分明感觉到黑洞是如此之深,就是开在自己身体上的,从而,久久维持着的尊严、勤劳和宽容全都没了。季红梅沮丧极了。
第二天早晨,黄西林一起来,就被季红梅催着去结账。黄西林前脚走,季红梅后脚就去找到一块三夹板将窗户上的破洞挡好了。然而,这个过程竟让她怀疑破洞真是被看门的老头敲碎的?这个可怜的老头啊!季红梅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之后就去街上买衣服去了。她十分肯定会见到莫小海,那么自然得体面一点去。天气阴沉,后来还飘起了雪花。季红梅走到街上,看着熙攘的人流,心情略略好了一些。她为自己买了一件灰色羊毛大衣,也为黄西林买了一件黑色的。后来还去洗发店洗了头发,将头发理顺了。做头的小姑娘很会说话,一口一个老板娘叫得人很是舒服。季红梅就大方地给了三十元钱说不要找了。做头的小姑娘却不领情,说正好,现在洗头涨价了。季红梅脸一红,匆匆离开了美发店。
之后,她又去菜场买了些水产送到乡下家里。没想到,冤家路窄,季红梅在家门口与黄西林的姐姐撞了个正面。两人都不说话,你让来我让你,最终是季红梅将菜搁在家门口又回来了。基于借钱的事,季红梅只能低人一等做小人。姐姐对此也十分恨着季红梅:你们没睡过,那他干嘛借钱给你?干嘛不是我弟去借?不然你们又干嘛要偷偷摸摸怕人晓得?你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我男人?!每次姐姐这么说的时候,季红梅的眼睛就会闭上,她很难过,也很痛苦,貌似姐夫汗毛茸茸的手就又伸过来了,姐夫还吐了一口香烟喷在季红梅的脸上,他也恶狠狠地:那时候家里穷,能娶个女人回来就行了。管她有毛和没毛的,能生娃就行——你大概也看见了,她腿上的毛比我还长?对了,她跟她弟弟怎么就长反了呢?她弟弟是不是从来不让你过够瘾?你看你,这么骚!总之,姐夫真野蛮和粗暴,整个过程,他仿佛都是在撒气,有着无限的委屈一样,为什么我的女人就那么难看!季红梅起初有些惊诧,随即就平静了下来,将眼睛一闭,想就当是被莫小海压着吧!直到这时,季红梅才发现自己跟莫小海在赌气,自己是那么不服气他凭什么平白无故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屁股就消失了?
好在,离开姐姐后,季红梅就接到了黄西林的电话,黄西林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季红梅,莫老板答应晚上吃饭了。他真是一个爽快人啊。季红梅也暗自高兴,可又失落,推断会不会弄错了人?便又仔细地问了一句:莫老板真这么爽气?他不是大老板啊。黄西林说是啊。季红梅又问你怎么请的呀?黄西林说,就说厂里吃年夜饭,想请莫老板赏个脸。季红梅就笑着表扬了黄西林:做事愈发聪明了嘛。难得啊。季红梅心满意足地笑了。
待跟黄西林一起出现在酒店豪华大厅里,季红梅发现大厅里都是亮晃晃的,一下子多出了很多个季红梅。什么叫金碧辉煌,足可以证实。季红梅没有放弃掉任何一次照镜子的机会,就连在电梯里,她也总是盯着自己瞅。她很满意今天的自己,将头发吹卷,散开来,穿着新大衣的自己完全不是昨天晚上站在黑玻璃里的人了。余光捕捉到黄西林在看自己,季红梅就朝他娇俏一笑。黄西林不解风情,问你没事笑啥哩。季红梅说:我想笑,我高兴。黄西林说:自己花钱吃饭也这么高兴啊。季红梅道:就是。咱们今天好好吃一顿。你要多喝点酒啊。
到了饭桌上,季红梅才知道,黄西林并没有请动莫老板吃饭,但莫老板说好唱歌了会过来坐坐。吃饭么只是夜生活的前奏部分,大家的心思都在后面的唱歌部分。结果黄西林没几杯就喝醉了。喝醉了的他就吆喝去唱歌,等莫老板来。但一到KTV,他就倒在沙发上不醒人事了。季红梅怕他吐,找到一个垃圾桶准备在边上。紧接着,就看见一群穿着蓝色礼服的“小姐”从金光闪闪的门口进来了,胸口处露出一大截白肉。季红梅眼看着“小姐”被一个个的男人拖过去搂在怀里,厂长还厚着脸皮问季红梅要不要给黄西林叫一个?季红梅忍住内心里的不高兴,笑道:他早就去周公那里领了,你们玩好就是。男人们叫了小姐,两个女会计唱了几首歌感觉没劲走了。季红梅正在暗自估算花掉了多少钱,坐在厂长边上的小姐站起来敬酒。季红梅盯着小姐雪白的胸口,板着脸不愿意喝,她心疼钱啊,小姐喝一瓶啤酒就喝掉了自己十几块钱。可小姐又不明白季红梅的心思,说大姐瞧不起人哪。季红梅敢瞧不起谁么,一把推掉小姐端过来的酒杯,急中生智地端起茶杯说自己要开车,不喝酒。喝茶吧。
季红梅一直在想,莫老板什么时候到?
就在这时,黄西林的手机响了,好一个末尾都是8的号码。季红梅看一眼醉得一塌糊涂的黄西林,掏出手机代接了。电话果真是莫老板打来的。花了很长时间,莫老板才听清楚季红梅所在的包厢号。季红梅不明白他说的话自己都听得到,为什么自己说的话他就听不到?赶紧理理衣服,起身去门口迎接莫老板进来。
季红梅刚走出包厢门,就看到莫小海打着手机财大气粗地来了。他整个人大了几圈。头发也剪成齐刷刷的板寸头,好一副“肥头大耳”。身穿一件藏青色羊绒大衣,大衣领子上镶着一圈貂毛。敞开的大衣里面,一件柔软的灰色羊绒衫包裹在圆鼓鼓的肚子上。羊绒衫的柔软是直接传递过来的,以至于他跟季红梅招呼,季红梅红着脸却没有反应过来。心里则早已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兀自认为他有意在暗中帮助?他对自己好。
季红梅便深情地瞥莫小海一眼。莫小海也大方地招呼道:好些年不见了,你好吗?
季红梅的脸火烧火燎的烫着,明白这声问候无疑是在提醒那把屁股上的热度!
厂长帮莫小海叫了一名小姐过来。莫小海没有拒绝,他摸了一把小姐的手,对季红梅说自己还有事,坐坐就走。另一只手则自然地放在了小姐的肩膀上。切!有钱就变了!季红梅搓着手,不想去看他们,眼睛却又老朝那边瞄,暗骂小姐不懂矜持。很快,她就发现莫小海弹烟灰的姿势很牛气,像是特意学过。他的手像一张芭蕉叶,肉肉的,动一动都能带起一股风,季红梅将屁股就朝里挪了挪。突然意识到跟莫小海的距离可不是一只沙发的长度了。
待莫小海身上的羊绒衫被小姐帮着脱掉,他就将话筒递了过来,邀请季红梅一起唱歌。季红梅躲开莫小海的眼睛,说自己不会唱《红尘情歌》。莫小海便起身坐到季红梅身边问那你会唱什么?季红梅摇头,将屁股又朝自己男人边挪了挪。莫小海笑着调侃了一句你怕啥哩,我又不吃你。跟过来问《选择》会唱吗,都老歌了。季红梅默默地将话筒接了过来。
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季红梅跟莫小海站在茶几前唱着,突然想起很多往事。往事如风,呼啦啦地摇着满树的叶子。每一片叶子就是一个情绪,在工厂里与莫小海是同事,他摸了自己的屁股,当自己被姐夫压着的时候,莫小海又出现了,还有在黄西林面前,莫小海也这么占据着。可是,他来了呢,却将自己映衬得像一个丑小鸭。他为什么要帮助自己呢?季红梅明显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讨饭的人出现在他眼前,是如此的卑微。一行眼泪悄悄地从季红梅的眼睛里流出。好在包厢里灯光幽暗,季红梅赶紧用手背将眼泪擦掉了。一群小姐在背后鼓掌,搞得很欢腾的样子。一股淡淡的烟草味飘过来,季红梅转头看到莫小海已走近自己,他的手很自然地搭在了自己肩膀上,像刚才搂小姐一样。季红梅抖一抖肩膀,跟莫小海分开一段距离。莫小海便拉着她的手唱着,就像屏幕上林子祥拉着叶倩文的手一样。
耳边不再是音乐。季红梅只觉得自己和莫小海正被密匝的织布机声音捆住了。莫小海的手指轻轻一转,就将手指落在季红梅的手板心里抠着,那里正好有一块老茧,他的动作落在老茧上就不走了,舒缓、轻柔,貌似无意又似有心地抚摸着那块老茧。仿佛那一块老茧是长在莫小海身体上的胎记。他抚弄,只是他认识它,这是他的印记。当然,这块印记也是季红梅的,整个晚上,季红梅都没有将这双手勇敢地伸出来,它太丑了,冻疮褪去后,整双手都是乌糟糟的。
你身上有什么味啊?唱完歌,莫小海浅浅地拥抱了一下季红梅,并拉在身边坐着。他的手又一次落在了沙发背后,直接对着季红梅的屁股捏了一把。
什么味?没有啊?季红梅抚弄了一下刚洗过的头发。身体扭了两扭。
可莫小海坚持说有一股味道,同时,他的手还在用力地捏着屁股。季红梅则担心被人看见,如坐针毡。莫小海喷着酒气,将嘴巴吹在季红梅耳边,固执地问季红梅闻到了没有。事后,他还开了玩笑,说骗你的,我闻到了新衣服的味道。你今天穿了新衣服。特意打扮了。季红梅知道被取笑了,出来吃饭不穿新衣服难道穿旧衣服?一时发窘,季红梅起身离开莫小海重新窝进黄西林的身边。柔软的沙发硬是让她的身体陷下去了好一截。季红梅不再说话,焦急地等着黄西林醒来。然后,她双手紧握,右手抠着左手的手板心,一会儿,又左手抠着右手的手板心。跟莫小海一样,对着那块老茧一点一点地抚摸着。恨不得将其抠下来。心里边默默地算计着今晚花了多少钱?在这之前,她听说小姐的小费又涨了,都要五百一个人。
(责编:张鸿)
李云女,1976年生。家居苏州。曾在《作品》、《山花》、《雨花》、《广州文艺》、《延河》、《青春》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数篇。获得2012年《雨花》杂志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2012年出版《云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