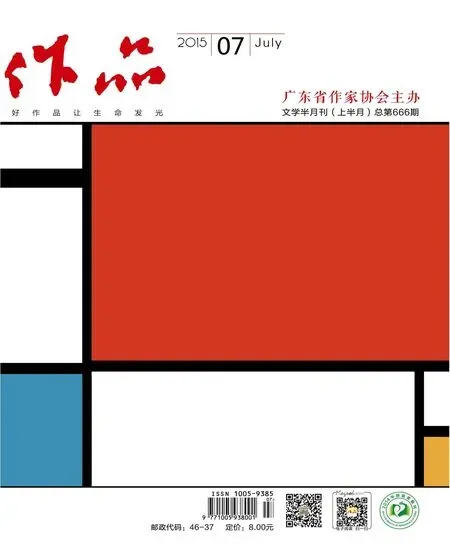《诗歌杂志》同仁作品展示
《诗歌杂志》同仁作品展示
黄昌成的诗(广东)
树根
它们走出来的时候,是不是
像武侠小说那样故意露一个破绽
你的思想马上插进去
你以为使用了最强的暗器
但结果却中了连环套
第一层
那些裸露的树根,与其说
告诉了你树的秘密,不如说
巧妙地亮出了树的来路,它们从
此开始,但此不是结束。你的
头颅一直跟到高高的树冠
还被漏下来的树叶笑声打得晕眩
第二层
树根就踩在自己的身上一直行走
树根到底是树根的道路
还是树的道路
第三层
好吧,就当树根跟在树的身后吧
跟着跟着,树根也长出了叶子
阳光由上往下捋下来
还以为在熨着树的连衣裙
这时候你还叫他树根吗
最后一层
名词解释:树根
树和自己的一场亲子活动
又叫树的双亲
李小洛的诗(陕西)
最后的
哪里也不去了,就在这个小城
坐南朝北,守着一条江
这是我最后的地址
一封信可以到达的地方
守着江水和两岸的秋天与渔火
看着寒风中的鹰、炊烟
棉田和菠萝。守着
麻雀的故事,老照片,邻居的旧生活
春天在安康,江南
江北,慢慢悠悠地长着
麦苗,水草在乡村、城池
慢慢悠悠地长着
这是我最后的地址
一封信可以到达的故乡
我一个人,慢慢悠悠地长着
变老了,左边的秦岭,右边的巴山
铁树,也在日复一日
慢慢悠悠地长着,变老
这是一个四季分明
雨水充沛的城市,我的
最后的地址,有樱桃
燕子、诗行和自由
两岸有一些和我一样的人
走过平平仄仄的大街
走过抑扬顿挫的小巷
哪里也不去了,就在这里
坐北朝南,守着一条江
守着我的土地,我花园里的
花,我的榉树和香樟
这是我最后的地址
一封信可以到达
一封信也不再到达的地方
谭越森的诗(甘肃)
在夜晚你行走于麦田
一株株的麦子中间
在你的视域里
那一株又一株站立的麦子
欲与你对话
当你察觉,它们又低头不语
麦田里沉睡的人
在空阔的原野之上
我去觅求麦田中传来的声息
每当我试图踏进它的深处
就发现它在缓缓关闭
如同一场宴会不宣而止
我无法放下自己的执念
未能放弃找寻的努力
我渴望唤醒那位沉睡的人
好让它收割我这样的收割者
曾居一的诗(广东)
谷子
一粒谷子端坐在香火缭绕的祭坛,洞悉着人的一生
洞悉着人如何认知色、香、味,如何追求功名
如何饱受疾病、孤独,和亲人死去的悲伤
一粒谷子一直在对人说话,却从来没有谁听懂
一粒谷子对人仁至义尽
它养活了人,人却嫌不够
把它煮了蒸,蒸了窖;把它熬出美酒来
再把酒糟拿去喂猪狗,把它欺骗了又欺骗
出卖了又出卖
一粒谷子从来不妄念有人把它高举在头顶
放到教堂顶尖,放在皇宫之上
一粒谷子没有尊严。成熟之时就低下了头
人的灾难与对一粒谷子的一知半解有关
昨夜,一个白发老者一边给我把脉,一边讲述
“吃五谷生长的人,一定会生病和死去
一粒谷子永远是最好的药石
一粒谷子没有国家,不会被写进宪法
从来不知道傲慢和愤怒。”
覃才的诗(广西)
远
那些一直赶路的人
在拥挤的城市里
彼此离得太远
我们所遇见的,除了车子
就是那群保持尖叫的动物
进进出出
街头的号码牌,连着房子和洞穴
我们像站牌,忙于漂泊
看了太多可能的地址
我居住的地方
靠近聋子、哑巴,语言稀少
我每天对话一个我
以解答某人孤独的疑问
所有的铁器过于冰冷、庄重
它们惯于忽视四周
向晚的诗(安徽)
老屋的房客
就像那时你曾在有限的空间里
做无限的游戏——
哦,是的,那并不比一座坟墓宽敞多少
有时夜里凭空打雷就像一次地震
而今认为那就是生活
的最平常不过的另一种玩法
后来那里住过学生,上班族,蚁族……
时隔今日已有十余年,老屋也翻新成了教学楼
至于那时的房客,就像某年雪地里
踩出的熟悉的脚印
院子里曾有一颗数十年的椿树,它被击倒的那晚
像一只灾难的风筝
跌在大地的怀里,那是我一直暗恋的那只
笑着和那些房客一起
谈论功名,利益,以及共有的童年
让人流连。像椿树上的一只鸟
抛弃妻子被天空大口吸去
白鸦的诗(北京)
霍家庵
秋末一声鸟鸣
驱车十里,逛破庙,如过家门
不喜不悲
村中庵门常掩,草木出墙
路过的人隔墙问安,想说的话只说一半
荒废一半
天底下,两只秋虫相遇,默不出声
坐在暮年说话的人
心思漫长,像一场绝育手术
这些年气候杀人
人间碰壁
活得似无道理
回城途中,路边桃花蒙面
忽听得身后庵门,吱呀一声,万物当面错过
已是暮晚时分
不远处,一头水牛的姿势
接近幸福生活
它一边吃草,一边给鹭鹚让路
末未的诗(贵州)
高级病房
朋友说,我的灵魂活跃
比俗世略高,病房也应该配套
就这样,我从人民医院转到了中医院
可那些房那些床那些电视,都是旧的
人也还是那些旧人,他们说的话也是旧的
因为他们曾经,也如此安慰过别人
唯有时光还算新鲜
像刚刚打开的来苏尔味
赵卫峰的诗(贵州)
午后的光线
午后的光线变着法子漂亮
午后的光线扭着身子降临贵阳
它在阳台留影
让兔子的雕塑更白,更乖
沐浴后的吊兰,以苗条
对映偶然
一个孩子,用颤音
唱出1987年
光线持续,联系额头、路牌与空想
似乎,想多久就多久
似乎想趁热
找一个叫做永久的地方来停放
那地方你知道,暗而不黑
让人心软,让人想起就不安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