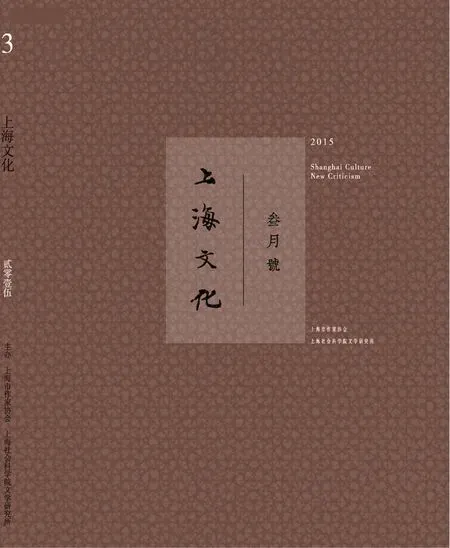整个空间里都是你的痕迹
2015-11-14 06:23陈墙吴亮
上海文化(新批评) 2015年2期
陈墙 吴亮
整个空间里都是你的痕迹
陈墙 吴亮
吴亮
:这个访谈的画家名单越来越长了,难免问的问题会有重复,不过你可能还觉得是第一次……我们就从你的第一幅抽象画开始。陈墙
:第一幅抽象画,当然记得,大学快毕业的期间画的,不是很完整。吴亮
:给我用语言描绘一下,画面上出现了什么?陈墙
:画面带着……嗯,带着保罗·克利的影响,明显有他的影子。当时我在纸上画了一批这样的,尺寸不大,打印纸,卡纸,钢笔铅笔毛笔,那时候用铅笔最多。1989年快毕业了,十几个同学,大家都在搞毕业创作,我们把两个教室分割了许多块,每人一个独立空间,这应该是我的第一个画室。然后呢,1995年李旭在美术馆给我做个展,记得你也来了,我的抽象画第一次正式亮相。吴亮
:你一连说了你的三个“第一次”,第一幅抽象画现在还在吗?陈墙
:还在。吴亮
:第一个画室有没有留下照片?陈墙
:有,我坐在照片里面,手拿着一个喝红葡萄酒的杯子。吴亮
:等会儿我们把它找出来。陈墙
:还有,我第一个个展肯定有照片,应该找得到,有的。吴亮
:我们总算找到一个新的开头,“第一次”。陈墙
:证据都留着,呵呵。吴亮
:再往前追溯,你的中学课程是在贵州完成的。陈墙
:之前一直在贵阳,初中毕业后我没读高中,去了技校学汽车修理,当了几年钳工和宣传干事,后来再复习,考大学。吴亮
:考到华师大美术系以后,就接触现代艺术了?陈墙
:对,大学还没毕业,就尝试抽象画……吴亮
:以后再也没回去,一直到现在?我指的“回去”,不是回你贵州老家,是说从此以后,你再也没有回过去重新画具象画。陈墙
:早些时候还有些群体展览,展览方的要求还是具象……就是说,曾经有一小段时间,自己私下创作是抽象的,仍有一小部分在延续具象。记得在1992年,为参加一个北京的展览我又画过一张具象画,最后一张,当时就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幅,写实画从此告别了。吴亮
:你有没有这样的前后比较——搁在二十多年前,你刚刚涉足现代艺术,画抽象画,或者从事前卫艺术,不管你怎么称呼,反正你画了一些周围的人看不懂的画,没有具体形象的抽象画,于是他们就会奇怪,包括你的家人,兄弟姐妹父母长辈都会问你,“这画的什么呀,你想表达什么?”很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现在是不是早已不再存在了,展览不断,拍卖行图录上有你的作品,我猜想不大再会有人再问你那个多余的问题,“陈墙你告诉我,你想表达什么?”陈墙
:还有啊,问这一类问题的人还是有。吴亮
:是这样吗,那你怎么回答他们?陈墙
:碰到很多次,就反复问我“你画的是什么?你想表现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你不要去读它,你去看就行了。吴亮
:于是,他们就立即表示理解了,就停止追问了?陈墙
:大部分人还是不理解,不满意……没有办法,因为,如果我很耐心对他解释,即便花了很长很长时间,也未必能用文字语言把这个画面上的图像究竟“是什么”说出来。吴亮
:听潘微说,他的抽象画在日本,不是时髦的年轻人喜欢,反而是老年人喜欢,是这样吗?陈墙
:潘微作品的收藏圈,的确大部分是老人,而且都是日本老人。至于日本老人为什么会喜欢他的画,我完全能理解——日本人和德国人在某些地方非常相似,他们思维严谨,理性,退休了他们还一直在学习,中国人不太容易理解他们。至于说到对抽象画懂不懂,这是需要学习的。吴亮
:艺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差别是一个大背景。陈墙
:对比我们国家的教育,几十年以灌输集体意志为主,强调集体意志的教育必然会忽略个人意志和个人意识。那么怎么形成集体意志呢,一个基本方法就是依靠读,依靠背诵,依靠统一标准。集体意志教育的结果,就是要求对一个东西一定要读出统一的意思来,一幅作品的意义一定要看得出来,如果看不出来,那么艺术家就必须亲自解释。吴亮
:他们不仅无知,而且害怕陌生。陈墙
:是呀,任何新鲜事物陌生事物,摆在面前,要大家立即一起去读,去认知,而不是去感知。如果是一个感知,再上升到理论,让它变成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共识,大家共同接受的统一答案,共同价值观,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吴亮
:你的意思,中国人在看画的时候,寻找的是共同认知,他于是求助读,而不是求助观看。但是,为什么“看”不是集体的,必定是个人的呢?陈墙
:我的抽象绘画首先“回避读”,因为你读了,或者一件作品“可读”,那它一定有它的叙述性——我的抽象绘画呈现的是纯视觉,是纯形式,它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把叙述表现抽空,把描述性全部屏蔽掉,这点如果做不到,抽象形式感就出不来。吴亮
:我们把讨论范围打开……现在不仅中国,整个世界范围里,当代艺术风起云涌,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被理解成了一个时尚,甚至达到了一种超级时尚的状态。今天对当代艺术有各种各样解释,其中有这样的一路,似乎成为主流,就是把当代艺术重新政治化,强调它必须重新介入现实,要对当下的各种问题发言。另外一路,仍然偏重形式,如果不针对历史,至少也是针对美术史的,抽象艺术已经被归纳进历史范畴,我们好像很难回避它,仅仅讲个人的感受,这套关于抽象艺术的解释系统差不多教材化,在学院里成为普遍认知了,你在乎这个知识系统吗?陈墙
:不在乎。吴亮
:为什么?陈墙
:我觉得,一个艺术家首先要关注他的绘画,有没有达到他的内心,走进内心。如果你对自己的这种自我认可都没有,一门心思的往外看,你的价值观都跟着人家走,标准永远是趋向外部世界,考虑大众的共同价值观到底在哪里,然后自己的绘画怎样要和他们价值观进行对应,这首先就排除了你自己。吴亮
:批评家们有一套解释系统,都说现代艺术史这一页西方已经翻过去了,而抽象画是属于现代艺术的,常常听到这样一种声音,认为抽象艺术过期了,从塞尚、罗杰·弗莱开始到格林伯格为止,这个现代主义终结了。陈墙
:这都是你们评论家的看法,不关我的事。吴亮
:哈哈,我是例外……国内有些评论家爱说这个,某某艺术过时了,某某时代终结了,其实这些结论都是外国人讲的,没有什么新意,每隔二十年宣布一次,老一套了。陈墙
:不就是在几个概念里兜圈子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当代艺术,各种各样的定义。吴亮
:你热衷抽象艺术,却不在乎批评家用抽象概念讨论抽象艺术。陈墙
:没有,我不反对批评家用抽象语言讨论抽象艺术,但是我对某些只在概念圈子里兜来兜去的东西不在乎。吴亮
:我知道,你反对读,因为读导致趋同;你强调看,不管别人说什么,你只管自己的看,用自己的看激发别人的看。陈墙
:对,你说的这个很重要……作品首先要跟艺术家内心有一个共鸣,然后再走出来,跟社会跟历史跟世界有一个碰撞点,也很关键。了解一个时代过去了,曾经是怎么样的过程,我当然知道,西方抽象绘画可能是过去了,但是在我们国家没有这个经历,跳过了现代主义,缺了这一课,很多东西不太清楚,就人类发展的一个过程,每一个有意思过程,我觉得肯定是经历一下更好。吴亮
:类似补课。陈墙
:差不多意思吧。有一次有几个朋友聊抽象绘画,大家都觉得中国没有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没有,因为中国几乎没有现代主义这个部分,很短的一个瞬间,引进一点点印象派野兽派,还没有轮到抽象绘画就匆匆结束了,民国初引进的现代西方艺术很不完善。吴亮
:在你看,西方人的抽象艺术背后,有没有他们自己传统的原因?陈墙
:真的是有,抽象绘画不仅仅表达理想和秩序,还表达了他们的个人情感和个人意志,真是很完善。他们一个普通大众,为什么都能看懂一幅抽象画,都能喜欢,就算这个群体里的一个个体,他的主观意志也比较完善;而我们国家的群体中,大多数个人的意志都不够完善,从他们看不懂抽象画这件事也可以明显反映出来。吴亮
:康定斯基在他《艺术的精神》里举了个简单例子,说一块白布上出现第一个点,我们眼睛只看到这一点,它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心,等你再画上第二点,于是这两个点就形成了一种关系,然后是第三个点,第四个,直到形成一个结构,一个面,好几个面。陈墙
:是这样的。吴亮
:我从你的画里也在找这个关系,第一个点,一个最小的也是最初的元素,它开始繁殖、衍生、对位、排列,不断扩张不断膨胀,无限的膨胀……陈墙
:一幅画的空间总是有限的,再怎么大,总有四条边。吴亮
:假如给你一个更大的空间……嗯,这是你的第几个画室了?陈墙
:那已经不太记得了,它是我迄今为止最大的工作室。吴亮
:让我们想象,假如你有足够长的手臂,工作室足够大……你目前作品的最大尺度,是由你在工作台两边最大限度伸出手臂加上一支笔的长度乘以2决定的?陈墙
:对啊,这样一幅画的半径就是我手臂的长度。吴亮
:假如你有更长的手臂,你尽情想象,甚至机械手,或用别的什么控制方法,随心所欲地把你的意念伸展出去,有点像阿基米德,他说“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起地球……”陈墙
:你是问我,我想画多大的一幅画?吴亮
:就是啊,如果给你足够长的手和笔,你能画、或梦想画多大的画?陈墙
:其实很简单,我没有太大的空间野心,人作为一种生命,哪怕不画画,只要你活着,只要活在无论怎样的空间里,我希望整个空间里都是你的痕迹……我想,在生命之初的时候,可能一张白纸放在你面前,你都会很害怕这种空白,但是慢慢地,你肯定会想方设法把它填满。吴亮:
你是不是潜意识里有一种控制不住的、一种扩张的欲望,就像一个森林,只要有可能,它就往外蔓延。陈墙
:某种程度上大概有,或许我潜意识里面有这个……如果你是作为绘画语言,一个形式,作品大小不是主要的,而是你的宗旨更重要,你要判断。吴亮
:你这些画的物理空间限度,是你手臂决定的吗?陈墙
:尺幅大小,应该是一个充分伸出去的手臂的范围。吴亮
:你自己看,大的作品与小的作品,感觉各有什么不同?陈墙
:大作品,视觉的满足感更强。小的嘛,感觉是小品,是个实验品吧。吴亮
:这么说,尺度对你来说还是很重要,你渴望大体量。陈墙
:目前来说是这样,大作品比较过瘾,因为年岁不饶人,如果我再画十年,慢慢就画不动了,所以说,近两年确实有这个欲望……以前没有这么迫切,以前我特别着迷小作品。吴亮
:你现在的空间非常宽敞了,以前我去你的画室,空间比较小,而且里面很凌乱,画好的作品都摞起来,靠墙堆着,作品的尺度也就一两米之间……你这幅画,应该有三米高了吧。陈墙
:三米六。吴亮
:你现在这样一个陈列自己作品的方式,让我感觉,你似乎有一种野心,兴致勃勃地在扩大你的私人疆域。陈墙
:也是一种,一种生命体验,其实画画,有时候就是你留下的痕迹。吴亮
:你的前面讲,人们满足于认知世界,看到一个物,就希望“读”出它是什么,然后才算“看”到了它。陈墙
:对。吴亮
:当你读不出它,就算没看到,是这个意思吗?陈墙
:所以我强调“看”,而不是满足于“读”。吴亮
:但是我们知道,“读”实际上是人的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有这样的要求,你如果看到一个东西,你却不能给它命名,或叫不出它的名称,你就会茫然,你等于没看见,当然这是哲学家的说法……画家可以不顾这个名称,不过人们还是忍不住要问,你画的是什么,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被命名了,没有不被命名的事物,你看不见的事物也被命名,因为有人看见了……陈墙
:对,但是作为一个人,他能读懂的东西很少,他看到的比读到的要多许多。比方一个文盲,他看懂了但是写不出来。吴亮
:所以读懂的人,就要向读不懂的人解释,如果你不告诉他,一开始可能会很茫然,也许他看了好几次你的画,以后他能辨认了,再看到你的画,就会说“这是陈墙的画”。“陈墙的世界”,你同意这也算是一种命名吗?陈墙
:我同意……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不告诉他,他好像很茫然,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害怕茫然,你只有在茫然的氛围里,你的感受你的想象力才不会受到局限。艺术本来就是探索未知的领域,绘画首先跟感觉有关,就在于你有没有感觉。如果你没有感觉,你是没办法画画的。感觉世界是无穷的,我们的文字语言所介入的这个范围,其实非常有限,物质的,技术的,日常生活,内心生活,人类社会越来越发展,感觉的这种微妙性、丰富性也在无限扩大,一到这个时候,它们就来挑战我们的语言了。有时候,我们突然有一个很微妙的感觉,很奇特,想用一个词、一个句子去说出它。我们搜索所有的语言,想通过一个关键词把它说出来,后来你发现一旦说出来了,离你心里的那种感觉还是有距离,这个文字还是有限,而人的那个未知的、说不清的那种微妙感觉,还在那里等待我们去表达,去开拓。对,我觉得艺术家应该是感觉的开拓者,这个非常重要。吴亮
:我明白了。陈墙
:如果你只停留在大众的一般语言的认知系统,艺术家也只停留在这个现成的认知系统,他的路肯定是很狭窄的。吴亮
:陈墙,你平时说话不多,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其实你的语言表达很清晰,也很逻辑,你的温文尔雅不会是与生俱来的吧!你从大西南贵州出来,年轻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状态?陈墙
:当然也有青春期躁动的,但不经常。在大学里,群架也打过……吴亮
:旷课?捣乱?陈墙
:都有过,但跟其他同学相比,这种不好的记录我还是比较少,我比较安静,小时候,我的性格就比较内向。听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她带我去看电影,1960年代有很多忆苦思甜阶级教育的电影,我坐在母亲的腿上,抓住她的手臂,周围观众哭成一片,母亲感觉到我抓住她的手,抓得很紧,她侧过身来看我,发现我屏着呼吸没有哭。吴亮
:你没哭,是恐惧?陈墙
:我忘记了,反正我没哭,所有人都在哭,我没哭,就两眼盯着银幕。吴亮
:当时的感觉,你已经想不起来了。陈墙
:我已经没有这个记忆了。根据母亲的形容,我自小就有这种对感情的控制能力。吴亮
:让我想象,一个非常安静的男孩子,话不多,你阅读吗,你用什么东西来消遣你的多余时光?陈墙
:也读,当然都是一些当时大家差不多看到的书。吴亮
:所以读的东西,留给你的印象不深刻,因为和你一个人安安静静想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陈墙
:对,我自己倒没有分析过。吴亮
:说一两件你记忆深刻的事,小时候的。陈墙
:有的……文革期间,那时候真是很混乱,父亲跑到北京告状,回来以后就被“文攻武卫”关起来拿鞭子抽。母亲带我去送饭,整个细节我都记得,我看见父亲从他的衣服里面掏出毛泽东像章,他当时算是有罪的人,不可以佩戴这个毛主席像章,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渴望得到这个东西,他给了我两个。这个场景我印象非常深……因为外面太乱,大人把我关在家里差不多有一年,印象最深的,是我自己跟自己玩,搭积木,搭两个军舰,我打你,你打我,一会儿跑过去变成你,一会儿就跑回来变成我自己……到了下午,我会根据那个门缝外面照进来的光线,拿一个小旗帜放在那儿,等到光线走到某个位置,我的母亲就回来了。吴亮
:做艺术家,曾经是你的梦想吗?陈墙
:小时候是很懵懂的,偶尔有一次,我画了一幅画,被我父亲大加赞赏,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爱好。吴亮
:你画了什么?陈墙
:其实很好笑,文革那个时候,母亲在单位做黑板报搞宣传,家里有几本大批判资料,其中有漫画,把“牛鬼蛇神”踩在脚底下,我把它临摹下来了。吴亮
:你的模仿能力被发现了。陈墙
:对,我父亲回来一看,他问是谁画的,画得好。吴亮
:你那时候几岁?陈墙
:八岁。吴亮
:你的绘画生涯就开始了。陈墙
:开始临摹,临摹连环画,小人书……后来读初中了,跟一个同班同学关系很好,下课后经常跑到后山草地上,两个人躺着,幻想将来自己要做什么,要当兵,要做医生什么的。吴亮
:你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将来要搞艺术?陈墙
:十二岁,跟我这个同班同学讲的,因为画画很有趣。那时候没有娱乐活动,没有电视。吴亮
:1972年,已经明确自己的未来志向了。陈墙
:只是爱好,还很模糊。后来当工人期间,听说高考制度要恢复,画画也能考大学,这样就明确自己目标是什么了。吴亮
:在工厂有几年工龄?陈墙
:技校毕业十七岁,工作八年,这八年期间我为考大学花了四年。吴亮
:录取是哪一年?陈墙
:1985年。吴亮
:二十五岁考进华师大,1989年毕业。迄今为止,一直在学校当老师,教美术,没有变化?陈墙
:对,我的履历很简单。吴亮
:现在课多不多?陈墙
:不多。吴亮
:你教学生们画抽象画吗?陈墙
:当然不会教,怎么可能?我们国家的美术教育大纲,近几年可能有了某种程度的改革,现在好一点,像我,教的基本上还是基础美术,跟老师个人的创作没有关系。吴亮
:你现在学校里具体教什么课程?陈墙
:素描和色彩。吴亮
:教你二十多年以前学过的内容。陈墙
:对,也是我现在创作不再需要的东西。吴亮
:你觉得这些内容还有用吗?陈墙
:至少对他们还是有用的。吴亮
:既然对他们还有用,为什么会对你没用呢,你那么厌恶?陈墙
:学生也这样问我过,其实我不厌恶……我对学生说,我教你们这个素描和色彩,跟你们看我的画,是两件事情。学校学习是一个过程,我年轻时候也像你们现在这样画画,这就像走楼梯,踏上第一个台阶,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第二个台阶,第三个台阶,经历了许多个台阶以后,慢慢就可能要选择自己的这个台阶了。它们都是一个过程,作为基础,踏上第一个台阶还是有必要的。编辑/张定浩
猜你喜欢
学与玩(2020年11期)2020-12-23
读与写·下旬刊(2019年7期)2019-07-11
智族GQ(2019年2期)2019-06-11
读者·校园版(2018年13期)2018-06-19
大观(2016年11期)2017-02-04
Coco薇(2016年2期)2016-03-22
读者(2016年7期)2016-03-11
爆笑show(2014年10期)2014-12-18
雕塑(2000年4期)2000-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