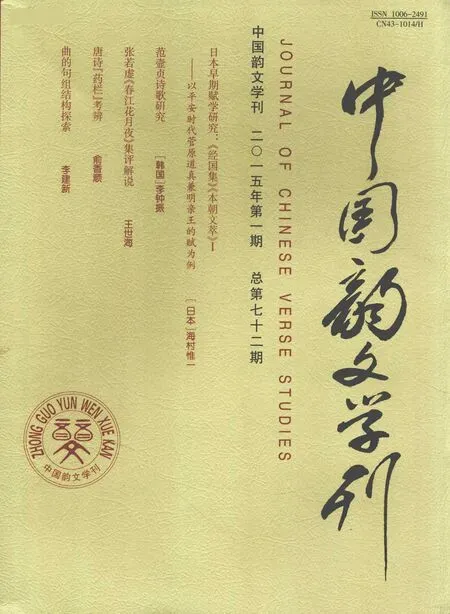作赋先须谨重,写诗且须放荡
——南朝宫体赋比宫体诗节制原因探析
李旭婷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作赋先须谨重,写诗且须放荡——南朝宫体赋比宫体诗节制原因探析
李旭婷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宫体赋指齐梁以后以描写宫廷生活和艳情为主的赋。赋作为一种敷陈直叙的文体,在描写清辞艳情的宫体内容时,本该比诗更显直露浮靡,然而却并非如此。究其原因,一是美人赋本身所具有的“曲终奏雅”的传统使其归于闲正;二是赋的书写内容没有诗歌那样私密化,使其不至流入艳俗;三是赋的诗化使抒情性稀释了艳辞。这三个原因导致在表现宫体内容时,赋反而比诗要含蓄节制得多。
宫体赋;宫体诗;含蓄;原因
“宫体”作品指产生于宫廷之中,内容以描写宫廷生活和艳情为主,风格则流于浮靡轻艳的作品。文学史上谈到“宫体”时,通常只有宫体诗的定义。《隋书﹒经籍志四》评价宫体诗说:“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宫体赋的写作成员与宫体诗基本相同,而其写作内容与风格也与宫体诗基本相似,因此,参照宫体诗的定义,可将宫体赋定义为:宫体作家所书写的以宫廷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赋作,其内容主要是“衽席之间”、“闺阁之内”,而其风格则是“清辞巧制”、“雕琢蔓藻”。《梁书·徐摛传》记载:
(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王入为太子,转家令,兼掌书记,寻代领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由此段记载可知,宫体之名,始于梁中大通三年简文帝萧纲入主东宫之时,然而作为一种文体,其风格形成应是早于此时间的,而此后简文帝、陈后主、隋炀帝乃至唐太宗时期,宫体写作都一直存在。本文将以宫体发轫且最为流行的南朝为着眼点。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传》)铺陈直叙是赋最重要的特点。按照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的写作方式,在表现清辞艳情时,本应是非常直露无遗的,然而,同时观照宫体诗和宫体赋却会发现,虽然同样多描写宫廷和女性生活,然而相比宫体诗的淫靡和工笔刻画,宫体赋却要收敛含蓄得多,反而多偏向抒情。如对比最重要的宫体作者萧纲的诗赋便能发现,其诗歌中多有“羽帐晨香满,珠帘夕漏赊”(《娈童》),“谁知日欲暮,含羞不自陈”(《率尔成咏》)这类浮靡香艳的描写,然而其赋中除《对烛赋》偶有略带香艳以外,其他赋作多未入此流。那么,为何本该直白敷陈的宫体赋却反而没有宫体诗那么工笔直露,本该走向艳情轻浅,却反而多寄情收敛。相较于宫体诗,宫体赋的节制与含蓄原因何在?前人谈到宫体赋时,多谈其艺术性以及对唐赋的影响,即使提到其不如宫体诗放荡,亦只是一笔带过,没有深入分析过其原因。本文将就此问题展开,探讨宫体赋较之宫体诗含蓄的原因。
一 美人赋“曲终奏雅”的传统
对女性的书写是宫体赋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虽然书写美人的赋作不都是宫体赋,(如《洛神赋》这样以写情为重,而非专为艳情描写的美人赋便不可归之为宫体赋。)然而前代美人赋中对于女性的细致描写却对齐梁宫体赋有所影响。美人赋的书写源远流长,在南朝之前已蔚为大观。历代美人赋的书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以讽谏为旨归,另一种以哀情为寄托。这两种书写方式都影响到了南朝的宫体赋。
第一种以讽谏为旨归的书写方式发轫于宋玉《高唐赋》和《登徒子好色赋》,前面大段文字从背景、容貌和行为极写美人之丽,终以“扬诗守礼”(《登徒子好色赋》)为劝。后来司马相如《美人赋》亦同,先极写美人之情色诱惑,而以“脉定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为一转,写美人之丽是为了与结尾之转形成强烈反差,达到讽喻的效果。而从汉末至魏晋,“止欲”系列的赋作亦是同样的表达方式,张衡《定情赋》之“定”,蔡邕《检逸赋》之“检”,曹植《静思赋》之“静”,陈琳、阮瑀《止欲赋》之“止”,应瑒《正情赋》之“正”,皆是同样的意涵,正如陶渊明《闲情赋》序中所言: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因并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其《闲情赋》极写“十愿”之放荡,虽然萧统认为“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陶渊明集序》),然而观陶之旨,却终归于“尤《蔓草》之为会,诵《召南》之余歌”(《闲情赋》),仍欲“抑流宕之邪心”,希望“有助于讽谏”。尽管在表达效果上是劝百讽一,然其“抑流宕”之旨归却不可忽视。
赋学批评发展至齐梁,发展出三派,一是以萧衍为代表的守旧派,以“丽则”为旨归,强调赋作为“古诗之流”的讽谏作用。二是以萧统为中心的折中派,虽提出好文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然而也强调“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由其对陶渊明《闲情赋》的评价便可看出其“丽”“典”的标准。三则是以萧纲为代表的趋新派,强调“寓目写心,因事而作”(《答张缵示谢集书》),同时提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虽萧纲极度提倡写情,然而他在《昭明太子集序》中却仍谈到:
窃以文之为义,大哉远矣。故孔称性道,尧曰钦明,武有来商之功,虞有格苗之德,故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卫九光之度,方珠喻龙,南枢北陵之采,此之谓天文。文籍生,书契作,咏歌起,赋颂兴,成孝敬於人伦,移风俗於王政,道绵乎八极,理浃乎九垓,赞动神明,雍熙锺石,此之谓人文。若夫体天经而总文纬,揭日月而谐律吕者,其在兹乎!
儒家政教的观念仍然影响着其辞赋观。故梁代三家的辞赋观念虽然有守旧趋新之别,却都无法背离儒家的观念。表现在美人类辞赋创作上,虽然极写美人之情与容,却终会回归到礼。如江淹《丽色赋》归于“宋大夫耀影汏迹,萦魂洒魄,赏以双珠,赐以合璧,拂巫荡祝,永为上客。”而沈约《丽人赋》为残篇,虽没有写到扬诗止礼,然从其前文的叙述方式来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如出一辙,可以推测后文应有自持的内容。这种讽谏的传统使南朝宫体赋终归于闲正。
而第二种以哀情为寄托的美人赋,则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神女类,以神人相悦,而终“恨人神之道殊”(《洛神赋》)。此类赋发端于宋玉《神女赋》,以曹植《洛神赋》为极致,发展到南朝则有江淹的《水上神女赋》,前段极写神女之丽色,从美人出现的背景,到其容貌服饰,再到其一举一动,美艳到极致,却终“苟悬天兮有命,永离决兮若何”。神女赋虽绚烂之极,甚至有云雨之喻,然而多是“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洛神赋》),这种美之极而生发出的哀情部分让赋“曲终奏雅”,显得动人,而不是浮艳。另一类则是思妇类,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班婕妤《自悼赋》,再到王粲、潘岳等人的《寡妇赋》,最终发展到南朝的荡子思妇系列的赋作。这一类赋以抒情为主,主要不是铺排外表丽色,而是渲染心中悲情,用感伤色彩消解了赋中的宫体意象。如沈约的《伤往赋》,虽有“虚翡翠之珠被,空合欢之芳褥。言欢爱之可永,庶罗袂之空裁。曾未申其巧笑,忽沦躯于夜台”这类偏于浮艳的铺陈,然而之后一转,“伊芳春之仲节,夜犹长而未遽。怅徙倚而不眠,往徘徊于故处”。思佳人的孤独和惆怅充斥着赋作,前面写艳情不是为写而写,而是为了后面的抒情铺垫,与很多为写而写的宫体诗有所区别。
故美人赋或极写其貌以喻讽谏,或极写其情以言其伤,终归至于曲终奏雅,不失闲正。
相比美人赋的曲终奏雅,美人诗的书写传统则不同,《诗经》中写男女情感的诗,虽然在汉儒的解释下多寓讽刺,然其本质是各言其情,有私会的男女,怀春的少女,亦有弃妇的悲吟,相思的诉说。汉乐府民歌中的女性亦常是情感丰富,如焦仲卿妻以及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至于南朝,更提倡“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越来越朝着私密化发展。相比于美人赋,美人诗所受到了正统限制较少,表现更为奔放,这种传统为宫体诗所吸收并大为发扬,乃至流于淫靡。
二 诗赋题材的差别
南朝宫体赋的题材主要有三类,一是正面描写美人的,二是通过咏物来咏人的,三则是表现荡子思妇之情。这三种题材在宫体诗中也有,然而于诗赋的表现又有所不同。
正面描写美人的赋作,如江淹《水上神女赋》、《丽色赋》和沈约的《丽人赋》。《西京杂记》载有司马相如论赋的一段文字:“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将这种“苞括宇宙”的观念投射到美人赋的创作上,便是要尽一切手段写美人之美,在时间上,用古往今来的极美之人衬托其容貌,“笑李后于汉主,耻西施于越王”(《水上神女赋》);在空间上,用天上地下尽美之物比喻其艳姿,“其始见也,若红莲镜池,其少进也,如采云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陆离,宝过珊瑚同树,价直琼草共枝”(《丽色赋》),最终要达到的描写目的,是“天下之至丽,孰能与于此哉”(《丽色赋》)。这种美到极致的女子是世俗之人无法承受的,故赋在写作时通常将其神化或者泛化,这使得赋中的女性与现实产生了距离感。
而诗则不然,诗不需要“苞括宇宙”,故不必因为写得太美而指向泛化的女性。也因此,宫体诗中的女性,多是世俗之人,存在于作者周边,或是倡妓,或是其家眷,因其实在,故可亲可近。因此写作时,便不必以仰望的姿态,而多以赏玩的态度,易流于浮艳。如萧纲的《戏赠丽人》:
丽妲与妖嫱,共拂可怜妆。同安鬟里拨,异作额间黄。罗裙宜细简,画屧重高墙。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长廊。取花争间镊,攀枝念蕊香。但歌聊一曲,鸣弦未息张。自矜心所爱,三十侍中郎。
诗吸收了赋的描写手法,工笔描写了丽人的鬟、额、裙、屧,然而与赋不同的是,这个女子与作者没有距离,其一颦一笑更具有诱惑,其一举一动也颇为轻浮,作者对丽人所持是一种赏玩亲近的态度,香艳色彩也就较赋为浓,发展到极致,甚至出现了咏《娈童》这样的诗。
通过咏物来咏人,是宫体诗赋的重要形式。南朝是咏物诗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的背景下,诗歌在体物上越来越细致。普遍认为,咏物诗是宫体诗的重要源头,宫体诗中对女性与物近乎工笔的摹写正是受到咏物诗影响,甚至在写女性时,亦是当作物来写。通过咏物来咏女性的宫体赋和宫体诗,其所咏之物多是与女性生活相关的,如乐器、灯、烛、镜之类,然而在表达上,诗和赋亦有所区别。就严格的咏物而言,赋的历史早于诗,楚辞中便有《橘颂》,而汉赋中也有大量乐器赋之类的咏物题材。赋在咏物时,通常就物的取材、历史、背景描摹一番,方才进入物本身,然后才提到与物相关的女性。如萧纲《筝赋》,如同汉代乐器赋一般,先叙述梓木的生长环境,突出其不凡,然后描写制筝过程,接着摹其音色,言其乐之动容,最后才提到弹筝女子之曼妙。又如庾信《镜赋》亦先谈镜子“镂五色之蟠龙,刻千年之古字,山鸡看而独舞,海鸟见而孤鸣”,然后才转到照镜之女子的描写。这种一定篇幅对器物本身的着墨描写稀释了赋的宫体色彩。
而咏物带出咏人的宫体诗,对器物本身的关注度远远不及赋,物虽有吟咏,然只是一个媒介,笔墨很快便转入到吟咏女性。如纪少瑜《咏残灯》:
残灯犹未灭,将尽更扬辉。
惟余一两焰,才得解罗衣。
其目的不在咏灯,故于灯着笔极少,咏灯意在咏人,故咏灯之处皆是指向人的。没有了赋那样对器物大篇幅的敷衍,对女性的吟咏的针对性和直露性就变强了。而宫体赋则因对器物的铺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宫体倾向,使其相对于宫体诗显得含蓄。
荡子思妇类的作品,在赋多为荡子赋,描述男子离家而妻子独守空闺的凄凉,在诗则多为离别诗和闺怨诗。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爱情题材的诗赋都属于宫体,此处所界定的宫体诗赋,其内容不仅“思极闺闱之内”,主要是宫闱的生活情思,而且偶尔亦有精致的器物陈述描写和“衽席之间”的寄托。至于那些大量存在的爱情诗和以闺闱寓意实则别有寄托的诗作则不属于宫体的范畴。这一类荡子思妇的作品,诗赋的表现方式都很相似,“衽席之间”的描写减弱了,都偏向于抒情。此类题材的诗赋恰恰都是宫体诗赋中写的最好,宫体色彩最淡的作品。如江淹《倡妇自悲赋》,虽然前面有宫闱的描写:
粤自赵东,来舞汉宫。瑶序金陈,桂枝娇风。素壁翠楼,明月徒秋。歌声忽散,伤人复愁。君王更衣,露色未晞。侍青銮以云耸,夹丹辇以霞飞。愿南山之无隙,指寿陵以同归。
此段细致铺排了宫闱的精美陈设,然而并没有沉溺于其中,继续展开其艳丽的描写,而是转向了抒情:
霜绕衣而葭冷,风飘轮而景昃。御思赵而不顾,马怀燕而未息,泣远山之异峰,望浮云之杂色,若使明镜前兮,碎孤雁之锦翼。
融景于心,托物寄情,显得哀婉动人。而此类诗的代表则有江淹的《休上人怨别》:
西北秋风至,楚客心忧哉。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露彩方泛艳,月华始徘徊。宝书为君掩,瑶琴讵能开?相思巫山渚,怅望阳云台。膏炉绝沉燎,绮席生浮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怀。
诗中虽亦有雕琢的闺中刻画,留有宫体诗的痕迹,然而其浓郁的抒情色彩却淡化了这种痕迹。因此,在荡子思妇类的作品中,诗赋达到了融合,各自是其宫体作品中最好的作品。
以上三种题材是宫体诗和宫体赋所共有的,然而,宫体诗的内容要远比宫体赋广泛,还有很多内容是赋中所没有的,相比于赋,诗歌要显得更加私密化,正是这些内容,将宫体诗的艳情推向了极致。
第一类是咏美人活动的,如萧纲的《美人晨妆》和《咏内人昼眠》,刘孝绰的《遥见邻舟主人投一物众姬争之有客请余为咏》等,对女子生活细节不厌其烦地描写使其极尽雕琢香艳之能事。第二类是咏美人衣着的,如沈约的《十咏二首》中的《领边绣》和《脚下屐》,这类作品承陶渊明《闲情赋》而来,却早已没有《闲情赋》中的归于雅正,只是愈加细致入微地摹写刻画,并最终流于淫靡。第三类则假托梦中作,如沈约的《梦见美人》,王僧孺的《为人述梦》,因是梦中之事,隔了一层,故描写可更加放荡。因此,在题材上,宫体赋少有涉及宫体诗那些最为淫靡的内容,而在诗赋共有的内容中,赋的表现也比诗要含蓄。
三 诗赋的异向发展
对女性的描写和男女之情的渲染是宫体文学最主要的内容。而此内容在诗和赋中的发展情况却有差异,“赋在女性描摹上走过的历程正好与诗相反”[7](P90)。
诗中关于男女之情的描绘,最早是以抒情的方式呈现,朱熹《诗集传序》谈《国风》云:
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诗经》中也有如《卫风·硕人》那样刻画女性之美的诗句,然而这样的细致描摹并不多,在谈到男女之情时,更多的是抒情的成分,所谓“各言其情”,如《王风·扬之水》: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诗歌以男子的口吻抒发对妻子的想念,不描摹妻子的容貌行为,只表达心中的感情。而“楚辞”中的女性,以《九歌》中的《少司命》和《山鬼》为代表。前者落脚于“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而后者虽有对山鬼的形象描写,却终归于“思公子兮徒离忧”的情绪化渲染。汉代民歌中的女性亦多痴情之人,《孔雀东南飞》中开始有了细致的衣着描写: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然而这样的描写只是诗歌的点缀,并不是主要内容,诗歌的题旨还在于渲染生离死别的哀情。这种哀情在短篇乐府民歌中表现更为明显,如《白头吟》中“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乐府中的女性多不以貌吸引人,而多以情动人。东晋玄学兴起,消解了诗歌中的男女之情感情。至南朝,随着咏物诗的兴盛,对女性的书写重新抬头,然而,此时的诗赋出现相互渗透的现象,诗歌受赋的影响,表现出赋化倾向,赋的铺排描写以咏物为媒介渗透到诗歌之中,如萧纲和《舞赋》写到舞姿时云:
扇纔移而动步,鞞轻宣而逐吟,尔乃优游容豫,顾盼徘徊,强纡颜而失笑,乍杂怨而成猜,或低昻而失侣,乃归飞而相附,或前异而始同,乍初杂而后赴,不迟不疾,若轻若重。
比较其《咏舞》一诗描写舞姿的部分:
逐节工新舞,娇态似凌虚。纳花承襵概,垂翠逐珰舒。扇开衫影乱,巾度履行疏。
诗歌在描写舞姿时借鉴了赋的铺排方式。这种对赋的借鉴在宫体诗中多有呈现,多用在对物与女性的描摹上,表现为对外在形态刻画精细,对行为叙述多铺陈直叙。这使得宫体诗在描写女性时更偏向直露雕琢。
而赋的发展则表现出相反的情形。早期的赋在描写女性时多是铺陈,如《神女赋》中对神女行为和容貌的铺排“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视。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这种铺排占了赋大部分的内容,只在结尾稍加点出因“不可亲附”导致的神伤。并且,因结尾有讽谏主旨,故前半部分的描写更可铺陈极致。到曹植《洛神赋》中,抒情的成分有所增加,不仅有君王的“怅盘桓而不能去”,亦有洛神的“长寄心于君王”,有了“楚辞”式的悲哀。而前所述发轫于《长门赋》的思妇之情也在此时达到极致,最好的是萧绎的《荡妇秋思赋》:
荡子之别十年,倡妇之居自怜。登楼一望,惟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天与水兮相逼,山与云兮共色。山则苍苍入汉,水则涓涓不测。谁复堪见鸟飞,悲鸣只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楼荡妇,对此伤情。于时露萎庭蕙,霜封阶砌;坐视带长,转看腰细。重以秋水文波,秋云似罗。日黯黯而将暮,风骚骚而渡河。妾怨回文之锦,君悲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远如何?鬓飘蓬而渐乱,心怀愁而转叹。愁索翠眉敛,啼多红粉漫。已矣哉!秋风起兮秋叶飞,春花落兮春日晖。春日迟迟犹可至,客子行行终不归。
赋出现了诗化的倾向,外在的铺排性降低,即使有也将其融入到浓郁的抒情氛围之中,尤其末尾四句,简直是一首绝伤的抒情诗,将思妇的容貌衣着都消释在悲情之中,一唱三叹。这种赋的诗化在萧纲《采莲赋》中表现也非常明显,其《采莲赋》最后有歌曰:
常闻蕖可爱,采撷欲为裙。叶滑不留綖,心忙无假熏。千春谁与乐,唯有妾随君。
用的便是其《采莲》诗中的成句,诗句的抒情性使赋的描摹显得不再生硬,而多了一些温婉。
因此,齐梁时期诗赋的发展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于宫体诗赋亦然,诗的赋化表现为宫体诗借鉴赋的铺排来摹写物象和女性,使诗歌多显得直露,其抒情意味相比早期有所降低。而赋的诗化则使宫体赋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方式,使赋在描写女性是有了更多的情感导向,这种抒情性稀释了其本该有的因铺排刻画造成的浮靡。
在描写清辞艳情时,宫体赋本该因其敷陈直叙的特点而比宫体诗直露浮靡,然而却并非如此,赋在描写女性时本身所具有的“曲终奏雅”的传统,赋的书写内容没有诗歌那样私密化,以及赋的诗化使抒情性稀释了艳辞,这三个原因导致在表现宫体内容时,赋反而比诗要含蓄节制得多,所谓写诗多放荡,而作赋则更谨重。这种含蓄使宫体赋在文学史上受到的诟病没有宫体诗那样多,同时却也使得研究者常忽视其存在,也算颇留遗憾。
[1]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徐陵.玉台新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7]胡大雷.宫体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归青.南朝宫体诗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9]阿忠荣.“宫体赋”略论[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
[10]张丽.宫体赋初探[J].齐鲁学刊,1996(6).
[11]祝凤梧.梁朝宫体赋试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4).
责任编辑 吕 斌
I207.22
A
1006-2491(2015)01-0088-05
李旭婷(1989- )女,云南昆明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