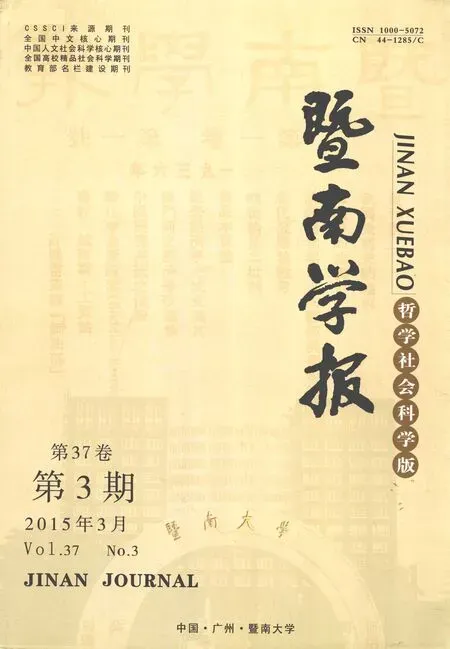中美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之比较
蒋亚娟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重庆 401120)
自1978 年以来,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环境法一改传统法学理论中视环境为中介物的观点和看法,将“生态损害”纳入法学范畴。2005 年之后,法学界就我国的生态损害的界定与分类等问题基本达成共识,对生态损害的关注度逐步提高。在国外学界,许多学者都曾试图定义生态损害,研究法律如何应对生态损害问题。美国、欧盟等国家(地区)的环境法研究较早,尤其是20 世纪70年代以来建立的美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在法律规制的广度和深度上有长足的发展,可资借鉴。
一、中美生态损害赔偿的法律内涵比较
在我国学界和司法界,生态损害的界定尚存争议,主要存在两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力图拓展传统环境侵权法的视野,认为生态损害包括环境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既包括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也包括与被损害环境相关的财产、人身、精神损害。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损害是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不仅包括经济价值的损害,还包括了美学、生态、文化等多重价值的损害。
在美国,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生态损害赔偿制度逐步发展完善。美国主要通过五部联邦法律以弥补自然资源所受的生态损害,主要有:《综合环境应对、补偿及义务法》(Th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CERCLA),该法规定任何有害物质的排污者都要为其损害行为承担责任;《石油污染法》(Oil Pollution Act,OPA),该法规定对水体或毗连区域泄漏石油的主体有赔偿的义务;《联邦水污染控制法》(The 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FWPCA)对石油污染法中没有规定的航道的石油或有害物质污染责任进行了规定;《国家公园系统资源保护法》(National Park System Resource Protection Act,NPSRPA),规定了对国家公园实施资源破坏的任何主体的法律责任;《海洋保护、研究和保护区法》(Marine Protection,Research and Sanctuaries Act,MPRSA)规定了在规划的海洋保护区内损害自然资源的法律责任。
1977 年美国通过《清洁水法》提供了生态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并对生态损害的成本、费用、重建等术语及范畴做了明确界定。1980 年美国《综合环境应对、补偿及义务法》创立了一项旨在消除、减少或者移除污染物质或者有害物质的超级基金。在无法确认环境污染者或者拒绝合作的情况下,该法赋予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清理污染地的职责。在清理工作完成之后,该法授予环境保护署补偿参加该工作的个人或企业为此所支付的费用。补偿范围包括了自然资源本身遭受破坏的事实、美感、价值上的损失以及评估该损失的费用与成本。
1990 年,George H. W. Bush 总统签署了《石油污染法》,授权使用1986 年设立的石油泄漏责任信托基金(Oil Spill Liability Trust Fund,OSLTF)。该基金虽然于1986 年设立,但在1990 年Exxon Valdez 漏油事件发生以前,国会并没有通过任何立法授权使用拨款或者财政收入以维持该基金的运转。基金的使用范围包括了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和修复、支付应当补偿而尚未补偿的拆迁费用和损害赔偿等。2005 年《能源政策法》将该基金增加到27 亿美元。该信托基金可以用作支付或缓解与控制石油泄漏威胁相关的费用,主要用途包括索赔和相应的管理、研究费用等,而发生拆迁费用或因溢油受到损害的任何个人或组织均可提出索赔。
2011 年,美国国家研究会减轻湿地损害委员会(Committee on Mitigating Wetland Losses of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S.))经研究认为,应当基于《清洁水法》第404 条之规定建立湿地的修复和重建计划。因此,在调研案例和掌握大量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委员会建议设立一个通过赔偿来减轻环境损害的机构,即:依照法律、法规和决策管理审批和损害赔偿的机构,所做的赔偿应当要达到湿地保护、保存和保育的各项生态行为标准(ecological performance criteria),以确保湿地水域的物理、化学、生物质量不会被减损。该计划需要达到下列三个条件:其一,应当事先就被赔偿地选址进行专门的规划设计;其二,减轻环境损害的赔偿方案应当先于或与许可行为同步进行;其三,该方案应当在法律和财政的支持下长效运行。
综上,两国对生态损害的法律认识的共同之处在于:一方面,均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公共品属性,认为生态环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应当让生态损害的责任方承担生态损害的全部成本。另一方面,均认识到了生态价值及其决定的生态利益的广泛性与复杂性,认为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涵盖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多元价值。两国不同之处在于,我国主要处于生态损害的理论研究层面,尚未形成专门的、系统的调整生态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体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理论观点的不甚一致,导致实践中立法缺位、执法无据和司法受阻;另一方面,由于“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经济价值、轻生态价值”的旧有发展意识的影响,理论成果向法律制度转化的进程减缓,法律对于生态问题的调控力度还不够。而美国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已经初步形成了生态损害的法学理念和制度框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美国多次修订环境保护立法,生态损害在各类单行法中的覆盖面逐步拓展,赔偿责任逐渐加重,实现了主要生态损害类型的全面调整;再加之立法根据生态损害的发生机理,对生态损害实行全过程控制,基本实现了生态损害赔偿立法“静态与动态”的结合。其二,美国有比较成熟的公民诉讼、环境应急管理等法律制度,较好的法律基础为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创造了前提。丰富的生态损害赔偿判例不仅相对于成文法可以更加灵活的解决现实问题,还使得生态损害赔偿法律调整的内容更加务实而具体。
二、中美生态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制比较
(一)总体理念
在美国,以生态损害为诉讼内容的案例中,政府和普通公众相互之间作为原告或者被告,这些判例大都体现出了环境保护法律重视生态保护和公民健康,鼓励公众参与以及政府积极作为的理念,如Mehaffy v.U.S.,United State v. Lambert等诸多案例。当然,虽然法院认同生态损害应当赔偿,但在如何认识生态利益的角度上,法院对环境保护及环境利益的保护范围存有两种不同的理念;相应的,秉持这些不同理念的法院分别产生了两类不同的法院判决。一类是对于生态保护和其他影响因素持保守态度的法院判决。如,United States v. Cumberland Farms of Connecticut,Inc一案涉及到水淹农场,要求被告将该湿地恢复至1977 年的水平。与此类似的还有United States v.Akers,该案要求恢复之前环境保护禁令,“依据过去及现在(本案)湿地的使用状况,以及有正在发生和潜在的行为,均不得滥用自由裁量权”。在New Jersey Dept’of Envtl.Prot. and Spill Compensation Fund v. Exxon Mobil Corp.一案中,法院认为,虽然被告公司依据《泄漏补偿和控制法》(Spill Compensation and Control Act),对自然资源及其修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并没有对“损害造成的损失”(loss of damage)有严格的责任。另一类是对于生态保护和其他影响因素持开放态度的判决。如Foresyth County v.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一案中,法院要求非政府组织应当事先给予地方政府以生态保证金。同样的判决结果可以见于Ohio Valley Environmental Coalition v. U.S.Army Corps of Engineers。该案中,原告提出,因为环境保护署基于《清洁水法》404 条(c)项而对被告公司行为有可能会行使否决权,应当限制被告Mingo Logan 煤炭公司的行为,为环境保护署留足必要的时间。尽管Mingo Logan 公司提出抗议,但这项动议显然已被法院认可,并且环境保护署已经采取了行动。
虽然我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了立法目的,即“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生态损害及其赔偿的理念尚未在立法中得到体现。然而,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关注到了生态损害,明确了生态损害应该赔偿、生态环境应当得到保护的理念。如,该法在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了:“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该法第三章“海洋生态保护”第二十条规定:“对具有重要经济、社会价值的已遭到破坏的海洋生态,应当进行整治和恢复。”
(二)生态损害之认定
在Ohio Valley Environmental Coalition,Inc,v.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一案中,原告对被告所属的Highland 矿业公司依据《清洁水法》第404 条之许可证规定向河流等水体排放、倾倒废弃物的行为提起诉讼。起初,法院先是扣押了被告的排放许可证,而2011 年4 月,被告公司重新授权其所属的Highland 矿业公司使用该许可证,直接导致了该诉讼的开始。该案的审结几经周折。期间,被告提出了一系列的减轻损害赔偿的计算和解决的方案,以对现有的损失进行填补,如,被告提出了详细的临时减轻生态损害的方案(Interim Functional Assessment Approach),以使河流恢复到之前的功能。并每年增加3%的投入直至生态功能恢复。尽管如此,主审法官Chambers 认为:“任何主体都无法对该损失进行界定,并且生态损失的衡量标准比较模糊,应当尊重原告对被告Corps公司做出的决定。《综合环境应对、补偿及义务法》第113 条规定,如果法院发现环境损害的应对计划必不可少且事先无法预见,即使是与法律规定不一致,法院也应当认可该反应计划的花费和其他减轻损害的措施。
在美国,有关生态损害的诉讼也并非无往不胜,只有在立法明确的情况下,生态损害才能得到有效的救济。在Commonwealth v. Shell Oil Co.一案中,原告波多黎各(Puerto Rico)就被告在波多黎各出售和使用甲基叔丁基醚(Methyl tertiary-butyl ether,MTBE)的行为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停止这一行为,并且应当对此行为所导致的生态损害、道德损害和经济损害进行赔偿。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Shira A. Scheindlin 认为,虽然被告这一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可以有不同分类,生态损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衡量,但是生态恢复基本上无法实现。与此同时,法院还认为,依照波多黎各民法典1802 条之规定,生态损害是指“由于自然人的疏忽,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损失”,主要是指“对私人财产中的自然资源带来的损害”。因此,法院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我国与生态环境损害有关的立法主要见于《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和各项污染防治单行法当中。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了“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然而,赔偿对象仅仅限于直接受到损害的主体,赔偿范围尚未涉及间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侵权责任法》的第六十五条虽然规定了“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该法第二条列举的“本法所称的”十八项“民事权益”,其中生命权、健康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均未直接指向生态利益,并未涉及生态环境权益。
综合上述立法观之,相较于美国环境保护的立法和判例,我国现行环境保护立法倾向于保护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将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作为“财产”或者“财源”来进行保护,现行法律条文的表述及法律规范还没有显示出对生态价值的关注,并且缺乏对该生态价值所需要的公法和私法制度的综合调整。当然,两国生态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也面临一些共同的需要解决的难题,如,在法律规范的结构和内容体系上,生态损害主体不周延、生态损害客体不明确、主体与客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平衡以及环境法律责任的完整度有所欠缺等问题还有待解决。
(三)生态损害之诉讼
1.诉讼主体。在1978 年修改《外大陆架土地法》(Outer Continental Shelf Lands Act,OCSLA)之前,州政府可以代表其民众对石油污染提起诉讼,公民可以就污染行为所导致的重建费用和渔业资源可期得的商业利益请求赔偿。依据美国《清洁水法》第331 条(f)(5)项下之规定,“总统或任何州的授权代表,均能代表公众作为自然资源的信托人,并可以就恢复或者重建该类资源的成本得到赔偿。”美国《综合环境应对、补偿及义务法》第107 条f(1)项规定,“在涉及自然资源损害的情形下,美国总统或者其授权的任何州代表,得以这些自然资源的所及的公共福祉以信托人的名义对此类损害采取相应的行动。参与生态损害救助(包括但不限于非政府组织)并为此付出对价的主体和生态环境本身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生态损害诉讼。”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立法对自然资源损害的起诉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即只能由政府机构对自然资源损害提起诉讼。尽管《清洁空气法》第304 条授权“任何人”对“任何主体”都可以依据该法就履行法定义务提起公民诉讼,但是《清洁水法》对“公民诉讼”的主体做了严格的限定,该法第505 条(g)款规定,所谓“公民”是指受到损害的利害关系人。在其他立法中,“公民”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是否可以就生态损害提起公民诉讼,要视不同的单行法律规定而判定原告是否适格。因此,对于生态损害诉讼,美国现行立法对公民诉讼主体有适格条件的限制,并非任何自然人或者环境保护组织都有相应的起诉权。特殊的规定仅见于《石油污染法》,该法赋予了自然人部分的诉权,即依据该法,自然人可以起诉联邦官员,要求法院限令该官员依照石油污染法实施法律、履行职责。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六条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解决因大气污染、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海事管理机构、渔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调解处理的前置程序。《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共同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 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但是,该法尚未规定对破坏自然资源、损害生态系统的行为,这些主体是否有诉讼的权利以及如何提起公益诉讼。
2.赔偿范围。依照美国法律之规定,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了生态损害评估和修复费用、拆迁费用、对生态环境本身的减损所应作的赔偿、研究发展费、管理费等多方面,力图通过制度的保障尽可能地进行生态恢复和生态重建。如,《综合环境应对、补偿及义务法》第105 条规定了国家有害物质应对计划(the National Hazardous Substance Response Plan),该法107 条第a(4)项下规定,任何有害物质的接受者或排放者,都有:(A)基于该计划对治理污染产生的所有费用的赔偿责任;(B)支付其他必要开支的责任;(C)支付因该行为侵权、环境资源破坏和减损而产生的费用和(D)支付该法104(i)款之规定的公民健康影响评价的费用。再如,《国家公园系统资源保护法》(National Park System Resource Protection Act)规定对国家公园造成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有:(1)重建、保护或者达到国家公园资源系统要求所付出的对价,以及在国家公园资源尚未得到修复和重建或者获得同样有效的资源之前所付出的任何巨大的代价;(2)国家公园资源一旦不能恢复或者重建时所带来的损失;(3)根据19jj-2(b)条款评估的其他损害价值。
3.计算方法。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了财产损失的计算,即“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该法第二十条规定了侵害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赔偿计算方法,即“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当事人可以委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提供有关监测数据。对于在审批过程中,如何申请生态损害的司法鉴定,法律的规定亦十分模糊。但是,两国的上述规定都没有触及生态利益如何衡量,生态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生态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害的评估定损体系还有待建立。
4.证明责任。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排污方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美国法律也做了相似的规定。如,《综合环境应对、补偿及义务法》第104 条、第106 条和第107 条规定,环境保护署启动超级基金(Superfund),采取了减轻(remove action)或者消除(remedial action)危险物质污染的“应对行为”后,如果下列要件具备,就可以要求相关主体支付该“应对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即(1)有依107(a)之规定的适格主体(potentially responsible parties),包括污染设施的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和运输者;(2)有处置危险物质的行为;(3)释放了危险物质;(4)产生了相关费用。这一支付义务非常严格,环境保护署并不需要就过失、知识、有罪或无罪等方面进行举证,且对四类主体追究共同民事责任。
三、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完善建议
(一)明确生态损害之诉权
追究生态损害责任,应当“立法在先,行事在后”。一方面,应当确立生态利益的法益归属。除一般民事诉讼所涉及的物的生态价值的情形之外,生态损害一定程度上属于“公共妨害”(public nuisances),其所涉及的生态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由于生态利益的主体不能归属于明确指向的私人主体,因此私人主体往往限于权利范域的局限而无法对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普通公民的享有健康、安全、舒适之环境权利及其实现也会受到影响。美国普通法已经赋予州政府反对“公共妨害”的诉权,政府仅仅只需要证明公共权利的行使受到由被告行为所导致的阻碍,就可以提起诉讼。《综合环境应对、补偿及义务法》第107 条、《联邦水污染控制法》第311 条、《石油污染法》第1002 条等相关立法授权政府在合理或必需的情形下,可以采取减轻损害的措施。同时法律赋予私人主体就污染行为对自己所造成的侵害提起消除污染和损害赔偿之诉。我国宪法尚未明确公民“环境权”,应当尽快完善立法,明确公众对生态环境和生态利益的权力,保护生态环境,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
(二)明确生态损害之法律责任
在现行立法内容体系之下,可以运用传统的“命令与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措施及理念,从生态损害相关主体法律责任的角度对生态损害行为加以规制。如,在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和各项环境保护单行法中,设立减轻和赔偿生态损害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规定政府部门、检察机关和社会环境保护组织代表公众提起生态损害之诉的权利。与此同时,我国还可以基于行为科学的考虑,从相关主体的行为动机的角度,通过法律制度的更新,扩大生态损害行为的法律阻止途径。如,逐步建立生态保护的经济利益激励制度、生态损害诉讼制度和政府的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形成结构工整的环境法律关系束。完善现阶段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立法,为法律调整与生态损害有关的社会关系提供依据。
(三)尽快建立生态损害衡量标准
生态损害如何量化是目前很多国家生态立法的难题。美国运用了许可证、银行、保险、税收等多种命令与控制措施以解决生态损害的问题。相对于诉讼途径,命令与控制措施的优势在于,能够就生态保护一般可能发生的状态进行制度预设。作为具有命令与控制措施特点的生态损害衡量标准,同样可以事先确立生态损害行为的违法成本。另外,我国应当借鉴完善我国传统的环境税费法律制度,确立与环境相关的行为的生态成本的衡量标准,将生态损害转化为污染者行为的内在成本。通过改革环境税费制度、制定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则,来提高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行为人的违法成本,实现常规状态下对生态环境的经济、美学、生态价值的综合保护。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生态诉讼中生态损害的衡量标准体系。
(四)建构生态损害多元调控制度
借鉴美国普通法的立法经验,建立灵活的生态保护政策体系,整理和研究生态损害的典型判例,实现不同部门法规则体系的良性互动。相对于传统的命令与控制手段,普通法的优势在于,对于制定法未规定详尽之事项及特殊情形,能够通过具有解释力的判决填补制定法之不足,行事灵活并较高效率地填补成文法之短板。在我国,可以充分发挥环保法庭代表性案例的示范作用,结合环境保护部及相关部门的执法案例,逐步完善预防和治理生态损害的立法经验。防治生态损害要多管齐下,通过环境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的协调,实现生态损害法律关系的全面调整。
(五)建构生态损害的全过程防治制度
依据生态损害事件的生命周期理论,在生态损害预防和治理全过程的不同阶段设置不同的法律制度,建立适合生态损害事件发生和发展特点的规则体系。如,完善生态保护常态制度以预防生态损害,建立环境保护的法律激励机制,加大污染者的违法成本,尤其是细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恢复和重建责任,控制生态损害的发生。在生态损害行为发生和控制过程中,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基础,借助公法手段固有的“强制性”,完善政府环境风险管理,将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职责具体化和明确化。完善生态损害发生后的司法救济规则,明确各级政府及其环境保护部门在生态损害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提起诉讼的权利及条件,拓展生态损害社会化救济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