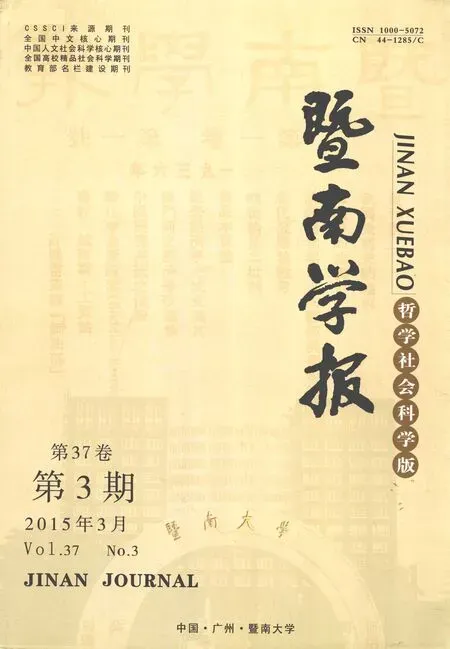莫言与高密东北乡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275)
一
无论就广义还是狭义的角度讲,文学与地域文化都是关系密切的。不能想象完全没有地域背景的文学作品的存在,即使卡夫卡和普鲁斯特这样以揭露内心秘密而故意隐藏国家和地域的作家,也同样如此。因为某种程度上,地域文化是文学通过语言叙述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的潜在的指南针,文学的语言,实际可以说就是某国文学或某位作家的地域语言。这已为中外文学史屡次地证明过。
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一定意义上是通过语言这个媒介体现的,没有语言这个媒介,所谓作家的语言个性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比如鲁迅和沈从文都是采用现代白话创作小说的,他们的白话运用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无人能比的天才的程度。但是,有心人可以仔细琢磨一下,剔除鲁迅所谓“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不说,光就他犀利、刻毒和深刻的语言看,就明显是取自他的故乡绍兴师爷的文风的;绍兴师爷寸铁杀人、老吏断狱的那种一笔就能致对方死地的犀利文笔,更深层次上是来自浙东人有仇必报的血性型的地域文化。而沈从文同样如此。他的散文化抒情化的文字风格,与湖南湘西山高皇帝远的偏僻闭塞,与当地多民族杂居,也就是说远离中原儒家文明和道德规范约束等等原因,是密切相关的。湘西文化,鼓励着人的野性、随心、无节制的自由和天然人性的培养,长时期浸润在这种地域文化中的沈从文,出笔就沾染着湘西山水、习俗和文化的滋养。这是连作家本人都意识不到,而对文学史研究者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潜在背景,是文学史专家非常在意,而作家在批评家们指出以后,则越来越强调自己的这种地域和语言特性了的,通读成名之后的几乎所有著名作家的访谈录、自述、创作谈等等,都强烈和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点。
不过,“地域文化”与“文学”不能一对一地一概而论,无法指望一篇鸿篇大论就能解决的。对不同作家来说,他们的创作与地域文化的亲密接触,可能是多方面的,处在不同分层上的,因人而异,精彩纷呈。确切地说,每个作家对故乡这个地域的理解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与其亲身经历有关,而且他们感触环境的差异性,也决定了是千差万别的结果。举例来说,如果老舍不是父亲早亡,又是层级较低并且破落的八旗子弟后裔,他不可能接触旗人下层社会,包括一整套的习俗文化。于是,他是以“穷人”的视角理解那个在历史大潮荡涤中,已成为北京底层社会的旗人世界的。这种穷人身份,使他感触这个社会时有了一点愤激,也有了一点温热;有了一点世俗烟火气,也有了一点希望超拔于这个阶层之上的胸襟和眼光。因此,让老舍来写北京旗人社会,他不用文人修辞,就复原和重现了后者的习俗礼仪、语言特点和处世之道;反过来,这些习俗礼仪、语言特点和处世之道,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老舍小说的叙述风格,他的表达方式。浓厚的北京地域文化,通过作家创造性的想象,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的舞台,他也因此获得了北京“市民诗人”的称号。
二
莫言因构筑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世界而举世闻名,这个地方也因为作家而为世人所知。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乡平安庄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小学五年级辍学,在故乡做了十年农民,1976年参军入伍。又经过将近十年的艰苦奋斗,因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走上文坛,又因小说《红高粱》被改编成电影而名满天下。底层出身,底层社会的挣扎和奋斗,使莫言接触最多的是高密县典型的底层文化和民间文艺。蒲松龄的《聊斋》、聂庄泥塑和高密剪纸、茂腔,是莫言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高密地域文化给这位家乡子弟最丰厚的礼物。
在莫言家里,人人都是讲民间故事的高手。“蒲松龄式”的民间作家,可以说遍布河崖乡平安庄的街巷胡同。莫言说:
那时我因为组织“蒺藜造反小队”被赶出校门,干农活又不中用,便有许多时间泡在大爷爷家。名曰学医,实则是泡在那里看热闹,听四乡八屯前来求医的人说一些逸闻趣事。大爷爷是地主成分,只因为有医术,土改时才免于一死。解放后政府对他特别照顾,没强制他下田劳动,允许他在家里坐堂行医。他那时已经年近八十,但耳聪目明,头脑清楚。他是个很健谈的人,尤其是三盅酒落肚之后。我从他的嘴里听过很多故事。这是事实,并不因为马尔克斯有个善讲故事的外祖母我就造出一个善讲故事的大爷爷来类龙比凤。后来听上了年纪的村人私下里说,大爷爷年轻时是个花天酒地的人,干过不少闻名乡里的风流事。听到祖辈的秘史,感到很亲切,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尊敬,反而感到敬佩。
管谟贤也认为,大爷爷才是莫言写小说的第一个老师,故乡人皆能讲故事的习俗风气,是他文学想象力的重要资源之一:“我的大爷爷、爷爷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我和莫言都是听着爷爷们的故事和集市说书人讲的故事长大的”,奶奶、母亲、姑姑们也爱听故事,冬天夜长,所以经常请村人郭茂刚来念家里那些64开木刻本的唱词本子,无非是一些秀才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的故事。女人做针线,男人搓麻绳,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另外,冬季村里向阳的地方,往往编草鞋和“村里闲人聚集的地方,有人讲故事,说荤笑话,传播乡间新闻”。70年代漫漫的北方冬夜,乡村文化生活极其贫乏,莫言就在这种环境接触了地域文化。他曾经说,不知道是他祖祖辈辈的家乡人赋予了那位距高密仅二百里的杰出短篇大家蒲松龄,还是蒲松龄的故事,本来就属于民间故事,而得以通过他家乡的祖祖辈辈的“口传文学”而流传到自己这个高密子弟心里。
与贾平凹受陕西商州和西安古墓、古碑、陶罐和书画等乡土文人地域文化极深的熏陶不同,莫言的辍学,使他接触不到更高的文化层级;这种不幸经历,反倒让他沉浸在家乡民间文化和文艺之中,成为后者最诚恳的授业弟子。80年代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极大之后,莫言在90年代开始觉醒。1995年,他在《〈丰乳肥臀〉解》中谈到观看雕塑油画幻灯片、走访霍去病墓、高密聂家庄泥塑以及母亲的死等等写作的缘起之后,明确地解释说,在这些东西里面:“感动着我令我冲动给我力量的是一种庄严的朴素”,“我在《丰乳肥臀》中描述了高密东北乡从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变成繁华市镇的历史,描写了这块土地的百年变迁。母亲们和她们的儿女们在这片土地上苦苦地熬煎着、不屈地挣扎着,她们的血泪浸透了黑色的大地又汇成了滔滔的河流。”有心人发现,在毅然扔掉外国文学这根“拐杖”后,莫言在向高密东北乡一带的地域文化和民间文艺,大踏步地后撤。他一反常态地从向西方现代派作家学习,退回几百年前到老乡蒲松龄那里。这是历经沧桑的中年人,或者说一个正在成为一个成熟作家的人的必然选择。莫言在《〈四十一炮〉后记》说:“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这是写作这个职业的唯一可以骄傲之处。”然而,“与任何事物一样,作家也是一个过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檀香刑〉后记》说:“1996年秋天,我开始写《檀香刑》。围绕着有关火车和铁路的神奇传说,写了大概有五万字,放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明显地带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于是推倒重来,许多精彩的细节,因为很容易有魔幻气,也就舍弃不用。最后决定把铁路和火车的声音减弱,突出了猫腔的声音。尽管这样会使作品的丰富性减弱,但为了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为了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牺牲。”他承认:“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
2014年10月中旬,笔者因开会参观距莫言家乡不远的聂庄祖传泥塑。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各种民间泥塑作品摆在那里,它们憨态可掬、拙朴生动,仿佛是来自几百年前的生灵,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效果。高密剪纸则细密繁复,又粗糙无拘,天马行空,来去放任,具有作品的“未完成性”,像一件件有待进一步加工的天籁作品,挂在展览的墙上。聂庄泥塑出自几代民间艺人手下,高密剪纸则纯粹是当地农妇所为,莫言的奶奶,便是其中的巧手之一。莫言回忆:奶奶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我不只一次地听我的大爷爷、外祖父夸她做的饭菜好吃,针线活漂亮。村里有人家结婚,窗花、馒头花常找她剪;丧事也找她去操办。奶奶还会接生,新中国成立后虽说新式接生已经推行,但找她接生的仍很多。”很久以来,我不了解莫言小说风格为什么这么汪洋恣肆、天马行空,他语言粗糙,非常有力量,像是还有待进一步修改细琢并最后完成的作品,但他都拿出来发表和出版了,当然也不断受到评论家的批评和诟病。看完高密聂庄泥塑和民间剪纸画之后,心里便知道何以如此。民间文艺的魂,早走进了莫言的文学世界,构筑了他的文学王国。这些带有奇思妙想和狂悍之气的齐国文化,具体地说,也就是高密地域文化,以它千百年非凡的艺术力量,塑造了这位当代杰出小说家。因此可以说,没有高密地域文化,就不会有莫言这个人。
因生于斯长于斯,让莫言来谈流传于他家乡几百年的“茂腔”这个地方小剧种,就有了不同一般的将心比心的见识。茂腔是一个流传于高密及周围几个县市的地方小剧种,当地人的喜爱程度不可言喻,莫言在家乡当农民时就曾登台演出过。但他承认:“茂腔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剧种,流传的范围局限在我的故乡高密一带。它唱腔简单,无论男腔女腔,听起来都是哭悲悲的调子。公道地说,茂腔实在是不好听。但就是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剧种,曾经让我们高密人废寝忘食、魂绕梦牵,个中的道理,比较难以说清。比如说我,离开故乡快三十年了,在京都繁华之地,各种堂皇的大戏,已经把我的耳朵养贵了,但有一次回故乡,一出火车站,就听到一家小饭店里传出了茂腔那缓慢凄切的调子,我的心中顿时百感交集,眼泪盈满了眼眶。”后来长篇小说《檀香刑》的创作,就缘于这次经历。他曾想写一部关于火车和茂腔的长篇小说,后来发现建筑已经百年的胶济铁路尽管与高密血肉相连,但不好写,于是决定主要写茂腔。他设想把茂腔变成这部小说的基本旋律,基本调子,萦绕始终。今天看来,这是每逢创作长篇小说的作家考虑的一个技术问题,没有起头、旋律、氛围,长篇小说没办法定个调子。然而,对莫言这个当代杰出的乡土作家来说,茂腔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小说调子了,而是这部小说的灵魂,是作者自己魂牵梦绕的东西,是他生命的一切。他要用茂腔来表达自己对大千世界和生生死死的理解。在高密地域文化的深处,他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三
尽管在第一部分的观点中,我反复强调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是需要通过具有当地特色的语言来实现的。不过,深究起来,这乃是作家整个的气质和灵魂问题。这种气质和灵魂,蔓延到他创作的小说作品当中,就构成了这些作品的一个个关键环节,构成了过去我们解释不了,到今天才渐渐明白的那些东西。比如,叙述的节奏、语言特点、调子、氛围、想象力和控制力、人物塑造、色彩旋律等等。莫言的小说一向长于运用色彩,他过去说是受到高更、凡高印象派画的影响启发,其实在聂庄泥塑和高密剪纸里,这些东西比比皆是。他的语言汪洋恣肆、无法控制,我们看高密剪纸那种粗糙和未完成的任意恣肆,也就一目了然。莫言小说题材大气,不拘于小节小情景,说好了是伟大作家的气质,说不好了是不善于大小结合,于小处就显随意随便,但是凡到过高密一游,与当地崇尚英雄好汉性格的普通百姓一接触,自然即知道这些东西的来处。莫言21岁离开高密去部队当兵,他在高密整整生活了21年,要知道基本完成了从出生、成长到性格气质完全固定的生命过程,高密当地民风和人民性格的一切,早就牢牢铸就了他的整个世界。当然,所谓“当地人”的性格性情虽然大同小异,各呈异彩,但千万条之中,只要有一条被作家接收,便敷衍发展成他整个气质的主要方面,成为他文学世界的灵魂。这种东西就是莫言在高密最好的朋友张世家所评价的。他说:“我知道莫言平生最反对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最崇拜英雄好汉,最仇恨王八蛋。交朋友他喜欢的是一见面就能把自己的全部缺点暴露处理的人,最鄙视装模作样的,最瞧不起的是钻别人的裤裆。他说:‘一个人若没有真本事真能耐,靠钻裤裆过日子是不会长久的。尤其是搞文学创作’。”我觉得这是张世家对莫言的一种归纳式的评价,是一个总的评价。这种评价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血性、正气,自然坦荡。举凡莫言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我们看得最多的,也许就是利用小说叙述技巧的掩护,去表达对人间不平的愤怒、批评,对农民命运的怜悯,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总的看法,从《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到《天堂蒜苔之歌》、《酒国》、《生死疲劳》和《蛙》等等都是如此,从来没有变过。
而这些庞大复杂丰富的内容怎么去体现呢?还是我这篇文章主要说的语言。很大程度上,莫言小说的语言是高密当地人的语言,就如张世家所说的是一种正直愤激的语言,是一种粗糙大气有力度的语言,也是一种充满血性的语言。这就应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古话,凡是优秀杰出的作家,莫不出自这一道理。鲁迅如此,沈从文如此,老舍如此,莫言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地域辽阔、文学资源广博的老中国培养出来的精魂。2009年8月22日,在建于山东高密县一中校园内的“莫言文学馆”举行的开馆仪式上,面对家乡父老,莫言说过一段非常质朴也很实在的话:“我一直认为,莫言文学馆里的莫言和站在这里的莫言不是一个人了,文学馆里面充满了溢美之词,充满了过誉之词,与我本人相差甚大。我实际就是一个放牛、放羊,在农村劳动了二十年的一个农民,然后当了兵,在军队的培养教育下,在家乡的父老乡亲激励下,拿起笔来写了一点小说,取得了一点小小的名气,没有那么玄乎,也没有那么了不起。”我以为这段话,就把莫言与高密东北乡最深层的关系概括出来了。对文学史研究来说,不需要太多玄奥抽象的分析,第一手的材料,尤其是作家本人的自述,已经是最好的文学史的分析框架。
——以高密茂腔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