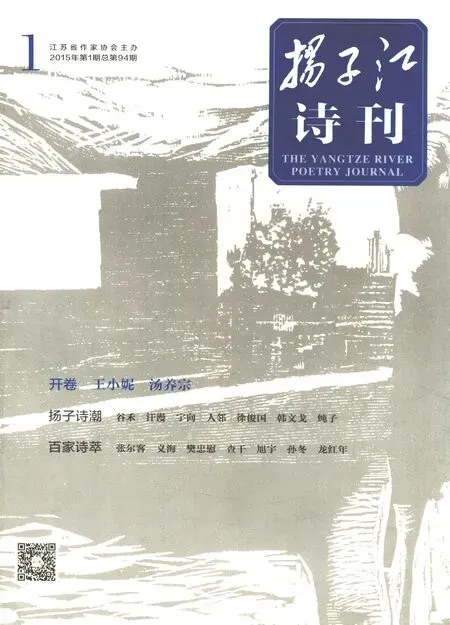谷禾的诗
谷 禾
○ 扬子诗潮 ○
谷禾的诗
谷 禾
窗 外
城铁站像一个人在沉睡
后半夜的灯光照亮了他体内
最隐秘的部分。那里有另一个人
在一根接一根抽烟
偶尔,望着夜空对应的星辰
——多少年,我始终不能看清他的脸
我走近,他就消失……
自行车之诗
我有过四辆自行车。一辆永久牌
加重的车型。那时我18岁,在小镇上教书
我用三个月的工资买来了它
我骑着它,回村里帮父亲收麦子
去县城约会女友,每天去邮局取回订阅的报刊
这个顶呱呱的家伙,一路载着我
风光无限地飞驰在大路上
如果不是晕头晕脑地扔在了邮局门口
我不会有接下来那辆28型凤凰,闪着银光的
小尤物,它在我梦里,也系着小偷的牵挂
终于在一个月明之夜消失了踪影
那一年,女儿磕破脸,妻子动手术,父亲外出被收容
倒霉事儿一桩接着一桩
它的丢失不过是我又触了小霉头
我甚至怀疑是小尤物主动选择了出走
第三辆只能算一夜情,我从车行里买来
扎在楼道口,去到屋子里招呼妻出来过眼
转脸已被谁顺手牵去
最后我买来一辆二手,骑着它,转遍了
这个城市的大小胡同
直到把它骑成一堆废铁
我的自行车人生,我的被时间磨损的青春
因为一次次丢失
才作为尴尬的供词,被一首诗记录下来
在消逝的途中停留了一会儿
旧天堂——我去过的一间书店
那么多书!那么多书那么多书那么多书
在夜的宁静里
仿佛睡熟的婴儿。灯光照亮的我的影子
是否惊扰了他们?
嗯。这是我想象的旧天堂的样子
虚掩的门扉
离咖啡和茶的人间只有一小步
我在旧天堂发现
久远的挚爱——寻归荒野。路法西效应。布罗茨基
和曼德尔斯塔姆……
旧天堂之外的喧嚣声,滚烫的咖啡
一点点变凉
我是怎样离开的?
亲爱的旧天堂,我走在星光低垂的黑暗里
忘了身在何处
但是,我穿过布罗茨基和曼德尔斯塔姆
一次次回去了
你的无雪的冬夜——
2月13日正午,在北运河岸边相遇蝴蝶
我看见蝴蝶
停歇在一片枯干的叶子上
铁青的岩石
托举着它
浩荡阳光让它的翅膀有了重量
我看见更多蝴蝶
从夏日的山谷飞出来,为我带来
缤纷的花纹和触须
这个冬日正午,我有瞬间的晕眩
怀疑自己
何曾看见一只蝴蝶
仿佛另一片叶子
它的阴影不断扩散开来。但石头是静止的
阳光也是静止的
当我转身,它消失在更多事物的深处
经过我们身边的河流
经过我们身边的这些河流
进入中年以后,我渐渐听到它
并且在自己的身体里看到了它宏阔的影子
我是说,每一条河流
的源头都居住在你的身体里
无论是黄河、长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
还是缠绕着村子的涓涓小溪
这是河流的秘密
它不会亲口告诉你
这么多年
我在河边遇见青草、树木、野花
布谷鸟、飞鱼
我遇见挖沙船、铁锚、呜呜的汽笛
葬身旋涡的快艇
我遇见执手相送的人、伤心欲碎的人、一步三回头的人
我遇见一个孩子
他放牧着羊群,一边望着汤汤大水
眼睛里疑云飞渡
到了对岸
放牧的人,变成了一个老者
他的目光明亮而澄澈
仿佛有着河流的宽仁之心
我知道,是流逝的时光粉碎并再造了他
就像这大水
它曾有涓涓的初始,惊涛拍岸的起落
越接近大海的地方
渐渐变成了一个虚无的存在
在暮晚的光线里
注视着落日熔金,一只笨鸟飞起又落下
或者干脆中途消失
成了地理学上一个神秘的词语
唉!我说出这些
从此将不再拥有一条河流的秘密……
两只鸽子之诗
它们有时撩动翅膀飞起来,有时落上门前柴堆
间或蹬开柴草,下到院子的泥地上觅食
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音。但更多时候
它们比我年迈的父母还安静。屋子的横梁上
悬着它们的屋子。它们依偎着
似乎不关心屋外的事儿,羽毛乱蓬蓬的
鸽子自己似乎也发现了,忙不迭地尖着嘴巴
给对方梳理羽毛,偶尔停下来
眼神汪汪地凝视一会儿。这时我年迈的父母
正坐在客厅的竹椅上,肩挨着肩
有一搭没一搭地念叨着什么。阳光从门楣上方的
窗洞里射出来,沐浴着父亲的光头
和母亲的白发,但他们似乎没有觉察
也没有瞭一眼屋梁上的鸽子
而是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念叨着,目光空落落的……
陀螺之诗
从被鞭子抽打,一只陀螺
越转越快
一只陀螺,越转越快
它跳上桌子
变成了一团光越转越快
一团呼啸的光
带动桌子的海平面
带动我的晕眩越转越快
鞭子消失了,它也不停下来
它呼啸着,吞噬了时间
写另一只蝴蝶
你有绸缎的肌肤,光线画不出的肢体。
你有颤动的茧衣,
以及正午滴落的雪的睡眠。
水与火的缠绵:从绷断的G弦,
闪电劈开石头。从漆黑的雨,到雨后山川。
这一刻,你如此安静。
一件标本,
你风干的身体,藏有多少隐秘的水分。
而更多个你,被我反复梦见。
白昼消失了
夜色多清浅:一片枯叶从纸的深谷升起来。
关于灵魂
物理学家确证:灵魂是不灭的
在高倍显微镜下能清晰看到,灵魂以暗物质的形式
和万物一起
参与宇宙的轮回和运动
一棵生长的树木,一棵迎风的杂草
一个奔跑的人
一头酣睡的猪,一片青绿的叶子,一颗露珠
都有灵魂在驻守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
灵魂都看到了——
它从不开口说出
一棵树伐倒了,一棵草被拔除
一个人停止呼吸
灵魂选择离开,脱离寄宿的生命体
烟雾一样飘散
在宇宙深处,寄宿在新生命上,第二次诞生
我的同事赵兰振因此说:所以一个人活在世上
不能滥用自己的肉体
要爱它,珍惜它,与它和谐相处……
这个年轻时的外科医生,如今也对灵魂之说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