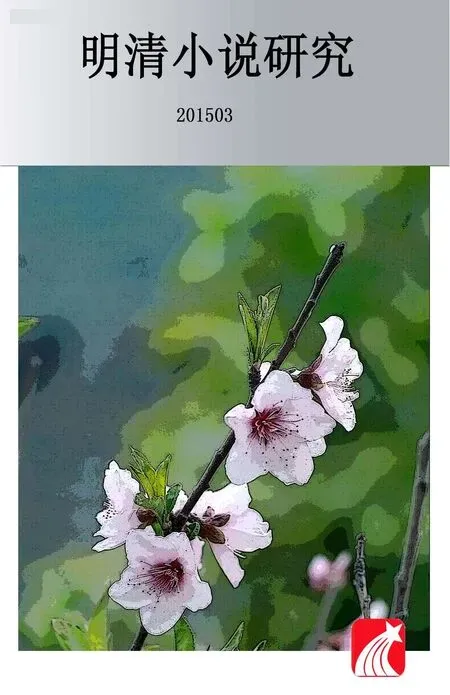论许鸿磐杂剧《三钗梦》对《红楼梦》原著的理解与误解
·郑雅宁·
在清代《红楼梦》剧中,许鸿磐的北杂剧《三钗梦》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在所有《红楼梦》改编戏曲中较有特色,余者多为平庸之作。”《清代杂剧选》并评为:“文不谫陋,且有佳句,足以动人。”限于体例,《三钗梦》并未试图展现《红楼梦》完整故事,而是以晴雯被逐、黛玉之死和宝钗之寡来演绎红楼女儿的青春、婚恋与人生悲剧。作为改编作品,《三钗梦》有着自己独出心裁的创造和剪裁,全剧一本四折,以宝玉的出走和黛、钗、雯三人的升仙、顿悟来揭示人生的虚幻和无常,故名“三钗梦”。
一、《三钗梦》对《红楼梦》精神的理解和演绎
《三钗梦》虽然篇幅短小,但对《红楼梦》精神的理解并不肤浅。原著第五回中《红楼梦曲》所预示的众多女性青春和生命的陨落,在剧中借晴雯、黛玉、宝钗三个人物得到了集中的展现和演绎。剧作者在《三钗梦北曲小序》中写道:“余谓读《红楼梦》,以为悲且恨者,莫如晴雯之逐、黛玉之死、宝钗之寡。”年轻美丽的女性的不幸命运正是《红楼梦》所展示的人生悲剧中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剧中所选的三钗,正是这一群美好而又薄命的女儿们中的代表人物。
在《三钗梦》中,三位“根器最深,遭逢亦苦”的女儿的悲剧命运,首先被理解为因情所困。开场时渺渺真人即云:“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色若不空,孽障无穷。……我想世上,惟情欲一关,最难打破也。”第四折结尾处警幻仙姑又劝告世人:“你道是情根种,哪知道孽债完时,回首也皆空。……世上有情的人呵,须看破,莫把聪明成懵懂。”《红楼梦》曾名“情僧录”,书中以“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字,表现有“情”、多“情”的烦恼。《红楼梦》中核心人物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二尤、香菱的终身之误,晴雯、司棋、芳官、四儿等人的被逐,龄官、五儿痴情愿望的破灭——种种不幸遭际都与各自的情爱纠葛有关。所以,《三钗梦》中将红楼女儿的大悲剧理解为由情引起、为情所困、“情关难破”、“因情生恨”的解读是适当和准确的。
《三钗梦》也时时流露出对世事无常的悲叹,和对人生虚幻的感慨。作者在《三钗梦北曲小序》中写道:“夫晴雯之逐,梦也;黛玉之死,亦梦也;宝钗之先溷尘而后证果,则梦中之又演梦焉!嗟乎!人生如梦耳!余亦在梦中。”剧中第四折宝钗也有唱词云:“世事等空花,人生如梦寐。”这种人生如梦的感慨,与小说原著中流露出的人生幻灭感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在《红楼梦》第一回中,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对顽石所说的一番话,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叹:“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
尤为难得的是,在人物描写上,《三钗梦》没有将宝玉和三钗演绎成一般的才子佳人故事,而是依照原著描写,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人物形象的个性。剧中所塑造的宝钗形象尤其比较符合原著精神。《红楼梦》小说中所刻画的宝钗端庄浑厚,不动声色,从未与黛玉有正面争夺婚姻的举动或言辞。在《三钗梦》中,宝钗这些性格得到了得到了恰当的演绎和保持。作者认识到宝玉宝钗婚姻不幸的本质是父母之命“强配鸾凰”,而非宝钗或他人对宝黛婚姻的故意破坏,这一点高出了其他丑化、妖魔化宝钗形象的同时代剧作。剧中的宝钗有这样的唱词:“我与你姊妹胜亲的,这心事有天知。……心灰,弄的你翠黛销,悲长逝;弄的我玉钗断,恨远离。”剧作家没有简单地将宝钗与黛玉对立起来,而是将她们同样看作爱情婚姻的受害者;也没有改变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又由这种悲剧意识上升到人生无常的哲学感悟,与原著中“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怀金悼玉”的悲剧境界有一定程度的吻合之处。这些解读和见识也远高于同时代的众多同题作品。
二、《三钗梦》对《红楼梦》精神的误解和背离
可是,《三钗梦》尽管在上述的几个方面对原著进行了比较恰当的解读,但剧本对《红楼梦》伟大精神的理解和诠释,毕竟仍有自身的局限。在努力接近和演绎原著精神的同时,仍有许多方面是对原作精神的误解和背离。
首先从视野上说,《红楼梦》中所写的悲剧,固然包含三钗,但三钗乃至更多红楼女性、整个家族、社会的悲剧,背后都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绝非作者笔下这种互不相连的偶然事件所能够解释和涵盖。其次,对人物、人物关系以及《红楼梦》之“梦”的涵义的理解都有与原著有出入甚至出入很大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三钗梦》中没有理清宝黛爱情关系和宝玉与其他女性关系的本质区别。
剧中的宝玉是一个博爱多情的公子哥儿:“惟是性爱温柔,情耽花月。且喜姨表姐薛宝钗、姑表妹林黛玉,皆羞花之貌,咏絮之才。同俺住在这大观园中,时亲芳泽,已属此生之幸。更有侍女晴雯,容貌竟与林妹妹一般。”而黛玉和宝玉之间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知己之爱则完全被忽略或误解。原著中宝玉黛玉的爱情是真挚和专一的,“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黛玉之死与宝玉出家都和婚姻的不自主有相当重要的关系,这一点在剧中也没有得到准确的呈现。虽然剧中借林黛玉之口表明两人“意合情投”、宝玉的“痴性儿只为咱日夜愁”,但宝黛相处、宝玉出家这些场面在剧中都未出现,也没有描写黛玉死后宝玉的反应。所以剧中黛玉对宝玉的爱慕,更像是一厢情愿的痴念。这样的处理表明,作家并没有真正理解、也就无法准确演绎宝黛之间有现代意味的爱情关系和情感追求。
同样的,对宝玉与晴雯之间超越主仆、类似朋友伙伴的追求人格平等的关系,在剧中也没有得到准确的认识和处理。剧中宝玉将黛玉呼作潇湘妃子、将晴雯称作潇湘次妃,这显然是对三人的关系暧昧化、庸俗化理解。将晴雯的死看作是擅宠、邀宠而遭到了嫉妒,因此引发的报复和迫害,无疑更是对晴雯与宝玉纯洁感情的一种歪曲。宝玉对晴雯的敬重、亲昵态度,是人格平等基础上对女儿的仰慕和怜惜,以及长久相处所建立的深厚情谊,这一点在原著宝玉所撰《芙蓉女儿诔》中对晴雯的悲悼中写得很清楚:“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眉黛烟青,昨犹我画;指环玉冷,今倩谁温?……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余衷,默默诉凭冷月。”
宝玉对晴雯的人品有敬仰,对晴雯被冤屈、陷害有愤慨和同情,对与晴雯的朝夕相处有不舍和留恋,对晴雯之死有痛惜和怀念。这种感情,在剧中却被描述成一般的男女情爱:“恨不哭卿哭死,同一搭,并葬在这花根下。化出些连理奇葩,并蒂奇瓜,便天荒地老也难甘罢。”这种缠绵悱恻与原著荡气回肠的情感氛围并不完全相同。
(二)对原著人物性格命运的误解和背离。《三钗梦》中,宝玉、黛玉,包括晴雯身上的诗意人格、叛逆反抗精神没有得到呈现,人物的塑造和描述过于简单化和平庸化。宝玉的形象尤其模糊并且矛盾,一开始以多情公子形象出现的宝玉,对众女儿表现出殷切的亲近芳泽之心,对晴雯的死也表现出沉痛的关怀和悼念,还比较接近小说中的人物;但这样的宝玉,突然没有理由地与宝钗成婚,没有理由地参加乡试,没有理由地遁入空门,这一系列举动之间,看不到任何前因后果。无论联系原著还是抛开原著,人物的行动逻辑都难以自圆其说。
剧中的黛玉虽展现出了命运不自主的痛苦,但也流于简单化和表面化——作者将黛玉凄苦处境理解为:“倒似那倩女魂异地沉浮。再休提的亲娘舅,和那假疼人的外祖母,谁瞅睬俺将死的丫头。”将贾府特定环境、特定人物关系看作造成黛玉悲剧的主要因素,未免肤浅。而黛玉死后立刻飞升的情节,严重消解了黛玉之死这个大悲剧的隆重、庄严、悲凉气氛,显得平淡乏味,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不仅如此,剧中还让黛玉在死后说出“言空色界,位列仙班,好不自在也”、“剪除了魔障也,莫忏悔风流……打破情关可也大撒手……把那些旧恨新愁,都撒在大荒山青埂峰后”这样的话。这些宣扬超脱顿悟的言词,与人物性格不够贴合,更像是作家自我意识的流露。而且升仙后的黛玉形象不但与临死之前所表现出的痴情、伤感、矜持性格相去甚远,而且更加浅薄直露,失掉了黛玉绛珠仙子的优美高洁风姿,相比原著中的描写更是大为逊色。
同样的,剧中对晴雯这个人物的处理,也值得商榷和讨论。晴雯既是三钗之一,并且首先出场,占据《悼梦》一折的篇幅,应是剧中一个重要人物。但剧中却未让晴雯上场,只用宝玉追述的方式来侧面描写人物的容貌、性格和身世,这不能不是一大缺憾;而且剧中宝玉所描述的晴雯,只是一位有着绝色的容貌、悲惨的身世的婢女,却缺少了晴雯身上那鲜明的灵动、情感的火热,以及“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不平之气和刚烈之气,这也是对人物神韵的一种损害。
(三)剧本对“红楼梦”之“梦”理解的简单化和表面化。《红楼梦》原著包括但却不等同于“三钗梦”或众女儿梦,众女儿“梦”也绝不仅仅是黛玉、晴雯的姻缘梦和宝钗的命妇梦。同样《红楼梦》悲剧包括但绝不等同于三钗或众钗之悲,更有家族衰亡之悲、人生无常之悲、美之消逝之悲和人生种种不如意之悲苦等等。正如学者艾秀梅在《日常生活的悲剧与解救——论〈红楼梦〉的悲剧主题》一文所指出的:
“人人不遂心”的《红楼梦》所揭示的绝不是爱情不能自主的时代悲剧,也不是青年男女被封建家长压迫、奴隶被主子摧残的部分人的悲剧,而是一种普世性的悲剧,即人为着类的延续而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接受一般图式安排的悲剧。这一悲剧是跨越一切空间和时间的,因此人们对林黛玉的悲痛并不会因为自己婚姻的自主而减少。更为特别的是,日常生活的悲剧是使所有人都深受其害,但却并无酿成悲剧的特定主体,甚至这一悲剧看起来是一种必要。
而这种普遍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个人对命运的逐渐消亡和磨灭的意志、信念和希望并没有在《三钗梦》中得到传达和表现。不仅如此,《红楼梦》中点明主旨的“好了歌”所表现出的命运无力感、“衰草枯杨”一曲的世事悲凉感以及“字字看来皆是血”的悲天悯人情怀,更远远超出了《三钗梦》所表现出的儿女情爱、哀怨感伤格局。
因此《三钗梦》对《红楼梦》的“梦”的精神的解读始终停留在抽象的“人生如梦”的个体生命体验。虽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但这种理解,在今天看来,也还带着更多时代局限,并且损害了作品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品位。
三、《三钗梦》对《红楼梦》精神误解、背离的根源
任何文学作品都直接或间接体现着作家本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取向。《三钗梦》作为改编作品,对《红楼梦》精神的不理解或误解,首先是两位作者人生处境的巨大差异造成的。
《三钗梦》作者许鸿磐所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他“年十九为诸生,二十三任乡荐,二十五成进士,三十六作县令”,早年仕途比较顺利,“壮年从军,晚而好学,善考据兼能度曲”,是一位标准的学者兼文人士大夫。许鸿磐的身世经历,与补天无路、报国无门、潦倒困顿中度过大半生的罪臣子孙曹雪芹自然完全不同;而他的平凡家世和读书做官的人生道路,也无法与曹雪芹所经历的家族巨变、一败涂地相提并论。故剧作家也无法完全理解小说贯穿始终的愤世嫉俗和叛逆精神,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悲悯情怀。而士大夫立场之下对皇权的不自觉依附,尤不同于潦倒文人对皇权制度某种程度的质疑,这些更决定了《三钗梦》的作者与曹雪芹的价值观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距离和鸿沟。这也使得《三钗梦》无法承载和表现原著精神中对现实的犀利洞察和批判态度。这是《三钗梦》对《红楼梦》精神造成误解的根本原因。
不仅如此,剧本和小说体裁的差异、剧作家与小说作者不同的创作意图也是造成剧本最终背离原著精神的直接原因。
从《三钗梦》的体裁和题材来说,《三钗梦》以杂剧的篇幅,根本无法对巨著《红楼梦》千头万绪的复杂故事进行全面深入的展现;从创作态度来说,对许鸿磐这位经学家出身的士大夫而言,戏曲本是案头消遣之作,是“困顿无聊”时的“破愁之具”,自然也只负责发泄和寄托作家本人的情感。所以剧中亦无意对《红楼梦》原著精神进行更加深刻和完善的解读,而是将原著情节加以剪裁,“自出机杼”,为己所用,借《红楼梦》故事写出自己的人生感慨。根据剧作家的创作意图,他在众多红楼女儿中,选取三钗作为寄托意旨的对象:宝钗、黛玉、晴雯的前世分别为五色神芝、绛珠仙子、芙蓉仙子;且同得神瑛侍者(宝玉)护佑,深有灵性。三钗来到人世,她们空有美貌才华而未受珍重、无法主宰自身命运,分别造成被逐、身死和寡居的悲剧。这与作家所处时代失意士大夫文人的普遍人生轨迹——怀才不遇、才高运蹇、潦倒落魄,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似之处,作者既身处其中,自然既有耳闻目睹,也有亲身经历。许鸿磐中年之后,“缘事落职,嘉庆二十一年捐复知州,补河南禹州知州”,亲历过仕途的沉浮波折。又在《六观楼曲谱六卷》卷首序自述身世:“中年宦走南北,加之遭逢坎壈。玉柱红牙,咸归零落。”他还曾作自传名为《鲁南废人传》,心事可见一斑。因而三钗的悲剧人生能引起剧作家内心的强烈共鸣和演绎冲动,自然也就在剧中的三钗身上,寄寓了自己宦海沉浮的深切感受和慨叹:
(一)晴雯被逐影射士大夫遭际之一——触怒权贵、遭忌放逐。剧中写晴雯被逐是因为身处下层而受到宠爱以致“颇招众忌……怨毒益深”。将晴雯的遭际比作“鸨鸩为灾,兰芝见刈”。这与士大夫文人常常遭遇的因位卑而才高遭忌,被排挤、被迫害的命运如出一辙。屈原的被流放,曹植的被排挤,李白的赐金放还,左思诗中所写的“英俊沉下僚”,孟浩然诗中所写的“不才明主弃”,苏轼一生被数次贬谪、下狱,都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作者自己也曾“罢官后贫无立锥,教读为事”。晴雯的遭遇正是许多有才华、气节的士大夫遭到诬陷迫害的一般身世命运的写照。
(二)黛玉之死影射士大夫遭际之二——怀才不遇、仕途无望。《三钗梦》中所写的黛玉死于婚姻无望、命运不自主,是困于情爱的牺牲品。剧中黛玉的容貌、才华和人品,本来堪配宝玉,但是黛玉家世、性格的不讨喜,逐渐失去了有权主宰她的命运的封建家长们的欢心。然而进一步考量,剧中黛玉对与宝玉的婚姻的憧憬,必须以封建家长的许可为前提,而无法由自己做主;正如文人将仕进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而无法完全取决于自身才华的多寡和品格的高低一样。黛玉拥有美好资质而无法得到婚姻主宰者的青睐,正如文人空有才华而无法得到君主的青睐和官僚体系的接纳一样,同样体现了世间美与才华的被埋没和被毁灭的悲剧,寄托了忠君恋主、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文人士夫们的仕途失意之感。
(三)宝钗之寡影射士大夫遭际之三——随波逐流、中道见弃。剧中将宝钗塑造成一位端庄贤淑、洁身律己的闺秀,并且将她“强配鸾凰”又无辜被弃的命运写得哀婉动人。宝钗的嫁与寡都非本意,然而作为女子,她始终身不由己,且无人关心她的“本意”。宝钗有才学、有见识、有人品,却因为没有感情的婚姻而遭到丈夫的抛弃,落得青灯相伴、孤独终身。儒家纲常之下,君主对臣属正如丈夫对妻子,前者有权任意处置后者。也就是说,文人士大夫亦因依附皇权而随时处在被君主任意处置的地位——而圣意变幻莫测,翻云覆雨,仕进之路往往荣辱沉浮不定,仕进者从来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唯有接受随波逐流、一朝被弃、终被埋没的命运。
“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义”的表现方式,本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正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所说:“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三钗梦》作者许鸿磐,正是以自身的人生经历和感悟为基础,在承袭《红楼梦》原著小说对青春、美丽的生命的痛惜和悲悼的基础上,借三钗的遭逢命运,影射着士大夫被逐、失意和被弃的三种普遍身世遭遇,自觉或不自觉地抒写了自己作为士夫文人的“弃妇逐臣”之叹。这一创作意图也是使得本剧背离《红楼梦》著作精神的主要原因所在。
四、余 论
《三钗梦》对《红楼梦》精神的解读和误解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红楼梦》改编戏曲作品的通病,这是一种普遍的状况。专就清代的《红楼梦》戏曲来说,除《三钗梦》外的其他作品,更是无视原著精神,而借小说的闺阁儿女之态写自己心中陈腐的才子佳人故事,正如许鸿磐所言:“传奇曲文,庸劣无足观者。”因此我们不必苛责某一位古人。纵观中国古代的戏曲作品,其实也从未有完全忠实于某种原著的传统。取材历史者,如《单刀会》《赵氏孤儿》《汉宫秋》等并没有拘泥于正史的描述;取材诗文者,如《桃花人面》《青衫泪》《杜甫游春》之类更是随意捏合人物事迹,以尽情点染敷衍为乐事;取材小说平话者,也未必完全依照原著格局来塑造人物,如《宝剑记》对林冲形象的改造和林冲故事的改写。说到底,戏曲作家的创作往往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是作家精神世界的写照和情感寄托,不一定要对原著亦步亦趋,也无需完全照搬原著的内容或精神。剧情或人物塑造的改造创新有时还会为原著带来更为丰富的审美价值,从而得到艺术品质的提升。
然而《红楼梦》又是一部特殊的经典作品,是一部伟大的、遗留着许多未解之谜的未完成的作品,也是一部无数文人学者力图准确完整地解读的作品,更是一部艺术上臻于完美的杰作,因而对这部作品的改编不能不抱着格外敬畏和谨慎的态度。直至今天,任何改编《红楼梦》的戏曲或影视戏剧作品,无论剧本或场上之作,都应该努力追求对原著精神的尽可能接近的把握和领会,力求将这部伟大作品的精神风貌最大限度地完整准确地传达出来,这才是对经典的尊重、解读和传承的正确态度。所以,包括《三钗梦》在内,对《红楼梦》已有剧作的分析评价之中,也必须有这样的态度——剧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原著精神、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其与原著精神的契合度,这些都应是重要的判断尺度。这个评判尺度应该而且要能够影响到后来的改编者和创作者,以及他们的创作态度和艺术追求。因此,以《三钗梦》为例,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够为今后新的红楼戏曲及《红楼梦》题材影视戏剧改编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借鉴。
注:
①王永宽《清代杂剧简论》,王季思等著《中国古代戏曲论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226-242页。
②③④⑤⑥⑦⑨⑩⑫⑭⑮⑯⑰㉔㉕ 王永宽、杨海中、幺书仪编《清代杂剧选》,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34、334、320、333、334、333、332、323、328、326、328、329、329-330、323、326 页。
⑧⑪⑬[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 3、82、1109-1112页。
⑱艾秀梅《日常生活的悲剧与解救——论〈红楼梦〉的悲剧主题》,《南京师大学报》2005年第5期。
⑲⑳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第二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1491页。
㉑㉘ 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二),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049、1048页。
㉒㉓㉖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7册第543页、第36册第616页、第7册第543页。
㉗[清]陈廷焯原著、屈兴国辑校《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