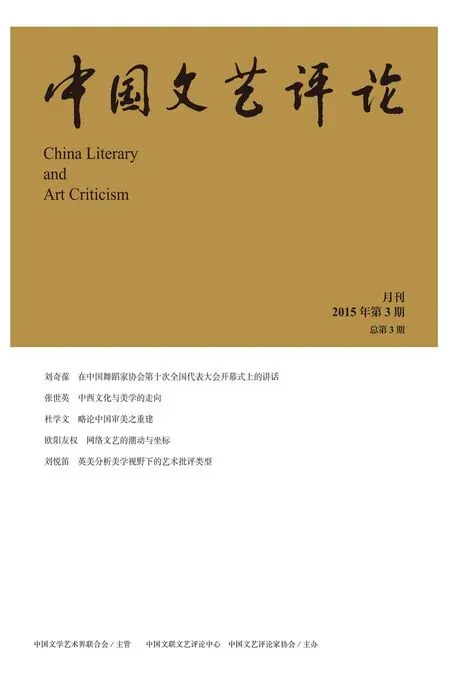论《三体》的人文内涵
刘永春 高强
论《三体》的人文内涵
刘永春 高强
2015年的中国文坛中,刘慈欣《三体》三部曲的获奖及其引发的热烈关注,恐怕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学现象。此次刘慈欣摘得素有“科幻艺术界诺贝尔奖”之誉的雨果奖后,一时间褒扬之词纷至沓来。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读者与批评者对《三体》的总体反应已远远超越了以往的雅俗界线,从更加广泛、阔大的文学语境中对其进行了深入解读。
《三体》现象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学创作成绩的显著提高及其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提升。围绕《三体》三部曲及其评价产生的诸种现象,也预示了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倾向与趋势。作为科幻小说的《三体》在刘慈欣的整体创作中具有哪些突破、其深邃的哲理思考与批判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和总结。其成功经验对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显得弥足珍贵。这也是2015年中国文学留给未来的重要文学遗产之一。
1. 基于科学的超凡幻想
科幻小说,姓“科”、姓“幻”,也姓“小说”,“加了科学味精,漂着五光十色的幻想油花,还撒上文学的胡椒面”。《三体》自然也是如此,不过它的科技细节更充实、幻想更绚烂、小说味道更耐人咀嚼。
科幻小说虽说不必以科学技术为其全部题材和描写对象,更不应该成为科普读物,但有关科学的内容是不可或缺的。科学不是科幻小说的全部,但毫无疑问是其骨架之一。科学技术在《三体》三部曲中随处可见,如理论物理、电磁反射、核爆炸、纳米技术等。而且《三体》里想象出来的未来科学,例如太空天梯、光速飞行器、人体冬眠技术等,尽管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甚至有可能是人类永恒的奢想,却都是在现有科技水平上推导出来的,每一项都有理有据。作者在小说里还不厌其烦地叙写了相关技术的原理、运行方式和影响。作为中国“硬科幻”的代表,《三体》的确在追求科学上的准确和严谨。
在精确的科学技术描写基础上,《三体》展现出了超凡妙绝的想象力,这一点也是最被读者称赞和让人印象深刻的。小说不仅充满各种超前的、高端的科学技术,而且一些非科技层面的想象更令人赞叹。三部曲的第一部《三体》通过三体游戏的方式展现三体世界的模样,在游戏里,作者还将周文王、墨子、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类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科学家汇聚起来,想象奇特,构思别致,韵味深厚。第二部《黑暗森林》则由人类思维的复杂性和三体人思维的透明性,构想出四位“面壁者”和各自“破壁者”之间精彩纷呈的故事。在第三部《死神永生》中,作者基于两条关于宇宙文明的基本假设和“猜疑链”“技术爆炸”的基本概念,独出机杼地构造出“宇宙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科幻小说中,创造出多种奇幻的新技术、新发明并非难事,但创造一个独特的、非技术层面的“宏细节”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而且,此类想象内蕴着作者丰富的人性感悟,尤见功力,发人深思。
2. 反思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在历史上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神话的人神同构,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空前高涨,再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大张旗鼓地反权威、反中心,把上帝赶下神坛乃至公然宣称“上帝死了”,人类的地位越来越高。日益膨胀的自我中心意识导致的负面结果就是人们变得越来越自大,越来越肆无忌惮,“人自以为随着传统人道主义训条的打破和固有理性的摧毁,人们可以凭借自己手中掌握的物质和制度的手段在这个星球上游刃有余,不再生活于奴隶道德的阴影之中了”。现代文明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越走越远,正在走向一个危险的结局。
刘慈欣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是一贯的。早期的中篇小说《人和吞食者》便是以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作为主题。这篇小说并未超越老套的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科幻小说情节模式,但作者的写作重点不是人类与外星人的冲突,而是“人类中心主义”受到挑战,进而被人类抛弃的过程。作者在小说中对于人类的自傲自大给予了无情的嘲讽,譬如对大牙吃人的叙写:“他伸出强壮的大爪,从人群中抓起一个欧洲国家的首脑,从三四米远处优雅地将他扔进嘴里,细细地嚼了起来。不知是出于尊严还是过度的恐惧,那个牺牲品一直没有叫出声,只听到他的骨骼在大牙嘴里裂碎时轻脆的咔嚓声。半分钟后,大牙唆的一声吐出了那人的衣服和鞋子,衣服虽然浸透了血,但几乎完好无损,这时不止一个旁观者联想到了人类嗑瓜子的情形。”这种冷静的笔法与新写实主义小说的“零度叙事”极其相似,并且刘慈欣还使用了“优雅”一词来形容这一“吃人”过程,用嗑瓜子这一平常的动作来比拟这一“吃人”过程,大牙吞掉的似乎真是无生命的食物,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戏谑与反讽的笔调,无情地剥掉了人身上的神圣外衣,暴露了人类的可笑和柔弱。
还有,《三体》中的一个人物叶文洁从人类的疯狂年代走来,目睹了亲人之间的背叛、师生之间的戕害和人性的极端黑暗,对人类之恶进行的理性思考使她陷入了恐惧的深渊:“也许人类和邪恶的关系,就是大洋与飘浮于其上的冰山的关系,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物质组成的巨大水体,冰山之所以被醒目地认出来,只是由于其形态不同而已,而它实质上只不过是这整个巨大水体中极小的一部分……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于人类外来的力量。”于是,她“狠心”地向三体文明发出了求救信号:“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
某种意义上,叶文洁跟五四文学中洞察到中国文明的落后性从而求诸西方文明的启蒙英雄是相似的。他们向我们揭示出了“人类的负面性”,并且“对于人类的负面,普通人并没有高级知识阶层那样全面深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受现代科学和哲学影响较少,对自己所属物种本能的认同感仍占强势地位,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背叛,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但知识精英们不同,他们中相当多的人早已站在人类之外思考问题了。”为了拯救人类,叶文洁只能“站在人类之外思考问题”,于是成了人类的“叛徒”。五四文学中的先驱者们与之相比,不过是站在民族之外来思考问题,然后对民族文化的负面因素有着“全面深刻的认识”,并将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反思。两者的“背叛”对象不同,但立足点是一致的,即都是出于不满足和失望而“反叛”各自的对象,以求改造各自所“反叛”的对象。
鲁迅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叶文洁仰望夜空感叹道:“地球生命真的是宇宙中偶然里的偶然,宇宙是个空荡荡的大宫殿,人类是这宫殿中唯一的一只小蚂蚁。”对于鲁迅而言,中国的封建文明不过是奴役的手段罢了,而对于叶文洁来说,人类的自大和盲目乐观不过是一种无知,如果站在宇宙的高度观察人类,我们只会茫然和战战兢兢。“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同样,若不是叶文洁对于人类的“反叛”,人类哪里会开始自我反思呢?“我们不知道外星文明是什么样子,但知道人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不抱希望……并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此外,《三体》也对线性时间观、对历史确定性有所反思。刘慈欣提醒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偶然,从石器时代到今天都没什么重大变故,真幸运。但既然是幸运,总有结束的一天。”人类费尽气力开发出来的所有高级军事装备,不是被三体世界的一粒小小的探测器毁灭了吗?宇宙要“毁灭你,与你有何相干?”在这个意义上,《三体》对人类文明的解构又与后现代主义宣称的历史的偶然性、人类的悲剧性遥相呼应。没有逃避,不是“思想不具有否定性的软弱无能”,《三体》恰恰确证了批判性思维的价值。因而,《三体》对人类的文化与命运既持批判主义姿态,也持悲观主义立场。在物质化、欲望化、科技化、数字化的复杂格局中,当今世界的文化与文学逐渐缺失了反思人类及其命运、批判现实生活及其无意义本质的能力与深度,《三体》则直面全体人类的鄙陋,向人们宣示着自身的文化缺陷,预示出人类并不乐观的未来命运,小说具有的文化含量和思想力度由此超越了对故事细节、历史背景和具体事件的深入刻画,呈现出全息的宇宙图景、无垠的宇宙时空和沉重的历史批判。
3. 科技的思想钢印
与科幻作品中流行的对科学的丑化和妖魔化相反,刘慈欣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科学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黑暗森林》想象出了可以控制人的思想、让人对某个信息信以为真、进而形成坚固信念的“思想钢印”。刘慈欣对于科学技术的信念也被思想钢印牢牢地确立起来。粗略一看,这种立场有其片面性,与人们的普遍信念有相悖之处,特别是当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环境危害、人也被科技异化之时,人们对科技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和疑虑感。“如今已经十分明显的是,这种对有着唯科学主义头脑的一代人起着严重迷幻作用的思想,不但是在描述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而且是从我们为特定的自然现象所确立的原理中毫无道理地演绎出来的。”刘慈欣对科技导致的异化现象不可能熟视无睹,可对他而言,“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预言科学的灾难”,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在大众中还是一支旷野上的小烛苗,一阵不大的风都能将它吹灭”的国度里,“社会面临的真正灾难是科学精神在大众中的缺失。”刘慈欣对科技抱持乐观的心态,他相信科技的力量。科学对他来说,是一种帮助人类进步和完善人类文明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科技并非简单的盲目崇拜。相反,他对科技的理解、使用和坚持都是在理性的视野下进行,惟其如此,科技才能助推人类进步,帮助人类解决所有问题。
与反科学主义者的立场不同,在刘慈欣的小说里,鲜有对科学技术的负面描写,他坚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针对现实社会中各种由科学技术的不当运用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刘慈欣也将之归因于科学技术水平不够完善,这种看法在《地火》《地球大炮》等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具体到《三体》里,正是因为人类运用科技的力量,才得以与外来文明相抗衡,进而一次次延续地球文明。尽管最后人类还是敌不过科技更加强大的黑暗森林,可人类正是败于科技上的劣势,何况只因程心这个“执剑人”无法割舍的爱而错过了两次挽救世界的机会,否则结局难料。作者创造的那些使人啧啧称奇的发明,连同人类被击败后苍凉悲壮的命运,都体现出了刘慈欣对科学的坚定态度。
科学的力量在于大众对它的理解,这是一句真知灼见。而让科学精神在大众中生根发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与之相比,科幻倒显得微不足道了。本来两者并不矛盾,老一辈的中国科幻人曾满怀希望让科幻成为这项伟大事业的一部分,现在看来这希望是何等的天真。但至少,科幻不应对这项事业造成损害。科学是科幻的母亲,我们真愿意成为她的敌人吗?如果不从负面描写科学,不把她写得可怖可怕就不能吸引读者,那就让我们把手中的笔停下来吧!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有许多别的有趣的事情可做。如果中国科幻真有消失的那一天,作为一个忠诚的老科幻迷,我真诚地祈祷她死得干净些。
在这个宏大叙事解体、科技被妖魔化的时代,刘慈欣逆流而上,坚信科技可以带给人类巨大的“正能量”,并积极守护科技的价值,这种态度十分独特。尤其是,刘慈欣赋予科学以深广的人文精神,将其由冰冷的技术转化为拯救人类命运的福音。这种姿态也是一般“硬科幻”中较为少见的。
4. 吃,还是不吃
刘慈欣曾和江晓原做过一次有趣的对谈,谈话中刘慈欣假设有一天人类将面临巨大的灾难,这时是否可以在人们头脑里植入某种芯片,以便统一思想,更有效地对抗灾难。刘慈欣认为这是可行的,而且必要的。进一步地,刘慈欣指着为他们谈话作记录的女士问道:“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对此,刘慈欣同样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极具争议性的设想和发问。《三体》中的英雄都面临着类似的终极抉择:第一部中从文革创伤走出来的叶文洁对人类失望透顶,发现“人类文明已经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善了”,可是该不该向外星文明发送信号,请求他们的力量来介入?第二部中罗辑在太阳周围布下足以发布三体星系坐标的大量核弹,如果向太空发送咒语,引爆核弹,地球和三体都将毁灭,罗辑想以此为筹码阻止三体人的入侵,问题是这样道德吗?章北海为了保存人类文明,选择“背叛”,以至于要牺牲无辜的战友,怎么评价?在第三部中,程心两次面对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选择,要么选择牺牲一部分人来挽救地球,要么选择所有人和地球同归于尽,选择哪些人去死,自己究竟应不应该导致“死忙面前的不平等”?
刘慈欣经常让笔下的人物置身于这类极其残酷、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中,是即使灭亡也不失去人性,还是为了生存而选择“兽性”?吃,还是不吃?这是一个相当折磨人的问题。
之所以这般残忍,是因为“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往小处说,这是科幻迷们很感兴趣的问题;往大处说,它可能关乎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而且,在刘慈欣的想象中,整个宇宙都遵循两条“宇宙社会学”的公理:“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由此衍生出两个重要概念,即“猜疑链”和“技术爆炸”。前者指永远无法确定两个宇宙文明之间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宇宙文明处于无限延伸的猜疑链。后者指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技术爆炸,从而赶超原先比自己先进的文明,给对方带去威胁,这样又反过来强化了宇宙文明的“猜疑链”。于是,整个宇宙就变成了“黑暗森林”:“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猎人,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是娇嫩的婴儿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还是天神般的男孩,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有人质疑刘慈欣的这番假设完全站不住脚,“因为道德律必须基于主体认知能力及其特定境遇”,拿三体人跟地球人来比较,两者“在思维文化等本质性的差异仍旧无法跨越”,因而“不同生命和文明类型之间连沟通都未曾建立。如此情况下,谈何共同道德。 更何况,假定宇宙间有众多文明,那么‘黑暗森林’状态也必须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所有文明所需要的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形式以及物质、能量是相同的。对于如此辽阔的宇宙来说,这样的假定就显得太没想象力了。”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却也过于苛刻,岂不知,科幻不是为了准确地预测未来,而是提供一个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往往都比较极端——然后围绕这种可能性展开追问和思索。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可能性,作者追问了什么,有何思考。无论如何,“‘思想性’才是科幻的‘灵魂’”,并且“只有科幻作品才有可能呈现反思科学的独特思想性。”同样,也只有科幻作品才有可能反思人类个体与所属种群之间的关系,反思人类道德与科学技术的巨大龃龉。刘慈欣的“残忍”和“极端”不应该成为受到批评的口实,相反恰恰是《三体》受到读者肯定的重要原因。
5. 冷酷的吃人英雄
从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直到后新时期名目繁多的文学样式,英雄主义日渐凋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裹挟下,更多的是不痛不痒的、软性的、轻松的文学,它们使人“作一刻的沉醉,然后随手一去,便完全抛入遗忘里”。虽然少数作家笔下还能见到英雄主义,但对于更多作家来说,不是对于英雄主义“避之唯恐不及”,转而关注庸俗人生的点点滴滴,就是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为英雄的标签,大玩特玩所谓“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醉心于表现世俗情怀和世俗欲望。
刘慈欣无疑对“非英雄化”写作现象感慨颇深,所以他才会说:“现代主流文学进入了嘲弄英雄的时代,正如那句当代名言:‘太阳是一泡屎,月亮是一张擦屁股纸’。”就是在这样一个崇高解体,英雄渐行渐远的时代,刘慈欣“逆流而上”,重新捡拾起被人们遗弃的英雄主义行囊,提供给了我们一群久违的英雄形象。只不过这群英雄和传统的慷慨激昂、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有别,他们少了一些高亢和热血,多了一些冷静和残忍。残忍跟英雄竟然联系在一起,并且在这个人们对英雄主义多少有些冷漠的时代,这样的英雄却赢得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个中三昧,值得玩味。
《三体》里那些遭遇“你会把你妈卖给妓院吗”之类的终极问题,并最终做出了“大逆不道”的肯定回答的人物,便是作者创造的另类英雄:冷酷英雄。他们包括前面提到的叶文洁、章北海、罗辑,也包括像维德这样的“恶魔”“野心家” “技术狂人”。之所以这些在“吃还是不吃”的情况下令人瞠目地选择了“吃”的人成为了刘慈欣笔下的英雄,是由于“宇宙不是童话”,人类的历史尽管比较幸运——“文明出现以来,人类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未面对过来自人类之外的能在短时间内灭绝全种族的灾难”——但是,这并不等于人类能一直免遭这样的灭顶之灾。于是,当地球面临外星文明的全面入侵时,为保卫我们的文明,必须得吃掉一些人才能挽救地球,“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学是否还要继续嘲笑英雄主义呢?那时高喊人性和人权能救人类吗?”这种情况下,“吃”人的冷酷英雄应运而生。这类英雄不能用单纯的道德准则去评判,“比较理智和公平的作法,是将英雄主义与道义区分开来,只将它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品质,一种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严锋称其为“超英雄”,他们的抉择关乎的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地球,而是整个宇宙。“成为英雄甚至不是他们的本意,关键在于他们偶然被卷入世界的危机,危机背后是宇宙的逻辑。当宇宙在他们面前徐徐展开,人类一下子显得那么渺小,他们的悲欢离合那么地微不足道”。这类人物是科幻文学甚至主流文学中难得一见的,刘慈欣的《三体》提供了一个场域和维度,让文学的目光再次宽阔起来。
另外,在刘慈欣看来,英雄其实是一个相当不稳固的概念,曾经的英雄可能会莫名其妙衍变为全民公敌,反之亦然。例如在《地火》中,“我”设计了全新的煤矿开采方案,以便助推人类的发展,却招致了地火的焚烧。“我”为了赎罪,最终葬身火海。然而过了若干个世纪,“我”的设计方案终获成功,“我”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英雄”,但“我”已葬身火海,无福享受“英雄”的赞誉了。所谓的“英雄”名号,更像是一种嘲弄。而在《三体》中,我们看到更多的英雄被人视为疯子、魔鬼,不能为民众所理解,更有甚者,他们不过是权势者手中的砝码,一旦失去价值便被一脚踢开。这跟五四文化启蒙英雄,尤其是鲁迅笔下不被庸众理解的先知先觉者何其相似。
比如罗辑,他在公众眼中的形象由一个救世主渐渐变成普通人,然后变成大骗子。虽然还保留着“面壁者”的身份,但他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了。最后,居民们甚至以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为由,将罗辑驱逐出小区。当他把执剑人的掌控权交给程心时,人类不感谢罗辑,反而指控他犯有世界灭绝罪,打算逮捕他。这样的例子三体里可谓多矣,除罗辑之外三个“面壁者”均不得好报,还有章北海、维德等等都有相似的遭遇。
在鲁迅那里,发现传统文化“吃人”真相的狂人就被人们视为“疯子”,在所谓“正常人”的谩骂、囚禁中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无可奈何之下又去“候补”。替大众谋求解放的夏瑜在人们看来却是“发了疯了”,他流的血被愚昧的人们拿去治病。文化启蒙英雄,要么最后妥协了,要么到死也不被群众理解。如此相似的结果赋予了鲁迅和刘慈欣笔下的英雄们以深沉的悲凉感。
第三部中,泰勒脑海里不时回想着一位即将出击的神风队员写给母亲的遗书上的一句话:“妈妈,我将变成一只萤火虫”。不谋而合的,卡莱尔也将英雄比作萤火虫,“里希特尔说:苏门塔腊岛有一种‘发光的金龟子’,即大萤火虫,人们用叉子把它们串起来,用作夜间行路的照明。有身份的人很喜欢借这种令人愉快的光亮旅游。伟大的荣誉应归于这些萤火虫。但是——!”是啊,但是……人类只记住了这些先驱者作为“萤火虫”的实际作用,却忘记了人类对他们的误解与亏欠。《三体》中的英雄们就是现实世界中那些勇敢献身却不被理解者的最好注解。
6. 结语
2015年,中国文学创作总体上获得丰收,一大批作品获得一般读者、专业批评家甚至世界图书市场的认可。其中呈现出来的总体趋势是,读者与市场不再单纯关注作品的题材,以往的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继续受到关注的同时,一些艺术质量较高、充满探索意识的作品获得了读者与市场的双重认可,也正是随着这些作品艺术质量的提升,中国文学创作在世界市场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与美誉。《三体》展现出来的批判性、反思性和人文关怀与2015年众多引起较大关注的文学作品相比,丝毫不落下风。其对于理想主义的坚执,对于英雄主义的礼赞,对于人类乃至宇宙之终极问题的思考,在当前的中国文学创作中实属难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三体》视作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当今社会的文学接受环境正在变化,文学之外的判断因素正在减少,读者对文学作品艺术质量的期待正在逐渐增加。中国文学未来必将沿着艺术质量提高的方向越走越远,其核心问题则是如何进行叙事创新、如何贴近读者、如何走向世界。刘慈欣有言:“主流文学描写上帝已经创造的世界,科幻文学则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再描写它。”在《三体》中,刘慈欣创造了一个令人震撼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空灵、大气、深邃,值得深入探究,因为其中不仅仅包藏着丰富的技术细节和磅礴的想象力,还蕴涵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久违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以及深刻的思想质地。
注释
[1] 叶永烈语,转引自孔庆东:《中国科幻小说概说》,《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9卷第3期,第37页。
[2] 刘珍珍:《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刘慈欣科幻小说研究》(硕士论文),复旦大学2009年,第10、22页。
[3] 刘慈欣《人和吞食者》,载《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集》,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第290页。
[4][5][6][8][10][11][19] 刘慈欣:《三体Ⅰ:“地球往事”三部曲之一》,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 第40、205、205、130、240、12、300页。
[7]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9] 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12][20][21] 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381、441、447页。
[13]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9页。
[14][18] 刘慈欣、江晓原:《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新发现》2007年第11期,第89、86页。
[15] [奥]F·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
[16][17][25][27][28][29][32] 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科普研究》2011年第6卷第3期,第68、69、67、68、68、68、64页。
[22] 陈新榜,王瑶,林品:《评刘慈欣科幻系列《三体》,《北大评刊》,2011年第3期,第105页。
[23] 江晓原:《思想性才是科幻的灵魂》,《中华读书报》2015年8月19日。
[24] 叶维廉:《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叶维廉文集》第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00页。
[30] 严锋:《创世与灭寂》,《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第74、75-76页。
[26] 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31] [英]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张自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19页。
刘永春: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高 强: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史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