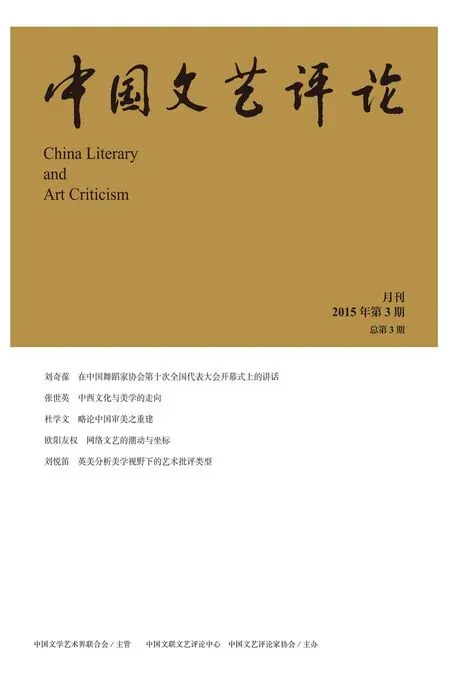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道观”的当代价值
余开亮
中国古代“文道观”的当代价值
余开亮
“文道”关系曾经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随着现代性美学体系的确立,“文”开始挣脱“道”的约束走向了独立发展之路。在反思现代性、面向全球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学术视野下,如何重新激活一些古典命题,使其发挥新的理论活力也渐趋成为学界关注重点。由于古典的“文道观”主要有文质与体用两种结合模式,故要重拾“文道观”首先要对“文道”关系的两大模式进行理论澄清,然后根据时代的变化再造其理论效应。
文道与文质
“孔子首倡‘文质彬彬’的道德人格说,其间隐伏着一个文、道关系的潜结构,开启了中国美学之文、道关系问题的文脉之门。”《论语•雍也》载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可见在孔子那里,“质”具体指的是一个人内在具有的正直、好义的道德品质,为仁善之质。“文”在孔子那里既指人文典籍(“博学于文”),又指包括礼乐在内的人文教养(“文之以礼乐”)。所以,“文”指的是人因学习或礼乐教化而具备的外在文饰,为审美之文。孔子道德人格上的“文质彬彬”和其音乐理论上的“尽美尽善”是一致的。文即形式之美,质即内容之善。孔子追求的审美理想是文质兼备、美善合一。
文质对“文道”关系的隐伏,昭示了后世儒者从“文质模式”来看待“文道”关系的基本思路。从先秦荀子、汉代扬雄到西晋挚虞无不遵循这种思路在论述“文道”关系。具体到唐宋文论,虽然提出了明道、贯道、载道、文与道俱、作文害道等错综复杂的内涵,但其在思维方式上,都侧重于以文辞形式(文)与道德内容(质)来言说“文道”关系。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儒家的“文道”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就一般而言,“文道”关系往往呈现为两种结合模式。其一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体用一源的结合模式,这是一种文本论。在这种结合模式中,“文”指的是包括形式与内容在内的整个文章,而“道”指的是形而上之道。在此模式中,道乃文之本,文与道一为形下一为形上,二者并不位于同一层面。其二为文与质的结合模式,这是一种作品论。在这种结合模式中,“文”指的文章之中的文辞形式,“道”指的是文章之中的道德内容。在此模式中,道乃文之实,文与道都是指向整个文章的,二者位于同一层面。由于古代文论语言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不但造成了不同理论间“表同实异”或“表异实同”的理论格局,也造成了后人因混淆了这两种结合模式而出现的评价上的褒贬不一。
事实上,虽然唐宋文论家谈“文道”关系时也有混淆“文道”关系两种结合模式的倾向,但他们的“文道”观主要谈论的还是文辞形式与道德内容的关系,其差别则在于对文、道的偏重,或文辞形式与道德内容互重、或重道德内容轻文辞形式、或重文辞形式轻道德内容。“文道观”从“文质模式”来说,意味着“文道”之文指的并不是整个文章,而仅仅是文章的外在形式;同时,“文道”之道指的也非文章之外的道,而是蕴含在文章之中的思想内容。从文学风格而言,有文而无道,是形式主义,以齐梁间“永明体”为代表;有道而无文,是实用功利主义,其文章谈不上是文学作品,以程颐“作文害道”说为代表;文道合一,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为古代儒家“文道”观主流。
唐宋“文道观”以韩愈的“文以明道”与周敦颐的“文以载道”最有代表性。韩愈“文以明道”观的提出直接针对的是兴于魏晋南北朝并延续于唐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试图通过古文(形式)运动来恢复儒家道统(内容)。韩愈说:“修其辞以明其道。”这里,“修辞”显然不是指整个文章之文,而是指文辞形式。“明道”是与“修辞”在同一个层面被提出来的,二者共同的指向对象是“其”,即整个文章。这就表明,韩愈的“明道”指的是文章内的道,即与文辞相对应的道德内容。事实上,“道”在韩愈那里,基本上都是一种以仁义为定名、以道德为虚位的具有现实具体性的辅时及物之道。所以,韩愈的“文以明道”讲的是“修辞以阐明道”而非“修辞以显现道”,因为本体论之“道”的显现仅靠“修辞”是无法达成的。显然,这是一个关于作品文质论的命题。韩愈谈论“文道”关系的很多观点都是把文辞与道放在同一层面对待提出的,如“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等。在《答尉迟生书》中,韩愈还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有诸其中”“慎其实”“本深”“行峻”“心醇”说的都是整个文章里的思想内容或者作者所应涵养的道德意志与行为。作者的道德气象发为文章,则形成文章内在充实的思想情感。韩愈在这里谈的依然是文章不应只着意于文辞的曼妙,而要具有符合儒家观念的道德内容。只有这样,文章才能不让人耽情于形式美感而有助于德性的充实。韩愈在《答窦秀才书》中曾反思自己的文学之路:“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学不得其术,凡所辛苦而仅有之者,皆符于空言而不适于实用,又重以自废。”“皆符于空言而不适于实用”,鲜明地表明了韩愈对形式主义的反思和“文以明道”的儒家教化理想。
宋人继唐韩愈、柳宗元等人之后,对“文道”关系进行了更丰富的探讨。文学家、理学家、政治家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文道观”。其中,算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对后世影响最大。《通书•文辞》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周敦颐把文辞之艺比喻为大车,而道德之实比喻为车上所载的货物。在他看来,一辆不能载实物的大车即使再美也只能是摆设。显然,周敦颐也是从文辞与道德的对待性或者“文质模式”来谈“文道”关系的。有学者曾着意阐释周敦颐的“文以载道”与韩愈的“文以明道”观的区别。这种区别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根本而言,也是反对那种“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的形式主义文风,而主张一种“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的“既艺又实”、“既文又质”的“美爱”之文。可见,虽然韩愈与周敦颐的“文道”观表述不一,但二者并无根本性区别,他们都属于持文质兼备的古代儒家主流“文道合一”观。
文道与体用
前面提及,“文道”关系实际存在体用与文质两种结合模式。虽然儒家的主流“文道观”体现为文质结合模式,但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文道”观就不存在体用结合模式。在道家“文道观”和非占据主流的儒家“文道观”中,体用结合模式的“文道”关系依然大量存在。它与儒家主流“文质模式”的“文道观”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文道观”的丰富景观。作为体用结合模式的“文道观”,其“文”指的是包括形式与内容在一起的整个文章,为形而下之文,其“道”指的是文章的根据与本体,是形而上之道。
文道的体用关系可追溯到老庄和《周易》关于道及其显现方式的哲学理论。在老庄哲学那里,道境作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形态,是无法用逻辑语言来说明的。但为了传道,又不得不对道进行言说。对老子而言,道作为形而上的实存者,创生万物又蕴含在万物之中并构成了万物的本体,为一种“大象”和“无状之状”;这样,道这个形而上的难以捉摸的恍惚之物就隐匿、同时又显现于天地万物的整体形象之中。所以,要想体悟道的真实存在性,人必须深入到物象的本质性领域。对庄子而言,他采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诗化语言来对道进行言说。虽然庄子最终要人“得意而忘言”以“一超直入”道境,但毕竟其保留了诗化语言开显道境的可能性。不论是老子的“象”还是庄子的诗化语言,都为后世的体用“文道观”埋下了伏笔。在《周易》那里,天地人生之道也是妙不可言、不可测度的,那它如何能被传达出来而开启人的心智?《易传》也抓住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一种独特的道之开显方式:立象以尽意。一般的逻辑语言往往被引向意识活动之对象和客观性一端,而无法达成对全体之境的知解。《易传》清醒地认识到了言的这种局限性和遮蔽性:“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传上》)既然日常逻辑语言无法尽意,《易传》于是提出了尽意的另一种方式:“圣人立象以尽意。”易象可以尽意、尽道的解决方案也直接为后世通过文艺意象来彰显道境做了铺垫。中国文人的审美精神恰是要通过对物象、意象(包括山水、人体、艺术品等)“澄怀味象”的审美直观,超越于物象、意象本身而去追寻一种“生于象外”的形而上的审美境界,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随着文艺活动的自觉,用诗化的“文”来彰显道境和真理的思路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审美形而上学。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惟性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的道虽是儒家之道与自然之道的融合,其“文道观”也存在杂糅“文质模式”与“体用模式”的矛盾之处,但其《原道》篇的主要立足处是文与道的体用关系。刘勰不但提出了天文与道的开显关系,而且也提出了人文与道的开显关系,由此将文学之“文”提升到了宇宙论高度。这种体用层次的“文道”观在古代文艺中多有体现。宗炳《画山水序》云:“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像 ……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这是说绘画;《世说新语•容止》载桓温称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这是说音乐;唐《李冰阳上采访李大夫论古篆书》云:“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矣。”这是说书法;谢灵运《石壁立招提精舍》云:“绝溜飞庭前,高林映窗里。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这是说建筑。晋蔡洪《围棋赋》云:“秉二仪之极要,握众巧之至权。若八卦之初兆,逐消息乎天文。”这是说棋艺。
就儒家“文道观”而言,到了朱熹那里,也开始较为明确地把“文道”关系沿着“体用模式”来展开。朱熹在《读唐志》一文中明确以本与实来区别三类文体:道乃文之本(体用结合的“文道观”)为圣贤之文;道乃文之实(文质结合的“文道观”)为司马迁等人之文;无本无实之文(形式主义文风)为宋玉等人之文。可见,朱熹对“文道”的两种结合模式有着清醒的认识。朱熹批判与修正了唐宋古文学家或理学前贤以“文质模式”来谈“文道”关系的思路,而把“文道”关系上升到了体用或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层面。“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在朱熹那里,道已经不再局限于功利性的具体社会伦理、政治之道,而是超越性的天地之道,是形而上的本体范畴。理学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在于他们把汉唐儒者的事功哲学自觉转化为一种心性哲学。由此,理学家对儒家之道的注重也不仅限于“上明三纲”“下达五常”,而是把儒家之道以天理的方式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同时,宋儒深入地阐述了儒家天理与“生”的关系,使得儒家之道具有了审美气象。“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鸢飞鱼跃”“赞天地之化育”“生意”“生理”“活泼泼地”等理学观都表明了理学家自觉地把现实性的道德伦理之道提升为一种宇宙之道而进入一种本体境界。“道之显者谓之文。”因此,“文”乃“道”所生,是天理的自然显现。朱熹批评了韩愈门人李汉的“文以贯道”说,提出了“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观点。朱熹还批评了欧阳修的“文与道俱”说,认为这种观点依然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在朱熹看来,不管是“文以贯道”还是“文与道俱”,其根本问题都在于把文与道看成了两个不同事物,而事实上“文便是道”。朱熹对上述观点的批驳在很多学者看来是充满矛盾并有些站不住脚的。确实,就“文质模式”来说,文与道虽然可以合一,但他们本身就是两个不同事物,于此立论,“文以贯道”与“文与道俱”本无可厚非。但如果站在“体用模式”来说的话,朱熹的批驳就还是有道理可循的。按照朱熹的哲学体系,道或理为形而上者、为体,而天地万物为形而下者、为用。天地万物的存在是因为都禀受了理,是谓“理一分殊”。“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虽然万物不同,但其之所以存在就在于有那个“浑沦无缺失”之理。也就是说,万物不能离开理,因为它与理在根本上就是一个东西。所以,从体用关系而言,万物就是理。把“理一分殊”的体用哲理放到“文道观”上,也必然得出“文便是道”的结论。
古代“文道观”在当代文艺中的激活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古代“文道观”的两种结合模式表述了文艺理论上的两大问题。“文质模式”的“文道”观说的是文艺作品中文艺形式与文艺内容的关系问题,而“体用模式”的“文道”观说的是文艺应该如何存在的问题。前者属于文艺作品论,后者属于文艺本体论,二者实在不能混同为一,否则不但会增添很多理论困扰而且无助于发挥其对当今文艺的理论指导效应。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就说:“形上和实用理论批评家都谈论文学与‘道’的关系,可是前者认为文学是‘道’的显示,而后者认为文学是宣扬‘道’的工具;至于‘道乃宇宙原理’的形上概念,与‘道乃道德’的实用概念这两者之间的不同,那就更不用说了。”虽然笔者不同意刘若愚把儒家主流的“文道”观看成是文学成为宣扬道的工具的实用理论,但其对文学与“道”的关系所进行的两种区分是极有见地的。把古代“文道观”从两种结合模式来进行区分并分别评价,有助于今天的文艺评论重新从古典美学中获得有效的理论资源。
今天的文艺创作处于一种多元化时期,有着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本身是时代进步的体现。就“文质模式”的“文道观”而言,对其理论评价应放置在总评和分评两个角度展开。从总体概评上说,讲究文质统一的“文道”观是具有很大的理论局限性的。首先,今天的文艺创作不一定必然要求有文有质,文质统一,如当今的文艺创作既包容了只注重“文”的形式主义艺术,也包容了只注重“质”的观念艺术和现成品艺术。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使文艺作品一定要有思想内容,但也不仅仅是儒家所说的那种道德性内容。显然,把“文道合一”定为唯一许可的文艺观,既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也不符合艺术内容的多样性实际。但是,如果从部分评价上说,作为文艺创作多元性中的一种,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文艺作品在当今又还是占据作品主流并最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因而又值得大书特书。同样,作为文艺作品创作多元化的一部分,要求文艺作品承载道德内容也体现了文艺作品关怀人性、关注现实的品格。就此而言,“文质模式”的“文道”观依然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事实上,当今的艺术哲学恰恰对艺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重新焕发了新的理论兴趣,这种理论兴趣是基于如何让艺术走出自律性胡同而重新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的反思而出现的。由此看来,儒家注重道德内容的“文道观”也许面临着再次激活的理论空间。
今天要重新激活“文质模式”的“文道观”,意味着在文艺创作领域继续倡导一种言之有物、承载现实道德内容的文风。当然,时代变了,艺术的形式与道德内容的内涵也在变化。一方面,文艺创作要不断进行文艺新形式的探索,以使文艺形式符合新时代大众的审美需要;另一方面,又要不断的扩展与更新艺术的道德内容。既要弘扬古代优秀传统道德如仁义、孝悌、礼让、诚信、公廉等,又要关注新时代的国计民生、生态环保、公平正义、和平友善等道德新目。注重道德价值传达的文艺观,主张文艺应用自身的艺术形式去切近务实、关注民生、止恶扬善、讴歌人性、化育道德等。这恰是文艺应当具有的一种责任担当。
当然,倡导一种具有道德内容的文艺观,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我们不能说只要具有道德内容的文艺作品就是好作品。很多人对古代儒家主流“文道观”的一大误解就是将之视为一种文艺或审美功利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在儒家那里,善就是美,文艺成为了道德与政治的工具,使得文艺自身失去了独立的存在性。儒家“文道观”理论庞杂,审美功利主义可以被用来评价重道轻文、“作文害道”等“文道观”,但用其来评价儒家主流的“文道观”就有失公允。按照现代西方艺术哲学的讲法,前者属于激进的道德论(radical moralism),后者则属于温和的道德论(moderate moralism)。审美功利主义或激进的道德论随意剪裁“文”以适应“道”的需要,使“文”成为了“道”的一种工具。从文质关系来说,审美功利主义表现为“质胜文”或“以质害文”。“质胜文则野”,孔子就明确地反对过这种粗鄙的审美功利主义。可见,讲究文质统一的“文道”观或温和的道德论并非把形式看作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要实现其与道德内容恰到好处地内在结合。第二,同样实现了文质合一的文艺作品,我们不能因某个作品中的道德内容高大上,就说这个作品一定要更优秀。区分何种作品更优秀的标准在于是否这种道德内容能转化为审美体验。也就是说,一个作品中道德内容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说了什么,而在于它的存在是否提升了文艺作品的整体艺术价值。有些文艺作品之所以伟大,恰恰可能是因为它倡导的道德价值观念打动了人心,促进了读者对整个作品审美体验的深化。所以,文艺作品优秀与否,关键要看其中的道德内容能否转化为感染人、打动人的审美力量。第三,我们不能说文艺作品就不能呈现非道德的内容。事实上,像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这样的作品,给人揭示了一种恋童癖的不伦之爱。而正是作品呈现在道德层面的罪恶给这部作品带来了极高的艺术评价。其实,这种作品中的不道德性的呈现与莱妮•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中那种大肆为暴力鼓吹呐喊并不相同,后者引发的道德反应是令人愤怒的,而前者引发的道德反应则并不与读者的道德感相悖,其作品表面上看起来的不道德属性恰恰揭示了人性在一定情境下的道德困境。也就是说,一部好的作品虽然具有不道德的内容,但它导向的并不是不道德本身,反而激发受众去反思这种不道德行为,其最终依然是道德的。所以,《洛丽塔》中的道德价值并不是作品表面可见的道德罪恶,而是对这种道德罪恶所呈现的人性道德反思,其表面的不道德恰恰反衬出的是道德性的内容。
古代“体用模式”的“文道观”对文艺本质的一个定位就是文艺应该显现道。虽然古代哲学对“道”有着儒家之天理、道家之自然、禅宗之性空等多重理解,但这种“道”都不是具体性的现实之道而是形而上的超越性之道。古人的“道”更多都体现为生命的精神境界之道。古人最高的文艺和人生理想正是通过文艺作品去追求一种“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虚灵境界,去趋于一种形而上的对宇宙和生命的深情领悟。它通过“文”之秩序和节奏,化入宇宙大化生机之中,通过构图、布局、显隐、开合、有无、节奏、旋律等文艺空间,通过气韵生动、色相变幻等文艺时间,通过所感所思的生命情怀展现着人生的道境,从而“赞天地之化育”,“上下与天地同流”,领略生命的真谛。所以,从“体用模式”的“文道观”看,古代的文艺并不是为文艺而文艺,而是为了人生而文艺。正是在文艺创作和欣赏中,古人感受到了人生的悲欢情爱、沉着痛快、高蹈飘逸等复杂心绪,从而对生命与人生进行反思,获得一种与道沉浮的生命真理。
今天继续弘扬这种文艺本质观,就是要让文艺不局限于经验世界的束缚,不受制于形式主义的技巧、感官主义的享受、商业主义的炒作,而重新回归对生命存在与生命精神的关注。虽然,形式主义、感官主义、商业主义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事有主次文有本末,一味地主次颠序、离本纵末最终导致的将会是文艺自身的边缘化。为此,当代文艺家应敏锐地领悟古典宇宙之道在今天的新变化,站在生命存在的时代境域高度去关怀人的精神需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艺术家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修养与生命底蕴,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去呈现个体与人类生命的时代性存在境域。生命存在境域的问题是一个亘古长青的人生问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人生际遇,文艺就是要通过自身的独特形态去呈现时代的生命之思。唯有如此,文艺才能突破经验世界的格局,生发“道进乎技”、“境生于象外”的生命本体价值,给人的精神世界提供终极性关怀。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时下的中国,缺失的正是关注社会现实、关注精神世界的好文艺作品。古今相似的是,古代“文道观”的提出针对的恰是这一类似问题。也许,古代“文道观”重新履行使命的时机到了。
注释
[1] 王振复:《中国美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2] 尤以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对 “贯道”与“载道”的区分影响最大,见《郭绍虞说文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4][5][6][7]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70页、第1527页、第1500页、第1462页、第1639页。
[8] 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5-36页。
[9] 刘真伦:《从明道到载道——论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的变迁》,《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
[10]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页。
[11][13] 于民主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第214页。
[12]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39页。
[14] 严可均辑:《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62页。
[15][1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页、第110页。
[17][18][1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05页、第3319页、第2409页。
[20]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21] 余开亮:《孔子论“美“及相关美学问题的澄清》,《孔子研究》2012年第5期。
[22] 卡罗尔:《超越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68-488页。
余开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韩宵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