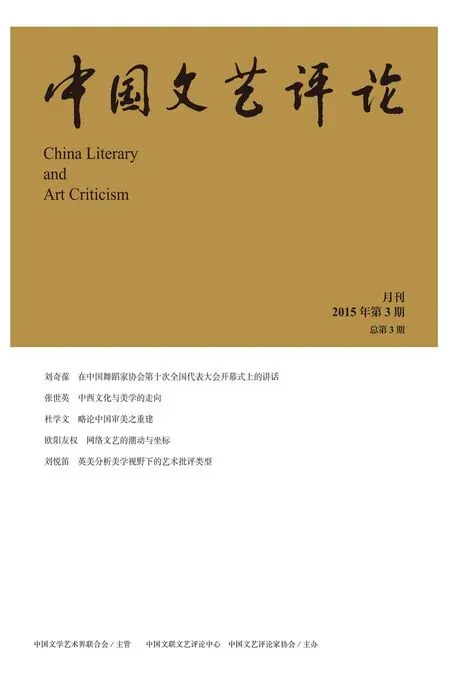从“表情”溯源现代戏曲理论之建构
罗丽
青年论坛
从“表情”溯源现代戏曲理论之建构
罗丽
编者按:青年文艺评论家是文艺评论的生力军、先锋队,是文艺评论事业继往开来、发展创新的力量源泉。从本期起,本刊开设“青年论坛”栏目,欢迎广大青年文艺评论家赐稿。
曾有研究者从梅兰芳重视“表情”切入,研究了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京剧精神”(推及戏曲美学精神)的表述,总结出这些不是梅对其表演艺术经验的完整总结,而是受他人影响替他人表述——梅兰芳并不真正理解京剧的美学精神,以此得出“‘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精神’实际上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戏曲美学思想泛西方化、泛斯坦尼化的产物”这样的结论。何谓“表情”?如果说表情是指演员在进行角色创造时的内心体验的话,那么,梅兰芳的表演该不该有“表情”?如果可以,那他是否应该重视这种体验呢?然而,是不是重视了“表情”,以“设身处地”的方法进行角色创造便是受西方戏剧观的影响,便是斯坦尼的体验论呢?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尝试通过对戏曲的“表情”的研究为切入口,重新挖掘“在体验基础上的表现”这一中国戏曲艺术的舞台表演原则,并力图指出在戏曲研究中“泛西方化的理论话语”的问题,实际是研究者对现代戏曲理论体系构建缺乏客观认知,更是研究者缺乏当下戏曲舞台实践的关注所致。
一、戏曲有“表情”吗
有的学者认为,促使梅兰芳对“表情”重视的,是一群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齐如山的充满西方戏剧思维的百十来封信件,冯幼伟对《宇宙锋》充满西方戏剧思维的‘称道’”,这一切“非但没有让梅兰芳意识到建立在西方戏剧摹仿意义上的‘表情’说与中国戏曲艺术的表演观相抵牾,反而更强化了梅兰芳对‘表情’的理解”。
戏曲表演可以有“表情”吗?有的学者的回答是:“从西方戏剧思维所注重的思想层面来加以解读,这自然和中国戏曲艺术更多地关注审美形式因的层面大相径庭。关注思想层面就必然关注其思想产生的环境、情境、即关注戏中的情节故事、人物性格、心理活动,由此,也必然注重表演的心理体验、表现的摹仿性、合理性等一系列戏剧原则,而这一系列西方戏剧的舞台原则是与中国戏曲艺术的非历史本事、非心理体验、非性格塑造的纯粹审美创造的舞台原则相冲突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表述透露出把中国戏曲表演艺术方法的实质与西方戏剧绝对对立起来的信息,即过分强调两者间非此即彼,而忽略了“戏曲艺术方法的实质是再现基础上的表现”,戏曲是情感体验与技术表现并重的,而并非“有技无情”的艺术。
往深一层看,急于把斯坦尼的“体验”与中国戏曲对立,实际也是受到一直以来在戏剧理论界讹传的“三大戏剧体系”的影响,却忽略了这一比较虚妄的实质;而且又以“梅兰芳表演美学”及“京剧精神”的概念片面地覆盖了中国戏曲的理论叙述,无视传统古典戏曲理论中的大量对戏曲表演的“体验”。 事实上,在古典戏曲理论中,有大量关于戏曲演员应该重视角色创造时的舞台体验的论述。明清两代的戏曲理论家李渔、潘之恒、黄旙绰论及表演时,均一再强调内心体验的重要性。因此,及时对戏曲“表情”以及中国戏曲艺术的舞台表演进行理论溯源是迫在眉睫之事。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记》的“声容部”中,有多段关于对演员进行表演训练的论述:“场上之态,不得不由勉强,虽由勉强,却又类乎自然。此演习之功不可少也。”也就是说,演员的表演是以非自然的状态对生活形态的模仿,并以此达到表演的自然,这样一来,便需要演员不断地演练——这既是技术化的体现,同时也需要情感体验。
明代的潘之恒则从“度、思、步、呼、叹”等五个方面讨论演员表演的内部和外部技巧。其中,“度”与“思”讲的是表演艺术内在的心理技术,“步”、“呼”、“叹”三者是对戏曲演员念做外部技巧的要求 。这里的“思”指向表演艺术演员创造角色的心理依据:西施之捧心也,思也,非病也。仙度得之,字字皆出于思。虽有善病者,亦莫能仿佛其捧心之妍。嗟乎!西施之颦于里也,里人颦乎哉!在潘之恒看来,戏曲演员就应该重视角色创造时的舞台体验,演员的一切表演动作都应是内心的流露。
在《梨园原》这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上少有的表演艺术理论专著中,黄旙绰对戏曲表演艺术的心理技术——体验和形态技术——四功五法均有深入的论述。他主张“凡男女角色,既妆何等人,即何等人自居,喜怒哀乐,离合悲欢,皆须出于几衷。”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使看者动情”,产生艺术感染力。戏曲艺术就是通过唱、做、念、打等艺术手段,创造出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为了使表演艺术达到“真如真实在望”的境界,首先要求演员要对其所扮演的角色的内心世界有深切的感情体验。黄旙绰认为,首先必须通过对所扮演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把握,演员才能进一步获得展现人物外部动作的可能。否则,缺乏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深刻了解,必然难以产生真实的感情体验,舞台上的表演何以达到真实感人的效果呢?
从李渔、潘之恒、黄旙绰等人的论述中不难看到,戏曲表演艺术不可能脱离一切表演艺术所共有的基本规律——体验。在中国戏曲这里,体验和技术是不矛盾的。一方面既重视演员技艺的外在表现,注意表演艺术的形态美,另一方面也重视演员对角色的内心体验,并要求演员通过真切的声态、情态、动态将之表现出来。故此,在笔者看来,梅兰芳对“表情”的重视,并非单纯是受到斯坦尼以及西方归来的新派文人的影响。戏曲中本来便有重视“表情”、重视体验的传统。梅兰芳固然并非戏曲美学家,但作为一位出色的表演艺术家,其对戏曲美学的体悟实在不应被全盘否认。正因为有着对传统戏曲美学的深刻体会,梅兰芳才感受到传统戏《宇宙锋》在“表情”上的不完善,才引起他一次次琢磨这出戏的兴致。
大量古典戏曲论著可以证实,早在梅兰芳及众多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戏剧以前,戏曲的表演便把演员塑造角色时的内心体验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对于“表情”的重要性,《梨园原》中“面目板”特别强调到:“凡演之戏,面目须分出喜、怒、哀、乐等状;而面目一板,则一切情状俱难发挥”。可见,黄旙绰实际上已经把面目的“表情”看作是演员表现一切情状的关键所在。那么,戏曲又怎么能少了“表情”与体验呢?如此看来,所谓梅兰芳“重‘表情’是受西方戏剧观念影响”的叙述便难以成立了。如此看来,认为梅兰芳“重‘表情’是受西方戏剧观念影响”的观点便难以成立了。
二、戏曲的体验与技巧
重视“表情”,并不意味着戏曲表演艺术便不需要技巧。正如梅兰芳所说:“对于舞台上的艺术,一向是采取平衡发展的方式,不主张强调出某一部分的特点来的”。事实上,戏曲表演重视对技巧的运用这一点,梅兰芳及多位戏曲理论家从来没有否认过。上文提及的李渔、潘之恒、黄旙绰等戏曲理论家均强调戏曲表演是外在技术与内在体验的结合,而并非只是“纯粹”的技巧运用。
戏曲表演所讲求的“舞台行动的再现”与“舞台动作的表现”结合,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美学里“观物取象”的原则等密不可分。从《周易•系辞传》的“立象以尽意”开始,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都包含着以外部模拟的形式进行内部实质表达的要求。这些原则对我国包括书法、绘画、雕塑、话本、小说、戏曲等在内传统艺术的实践和理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如逼真、肖物、传神等概念都一脉相承。“观物取象”的美学原则,是要求戏曲表演要从生活出发进行人物塑造,取其神摹其形,其中必然包括再现和体验;而戏曲表演的舞台动作,实际上并非写实地逼真地对生活形态的模仿,而是虚拟地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对生活形态的表现。
黄旙绰在《梨园原》中,一方面强调心理技术的重要性,要求演员体验角色的感情“皆须出于几衷”,而“使看者触目动情”;另一方面也对演员在外部形体的表现技艺上,要准确地摹拟角色,做到“传神形似”,“宛若古人一样”。潘之恒在《鸾啸小品》中论述:“故能痴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能写其情”意味着“演员需要懂得唤起自己感情的那种规律”。“能痴”“能情”是先决条件,“能写”则需要通晓舞台艺术的创作规律和演员技巧。
“舞台艺术,是直接靠演员的形体、思想、情感来创造的。”“演员除去他是一个艺术家之外,同时又是角色创造的手段和材料。这里当演员的就必须具有两门本领,一门是具体体验生活的本领,一门是具体表达生活的本领。前者要从生活出发,后者要从技术入手。”斯坦尼演剧体系是典型的写实型演剧体系。演员创造人物时的思维特征是“体验”性思维。斯坦尼强调的是演员和角色完全一样,去体验人物的思想、行为和动作,并一一通过手段体现出来。在创造角色时,演员内部的体验在前,外部的体现在后。体验是心理的,体现是形体的。演员在表演时便与角色合二为一,“忘我”地达到心理和形体、内部和外部的交融。
中国戏曲的表演体系和斯坦尼演剧体系相比,确有不同。首先要“设身处地”,要求演员化为剧中人,按照角色的身份、性格等去进行内心体验。其次要“手为势,镜为影”地进行“对镜自观”的身段设计,要求演员按照戏曲表演程式赋予自身形式化的表现形态。最后,戏曲演员要在演出时达到“有我与无我”“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结合。阿甲在谈到戏曲表演时曾这样说:“体验和表现各以其复杂的形式交织在一起,依表演的需要而出现复杂的转化。有的戏体验多一点,有的戏表现多一点。”
戏曲演员从来就都清醒地意识到:他是在扮演角色,这是一种艺术创作,并非与现实中的情感等同,这便是所谓的“跳进跳出”。潘之恒以“具情痴而为幻、为荡,若莫知其所以然者”论述戏曲表演。这里的“若”字,便道出了戏曲演员在舞台上那种“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的内心创造状态。
就表现的外部手段而言,戏曲演员既通过展示角色在特定情境中的心理内涵以获得戏剧性,又在舞蹈化的表演动作中展现韵律和抽象意味。“通过特殊的表演手段,让这些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动作也具有‘戏感’,也能够让观众感到是在‘看戏’,演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摹仿日常生活中喂鸡和做针线的行为方式,他必须在这种摹仿的基础上超越摹仿,体现出表演性,并且还需要通过这种具有特定表演性的超越,刻意表现出国剧表演与日常生活中的动作之间的不同。”
中西戏剧演剧体系之间存在差异,并不代表两者完全对立。正如前文所述,戏曲表演艺术亦需要体验,而西方戏剧也并非只有斯坦尼体系一种。更何况,上溯古希腊戏剧,下启布莱希特,西方戏剧的表演体系也是多种多样的,此处只是以斯坦尼演剧体系一派作为代表。再者,斯坦尼演剧体系也并非单单只依靠演员的内心体验,而毫不需要外在的表现技术。事实上,中西方演剧体系均需要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只是在程度和表现状态上存在差异。由此可见,把“戏曲重技巧,斯坦尼重体验”推至极致的观点是偏颇的。
而且,在梅兰芳这位杰出表演艺术家的演出中,确实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戏曲体系的许多特点。梅兰芳不愧为中国戏曲表演美学的集大成者,但这并不代表梅兰芳本人的论述便是对中国戏曲表演美学的总结。故在“征引梅兰芳的言谈来论证‘京剧精神’时”确实应该有所鉴别。
三、现代戏曲理论体系的构建
有的研究者不断指出,梅兰芳及众多留洋知识分子是使用西方理论话语去解释古典戏曲的理论问题甚至以此建立戏曲理论体系之时,自己实际也正使用着这样一套泛西方化的理论话语,甚至没有回到古典戏曲理论去解释中国戏曲的表演美学。其问题的症结,实际是在构建现代戏曲理论体系时,没有对古典戏曲理论资源进行充分的现代转换,对西方现代戏剧理论缺乏本土化的对接,更缺乏对现代戏曲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含混不加区分地对待传统的古典戏曲或现当代戏曲剧目,或一切照搬西方文艺理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评价标准观照戏曲等现象都有存在,这都是评论界值得反思和厘清的。张庚建立的中国戏曲研究体系,实际是现代戏剧理论家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戏剧理论,总结现代戏曲实践经验而创建的。
古典戏曲和现当代戏曲虽一脉相承却又绝不完全一致,在戏剧观念和审美形态等诸多方面均已不同。毋庸置疑,中国现当代戏曲理论是在西方戏剧理论的碰撞和交融中形成的,王国维是承前启后、创立现代学科意义上戏曲学的重要人物。他运用考证方法完成了戏曲史学开山之作《宋元戏曲史》,并以“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对戏曲形态作出简练而准确的概括。在理论话语的运用上,王国维明显感觉到古典戏曲理论的文言表达已经与时代提倡的白话文脱离,需要引进“新学语”,创造用现代语言表述的理论。
王骥德的《曲律》和李渔的《闲情偶寄》,是中国古典戏曲的集大成者。王骥德把戏曲看成歌唱的诗并在严格的规范的理论基础上所建立的“曲学”框架。李渔不只把戏曲看成可唱之诗,更把它看成在舞台上演出之戏,建立起了“剧学”的理论框架。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有自己的理论话语,如“本色”“当行”“化工”“意境”“传奇”“机趣”“雅俗”,以及谈及创作时的“立主脑、减头绪、脱窠臼、密针线”,评价作品分“神、妙、能、具”各品等。这些古典戏曲的用语在今天依旧有生命力,但仍需要进行表达上的现代转换才能真正用于现代的戏曲评论。
对于现当代戏曲评论的话语,应努力激活古典戏曲理论中具有传统审美意蕴的用词,例如“机趣”“神、妙、能、具”等。而对于古典戏曲理论与西方戏剧理论中共有的用词,也应仔细分析体会其中的不同,乃至微妙的差异。以“情节”为例。古典戏曲理论中,“情节”多指剧情节奏。明末冯梦龙在《墨憨斋定本传奇》的总评及眉批中,常常提到“情节”,用以指情感运动的节奏,实际上即是指剧情的发展节奏,因为情感运动本身就是剧情发展的动因。冯梦龙主张情节要紧密,“情节关锁,紧密无痕”(《洒雪堂》总评);但情节又不可太直,“传奇情节恶其直遂”(《永团圆》眉批);情节要有头绪呼应,“末折草草一面,殊欠情节,得此折预先领出头绪,末折不费词说矣”(《永团圆》眉批);情节关键处不可草草,“情节大关系处,必不可少”(《酒家佣》眉批);“《看录》是极妙情节,胸中应有许多宛转,自非一曲可草草而尽”(《永团圆》眉批)。
五四运动时期,对西方戏剧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使得“主题”“情节”“戏剧性”“动作性”“冲突”“高潮”“悲剧”“喜剧”“潜台词”“人民性”“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等外来词语进入到现代戏曲理论和评论话语中来,丰富了中国原有的评论话语。但必须清晰地意识到这些新的表述方式背后,存在着戏剧观念及审美差异上内涵和外延的差异,不能把西方戏剧的话语生搬硬套到戏曲评论之中。
而在西方经典戏剧理论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是“第一要素,并且可以说是悲剧的灵魂”。他在《诗学》里提出的这一定义,一向是很多研究者讨论“情节”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称情节是“对一种活动的模仿”,也是“对事件的安排”。被模仿的活动应该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它应有开端、中间和结局。所谓开端,指它本身不因因果必然性由任何事物引起,而是在它之后某些事物自然出现或发生;所谓中间,指它接着某种事物出现,然后另外的事物又接着它发生;而结局则指它接着另外的事物出现,不论是因为必然性还是作为一种规则,但它之后再无事情发生。亚里士多德指出,情节应有“统一性”,它应该模仿一个完整的活动,各部分在结构上融洽一致,如果去掉或替代其中某一部分,整体就会脱节和破坏。他不喜欢插曲式的情节,因为在这样的情节里,行为互相接替而无可能或必然的前后顺序或前后关联。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因果关系是情节的一个基本特征。他认为,作家“应该首先勾划出(情节的)整个轮廓,然后补充插曲并扩展细节”。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知,词语的内涵和外延是与戏剧观念相联系的。因此,评论现当代戏曲作品就不应笼统地用西方的词语来评判,当然也不应生硬地排斥外来词语。
针对时下不少评论者仍然以单一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念来进行戏曲批评等问题,在进行现当代戏曲评论时,更应该彰显古典戏曲美学精神,挖掘古典戏曲理论的生命力,结合新的戏曲实践来阐发古典戏曲理论。评论者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古典戏曲理论是现当代戏曲理论运用和发展的立足点,古典戏曲理论在现当代的艺术实践中仍然具有价值。反过来,对于西方戏剧理论的研究也需要注意,西方戏剧理论风格流派众多,应及时关注外国戏剧的最新发展,对新的趋势和探索,应敏感而宽容,不要只抱着“现实主义”和“斯坦尼演剧体系”不放。
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戏曲在现代转型中的实践并及时进行经验总结,以推动现代戏曲理论以及评论话语的完善。1949年以后,中国戏曲的创作实践发展得很快,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并在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创作上都作出了新的开拓,而随着进入剧场演出后戏曲舞台技术条件和演出方式的变化,又带来现代戏曲在审美原则上的变化。正如有的剧作家所呼唤的那样:“理论发展的缓慢,用既成的历史剧创作概念和标准来评论和评价不断发展着的历史剧创作,自然难免似是而非,捉襟见肘,勉为其难。戏曲历史剧创作需要不断发展,戏曲历史剧理论同样面临时代更新。”
当代戏曲演出实践的巨大变化,单单凭借古典理论和外来理论是无法应对其理论发展需求的,张庚的“剧诗说”、罗怀臻的“传统戏曲现代化”和“地方戏曲都市化”等一批新的现代戏曲理论,正是在新的戏曲艺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此,要看懂戏曲的“表情”,构建现代戏曲理论体系,还应进入剧场、关注舞台,真正“在场”。
注释
[1][2][3][16] 邹元江:《梅兰芳的“表情”与“京剧精神”》,《文艺研究》(北京)2009年第2期,第105页、第99页、第97页、第99页。笔者曾于2010年7月在《南国红豆》上撰文,与邹先生商榷。
[4][10] 张赓,郭汉城:《中国戏曲通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24页、第224页、第228页。
[5] 李渔:《闲情偶寄》(上),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6] 潘志恒著,汪效绮编:《与杨超超评剧五则》,见《潘之恒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又见傅晓航:《戏曲理论史述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
[7][8] 黄旙绰:《梨园原》,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1页、第16页。
[9]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全集》(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
[11] 同[7],第11页,第13页;又见傅晓航:《戏曲理论史述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第229页。
[12] 潘志恒著,汪效绮编:《情痴》,见《潘之恒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又见高宇:《古典戏曲导演学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第175页。
[13] 阿甲:《再论生活的真实和戏曲表演艺术的真实》,李春熹选编:《阿甲戏剧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14] 阿甲:《论中国戏曲导演》,见《戏曲表演规律再探》,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61页。
[15] 傅谨:《中国戏剧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17] 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98页。
[18] 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93页。
[19] 罗怀臻:《怎样看新时期的历史剧创作》,《解放日报》2015年9月23日,第11版。
罗丽: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戏剧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胡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