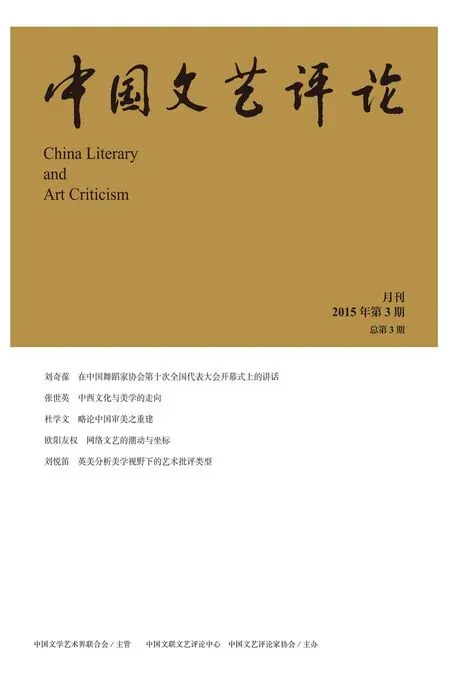《平凡的世界》的“返乡”意义
胡晓军
《平凡的世界》的“返乡”意义
胡晓军
“返乡”的他觉与自觉
观赏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感觉像被一辆老旧却有力的牛车,缓缓地拉上返乡之路。所谓返乡之“乡”,便是记忆、是心灵、是曾有的理想,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还记得和已忘却的。这部电视剧篇幅很长,不仅与小说的容量与风格相对应,而且对应那段漫长难熬的过去、深不见底的记忆以及理想远去的距离。所谓“老旧”,不是指历时太久,而是指社会转型太快、人心变化太大,于是才几十年前的事就已显得老旧了。不过,惟其如此,这段历史反而最有可能被后世提及并关注。所谓“有力”,首先来自该剧的主创阵容,这群“60后”“70后”把回溯记忆、留住美好的希望,变成了能力及作品。由于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等原因,他们十分愿意承担这类任务,用自己的心路历程昭示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反思,从而完成一场“个人史即社会史”或“社会史即个人史”的演绎。据报载的访谈文章,这群“60后”“70后”确有用这部作品去影响“80后”“90后”的意图。在明知“80后”“90后”早已拥有属于他们这一代“心灵鸡汤”的情况下,“60后”“70后”仍在坚持行动,表明他们依然保有强烈的传统价值观、深重的社会使命感。随着观赏的继续,我更发现自己竟从一个坐牛车的人,变成了一个拉牛车的人。我的返乡之愿被唤起,自发地产生了缓慢而坚执的回溯动力。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力量,能让人从不自觉变得自觉、从外观到内省、从过去到未来。我认为该剧对于“60后”“70后”是感动成分大于说服成分,对“80后”“90后”是说服成分大于感动成分。鉴于原著所具有的经典意义,该剧的说服力完全可能漫过“80后”“90后”达到更远的未来。也就是说,若小说《平凡的世界》在几百年后成了与《三国》《水浒》同等量级的作品,那么隔几十年翻拍一次影视剧便是常事、便是一次对经典的致敬与弘扬。同时,也会带来早期影视作品的重播,犹如小说再度畅销那样。旧片重播与原著的再度畅销,都是返乡,只是路途短长而已。
“经典”的特质与特征
经典是时间流逝和时代变迁的产物,它们一般不会在诞生的时代就被认定。比如一部小说问世,就算畅销也不会立即成为经典;若它成了经典,未必畅销——因为属于它的时代必是结束了的、与它同时代的人必然是老去了的。然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它记录的是它的时代中最本质的东西,包括最铭心的思想、最刻骨的情感和最不能被替代的行为,最终指向了本民族甚至全人类在任何时代都不该失去的东西。因此,经典不会仅停留在畅销于一时,而是会长销于万世,书店家庭常备、销售波澜不惊,只在被其他的文艺载体二度演绎时,可能出现畅销的场面。所以,经典应是在“流行”与“非流行”之间,作了至少一次反复之后方能形成的。
我认为,小说《平凡的世界》具有成为经典的特质与特征,因而其返乡的说服力可能覆盖“80后”“90后”以至此后、再后。凡是仔细读小说的读者、认真看电视剧的观众,不论是否有农村生活的经验,都有可能从心底里产生从“坐牛车”到“拉牛车”的转化。这种转化绝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因厌倦了城市生活,便试图重返田园故土以求一片纯净精神家园的认识——说到底,这种认识仍是一段“物觉”的短途,是物质刺激的一种,本质上与用金钱、物质去填补精神虚无,没什么不同。我所说的“转化”,指向发现我们自己作为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传人,即使身上纤尘不染,却在心头永远保有一片抹不去的泥土。对这片泥土,我们也与路遥对待自己笔下的道德与爱情那样,是加以理想化和神圣化了的,包括人生在世要自食其力、努力进取,要孝悌诚信、知足常乐,要穷则思变、实现自身价值……这些道德准则、社会责任、价值标准,植根于农耕社会生长、壮大的中国传统精神,并不因我们进入了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而消除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异。从这意义上说,这片泥土,正是所有中国人的立身之本、养命之根、发展之基。电视剧通过立体的形象,阐发了小说中最经典的思想精髓,将镜头对准了中国人这一片心灵深处,好比提醒忘了时间的人们:“太阳出来了,该起床了”“春节到了,该回家了……”
“现实”的歌颂与批判
在创作理念、方法与风格上,电视剧忠实地弘扬了小说的现实主义,情节典型、性格鲜明、语言生动、细节真实饱满、制作严谨精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在上世纪大力倡导“现实主义”的年代,恰恰是罕有的。这也正是路遥的过人之处。回头看来,只有像路遥那样的极少数作家,才完成或部分完成了真正的现实主义或曰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我认为现实主义的精髓与命脉,主要不在歌颂而在批判,并在批判中树立理想。而在路遥前后的绝大多数文艺作品,多将歌颂掩盖了批判、把现实当做了理想,充其量是偏侧的、不完整的现实主义创作。
在我的记忆中,最后一次接触农村题材的影视剧,似乎是二十多年前的“牛百岁”和“茂富大叔”。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反“左”倡“改”,形式和风格都是轻喜剧。轻喜剧受人欢迎,本身没有问题;但当其成为一段时期中的唯一审美形态时,就有了问题。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秉承了小说中极为珍贵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用平凡的镜头展现出真实的历史,令人再度反思人与意识形态间曾经发生的关系,痛感错误的意识形态不但能毁灭人的道德,且能全方位地泯灭人的发展天性;且当错误的意识形态与邪恶的人性相媾和时,其破坏力是极可怕、极难以收拾的。该剧在描述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穷愁的同时,也与原著一样彰显出虽贫贱而不移的良心、虽困苦却不泯的道德以及其中的优秀者们直接为改变个人命运、间接为改变民族命运而作出的努力、获得的回报。相比之下,作为“近景”的孙少安与田润叶的故事,其表现力虽大,但震撼力较弱。因为门户悬殊的青春爱情悲剧,无论过程还是结局,在任何时代都是相差无几的。
笔者以为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之后,农村题材尤其是70年代的农村题材,可能会出现一拨小小的创作热潮,农村题材也可能迎来一场久旱后的大雨。若真如此,创作者应在演绎贫困、爱情和表现“土”(落后)上把握分寸,在表现理念、人性挖掘和中国式审美上多下功夫,从而尽可能避免同质化创作,特别避免走向当年“现实主义”的反面,即以单纯揭示为目的的庸俗现实主义(自然主义)。
“人学”的现实与现代
路遥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即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这表现在他笔下的道德、爱情还有政治等各方面,在《平凡的世界》中分别对应的人物是孙玉厚、孙少安兄弟和田福军。
这部小说问世后,曾一度遭到受现代主义思潮熏染的文坛的冷遇,特别是一些城市大型文学期刊将其拒之门外。路遥为此愤愤不平,说过“一夜之间,托尔斯泰和曹雪芹好像都成了那批小子的学生”之类情绪性的话。听起来,他在为自己所坚持的理想现实主义及成果鸣不平的同时,似对现代主义有所抵触和排斥。其实不然。路遥此后也接触过现代主义,若是天假以年,难保他不会在他未来的创作中加入相关因子。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只是来自两个阶段,且能并处于此后的所有阶段,并不存在“有你没我”的本质矛盾。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如果说《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弘扬的是人的初级价值,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有意义;那么现代主义拷问的是人的终极价值,包括有意义与无意义。总之,两者都属于“文学即人学”的范畴,一个清醒的作家如果寿命够长,必会觉察到这一点。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说现代主义都是不好的,如同也不能说现实主义都是好的那样。事实上,相信我们迟早会对这种西方人发明的治疗物质极度丰实、精神极度匮乏的“富贵病”的疗剂爱不释手。然而在《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问世时,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坛的流行很可能为时过早,并因此带有不理性、不成熟的弊病。不可否认,现当代中国文坛的主要话语权从来都不在乡下,中国城乡差距之久之大,文坛不可能置身于度外。时光流逝了几十年后,当中国文坛的有识之士对现代主义的精髓感同身受时,他们顿然发现了追求人生理想、社会意义的现实主义与表现人生荒谬、拷问世界存在的现代主义,只要是发自作家艺术家的真心实情,其本质都是对人性的解析与探究,是最初背道而驰、最终汇成圆形的两根线条。于是终于发现,路遥的理想现实主义,其实是越过了他创作生命的天际线,遥遥地指向了现代主义。看来,路遥在有意无意中为我们提示的思考空间,正是将“贫穷”二字从物质的层面推演到了精神的层面。以路遥小说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所着意弘扬的人性之真善美、人生价值与社会理想,这些被西方现代主义所否定了的,正是当代中华民族、中国文艺必须回溯、重启和再创造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通过对小说的改编,提醒我们改变人的命运,必然包括改变人的精神命运。《平凡的世界》“贫而不贱”的理想,正是对目前“贵而不高”的当代人的一种心灵疗剂。
结语
与主创团体年龄相似,我也是一名“60后”,坚信文艺作品有疗治人心、启迪后人、改良社会的功能和作用。唯一需要修正的是,这个功能是有限的,这个作用是“无用之用”的,因为真正的文学艺术,只会令人自愿而行,从来不会迫人而行。于是,令人担忧的事就在面前——如今确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愿读主旋律小说、爱看正能量影视,却只停留在精神慰藉,并未见诸具体行为。在书本和屏幕前,他们往往热泪盈眶;回到现实,他们照常排队加塞、乱扔垃圾、随便骂人。
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可以质问——为什么人人想往高贵但整个社会就是高贵不起来?到底是路遥过于理想还是我们过于现实?是不是当代人早把文艺与生活作为了两件毫不相干的东西?除了质问,具体可做的事情大致有二。一是通过传统和理想现实主义经典的“再生”,引导人们返乡,为曾经的道德和理想感动并惭愧着;二是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乃至多种创作思维、方法和风格相结合的新作,探寻人类走向。我认为后一件事更为重要,因为城镇化的大潮正势不可挡地滚滚向前。路遥早已去世,轮到当代作家艺术家着手创作另一对“孙家兄弟”、另一对“田家兄弟”、另一个田润叶和田晓霞了——当然,不一定非从小说开始,就像不一定非要从传统的、理想的现实主义开始一样。
让我们缓慢而坚执地返乡,好让我们充满理性且不失感性地前行。
注释
[1] 赵振江:《路遥一生活在自己悲壮的梦里》,东方早报,2015年3月4日。
胡晓军:上海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杨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