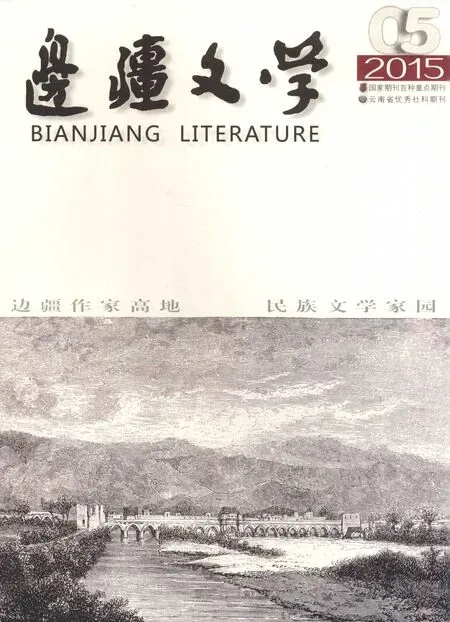光线、灵度与空间
——谈杨璇作品《巴别塔影院之梦》幻象的消遁与停驻
◎和晓梅
光线、灵度与空间——谈杨璇作品《巴别塔影院之梦》幻象的消遁与停驻
◎和晓梅
光线、玻璃、幽暗、透明、水晶、跌落、旋转、消失、停顿、空白……和每一次读完杨璇的诗一样,读完《巴别塔影院之梦》,眼前跃动着太多的词汇,它们内容庞杂,活灵活现,仿佛一些充满生命活力的精灵,相互交织,重叠,或者错开,组合成一个奇妙的立体图形,在一个黑色背景的广袤空间缓慢旋转,将它每一个特殊的角度都呈现在你的眼前。这种阅读经验来自诗集《那个绿头发的女孩》,其间收录有杨璇早期的诗作,这本书从书名来看带有浓郁的青春文学气息,甚至是童话情结,这会将它挡在成人世界庄重文学的视线之外,但是假如有人翻开它,找到一首诗,读下去,你会发现,所有内容,以及内容之下的内容,跟那个翠绿色的封面和封面上那个长绿头发的卡通女孩相去甚远,你会有点搞不明白,书名从何而来。当然,我们都相信,这里面,也许存在一个只属于诗人自己的秘密,也许,什么都不存在。
我吃惊于这个80后纳西族女孩的灵性,我相信上天赋予一个人特殊的灵性一定是别有用心的,当我读完《巴别塔影院之梦》之后,这个想法变得更加坚定。这是一首困难的长诗,困难不仅仅针对于阅读者而言,也同样存在于创作者,险象环生的景象,迷离诡谲的梦境,似曾相识的遭遇以及交替更迭的悬念,构成无数次幻象,仿佛可以抓住,却又瞬间消遁。你犹豫、质疑、反复观望,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和她一起跌落陷阱,在黑暗的漩涡里挣扎,寻找微弱的光。你当然不想这样,但最终,你有点悲哀地发现,你已经这样了,于是你再度进入犹豫、质疑与反复观望中,进入她的另一个圈套,重蹈覆辙。
这个过程中你尝试着站稳阅读者的立场,保持必要的审慎和理性,但你发现这是困难的,我们刚才说了,这是一部困难的长诗,你的阅读艰巨而充满挑战,首先你被置身于光线之中,光线的来源不可追寻,不可探究,它存在于黑暗之上,消失于黑暗之中。正如一场老式电影,当它开演之后,就没有更多的人再去关注那扇透出一束光线的窄小的窗。“晃动的灯火”是最早出现的光,“偶尔一些背影在火光中下到黑暗深处”,幻象开始产生,电影开场前的骚动,因为火光呈现出动态的虚幻感。骚乱平息了,在出奇的静中,一个闪亮的光点在远处突然出现,“你觉得有点像滴落在电影票上的眼泪”,它在扩大。诗的起始处,光线是遥远、模糊和不可触及的,幻象因此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接下来,电影似乎是开始了,但邻家女孩的出现变成一个严重干扰的因素,消解了电影的内容,“你发觉有什么地方在闪光/却不是来自电影屏幕/你留意到有什么在暗暗闪烁/就在你的指尖。”屏幕上跳跃的光亮在作者那里,只是一个不为人理解的巨大幽灵,真正的秘密,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此时的光线,已经非常接近,近到指尖,它促成了幻象的扩大,这是在感觉到黑暗的存在和黑暗的微言大义之后,对光的渴望与追求。“我似围绕着黑暗的太阳爬行了一万亿步/而终于循着黑暗的漩涡升起/重又长出翅膀在光芒中飞翔。”一度保持着低沉、神秘、空虚的光终于回归到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界。这有点像好莱坞大片的结局,尽管落入俗套,却让人心境明亮,幻象伴随着光线的回归而消遁,整个梦境被遗留在那家也许并不存在的巴别塔电影院。
奇思妙想是一部意识流作品的外壳,灵性的思考则是一部意识流作品的核心,虽然说这样的观点适用于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它很难被推翻,但就幻象构筑的作品而言,意义更为深远,因为意识与想象作为一种表达,有着更复杂更纠缠的枝蔓,梳理它们需要足够结实的根基。可以想象,没有这样的灵度空间,一首依靠幻象存在的长诗,将会陷入到故弄玄虚的泥淖中,成为那些只有躯干没有灵魂的作品。“灵魂”是诗歌创作面临的又一座巅峰,尽管塞·约翰逊说过:“诗歌的灵魂在于创新。”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灵魂的问题并非靠创新就能解决,它凌驾在语言,技巧之上,它的存在就是作者本人的存在,是长期思考、阅读经验与生活经验的共同积淀。
杨璇不是那种信手就动笔写诗的诗人,她的诗,每一首都经历一次成熟的思考,这个轨迹清楚而成形,所以她的诗总有成功的表达,既有坚实的根基,充盈的信息,也有向上飞扬的情绪,是厚实、坚韧而丰满的,是有无限多的牵引力的,它牵引你的眼球、心绪和神经,让你在无形中完成一次极其隐秘的哲学拷问。
“你突然记起你并未思考/应走入哪一扇门/你所作出的行动仅仅出于臆想。”丧失方向是人类共同的困境,它出现在命运波折、人生迷茫、人性受到拷问的当口,找寻方向是摆脱迷境的唯一选择,但是终究有多少人能找到正确的通往光明的道路呢?这是一个普遍的困惑,诗人用它引出“人生如一场电影”的主题,用一道道犹如通向迷宫的神秘之门构筑幻象,阐释人生的复杂、多变与不确定。
接下来,诗人继续着她的寻找;“你的眼睛像磁石一样盯着电影的屏幕/可是最终你泄了气一般瘫在椅子上/心中再度涌出/无限个问号/你看不懂其中内容完全/无论画面抑或声音/那电影里的任何东西/你甚至分辨不出屏幕上的色彩/没有一种声音像自然界的声音甚或人类的音乐/无法进入的电影剧情/把你拖入残酷的现实/”无解是更多命运的结局,每一个人,每一种生存状态都具备唯一性,你可以找到相似点,但永远得不到共同的结论,这是人与人之间很难做到真正理解的原因,我们也许认为彼此是熟悉和理解的,但事实上我们永远站立在另外一个人的门外,诗人用这样的方式解释这个世界的陌生感,她说:电影已开始/开始的时间:你生命诞生的时刻/结束的时间:你生命终止的时刻/售票人:你的命运/她说:屏幕上跳跃的光亮只是一个不为人理解的巨大幽灵/我们被活埋了。
看起来,意识的流向并不乐观,然而,大量的幻象开始产生了,从我看到了将我引入某个世界入口的信号,到我开始脱离无边的黑暗,踏入神秘且奇妙的幽径,再到我安详地折叠双翼涌入这流动的透明球体。每一次转换,消失或者逐渐清晰,幻象都呈现出巨大的魔力,它像魔幻作品中一只依靠高科技制作的大鸟,一旦张开巨大翅膀,就张开一片充满灵度的空阔世界。于是:“到处皆是我/我融入你的气息/与你对话。”诗人收束她那放纵的意识,以一个清醒的我,理性的我的形象出现。
到底该如何确定事实,真相与虚妄之间,永远只有一扇门的距离,我们被问题困扰,被幻象困扰,有点想发疯的感觉,幸运的是,这个清醒的我及时挽留了我们,也许好的诗,最终都能实现某种程度的心灵救赎。
空间,为什么一定要谈到空间?在这首诗里,它是除了光线与灵度之外,支持幻象存在并发生变化的又一个重要元素,这是一首格外有空间感的诗,抛开一切杂念,单纯研究这首诗的空间感都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可惜,这样一首信息庞大,错综复杂的长诗,蕴含有太多的美妙,舍弃哪一块都会有负罪感。
选择使用空间维度来打开幻象,在这首诗里似乎成了一种“必须”,电影院已然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梦境在这里发生发展,只有人为地创设更多的空间,才能让幻象的荒诞与不羁得到更好的承接和延伸,至少,让意识貌似合理。就幻象而言,过度的冲破只会适得其反,弄出一堆废墟出来,必须是有节制的冲破,才能在废墟上绽放玫瑰。空间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它是一根细小但无比柔韧的缰绳,在必要的时候,紧紧勒住那匹疯狂奔跑的意识之马。
“那么多扇门/在回声的漩涡中展开/通向幽深入口的翅膀/在自身的复制中颤动/人群的声音很深很深/渗入漩涡立起的无限结构/”漩涡是出现得最多的空间,在这个封闭的大空间里,无限多的漩涡划分出不同的世界,看看这些世界里呈现的幻象吧:围着你旋转的人流,模糊的形体,听不懂的语言,无边的黑暗,没有温度的脸庞……你重温这一个又一个的虚幻,仿佛只身一人在空旷的影院里行走,绕过高大圆柱投下的阴影,抚摸过整齐但冰冷的座椅,你甚至还听到梦境张大嘴呼吸的声音,求饶的声音,愤怒的声音,于是你被巨大的陌生感覆盖,急于寻找熟悉,寻找真相,但是一个又一个的空间容纳着一次又一次的虚幻,阻挡着你寻找真相的步伐。
当然,和作者一样,最终你们都走出来了,像颗急速飞翔的流星,到达无限远的边缘,到达有着晴朗天气以及一切的存在的空间。
那么幻象呢?它们依然存在着,存在于作者精心构筑的空间里,在那里消失或转化成另一种形象消失,在那里停驻或转化成另外一种形象停驻。总之,它们被诗人巧妙而机智地利用在意识流里,让意识变得有序可感鲜活。
在《巴别塔影院之梦》中,杨璇给我们带来非常别样的阅读体验,神秘、魔幻、焦灼、释然,在一首以意识为主导的诗里,在一条以幻象引导的途径里,反复经历情绪的转换和交叠,不得不说这是表达的成功,文字的成功。更为重要的是,她透过诸多的幻象触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深刻而尖锐的:在一个以物质主导的时代,普遍丧失的信任正在给人与人的交往制造危机,彼此的戒备、防御抵制心理带来了巨大的隔阂感,人与人近在咫尺又相隔千里,生存状态变得越发难以捉摸。难以捉摸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她渴望越过鸿沟,实现一个清朗的彼此理解的世界。
读完她的诗,你会觉得杨璇是个有奇特阅读经验的女孩,对生活对世界有特殊感悟的女孩,你会觉得她离文学应该近些,再近些,因为她就是为诗而生的。
(作者系丽江市作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