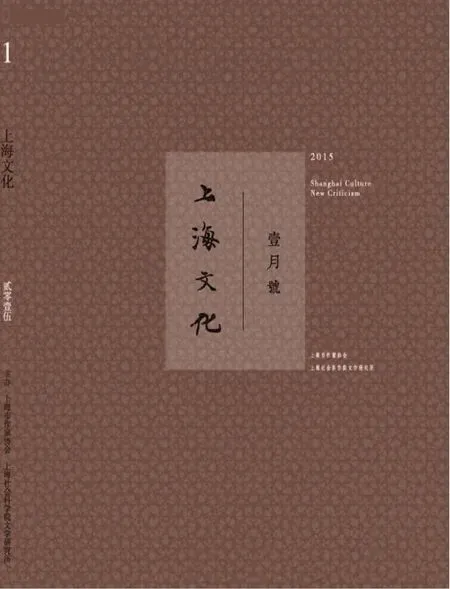在世俗的门槛上阿城《洛书河图》及其他
黄德海
在世俗的门槛上阿城《洛书河图》及其他
黄德海
作为文学的学术
毫无疑问,阿城是个一流的小说家。如果怕这句话不够严谨,那在“一流”前面随便加上一个“汉语”或“中国”这样的定语好了。不过,作为小说家的阿城似乎没有表示出对此一文体的足够热情,以至于许多年前,作为好友的唐诺就有个担心:“很长一段时日被我个人(以及朱天心等)认定为海峡两岸小说第一人的阿城,小说书写极可能也只是他对眼前世界的‘公德心”部分,阿城极可能不会久居此地,毕竟,他太喜欢那个更火杂杂、更热闹有人的世界。”唐诺的担心有道理,不知是因为没有写成的“王八”挫伤了阿城的士气,还是因为常年的游荡磨损了虚构的热情,反正阿城不写小说了,起码我们看不到他的小说发表了。只是与唐诺担心的不尽相同,不写小说的阿城,没有全身心地投身于热闹的人间世,反而转向了一个初看起来跟他素来擅长的文学不太相同的地方。
如果在《闲话闲说》和《常识与通识》中,这个转向还不够明朗,那当《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出版之后,大概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阿城的注意力,的确已经从文学偏离。在《洛书河图》中,讲解完屈原的《九歌·东皇太一》,阿城说,把它“当诗歌文学来解,浪费了……文学搞来搞去,古典传统现代先锋,始终受限于意味,意味是文学的主心骨。你们说这个东皇太一,只是一种意味吗?”既然阿城如此慢待文学,《洛书河图》又有很多学术方面的内容,不妨就把这本新书当学术著作来读试试看。
这本书的学理,挑要紧的讲,是创造性地释读出天极和天极神符形,并在冯时的研究基础上,揭开了素称难解的河图洛书之迷——洛书符型是表示方位的;河图的河,历来认为是黄河,书中将其指为银河,所出的图呢,是围绕北极旋转的星象。结论很斩截,论证却稍嫌不足。不过,既然天极和天极神符形是首次释读出来,论证粗略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漏洞。这一点,可以算是阿城独特的学术见解。但河图、洛书呢?先不管阿城是全面借鉴了冯时的研究成果,还是对其学术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只看这个结论本身好了。虽然我们无法从早期文献记载中得到有关河图、洛书较为确切的内容,但其流传,大概未必像阿城相信的那样充满阴谋论色彩。河图、洛书包含的数学思想,记载有序,确实古已有之,并非出于后来者的附会。而其中的精密象数结构,历来研究毋绝,近代以来更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不只是方位和星象可以解明的。类似这种发前人未发之覆的大翻案文章,总归让人有点没来由的怀疑,即便讲这话的人是阿城。
大概是因为阿城对天象太过着迷,在解释《易经》的乾卦时,他坐实了爻辞与苍龙七宿的关系,比如“初九,潜龙,勿用”,解为:“这是说苍龙七宿处于日躔的状态,躔就是与太阳同升同落,观望不见为潜。汉代的《说文解字》龙部解释龙,其中说到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所以这个卦象表示秋分时的苍龙七宿状态。”以下依次解释了九二、九四、九五、上九和用九,说明都与这苍龙七宿有关。虽然书中配的那帧鱼眼镜头拍摄的“苍龙(星象)出银河图”气象宏阔,乍看之下确实会让人的心着实紧跳几下,但不知是出于疏忽还是故意,解释漏掉了九三爻。而这一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确实很难用天象说明,不知聪明如阿城,有什么办法弥补这个漏洞吗?
即使不谈这个小小的漏洞,《易经》的取象于天文,也算不得什么稀奇,只是《易经》取象系统的一部分罢了。《系辞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其取象方法,上及天文,下及地理,旁及动植物,关涉人身和人事,错综复杂且洁静精微,历来有很多精深宏富的研究,不是一句天象就可以涵盖的。如此以来,《洛书河图》的学术价值就显得有点可疑。那么,这本书究竟该看成什么?
前面说了,因为所谈与天文有关,《河图洛书》的时空数量级就显得较一般作品大。先不说其中远至银河系的空间范围,大体统计一下,书里写到的最早时间,不是春秋、商周,甚至也不是新石器时代,而是十一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最晚的时间,则是公元28000年。在现今人文学科的书里,这样的时空量级已属罕见。何况,阿城并非凭空写下这些数字,后面有具体的天文、地质学基础,比如对岁差的认识。因为重力作用,“地轴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它的指向会有微小的变化,就是所谓岁差”。岁差七十二年左右偏转一度,一个周期约两万六千年,变换期长,变化又极其微小,几乎不易觉察。一个人一生都未必能看到岁差的一度变化,更不用说看到岁差周期了。意识到地轴指向的恒定天极也会暗中变换,可以稍微去掉一点人的固执之心。对岁差有所体认,凭一己之力根本不够,必要与古人记载呼吸相接,那时身心一振,“鹊桥俯视,人世微波”。
发前人未发之覆的大翻案文章,总归让人有点没来由的怀疑,即便讲这话的人是阿城
阿城文章动人的地方,大概正在这似文学似学术,却非文学非学术的“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的闪闪烁烁之间
不光是时空数量级,阿城在这本书里,仿佛用足力气往高处走,往一个自由的、神圣的状态里走。如《论语》中反复讨论的“仁”,阿城认为在孔子那里不过是个起点,艺术状态的“吾与点也”,才是孔子的志向所在,“孔子在这里无异于说,你们跟我学了这么久,不可将仁啊礼啊当作志,那些还都是手段,可操作,可执行,也需要学啊修啊养啊,也可成为某些范畴、某些阶段的标志,但志的终极,是达到自由状态”。讲屈原的《九歌·东皇太一》“穆将愉兮上皇”时,阿城甚至一下子讲到了极高:“穆是恭敬的意思;愉兮上皇,上皇就是东皇太一,我们要恭敬地弄些娱乐让上帝高兴高兴……在巫的时代,是竭尽所能去媚神,因为是神,所以无论怎么媚,包括肉麻地媚,都算作恭敬。神没有了,尼采说上帝已死,转而媚俗,就不堪了,完蛋”。阿城这是要把诗或艺术高推到神境吗?或许是。“(陶器上的)旋转纹在幻觉中动起来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一路上升,上升到当中的圆或黑洞那去,上升到新石器时代东亚人类崇拜的地方去,北天极?某星宿?总之,神在那里,祖先在那里。”是不是觉得,阿城从《诗经》的“风”,一下子跳到了“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这种铆足了劲儿往高处走的劲头儿,不再像那个蔫头耷脑地喜欢在闹市里看女子的阿城,多了一种庄严的神情在里面。阿城这本书,甚至还有他那些锁在抽屉里从未公开过的篇章,按现下的学术或文学定义来评判,大概都不符合标准,却自有它天马行空的神骏和洒脱。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文章,只好来听阿城讲《洛神赋》。一篇长赋,不过讲了两句,第二句是“若将飞而未翔”。“你们看水边的鸟,一边快跑一边扇翅膀,之后双翅放平,飞起来了。将飞,是双翅扇动开始放平,双爪还在地上跑;飞而未翔,是身体刚刚离开地面,之后才是翔。这个转换的临界状态最动人。”阿城文章动人的地方,大概正在这似文学似学术,却非文学非学术的“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的闪闪烁烁之间。
如果非要把阿城的这类文字定位,或许可以说,这是一本奇特的文学作品。在这本书里,我们习惯称谓的学术,有效地转化为一种文学质素,也让它脱离了单纯的意味状态,成了视界更为扩大、涵容更为丰富的文学,从而扩大了文学本身的容量,并有可能改变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狭窄的关于什么是文学成见。
残酷的常识
阿城喜欢谈论常识,谈论常识的阿城往往显得冷酷。常识不应该是平常的、温和的吗,为什么谈论常识的阿城居然显得冷酷?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现在的中国,被谈论得最多的常识,是托马斯·潘恩意义上的。潘恩在《常识》一书中,“要求读者作好准备的,只是摆脱偏见和成见,让理智和感情独自做出判断,持真守朴,不受现时代的拘束而尽量扩大自己的见解”,以普及他认为需要作为常识的现代政制基础。谈论这意义上的常识极其重要,因为人类最离不开的事情就是如何在一个共同体中生活,而一个共同体事务的重中之重,就是古希腊称为politeia(政制)的问题。
乍看起来,阿城谈论的常识与潘恩不同,他的重点,在孟子“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几”,深入的是人从生物性生发的种种情状。这些常识都是什么呢?思乡与蛋白酶、爱情与化学、艺术与催眠、攻击与人性,鬼与魂与魄与神的关系,情商与基因……多与人的生物性基础相关。思乡不过是思家乡的饮食,背后作怪的是胃里的蛋白酶;爱情呢,起因于人脑中的化合物;攻击性是人的本能,婚姻是基因利益的选择……这些常识,有些是极好的提醒,可以让我们在日常中不要任意而为:“千万不要拿本能的恐惧来开玩笑,比如用蛇吓女孩子,本能的恐惧会导致精神分裂的,后果会非常非常糟糕。”其他的呢,多显得不近人情,起码对人构不成安慰。比如:“爱情是双方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败坏对方的记忆,而因为基因的程序设计,双方都面临基因的诱惑。我们可以想想原配婚姻是多高的情商结果,只有人才会向基因挑战,干这么累的活儿。”比如:“青春这件事,多的是恶。这种恶,来源于青春是盲目的。盲目的恶,即本能的发散,好像老鼠的啃东西,好像猫发情时的搅扰,受扰者皆会有怒气。”
煞风景是吧,甚至有些残酷,不过真相却大概正是如此。让人稍许宽心的是,阿城所讲的常识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既然是科学,就有被证伪的可能,将来或许会有所改变。不过,不管在这些常识被证伪之前还是之后,诚恳地认识人的生物性本然,进而与本能周旋,或许是人生不再那么残酷的起点。
即便是每个结论看似从生活中摸索出来的阿城,较真起来,他的许多想法,也并非横空出世。比如他谈论常识的这个生物学起点,相似的意思,周作人就曾说过:“我很喜欢《孟子》里的一句话,即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一句话向来也为道学家们所传道,可是解说截不相同。他们以为人禽之辨只在一点儿上,但是二者之间距离极远,人若逾此一线堕入禽界,有如从三十三天落到十八层地狱,这远才真叫得远。我也承认人禽之辨只在一点儿上,不过二者之间距离却很近,彷佛是窗户里外之隔着一张纸,实在乃是近似远也。”在周作人看来,道德高调唱了千八百年的中国,“应当根据了生物学人类学与文化史的知识,对于这类事情随时加以检讨,务要使得我们道德的理论与实际都保持水平线上的位置,既不可不及,也不可过而反于自然,以致再落到淤泥下去”。阿城谈论建基于生物性基础上的常识,大约用心与周作人有些相似。不过,除此之外,阿城提倡常识,还有另外一个指向,即他从自身经历的动荡中,发现了一种脱离常识改造社会的行为。这行为,不妨称之为”乌托邦催眠系统”。
诚恳地认识人的生物性本然,进而与本能周旋,或许是人生不再那么残酷的起点
较早的乌托邦设想,因为设计者的审慎美德,原本不会和煽动狂热的催眠系统联系在一起。在被认为是乌托邦源头的《理想国》里,柏拉图要建立的,不过是一个“言辞的城邦”,它只存在于言辞的领域,从来不在地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一切都必须被认为是神话,他只是藉此表达出他的思想。如果你想创建这种国家,就可能上当受骗。”在莫尔提供了“乌托邦”一词出处的著作中,他也并不召唤针对现实的极度变革,遑论革命了。更何况,禀性温和的莫尔乌托邦的实施范围,跟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的城邦相同,也不过是局限在一个小岛上,并没有普世推广的雄心壮志。要到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以来,对理性越来越自信的人们,对乌托邦的热爱才到了狂热的地步,不但要求实施的范围一步步扩大,直至扩大到几乎全世界,而且推行的强度越来越高,差不多总是以大规模杀戮结束。
等这个乌托邦的狂热加温升级,藉助一个据说是“宁静安详的人”,远兜远转地传到中国,跟中国所谓的“人人可以为尧舜”结合,抟弄出了一个更加变本加厉的乌托邦催眠系统。这个催眠系统打破了催眠小型封闭空间的局限,无视世俗的复杂生态与人性的参差不齐,集中力量煽动狂热,对外要求世俗整齐划一,对内要求人变成一张“擦净的白板”(tabula rasa),以便在社会和人心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那个在谈论常识时显得冷酷,有时冷酷到有些庄重的阿城,背后深藏的,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热心
难以避免的,这个庞大完美要落实到地上的乌托邦,会突破常识的禁忌,藉助催眠导致的迷狂,造成难以避免的社会生态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单说,就是失去常识能力的闹剧。也因此我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悲剧性,悲剧早就发生过了。‘反右’、‘大跃进’已经是失去常识的持续期,是‘指鹿为马’,是‘何不食肉糜’的当代版,‘何不大炼钢,何不多产量’。”这一迷狂的背后,有强大的权力之剑,在这把剑面前,说出常识,有说出“皇帝没有穿新衣”的危险。即使这狂热造成的巨大迷狂已经时过境迁,藉由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人仍旧在乌托邦催眠系统的控制之下。阿城在被催眠的人群中讲常识,目的就是为了把人从包括乌托邦催眠在内的各种有害的催眠系统中唤醒,回到那个我们置身其中的,无法被化约的复杂真实世界。但陷入催眠狂热的人,怎么会愿意醒来呢,惊扰甚至惊起人的美梦,当然就显得冷酷。在这个冷酷里,我们大约会发现,起点与潘恩相异的阿城,在用心上却表现出某种一致。
虽然惊醒梦中人的常识讲得这样有板有眼,阿城却并不一例反对人在催眠中做美梦。他曾讲过一个巫医给知青治牙痛的故事:把牛屎糊在脸上,在太阳底下暴晒。后来,巫医说牙里的虫子出来了,知青的牙居然也不痛了。按现代医学常识,这有些荒谬。但是,阿城提醒,“不要揭穿这一切。你说这一切都是假的,虫牙不是真有虫,天天牙痛是因为龋齿或牙周炎。好,你说得对,科学,可你有办法在这样一个缺医少药的穷山沟儿里减轻他的痛苦吗?没有,就别去摧毁催眠。只要山沟儿里一天没有医,没有药,催眠就是最有效的,巫医就万岁万万岁。回到城里,有医有药了,也轮不到你讲科学,牙医讲得比你更具权威性”。这就是阿城对具体的人的体恤,他知道常识对有害催眠系统的祛魅,同时也知道不能在不具备祛魅条件的情况下讲常识。对催眠系统的点破或保留,要根据不同的具体,盲目地陷入或反对,都是“常识缺乏”。
如此看来,那个在谈论常识时显得冷酷,有时冷酷到有些庄重的阿城,背后深藏的,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热心(跟阿城给人的印象不符是吧)。其实,对一个如此热心的阿城,面对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我甚至不愿意把他所讲的这些称为常识,而是一个热心人的卓绝见识。当然,还是阿城自己说得更好:“任何高见,如果成为了生活或知识上的常识,就是最可靠的进步。”
在世俗的门槛上
阿城对世俗的热爱是出名的,其俗态可掬也流传得很广。但是不是可以就此断定,阿城是个结结实实的世俗中人?
习惯了,或起码在想象中习惯了阿城对世俗的随和态度,听多了他不紧不慢的俗腔俗调,读到他《洛书河图》一段挖苦嘲讽又略显峻急的话,会不觉一凛:“你们大概将来是要做艺术家的,志在画价一亿以上吧?其实只要恪守不损害他人为底线,无所谓对错。又或者留心文论,嘴能说诸多概念手能画各种文本渐渐成为公知,也是蛮艰苦的。其实追求虚荣等等都不是什么罪过,最终也是火葬烧成骨灰还算一生圆满,不在乎内心是否达到自由状态。如果你们的志向是这样,上面的算我白说。”
这话严肃,甚至有点愤世嫉俗,几乎让人看破了阿城不满世俗的一面,也差不多要毁掉此前阿城世俗中人的形象。不止如此,在这本据讲课整理、文字不算多的书里,阿城在辨认出青铜器上的天极符型之后,说完它“源远流长,又高贵又可爱”,便开始调侃:“我看出来了,你们正琢磨着怎么抢先去注册个图形专利吧?”话锋一转,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且慢,这个符型是中国从古到今的公产,虽然远古只有王才能祭祀它,同时也靠祭祀它来证明祭祀者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又由社稷血脉承认,所以实际上它是保佑着我们的血脉流传,申遗还差不多。”说这番话的,还是那个衣敝缊袍、髭须不剪以与世俗处的阿城吗?
我们往往会把一个人平常喜好谈论的东西误会为这个人本身,认为阿城是世俗之人的想法,大概就源于这样的误解。没错,阿城是喜欢谈论世俗,他讲谈小说的《闲话闲说》的副题便命为“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这本小书的胜义,我以为也正在对世俗的精深体察。阿城承认,不少评论里提到他小说《棋王》里的“吃”,“几乎叫他们看出‘世俗’平实本义”。我们并不会把柏拉图笔下整日谈论铁匠、鞋匠和皮匠的苏格拉底当成工匠或其他什么人,而坚定地认为他是一个爱智的哲人,为什么阿城因为谈论了世俗就该是世俗中人呢?
阿城对世俗满怀情意,是因为他明白世俗是一个自为的完整生态,如天然的热带雨林,用不到置身事外的极力维护或大张鞑伐,知道谨慎地爱惜就好了:“我在云南的时候,每天扛着个砍刀看热带雨林,明白眼前的这高高低低是亿万年自为形成的,香花毒草,哪一样也不能少,迁一草木而动全林,更不要说革命性的砍伐了。”对阿城来说,“扫除自为的世俗空间而建立现代国家,清汤寡水,不是鱼的日子”,作为鱼的老百姓,也就难免老是进退失据。在他心目中,世俗应该是“无观的自在”,其中有男耕女织,也有男盗女娼;有快乐的瞬间,也有无奈的叹息;有种种的小烦恼,也有各色的小得意……总之,世俗是一个长期共生而长成的空间,人可以在里面宽裕地爱或恨,欢欣或失意,容得下放肆的举手投足。
阿城懂得,世俗的“糟粕、精华是一体,‘取’和‘去’是我们由语言而转化的分别智”。有这份见识和爱惜在,他当然不满于对世俗颟顸的指手画脚,更不用说借助强力推动的改造了,因为对世俗自以为是的规训会束缚世俗中人的手脚,生态复杂的自为世俗不免变得单调刻板。不过,爱惜并不等于溺于其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为自己申辩时说:“你们不会相信……你们听我省察自己和别人,是于人最有益的事;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这些话你们更不会信。”把苏格拉底和他谈论的对象区分开来的,正是这个省察的态度。就像能省察“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并非百姓一样,不妨这么说,阿城谈论世俗,在起始意义上就有一种省察的态度在里面,并非他自己是世俗之人的声明。
阿城谈论世俗,在起始意义上就有一种省察的态度在里面,并非他自己是世俗之人的声明
虽然强调“世俗是自为的,是一种生态平衡”,有其勃勃的生机,但阿城并没有陷入民粹式对世俗自上而下的赞赏,并进而单向地与世俗一致。他始终保持着对世俗的谨慎距离,因为知道世俗里也有人类共有的“生命本能在道德意义上的盲目”,有其肮脏和污浊,不只是赞颂的对象。在几乎被人看出阿城世俗用心的《棋王》里,有这么一段:“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这或许就是阿城与世俗的共生方式,懂得世俗的自为,自己也长在俗世里,却并不囿于其中,而是能跳出来观照。把阿城的谈论对象等同于阿城本人的人,大概是把阿城对谈论对象的真挚诚恳当成了他自身的选择,混淆了省察者与单纯置身其中者的不同。
不管一个人有怎样卓绝不凡的内心世界,他一旦在世俗中出现,就必须,也只能置身于在世俗之中
需要强调的是,省察者并非由可以藉由省察获得置身世俗之外的特权。一个省察世俗的人必须认识到,由完全超越世俗的人组成的社会,不可能存在,世俗之所以是世俗,就因为它对超越世俗有一种本质性的、不可救药的抵抗。不管一个人有怎样卓绝不凡的内心世界,他一旦在世俗中出现,就必须,也只能置身于在世俗之中。如果把世俗与自己超越的内心世界对立起来,所谓的超迈世俗者就与世俗悖谬地站在了一起。因而,一个超迈世俗的人该做的,不是对他以为不合理的世俗愤怒或指斥,而是必须倒转过来,其所作所为要经过世俗的检验。所有不懂得世俗和世俗人心的人,都配不上超越世俗者的称谓。
从这个方向看,阿城倒真是超越世俗的人。不过,这样说并不准确,经过世俗检验的阿城,确切地说,应该是在世俗之外又置身世俗之中的。他虽能跳出世俗来观照,却并不离开俗世,而是生长在里面,觉得自为的世俗从容宽裕,待在里面舒服——虽然近代以来,这个宽裕的世俗愈加狭窄。这正是阿城的方式,观看,理解,欣赏,可自己并不就是对象本身。阿城仿佛总是这个样子,跨在世俗的门槛上,一脚门外,一脚门里,我们刚刚觉得在某处抓住了他,他又在相反的方向出现了,蔫蔫地不言不语。
编辑/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