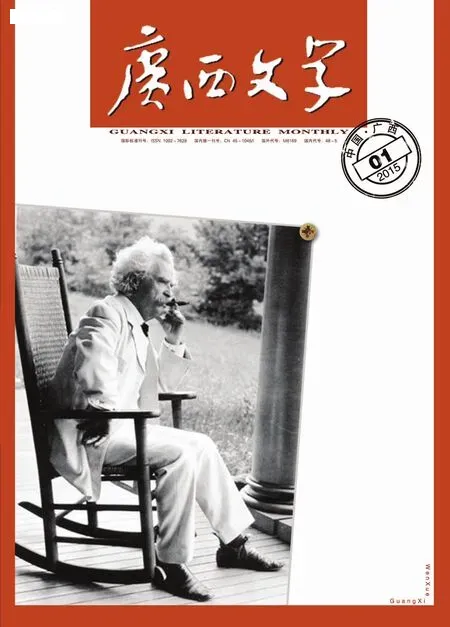罗晓玲散文二题
罗晓玲/著
天堂的模样
我心中暗暗猜想,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阿根廷)博尔赫斯
——题记
(一)
每次进入藏书室,犹如独自穿越荒野。阴森森的书架在灯光下影影绰绰地晃。年久失修疏于更换的灯管,在低矮的天花板下散发着柔弱的光。之中总有两三盏在一闪一闪地跳动,仿佛下一秒就会立即暗下去,但它偏不暗!于是整个藏书室也随着跳动的灯光一明一暗地变得诡异起来,这极容易让人想到灵异片里鬼魂出现时,灯火“唰唰”齐灭的情景。谁在这样的环境下都会变得有些发怵,精神开始不安。而我觉得那些闪着的灯更像野外墓地里飘来荡去的磷火,一扑一闪地让人恐惧。
我一个人在书架间惊惶地拐来拐去,终于进入到了最里面的书架了。而惯常的心理作用又让我觉得一股阴风从后脊梁旋起,鬼魅一般进入我的身体,让我情不自禁地颤抖了一下。
我去为读者检索一本叫《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书。这是一本法国名著,我清楚地知道它的分类号和在书架上的具体位置,我想它或许有些吸引人,因为这本书有几个人借过了。但我却极其讨厌它。因为越多的人来借,意味着我就要越多地进入这片阴森之地,我的心脏就要接受一次次的考验。每一次,我都用最快的速度把书从书架上取下,然后迅速地逃离。这鬼魅之地,如果可以选择,我宁可一辈子也不进来。博大叔的话是不可信的,他说,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怎么可能呢?这里简直就是地狱。
(二)
他们说我有学问了,我问为什么?回答:在图书馆工作呗。面对这一简单的生活结论,我只想到它应该来源于那句俗语: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至于有没有学问,我当时是不关心的,我更关心的是,一个月的工资能买得起多少斤猪肉。对于不爱读书,不热衷于文字的人来说,图书馆工作更多的是与清贫寂寞、无所事事、无所作为这类清冷消极的词语联系在一起。
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座图书馆当管理员。当时的图书馆建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它处在公园一角的边缘地带,往东走几十米,是公园喧闹区,往西,便是较少人去的郊区。图书馆是个分界点,在繁华与冷落之间等待着别人的选择。但它并没有因为处在公园内的位置而吸引更多的读者。“风水不好,阴气太重”这几个字是我一去到馆里就经常听到的。它常常从女同事诡异的表情里说出来,让人不寒而栗。的确,图书馆被包围在一堆居民房里,如果不是因为它的建筑略高于普通的民房,从外面看,你很难发现它竟然是个图书馆。图书馆里的每个角落都拥挤逼仄,特别是进入藏书室,犹如进入了阴暗的密室。室内灯光昏暗,空气对流不好,里面的书架间距勉强能容一人走过。架上塞满了旧书,尘封已久的霉味和尘土味混杂在空气里让人窒息。有些书已经有虫蛀的小洞,一翻开还能催你打出一连串的喷嚏。藏书室里大概放着十多万册书,一整片看过去,像死寂的森林找不到一点儿生气。那时候,藏书室经常是一个人值班。当我每次进去为读者索书的时候,心跳不由加快,总觉得在某个书架后面,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如果再多呆一会儿,惊悚片的种种画面就会涌出脑海。取好书后,我像盗墓者仓皇而逃,一出来就迅速地反锁上藏书室的门,生怕里面的阴气也跟着跑出来。借书的读者看着我一脸惊惶,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当然不知道那里面是怎样的一种景象。那些被视为知识海洋的书籍,其实是充满诡异色彩的迷雾森林,我对它们避之唯恐不及。好在图书馆总是管理员多过读者,借书者寥寥无几,我也不用经常到藏书室去索书,更不会主动跑到里面,找一本书阅读来消磨难挨的上班时光。
没有人喜欢这份工作,确切地说,没有人喜欢这个地方。馆里女人居多,她们上班除了应付仅有的几个读者,做一些零碎的馆务工作外,基本上都是闲着的。我看到她们有时候拿着一件毛衣从上班织到下班,更多的时候是聚在一起闲聊,说这菜那菜怎么做,说谁又这样那样地度过一整天。极少有人去想前途如何,图书馆如何走出困境。一开始我加入了她们闲聊的行列,做着长舌妇虚度着光阴,后来渐渐觉得无聊与乏味了,却又不知道除了用这样的方式打发日子,还能做些什么。
图书馆被我们冷落着,像被打入冷宫的妃子无人过问。我们每天在图书馆的肺腑里穿行,却从不关心它身体里暗长的肌瘤。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哀怨孤独的。好几年,我看到许多书在书架上的位置都没有挪动过,就像一个瘫痪的人躺在床上无人打理。我隐隐感觉到,那里面暗生的蛀虫、堆积的尘埃、发酵的霉味,正集结成一个暗涌的世界,它日夜悄声无息地膨胀,迟早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爆发出来,给我们施以报复。那是另一个令我害怕,不想感知的世界,它像一个巨大的无底洞,用一种阴绵的力量将我们慢慢地吸入一个绝望的境地,我们身体里的青春、活力、希望,在这种力量的牵引下变得越来越少。
有那么一段时间,馆里的同事接二连三出事。今天是某人离婚,明天是某个家属得癌症死去,后天又是谁出车祸,突然谁家又惹了一场官司。图书馆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控制着,制造着事端与灾祸,弄得人心惶惶。后来,能调走的同事,拼命地找关系调走了,不能走的同事,初一十五只好多买几炷香烧烧。我也开始忧虑,常年萎靡的工作状态,不思进取的生活,迟早会影响到自己的命运。我也必须做些什么,来对抗这虚无的生活。百般无奈之下,我终于拿起一些书阅读打发时间,但读书的时光让我如坐针毡,阴暗冷寂的氛围让我无法专心下来。这样的阅读,犹如给半封闭的罐子挤入几滴清水,无法改变什么。
(三)
这世上的境遇你永远也想不到,就像一本书,你若将它放在藏书室,或许久久无人问津,但若你把它放在开架书库里,这本书便有了更多出借的机会。我就幸运地遇到了这样一次机会。同样的图书馆工作,我被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境遇有了改变。
母校图书馆在环境上与之前所在的图书馆竟是天壤之别。馆舍大,宽敞明亮,环境异常地好。周边都是教学大楼与学生宿舍,窗外桂树环绕,鸟语花香。特别是秋天,成片的桂花树一起开放,花香从窗外灌入,其景其香真是让人沉醉。
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很少,每人管理一层,每人就可享受一个偌大的“办公室”。我欣喜若狂,离开逼仄的环境,心情像飞出笼子的鸟儿,一下豁然开朗起来,肢体也像生锈的镙丝被人扭动了一下,点上了润滑剂,整个人开始灵动起来。我每天把图书室打扫得整洁干净,地板拖得锃亮,在里面一边放着音乐,一边编目图书、整理书籍。阳光从南北墙镶嵌的大玻璃窗外倾斜而入,洒在图书室的地板上,投射到书架上,充满光明与温馨。这时候,纵使一个人呆在图书室里,也不会感到冷寂孤独。图书馆在学生上课时间,几乎是没有人光顾的,于是我开始为所欲为,包括在书架上劈腿,在书架间慢走锻炼身体。音乐轻盈地流淌在每个角落,我在办公桌上泡好茶,由此开始了“天堂”般的生活。那时候我甚至觉得两个假期对我来说都是多余的,我喜欢呆在图书馆里,享受音乐和花香。学校图书流通率高,也常有新书像活水源源不断地注入进来,充满了流动的生命力。我在这样的流动里,找到了书籍存在的意义和自己的工作价值。
而我知道,博尔赫斯对于“天堂”的理解,并不是因为图书馆的“清闲”,而是因为能在它的氛围里,享受知识的洗礼与馈赠,获得写作的时间与宁静。图书馆工作,让他在工作、阅读与写作之间找到了最完美的契合。学校图书馆的工作依然是相对清闲的,我确实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如何补救之前虚度的那几年时光。我开始有了一些读书的心情,书看多了,也偶尔动笔写些文字打发多余的时间。但零星的阅读与写作也并没有让我快乐起来,成为一名像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并不是我的理想。我隐隐地觉得,波澜不惊的生活里,总少了些什么。我的世界里,除了书架与书,一成不变的生活,而外面的世界呢?
(四)
一年多后,命运又一次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与图书事业毫无关系的地方。在外面的世界起伏几年后,我像围城外厌倦喧嚣的人,又开始张望围城内的宁静的生活。现在常常回味着,那个每天拿着鸡毛掸子打扫书架的自己,仿若世外桃源中栽花种草的仙子,美得让自己都觉得眷恋。于是在忙碌劳顿的时候追悔没有坚守在“天堂”里,也没有早日与文字结缘。但图书馆毕竟是回不去了。后悔归后悔,我又常常反过来问自己,现在,真给你回到图书馆,你还愿意去吗?结果内心是迟疑的。
学者们说,图书馆本身就是一种内涵深厚的文化。但在不发达的县域,图书馆是一处被闲置的文化,它往往被撂在经济建设的大潮后面,在物质与精神青黄不接的冷落中,散发着黯亚的光。而一块充满活力的铁,在这样闲置的环境里,不经历扳拗与打磨,是容易生锈的。因此,图书馆工作,只适合像博尔赫斯这种以图书为事业,又兼当诗人与作家身份的人长待。在这样的人眼里,图书馆才是一处无与伦比的天堂。有朝气有抱负的年轻人是不适合长期待在图书馆的。释达济禅师有一则著名的禅经故事叫《安逸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地狱》,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死水一潭毫无涟漪的生活,会让人麻木与厌倦,庸常与琐碎久了,容易让人觉得生活黯淡与无望。我想我那过于安逸的生活,正是需要一场大风大浪的洗练才足够圆满,因此我最终愿意离开“天堂”。我期待图书馆外的世界,将我引向了另一种未知的辽阔。
朱熹的佳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阅读的良言。沉滞不可取,流动运动着,才能吸取新的东西。“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世间万物的运动,是存在的根本。知识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每天在同一个地方蹲守着,不如挪动脚步,到另一处吸取新鲜空气。书籍是知识的源头,而我们打开视野吸纳活水的内心,更是这个源头的源头。莫言的学生时代只读到中专,但他在土生土长的高密乡,汲取了所需的文学营养,最终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如八十岁的杜拉斯说,“每个人都是作家,重要的是如何不写”。套用这句话,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我们如何不读?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图书馆,我们如何能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要我们的心灵在阅读,身边的一切,就是图书馆。
所以,在不在现实意义上的图书馆有何紧要呢?我们的内心源头能洞开多大,我们吸纳的活水就有多少,心中的图书馆就有多大的储藏。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善于吸纳的活源头——一颗求学的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图书馆的承载体,每个人的体内,都放着无数个空书架,等着我们把自己编目的人生放上去。我们是带着图书馆行走的人,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部可以行走的图书馆,之中放着学识、阅历、情感、思想,以及由这些元素混合起来,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质与气场。天堂就在自己的身体里,模样取决于我们要从纷繁杂乱的生活中提取什么样的素材,从知识的天空中采撷什么样的颜色。当每一份要素都暗合了自己身体的温度与气场时,我们就拥有了一个最理想的天堂。
婶娘的瑶服
我们来作个假设:假设身穿彝族服装的阿诗玛,或者穿壮族服装的刘三姐,某一天突然着一身现代装出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我想,或许大多数人都会不太适应,因为一般人很难从惯性的审美当中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
在我结婚那天,婶娘的换装就给了我一次莫大的惊诧。那天,她破天荒地穿了一身时下中年妇女都穿的“的确凉”碎花衣服!
这是我自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看见婶娘换装,在此之前,她一直都保持那身天空一样蓝色的,代表着农村瑶族中年妇女的装扮:头上裹着一块深红色的方帕,上身永远都是那种平板、硬直、不透气的蓝色右衽开襟短衣,裤子也是同样布质的黑色窄脚粗布长裤,一年四季从来没有变过。我看着婶娘竟然说不出话来,婶娘的表情却比我更窘,她觉得自己改了装在别人眼里就像个怪物一样。“玲子结婚,我怕那身衣服穿着太土,怕咱们亲家看不起不是,所以就换了一身,其实我穿着这身衣服也怪别扭的。”婶娘发窘地说着,听到这儿,我眼泪“吧嗒”一下就下来了。
我出生在一个僻远的小村庄,那里世世代代住着讲瑶话的农民,那里的中年妇女一律都穿着蓝色的粗布衣服,她们的头发几乎一辈子也不剪,编成长长的辫子盘在头上,一圈又一圈,像树的年轮,年龄越长,圈数越多。然后,用方帕从外面层层围住,把岁月的秘密掩藏了起来,也把风尘世事都隔在了外面。她们无休止地奔忙于粗陋的泥砖房和田地之间,村里村外地穿梭在猪圈牛栏当中,劳动,几乎是生活的全部。婶娘就是其中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平凡得像田埂上一棵不知名的小草,无怨无悔生长在一方土地上。从小我就发现了婶娘与母亲在穿着上的不同。母亲是民家人(在富川对讲桂柳话的人群的称谓),一直以来穿的都是各种布质的碎花衣服,而婶娘却不是,据母亲说,婶娘从小就开始穿那套蓝色的瑶服,从来都没有变过。有一天,我好奇地问婶娘为什么总穿这身衣服,婶娘先是笑笑,然后就开始跟我讲关于瑶王始祖盘王的故事:“盘王是咱们瑶人的祖先,是个有着大本事的英雄呢,”婶娘在讲故事的时候,脸上充满了虔诚与自豪,眼睛凝望着远方,仿佛神圣的盘王就在她正远眺着的大山最深处,“咱们瑶人以前住在大山里,盘王说,那是和天界最接近的地方,所以,盘王喜欢穿蓝色的衣服,因为穿上蓝色的衣服,就像与天空融为了一体,就能够与天神最靠近,最容易让天神知道咱们族人的请愿,还族人一个风调雨顺的节气,让族人过上平安吉祥的日子。所以,咱们瑶族后人不管男女,为了纪念盘王,都穿这样的衣服。”于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穿这样的衣服,是为了纪念一位英雄的祖先,那个祖先喜欢穿蓝色的衣服,是因为这种颜色的衣服与蔚蓝的天空一样美丽。
当我知道瑶人还用歌舞祭祀盘王的时候,已经是六岁了。那年,为了参加那场隆重的祭祀,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而这件事,成了我童年乃至人生中一道永不磨灭的印记。
镇上举行四年一次的歌圩节,这可是瑶人里最隆重的节日。附近十里八寨的瑶人,在这一天都要聚在一起,穿上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地祭祀祖先。这一天,男人们穿的是通身的黑色粗布瑶服,扎一根五彩腰带,再搭配一块深红色的方帕。女人的穿着则丰富多了,比起平日里简单的瑶服,她们的服装可谓五彩斑斓:头上戴一顶浅蓝色的蝴蝶帽,帽子前沿垂吊着一排银晃晃的状似叶子或珍珠的银器。上衣以蓝色衣服打底,衣袖从袖口开始,用黑、红、蓝、黄等几种颜色依顺序缝制。在底服的外面,穿一件镶金边的黑色外褂,腰间系一条绣着大朵云花的裙兜,一条镶着格子花纹的腰带将裙兜固定在了腰上。裙兜下面,垂吊着一排大红的流苏。下身穿的是过膝的黑色百褶裙,小腿上绑着黑色绑腿布,脚上着一双干净崭新的绣花鞋。从帽子到裙裾,每件衣饰的边缘,都镶着不同颜色与图案的花边,颜色多种多样,看上去五彩缤纷,错落有致。而最吸引我的,是上身褂子上那做成蝴蝶状的布扣子,像栩栩如生的蝴蝶栖息在人的身上。婶娘说过,这是因为瑶人都喜欢唱蝴蝶歌,衣服上绣着这样一种灵物,既是一种象征,也彰显着一种人与自然相处的和谐之美。
婶娘是从高山里的瑶族嫁到这儿来的,这样隆重的歌圩节日,也是少不了她的。大清早,为了穿上这一生中最美丽的衣服去参加节日,我看见婶娘早早地把所有的家事都打理好了,然后便开始仔细地洗漱,准备梳妆打扮。记得母亲说过,这身衣服是婶娘的母亲在婶娘出嫁之前,用了无数个夜晚,一寸一寸地用织布机织出来的,身上那些漂亮的扣子和金边也是婶娘的母亲亲手一针一线地绣出来的。所以,瑶族的女子只有在出嫁、隆重的节日,还有死去的时候,才会穿上这身美丽的衣服,平日里穿的,都是为了方便劳动而裁的最简单最朴素的瑶服。
太阳已经照到了瓦背上,我仿佛听见从不远的镇上传来熟悉的旋律,女人们“依呀拉的哎”的清亮歌声拂过田野,和着乡土的气息萦绕在小村的上空。男人们吹起芦笙,舞动长鼓,伴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齐整地踩踏着土地掀起层层热浪。小镇已经在沸腾,搅得我的心也跟着沸腾起来。我迫切地想要看到这难得一次的盛大场面,竟然等不及婶娘换好衣服,就偷偷地跟在一帮伙伴后面,私自一人逃出了家人的视线。为了早一步到镇里,我选择了近路,结果在经过一根必经的独木桥的时候,不幸掉了下去,头刚撞上河里一块大石尖上,当场就晕了过去。幸运的是,河里的水早已涸竭,我并没有被淹死,等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满脸鲜血。剧痛与惊惧把我吓得“哇哇”失声恸哭起来。还好河岸不算高,我用尽所有的力气,摇摇晃晃地爬到了岸上,朝着奶奶房子的方向拼命地哭喊起来,直到有村民看见,直到爷爷奶奶叔叔婶娘们一起从村里发疯般地赶了出来。(我并没有看见母亲,据说她当时正好在村后的地里捡猪菜)。奶奶看见我满脸鲜血,惊骇得直掉眼泪,呼天抢地地骂着河里行凶的鬼。婶娘急中生智,跑到附近的村民烧炭的炭窖里抓了一把灰,捂到了我的伤口上,在这阵慌乱之中,不知谁从村里拉出了一辆双轮车,婶娘的大手一抱,就把我抱了上去,叔叔带上车把便把我往十几里外的乡卫生院赶,婶娘则一只手帮我捂住伤口,一边忙着推车,爷爷奶奶跟在车后面,家人一阵手忙脚乱。可乡下的路不平坦,双轮车一边颠簸,我头上的炭灰一边往下掉,还没出多远,伤口又开始流血了。婶娘只好又跑到炭窖里抓了一把土灰加在伤口上。接着,婶娘让奶奶帮我先捂住伤口,略犹豫了一下,就从崭新的衣服的一边猛力地一扯,围着衣服的边缘扯出了一条蓝色的长布带,利索地往我头上一绕,便牢牢地把灰土裹在了里面,结结实实地绑住了我出血的位置,伤口很快止住了血。我惊惧的心灵竟然在这一刻得到了不小的安抚,一路上停止了痛哭。而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婶娘已经穿上了那身盛装瑶服的上衣和裙子,只是腰带和裙兜还没有系好,帽子也没戴。想来是因为正在装扮的时候,听到我的哭喊声,不顾一切地跑了出来。双轮车不停地往前赶,我听见婶娘的腿在裙子里奔跑发出不停摩擦的声音,穿过泪眼,看见婶娘粗粗的辫子垂吊在身后甩来甩去,光洁的脸上已经渗出了密密的汗珠。然而双轮车毕竟还是太颠簸,失血过多的我本来就体虚,再加上颠簸,更是难受,婶娘看见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索性把我背了起来,迈开大步,“扑哧扑哧”地往乡里赶。一路上,我趴在婶娘的背上,明显地感觉到婶娘那身蓝色的衣服早已让汗水湿透,听着她的喘息声和怦怦的心跳声,竟然晕乎乎地睡了过去。婶娘一刻也没有停,一直把我背到卫生院为止,伤口到了卫生院,就再没有大出血过。后来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要不是婶娘及时帮我止血,我的小命可能早就没了。
伤好出院后,我发现婶娘已经把那件被撕了一条边的衣服用来当日常装穿了,衣服显然被她用剪刀修齐了边,往里缝了一路针线,所以看上去像没撕过的一样,但是比其它衣服短了一大截,看着怪不舒服的。我从母亲的责备里知道,为了抢救我,婶娘撕破了那件华丽而珍贵的衣服,也没有来得及去参加那场她期待已久的歌圩会。那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衣服,那一生中只能穿几次的美丽嫁衣,因了我的年少不懂事,早早地结束了它在一个农村妇女一生中的光彩命运。这件事让我内疚得无以复加,问了几次母亲这样的衣服市场上有没有卖,但母亲总是无奈地摇头。后来母亲叫人照着颜色跟尺寸给婶娘做了一件新的,虽勉强能穿,但衣服上那些用手工缝制的精致的花边、绣饰,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复制了,少了这些珍贵的手工绣饰,这身衣服就没法还原到本来的韵味与特色了。但婶娘一直安慰我说,没事儿,一定是祭祀的歌声召唤到了盘王,让他看到了我受伤的那一幕,然后用神的力量驱使她,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搭救自己。所以,以后要是穿着这身衣服去祭祀盘王,盘王也一定会理解的。听了婶娘的话,我和母亲这才有些释怀。后来,那件瑶服里的“短装”被婶娘压进了箱底作了永久的纪念。而自从那次事故之后,那身蓝色的衣服,也让我多了一种说不出的神圣与踏实感。
20世纪90年代末期,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服饰也自然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年青一代的人再也没有人愿意穿那既“老土”,也不适用的瑶服,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轻便与时尚的服装。现在在老家村里,穿这种瑶服的,只有像婶娘这样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了。堂哥堂妹们也去了外面打工,每逢节日回乡,总不忘记给婶娘买几件漂亮衣服:纯棉的,莱卡的,南韩丝的,羽绒的,而不管他们买的衣服多贵,质量多好,最终都被婶娘压进了箱底,她总是说,“我还是穿这身衣服惯些。”我也问过婶娘,为什么现在还不愿意换装,婶娘便语重心长地说:“玲啊,咱们是瑶人,瑶人信自己的祖宗,穿自己的衣服,瑶人就得有瑶人的样子啊。”
现在,每次回到老家村里,看着穿着蓝色瑶服的大婶大娘们,总喜欢盯着她们多看几眼,那身蓝色,总能让人想到阔蓝的天空,祥和而宁静。而每次收回眼光,心里又免不了生出几分怅然,想着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随着这代人的离去,这身衣服也将渐渐地消失,当我们想要再看到它时,只能是在博物馆里或者是某张相片里了。在这样一个日益走向富足的村庄里,我们也许会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的机器,小洋房,交通工具,富裕的生活在慢慢地把传统的风俗侵蚀掉。那个时候,我们是否还能想起这身质朴的穿着,是否还能看见穿着瑶族服装的阿娘阿婶们,她们一手挽着簸箕,一边怀着无限的憧憬,走向那片年年耕种的田野?
我常常怀想这样一幅场景:一群身穿蓝色瑶服的妇女,身影起伏在一片田野之中,蓝天之下,她们的衣服和阔蓝的天空一样,柔和,美丽,洋溢着质朴的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