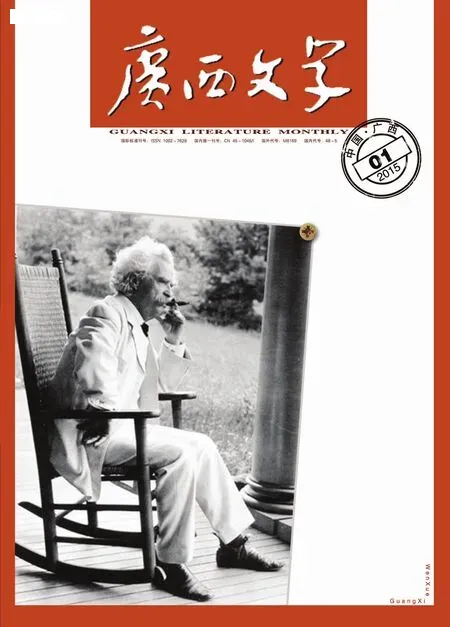父亲和树
短篇小说·莫灵元/著
1
我们老家那地方,有个习俗,就是谁家添丁生个男孩的,都要种下一棵树,种在房前屋后或者种在自家自留地都行,但必须要种,而且必须管活。
我小时候,老家地多人少,到处都有鸟叫声,每个村子都是裹在树林里。我老家那个村,那时候只有五六十户人家,村后面,林子成片地长,乔木、灌木簇拥在一起,人躲在树林里根本看不见。村前是一片汪汪的水域,水从东往西流。
我的家在村西头。
父亲是独子,住的是祖屋。祖屋是一座平房,青砖碧瓦,五间相连,中间是厅堂,两边是居室,前面有走廊,柱子亦是青砖所砌。平房前面两边还有两间小厢房,也是瓦盖,只是墙换成泥筑的了,一间是厨房,一间用来堆放农具等杂物。
砖砌的祖屋在我们村子里只有两三家,这些年来其他两家同别的老房子一样先后都被拆了重建。因为父母还健在,我每年春节都要回老家过年。年年回家,年年所见不同。现在我们村已经看不到多少树木,一座座钢筋水泥建成的两三层楼房逐步取代了过去的瓦房。
我家祖屋有矮墙、荆条围着。正前方七八米便是水塘,水塘到厢房墙脚这块地面做了晒谷场,我家大门就开在晒谷场的东边。这个地方曾经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在这里捉迷藏、数星星,还练过拳脚。父亲得意的地方却是在屋子的西面。屋子西面是我家菜园子。菜园子约有半亩地,呈半月形,从屋后根一直延伸到晒谷场最南边,三面种了荆棘,用作围墙。荆条密匝匝的,高过人头,猪鸡牛狗都进不来,园子里除了种菜,原先还种有一棵龙眼树和两棵番桃树,在我读初中时这三棵树却先后不明不白地枯死了。父亲给我们种的树也是种在这个菜园子里。父亲给我种的是榕树,给老二和三弟种的是苦楝树。为什么?父亲说,榕树长得茂,苦楝长得快,榕树拿来遮荫,苦楝用来做衣柜。如今两棵苦楝树已经砍去了,不过不是用来做衣柜,是卖给了人家。剩下的这棵榕树,突兀在村里,成了一道风景。它遒枝苍叶,蓊蓊郁郁,斜出的枝桠挂着根须,树上白天虫鸣,夜间宿鸟,这让父亲喜不自胜。
父亲对这棵幸存的榕树非常爱惜,容不得有谁加以任何伤害。有一次,父亲不在家,村里一位大叔为着要清扫自家屋内房顶、墙面的蛛网和灰尘,擅自到我家榕树下,用长柄钩刀砍下一杈树枝,拿回家做扫把,这事第二天被我父亲知道了,他望着树上的伤疤痛心不已,于是气冲冲地上门去同那大叔理论。
父亲对我家这棵榕树的喜爱和珍惜众所周知,但这并不等于说父亲就放任这棵树自由生长,不加修整。其实,父亲是很在意这棵树的造型和实用性的。一般来说,榕树的树枝多是横着生长的,所以往往树冠都很大,天长日久,从树杈上垂挂下来的气根还会连接到地面,扎入地下,渐长渐大,形成树干,故有独木成林的景象。当然,能够这样得有些年月,需要较长的生长期。父亲显然不想看到我家这棵树也要独木成林。不是他不喜欢,是因为家里的地盘实在不够宽,如果由着这棵树随意生长,不但要占着菜地,还可能会毁了祖屋。
我在外地工作,每每想起老家,这棵树总是不思自来,进入我的脑海里,连着祖屋,也连着父亲的音容笑貌。
2
恢复高考以后,我和老二、小妹都相继考了出来,我考取了中专,老二考上了大专,小妹进了重点大学。
我毕业后分配回本县工作,后来又参加了本科函授学习。函授毕业,便调到南宁工作。老二毕业后去了柳州,进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娶了老板的女儿,家便安在那边了,活像个上门女婿。小妹最初的愿望是去当兵,考上大学后还是初衷不改,向往军营,毕业不久即嫁了个军人。妹夫运气好,转业到了上海,并进了金融部门。小妹有高文凭真本事在身,不费什么周折也安排到了银行。
我们三兄妹都跳出了农门,在老家自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也让老爸扬眉吐气了好长时间。老人家唯一恨铁不成钢的就是三弟了。
三弟是尾儿,最受父母的宠爱。宠爱的结果,是让三弟无所事事。
父亲上过中学,只是没能读到毕业,但在他那一辈人里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父亲非常看重读书,甚至是逼着我们读书。在我们小的时候,他常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过年时他写的对联也往往是“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
三弟对读书全不上心。我们兄妹三个还没有考出来的时候,父亲叮嘱我们多教教三弟学学算术、背背唐诗。三弟坐在我们面前,浑身像有蚂蚁咬。
三弟读小学留级过一年,读初中读到初二下学期就辍学了。
那时,读大学已经不再有工作分配,毕业了还得自己找事做。读书读出这样的结果,农村人就觉得读也没用,不如早早出来打工。所以,村里有几个与三弟同龄的伙伴干脆连初中也不上了,到广东打工去了。三弟找他们联系,也去了广东。父亲无奈,他的“唯有读书高”对三弟等于古老的传说。
三弟弃学出去打工,在广东那边找工作,找了两个星期也没有着落,钱花光了便打电话来让我给他寄。
我一听就冒火,叫他马上给我回家,他听了好久没有出声。我又说,我只给你寄路费,你不回来死活我不管你。
三弟最终屈服,回了家。他回来的第二天,我也抽空回了老家。我想帮他复学,他那初中校长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不好意思只打个电话就接受人家的恩典,我得亲自带三弟去认错。
我回家,老爸当然高兴。老爸在我面前再一次把三弟骂个狗血淋头。我也跟着老爸把三弟再教训了一遍。
经过这一番折腾,三弟还是复了学。
但三弟终究不是读书的料。他初中读完了考不上高中,去读了个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汽车修理。毕业后帮人打下手干了三年多,除了死不了一个钱也没攒下。我打电话给三弟说,反正你赚不了钱,回去找个老婆跟爸妈过日子算了。
我的这个想法,正合二老的意,但三弟说,结什么婚,谁爱来我们家?人家都建了新楼新屋,我们家老土了,我要是女的都不愿嫁进来。
想想三弟说得也在理。于是我跟父亲说,我们家也建楼吧,钱我和老二、小妹分摊。
父亲说,不用建新的,这座老屋够高,好住,换些新梁新瓦就可以。
父亲大概是恋着这座祖屋,不愿毁了它。于是,我们听从父亲意见,把老屋翻新了一遍,依旧是木梁青瓦,剥落的墙面补平了灰色的沙浆,还按砖的样子划了格。我揣摩父亲的意思,尽量保持老屋的原样,参照了文物保护“修旧如旧”的原则。只是前面两间小厢房改为砖砌的了,但还是瓦盖。
老屋修好后,父亲就催促母亲抓紧托人为三弟物色对象。
然而,没等到父母相中谁,三弟却已经把自己的个人婚姻解决了。
那天,三弟从柳州回来,还带回了个大肚妹。三弟对正尴尬着的二老说,爸,妈,这就是你儿子的媳妇,叫阿香。
这阿香是个北方妹,嘴巴甜,见了我父母,未待三弟介绍完毕就问候爸好、妈好。她用的是我们家乡的方言,半生不熟的,显然是三弟提前做过了培训。看到阿香懂礼貌,人又大方,两位老人家由尴尬转为自然,由自然转为眉开眼笑。他们认了这个儿媳妇。
三弟结婚后,就不再出去打工了,夫妻两个从此待在家里务农。弟媳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对老家的生活环境适应较快,没有什么不习惯的,还逐渐学会了我家乡的方言。
有三弟在家,父母亲不再冷清,见人都是笑脸相迎。
没多久,阿香生了个女儿。婴儿的啼哭声,为父母亲带来了天伦之乐。
孙女出生三个月后,父亲轰轰烈烈地为她办了一场百日宴。全村每家每户都来人参加,我家所有的亲戚都到齐。我和老二当然不得缺席,带着老婆、孩子回来。小妹没有回,她说单位有事,她请不了假,老爸在电话里把她骂了一番。
宴席主要摆在晒场上,小院子扯盖起蛇皮塑料布帐篷,用做炒菜操作和洗碗洗筷的地方。那棵枝叶婆娑的榕树也被装点一新,挂满了红红的小灯笼。这是父亲别出心裁,学着城里的喜庆做派。
父母亲两个穿戴齐整,一会儿走这走那,一会儿又凑到抱着孙女的儿媳身边,迎候着、接受着客人们的声声赞美和祝福。
三弟这回算是做了件最对的事。他曾经带给我们的所有不快,被父亲一笔勾销了。父亲讨好地盼望三弟再生个胖儿子。
家里添了两个劳动力,租出去的田地又要了回来。
父亲依旧做着他力所能及的活,放牛、种甘蔗、晒谷……空闲下来,也仍旧爱在榕树下纳凉和听收音机,有的时候,偶尔还会传来他那不高而扬的歌声:“……鹧鸪飞过岭(哪),凤凰落吾家……”
我完全想象得到,父亲躺在树下那怡然自得的样子,那多像一幅画,一幅乡居野趣的画。而这幅画的美好意境,则有赖于我家这棵榕树的存在!
3
去年夏秋之间,我老家暴雨成灾。据说是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水。那天,雨下个不停,大水说来就来。三弟和老爸老妈以及弟媳阿香手忙脚乱地搬东西,东西尽量往高处搁置。因为没想到水会这么大,后来许多家具、粮食还是被泡了。
这场大水对我们家最大的危害是把祖屋泡成了危房。由于地基松软沉陷,祖屋东边两间房的墙面开裂,墙体倾斜,如果不是有木梁牵拉,随时都会倒塌。
祖屋变成了危房,当然不能长住了。三弟建议推倒重建,像村里别人家那样建楼房,钢筋水泥的,风雨不动安如山,不怕大水泡。我支持三弟的意见,老二和小妹听了也都说要建楼。母亲从来都是站在儿女一边,也说是建楼好,全村都建,没有哪家住瓦屋了。父亲这回不再唱反调,大概是不想逆了全家人的意吧,说,我老了,你们爱怎么建就怎么建吧。
于是,三弟着手建楼。
三弟问我要建几层楼,我说建两层吧,两层够住了。三弟匡算了一下,说建楼大约需要十来万,我没钱,你们在外工作的要分担。父母在,不远游,我、老二、小妹三个做不到,就指望三弟了。我答应三弟,我们每人先给三万。
秋收过后,天空已不再有雨,老家建楼的事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
建新楼得先拆老屋。菜园子宽度不够,不拆老屋就没有地方建。三弟到集市买回了两个大帐篷,搭建在晒谷场上,用作临时住所,其它家什也都搬出来放在旁边。
按照以前的做法,拆房子得先把瓦片和木梁卸下来,然后再推倒墙壁,如今是建楼房,那些瓦片、木梁已用不着,想卖也没有人要,所以也就不再多此一举了。三弟把拆屋和建楼的活全包给了施工队,自己倒变成了袖手旁观的闲人。
家里住的地方不成样,像是个难民户,三弟就建议父母亲带上三岁的孙女到我和老二处住上一段日子,等建好楼再回来。
父母亲以前也来跟我们住过,这时觉得在家帮不上什么忙,反倒碍手碍脚,便听从了三弟的意见。
二老先是到老二那住了两个星期,再来我这住了差不多一个月。这个时候,小妹那边搬了个新居,由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换成了三室两厅一厨两卫,宽敞多了,所以也要求父母亲去跟他们住一住,顺便看看大上海。小妹说,老爸老妈还没有来跟她住过,这回有条件了,一定要来。父母亲到小妹那里一住就住了一个月。
就是在父母亲离开老家的这段时间里,三弟做了件父亲认为最不该做的事。
三弟把家里那棵榕树给卖了。
三弟拆了祖屋,又即刻让施工队按图纸开挖新楼地基。这下子问题来了。祖屋旁边那棵榕树地下的根串到了地基下面,地上树枝树叶也显然占着楼身的位置,不砍树就建不了楼房。其实也不用自己砍,大概我家这棵树早就被人看上了,这时候有人过来问三弟,说要买这棵树,开价一万元,三弟稍懂些行情,就跟他讨价还价,最后以两万元成交,由买方自己挖树搬走。
三弟把树卖了才告诉我。
我说,这事你不先跟老爸说过恐怕不好,你这是先斩后奏,你也太自作主张了。
三弟说,屋是老爸同意拆的,楼也是他让建的,树挡着建楼还留它干什么?又不是白送人,有钱不赚傻呀?
我说,算了,卖就卖了,赶快把楼建起来,以后有什么先商量。
楼房落成的时候,父母亲回来了。
正如我所料,父亲回来后看不到那棵榕树,周边空荡荡的,一下子就铁青了脸。
这个神情,三弟自小就没有见到过,我们也是很少见过。
三弟是在当晚就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情况的。这个时候他已经被父亲骂了一个下午。
父亲骂三弟,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千不该万不该毁了那棵榕树,二是为什么不事先问过他的意见。三弟的解释,父亲听来全都是在顶嘴,三弟只好默不作声,任由父亲数落。
母亲也是喜欢那棵树的,但不至于像父亲这样痛惜,说没有就没有了,以后再种就是了。
父亲迁怒于母亲,说,这不是种不种的问题,是家的问题,村的问题,这个败家子一点都不懂。他说,现在村前村后都没有树了,光秃秃的,成什么样子,哪里是个村。要是还像以前那样,到处是树,护着村子,房子肯定不会被大水冲坏的!以前,树多,雀多,水里鱼也多,现在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可惜啊,太伤心了!
父亲说的是事实,也有道理。
在我印象中,老家那里也曾经发生过两次大水,只是洪水涌到村边,被树木挡着,再加上大家用麻袋装上泥土垒到墙头、树旁一堵,水就会绕道两边,从村前水塘和村后沟渠流过,对村内房屋构不成威胁,所以村里总是能够有惊无险地度过水灾。如今不同了,村周围一棵树也没有,洪水一来,挡都没有什么挡了,只能任由大水肆虐。
树木生态对村庄的保护作用,父亲先前也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但他对于村里人毁树建房持反对态度却是一直不变的。他说,有村就有树,有树才是村。然而,说归说,没有谁听得进父亲的话。特别是那些孩子多的人家,有了几个钱以后,都想着扩地起楼建屋,老屋宅基地不够,就只有异地而建了,于是你争我抢,你占我建,有的人家甚至为此大伤了和气。在此种情势下,只几年时间,那些曾经围着村子的树木便都一一罹难,被砍伐殆尽。
村里不再有树,我家幸有那棵榕树,这让父亲还不至于彻底失望。
可是,现在三弟把这棵硕果仅存的大树给卖了,父亲能不生气吗?
不生气,那就怪了!
我家有架老式自行车,那是父亲年轻时买的。当时全村上下仅此一部,时髦得很。现在这部车早已不能用了,钢圈生锈,牙轮断齿,链条也不知跑哪里去了,但车身尚好,车把和后座仍在,父亲就是舍不得扔掉,一直保存着。我家那么好的一棵榕树,现在说没有就没有了,父亲能不伤心,能不生气么?
但事已至此,我们又能怎么办?人死不能复生,树移了还能搬回来吗?
不能了,绝对不能了!三弟在电话里头大喊,说,钱都拿来用了,还退得了?人家自己来挖,自己来搬,你知道那树是拿去干什么吗?人家早运到深圳那边,种了,还能搬得回来?你当是小孩做生意啊!
我说,你怎么知道?
三弟说,我怎么不知道,那个买树的人跟我熟,他只是个中介,挖树时他也没有钱给我凑齐,只给了一万,树送到深圳那边了,他拿到老板的钱了,才再补送来给我一万。
我说,原来你做事这么马虎啊?不怕人家骗了你?
不怕的,我有他电话,也知道他家住哪里!三弟接着求我说,大哥,你回来一趟吧,帮我劝劝老爸。
第二天一早,我告个假,开车回老家。
我心里想好了个办法。榕树卖了肯定拿不回来了。人挪活,树挪死,我们若再把它搬回来,绝对是瞎折腾,我们不懂技术,那树必死无疑,这一点要向父亲说清楚。人家懂技术,才敢挪,也挪得了,而且能够保证把树种得活转过来。如果这样讲还说服不了父亲,我还想换个角度去劝他,我们家这棵树在农村活了几十年,现在是去了大城市,是全国最开放发达的地方,是时来运转了,富贵显赫了,这对我们家是个好兆头,我们应该高兴。只要那树在那边种下去,种活了,就是好事、吉庆的事。如果不相信,父亲可以亲自去看一看,看了再说三弟做得对不对。
我猜想,那树肯定种活了,说不定已经发了新芽,长了新叶,只要父亲听得进我的话,就可以化解他同三弟的矛盾了。如果听不进,或者半信半疑,大不了,就带他去深圳那边看看,眼见为实,包他放心。父亲老了,但还能行走,若有机会带他出去走一走,让他在有生之年多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也算是尽了我们做儿女的本分。
回到老家,还不到晌午。眼前所见一片零乱:那棵老家标志性的大榕树当然不见了,刚落成的两层新楼旁无所依地兀立着,菜园子有一半遭了践踏,泥块、砖头、砂浆杂陈,用作围墙的荆条也被打开了好长一个缺口,一切都显示出重新再来的样子。我悄无声息地绕过新楼,走到屋前的晒场上,看到母亲正在喂孙女吃红薯,阿香在临时厨房里烧火煮什么,没有看到三弟和父亲。我问母亲,母亲说,三弟早早出去放牛了,你爸那个老不死的,刚刚还在,不知转哪里去了。
我送小侄女一袋糖饼,便去仔细参观新楼房,看到底建得怎么样。
我在二楼看到了父亲。父亲其时正在拣拾整理房间内的砖头、木片碎块,嘴里叼着烟,神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金刚怒目,已经完全是我往时见到的模样了。
我打招呼说,爸,你不用理这些东西,这由工匠来做,去歇着吧。
父亲回头看见是我,说,回来了?早回来就好了,你三弟那个盲头虫,也不至于毁了那棵树!
我心里打鼓,但还是笑着说,这楼建得不错啊,够宽敞,够大气的。
父亲说,是不错,就是旁边没有了树,总觉得缺了什么。
我说,我也觉得是,家里有棵大树多好!不过呢——我望着父亲,见他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才接着又说——我听三弟说,那棵树地下的根太长太大了,不挖掉它们,这楼地基就不牢,再说,树也傍着屋,截了根,风吹倒下来怎么办?三弟也曾想挪到菜园那边起楼,可那里位置又不正,所以就……
父亲叹了一声,说,算了算了,楼都建起来了,还能怎么样,只是,太可惜那树了,也不知它能不能活得下去。
我说,放心,现在什么技术都先进,没有种不活的树。何况,我们家这棵树是去了深圳,是去了好地方、大地方。
父亲的眉头舒展了开来,脸上也有了笑意,说,能够这样子也好,也只能这样子了,那树要保管活,千万别整死了。
我说,死不了,绝对死不了!你若不信,可以找个时间去看看,深圳离这也不远。
父亲有些不信,说,屁,那种大地方,你知道人家把树种在哪里?找不到了,还能看得见?看不见了。
我说,怎么看不见?三弟知道人家送去哪里,问问就知道了。
父亲一脸灿烂起来。他低头想了想,最后说,是得去看看,也怪想它的。
临近吃午饭时,三弟放牛回来了。他看见我同父亲坐在晒场上欢欢喜喜地说话,知道我做通了工作,一块悬着的石头从他的心上落了下来。
带父亲去深圳看看,原本只是我想走的第二步棋,现在看到父亲心情这么好,这么理解儿女,我决计要让父亲和母亲去一回深圳了。
但由谁带二老去呢?老二是指望不上的,小妹又太远,我也没空,那只有派三弟了。
吃午饭的时候,我乘兴把这事安排了,说深圳那里有个“世界之窗”,三弟你顺便带老爸老妈去看看,相当于出国旅游了,便宜了你这小子,做错了事还能捡到好处捞。
三弟犹豫说,哥,我装修,这屋,你看……
我向他使了个眼色,说,外墙做完了,架子也拆了,不就是铺铺地砖、抹抹内墙嘛,你买好材料给工匠,不就成了?出去又没用几天,飞去飞回两三天也就够了,我叫深圳的朋友接送你们。
三弟看了看父亲,父亲正伸出筷子将孙女嘴里掉在桌上的一颗米饭夹起来。三弟说,好吧。
就这样,父亲从上海回到老家没待上几天又再次外出。他一辈子没坐过飞机,来我这和去老二那坐的都是班车,去小妹那里坐的是火车,一方面是嫌坐飞机贵,二个主要是母亲不敢飞上天。这次,我咬咬牙,打算多支几个钱,要让老爸老妈尝试一下坐飞机的感觉,享受享受一回。但母亲还是不敢坐飞机,也不愿再出去走,于是留在家里同三弟媳阿香一起照看房屋装修。父亲由三弟陪着从老家坐快巴出发,我到车站接了直接送机场飞深圳。我朋友在那边接机,帮安排食宿和出行。
4
那天,父亲和三弟到深圳后,我那朋友把他们接出机场,找地方吃了个便餐,就直接去了宾馆。其时,深圳那边正下大雨,雨脚如麻,积水满地,哪也不方便去,所以不如住下来好好休息。
第二天雨不下了。父亲和三弟早早起床,洗漱拉撒收拾行李,专候我朋友来接。
将近十一点钟,朋友才来。得知父亲和三弟早早起了床等候,便连连抱歉说照顾不周,然后问今天是先去“世界之窗”还是去哪里?
我父亲说,去看树吧。
于是,三个人坐上车直奔种树的地方而去。
来前,三弟向那买树的中介问了栽树的地点,跟我朋友说了,那是个公共场所,朋友知道,所以并不难找。
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父亲他们到了种树的地方。
这是一处新开发、新改造的商住区。十几二十幢摩天大楼错落有致地簇拥在一起,中间挖掘出一个人工湖,湖上曲桥卧波,把湖面分割成一大一小两块,湖岸四周辟为市民休闲游乐功能区:西面用作儿童乐园;东面是广场;南面建有凉亭、走廊供人休憩;北面为不规整的坡地,种着草皮,点缀着奇石,移栽有各种大树。我家那棵榕树就移种到了这里。
父亲来到这里,寻来寻去的,就是找不到自家那棵树。三弟也同样找不到。
这里没有铺天盖地、枝繁叶茂的大树。所有的树都截去了枝杈,仿佛被砍了头砍了手一般。有的还包扎着草绳、挂着水瓶打点滴,有的在树的根部斜插着手臂一样粗的塑料硬管。父亲看着这些受伤的树木,就像看着满营伤兵,有悲无喜,感同身受。
三弟怀疑是看错了地方,于是打手机再问那个中介,中介确指是找对了地方,并且说移栽的树都是这样的,不砍去枝叶就运不走,也种不活。
三弟似懂非懂、半信半疑,就地继续寻找。
终于,在中间稍为凸起的地方找到了我家那棵树的影踪。
三弟急忙招呼父亲过来看。父亲其时正无精打采地弓腰坐在一颗滑溜的大石头上吸烟,听到三弟的喊叫,便即刻站起来,循声径直走上去。将近那树时,父亲却又站定了,先是用疑惑的眼神张望一番,足有两分钟,之后,才慢慢地走过去,审视着绕树一周,然后停下来,伸出颤抖的像干树枝一样的手,轻轻地抚摩树身,嘴里不停地说:“造孽啊!造孽啊!造孽!”
父亲抚摩的这棵树犹如一根盘龙柱,有水桶那么粗,高约两米一二,所有的枝桠几乎都齐根砍了去,直挺挺地裸立在那里,无语问苍天。
这无疑是我家那棵榕树的树身。父亲早年把树桠上长出的根须集蔟到一起,绕树而下,特意制造的那条“龙”仍然攀盘在树身上,粘连为一体,颜色依旧,“鳞片”依然,只是“龙首”已不知所终。
父亲说过“造孽”之后就再无言语,眉头紧锁,双目微闭,神情无奈而沮丧。也许,他正在缅怀,正在追思,正在痛惜,正在愤懑。他的脑海中,也许正活现着那棵已经逝去的榕树。它,深深地扎根在我家的祖屋旁,高擎如伞,浓密的枝叶间鸟鸣啾啾,高低错落的遒枝四向伸展,父亲把鸟笼挂在树枝上,把吊床拴在枝桠与枝桠之间,烈日晒不到,小雨打不湿,那些鸡啊、鸭啊、鹅啊,在树荫下无惊无扰地觅食或者打盹——可是,所有这些,现在都已不复存在……
三弟看见父亲这个样子,便想安慰老爸。他仔细地察看这棵与其说是树不如说是木头的树干,希望能够找到一丝惊喜。果然,他找到了,在树的顶部,一条断臂一样的枝桠下方。他兴奋地用手指指上去,说:爸,你看,这树出芽了,活了!
父亲抬头望上去,什么也看不见,以为三弟是蒙他,于是喝声说:活你个头!走,不看了,回去!
父亲说着转身就离开那树,向停车的地方走去。
三弟紧步跟上来,问:去哪里,爸?
父亲不答,只管走。
我朋友没有陪我父亲和三弟去找树,老是在打他的手机或者接听手机,见我父亲走来,便问:看完了?那我们就换地方啰?
父亲说:哪也不去了,回去。
朋友问:回宾馆?
回家!父亲没好气地说。
三弟觉得父亲那样冲我朋友说话有些失礼,忙接过话说:刚来就回去呀?我还想去看“世界之窗”呢!
父亲剜了三弟一眼,说:看什么看,回去!你个盲头虫!
那我要问大哥看看,原先是怎么安排的。三弟不甘心白来深圳一趟,什么特色的东西也看不到就回去,于是抬出我来想劝阻父亲。
父亲狠狠说:问什么问?你们两个,一路货!
回就回!三弟顶了父亲一句,便请我朋友送他们到机场,买票飞回来。
这就是父亲去深圳的全过程。
我原本要让父亲出去寻开心,没想到却找来了伤心!
5
从深圳回来,父亲和三弟在我南宁的家住了一晚。
我家是三房一厅。我儿子上大学不在家,正好让父亲和三弟一人住一间房。要是儿子在家,三弟就只能睡沙发了。
父亲不喝酒,与我们不说话,无声无息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早起来,独自出门去了。
我起床时,三弟还蜷曲在小床上鼾声如拉断锯一般。父亲出门我不知道,他肯定也不知道。我由房间到卫生间找不见父亲,只好把三弟推醒。三弟急急忙忙掬水洗脸漱口便跟我下楼去。
我和三弟下了楼,来到小区的花园,一眼就看到保安正在训父亲。父亲像个做错事的冥顽小孩,笑非笑、哭非哭地低头站在那里,任保安呵斥。我们迅速跑过去,我问是何原因,三弟伸手就想推那个保安,被我拦住了。
原来,父亲走在花园里,尿急了,就站到花带旁撒尿,被保安及时发现了,所以训他。
父亲平时是个很保守的人,讲究公德和礼节,怎么就变得这样随便,这样不知羞耻了呢?
我向那保安道歉,随即把父亲带回家。
家里,老婆刚煮好面条。我让父亲去洗手,然后吃早餐。父亲不说话,像个乖孩子,端起碗来就吃,吸溜吸溜的声音很大。老婆看了我一眼,我看了父亲一眼。父亲的样子——他眼里兴许就没有旁人了。
三弟三下五除二扒完了他那碗面,便悄悄对我说,哥,爸的样子,看来是病了,你带他去医院检查检查,我先回去装修房子,得空了我再来接他,或者你把他送回去。
我接口说,我也没空,不过,万事爸为大,你也不要急着回去,我请个假,我们一起陪老爸去看看,看了再说。
我和三弟带父亲到医科大,做了心电图,做了胸透,量了血压,七七八八的检查了好多个项目。最后,医生说,我父亲什么问题也没有。
我和三弟听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从医院出来,我和三弟顺便带父亲到南湖公园逛逛,有意让父亲看到那些移栽的树木。我推想,父亲心中有郁结,那郁结可能就是因为树。
我和三弟指着一棵又一棵形形色色的大树,向父亲介绍,说这些树都是从别的什么地方移过来的,现在长得又青又绿又好看。
父亲终于开口说话。他说,移就移嘛,非得要砍去那些树枝?
我说,不砍呢,反倒种不活。
父亲说,我就不信!
我把父亲和三弟送到车站坐大巴回老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看过父亲,关于老家的情况,关于父亲,我只能时不时打电话向三弟了解。
三弟说父亲已无大碍,只是比以前老态了一些,也沉默多了,有时还丢三落四的,记不了多少事情,再也不能放心给他做事。三弟开玩笑说,现在牛都不愿意给父亲去放了,说不定哪天不是牛不见了,是老爸自己把自己搞丢了。
我想想,父亲可能是得了轻度老年痴呆症。如果加重,那就更麻烦了。这种病现在比较常见,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农村也偶有所见。父亲的症状,分明就是这种病了。细究原因,这十有八九跟三弟毁掉我家那棵榕树有关系。父亲的心情,父亲的性格变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是三弟的错,也是我的错!但错就错了,后悔的药是没有吃的。我希望三弟能早日生个儿子,这样,我家就再种一棵树,不,就直接种一棵大树,让父亲看着高兴,盼着高兴——说不准,他的病就好了。
然而,非常痛心,非常遗憾——父亲他等不来这个让我们弥补过错的机会!
在我老家推倒祖屋、建了新楼的第二年,也就是我下去挂职的第十四个月,父亲爬上楼顶,去喂一只不知从哪里飞来的麻雀,摔下楼,去世了。
我闻讯,不顾一切从数百里之外赶回老家奔丧。
我到家时,父亲已经入殓,厚重的棺材搁在厅堂中间,用碗做成的油灯置于地上,火光如豆,我与父亲已阴阳两隔。
我端详父亲的遗像。相片中的父亲,眉开眼笑,嘴巴微张,我仿佛还能看到听到父亲一边在劳作,一边在歌唱:“牛吃江边草……”
我止不住泪眼朦胧……
又再过两年,三弟果然生了一个大胖儿子。
三弟有了儿子,三弟高兴,阿香高兴,母亲高兴,我也高兴,全家谁都高兴。
我想到了父亲。我对三弟说,你生了儿子,赶快种一棵树吧,看看种在哪里,我看种在屋边就最好,像老爸以前那样。
电话那头,三弟大声回答我:大哥,你神经病啊?现在还有谁生了小孩要种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