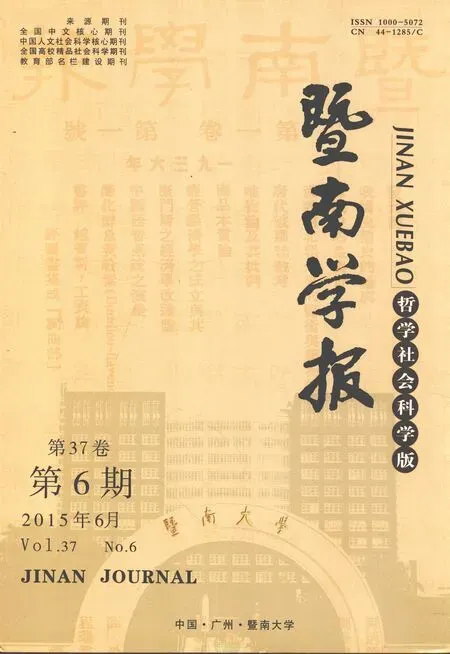前近代以来民间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和影响
陈碧芬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社会救助是近代社会才出现的概念,它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生活出现困难,基本生活无法维持时,由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物质援助和服务的一种社会活动和行为。其实,中国传统社会类似的大量社会救助活动和行为早已有之,它源远流长,影响广远。上古时代,《礼记·礼运》就为人类社会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归宿:“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其亲,不独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强调历代统治者必须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尤其是对那些丧失独立生存能力和基本生活所需的社会成员,要实施一定的社会救助。在追寻这一理想社会的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救助实践活动。
前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加剧,社会矛盾凸显,灾荒频繁发生,人类抵御各种灾难的能力尚弱,单纯的官方层面的社会救助已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的需求。民间社会救助凭借直接、灵活、方便、有效的特性,成为配合甚至填补官方救助活动的重要形式。这时,传统的“立君养民”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趋势,政府不再被认为是社会救助的唯一主导,“以民养民”论大量出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已发展壮大的地方社会力量——富民阶层被动员起来或自发地行动起来,承担起救助困者、贫者、弱者的主要责任。与此相对应,民间社会救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学术界对前近代时期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内容涉猎已多,本文拟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前近代时期“养民”思想的变化及民间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等内容进行探讨,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前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的轨迹。探讨前近代民间社会救助的实践活动,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民间社会救助活动兴起的表现
在中国传统社会,每当发生大范围的饥荒、灾害时,往往需要政府很好地发挥救助功能,用于解决民众的基本生活问题,维持社会的稳定。前近代时期,虽然政府也极为重视地方社会的救助事业,但各种官办的社会救助机构,往往仰赖地方富民的田银捐助才得以维持。并且官办机构在经营管理上容易滋生弊端,如果再遇上政府财政空虚,必不能对地方上出现的困难提供正常的财力支援,所以,在地方基层社会,政府的救助能力日益弱化,救助功能日益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民间自帮、自助、自救、自恤的社会救助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这里所说的民间社会救助活动,是指由地方社会自发举办,对因各种原因导致的生活处于困境的成员提供物质援助的行为。施济行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行为,不过长期的、持续的由地方社会力量筹集资金,大量举办社会救助活动,甚至建立、管理民间基层社会救助组织,则是前近代以来比较突出的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前近代时期的民间社会救助在秉承中国社会传统的同时也有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表现形式。
(一)民间举办的仓储形式日益占据主要地位
建立各种仓储,积极备荒是我国古代传统社会实施社会救助的一种重要方式,其种类繁多,功能各异。前近代时期,主要的仓储形式有官办的常平仓,民办的社仓、义仓等,它们平日积粮,灾年救济,相互补充,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备荒救灾体系,对保障民众生活、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
常平仓、社仓和义仓都是通过建立仓库储存粮食,在灾荒之年或青黄不接时,出仓以赈济百姓。但在备荒救灾的实际过程中,因为官办仓储与民办仓储各自设立和运行的特点不同,它们在救助民众的作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民办仓储的优越性、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
它们在设立地点上有所区别。“由省会以至州郡俱建常平仓,乡村则设社仓,市镇则设义仓。”可见,“常平仓”一般设于省会、州县及其附近的城市,受资助对象自然是这些地区的居民,乡村及边远地区的民众,因为受到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不容易得到救助。而社仓和义仓广泛建于乡村或市镇,“在城居者,或设仓于祠堂以周宗族,或设仓于近境以济邻人;在乡居者,或各堡创设之,或一都合力为之。”直接面对的就是乡村地方社会的民众,他们不论是数量还是贫困程度,都应成为社会救助的主要对象。社仓、义仓等仓储形式就成为整个国家仓储体系的重要内容。
它们所储存的粮食来源也有所不同。常平仓是储存官府筹集来的粮食;社仓是储存当地民众聚集来的粮食或是官府贷给的粮食,义仓是储存乡村各种社会力量义捐的粮食。官仓的谷源由官府提供,发展受政府财政状况好坏的影响。社仓和义仓的谷本易于筹措,来源充足,日益成为各地备荒积谷的主要渠道,政府也极为重视。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 年),明廷“令各郡县立社仓备赈。”嘉靖八年(1529 年),又“令各抚、按设社仓。”清康熙十八年(1679 年)亦倡导各地广立社仓、义仓,“在乡村镇店内有古寺庙及空房,百姓自立社仓、义仓,该地方官每年秋收之时,劝谕各土著乡绅士民商贾,不论米谷多寡,捐输收贮。”民办民营的“社仓、义仓不可不广”,承担起积谷备赈的重任。时人有评:“官仓,盖发官银以籴者,此必甚丰乃可以举……社仓,盖收民谷以充者,此虽终身皆可以行。此两仓者,社仓举之甚易,而效甚捷。”
它们的救助方式最为不同。常平仓由官方办理,主要是把官仓储存的粮食平价卖出,调节粮食价格,避免因灾荒发生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但开仓时程序颇为繁杂,必须“详报踏勘,往返察验,未免后时”,往往错过灾荒救济的良好时机,“远者艰于跋涉,近者亦难于守候,徒为奸胥一二无赖之徒之利,而民鲜沾实惠焉。”民办仓储则能弥补官仓效率低、受益慢之不足。社仓是官方倡导、民间办理,以借贷的方式解民众生活的“燃眉之急”,一般是“春借秋还”。义仓纯粹由民间自发举办,是无偿赈给,所以最为便捷有效。所谓“各省社仓为粮户借放而设,义仓专为赈恤之需。”社仓的“及时”、义仓的“无偿”能够直接使灾民受惠,“各济各坊,随投随给,其周之若烛照,而予之如取携”,在地方基层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办仓储存在的弱点、问题日渐暴露出来。一是因为地方有司的侵夺,仓谷多被侵盗、挪用,导致官办仓储废弛,出现“谷散不收,甚至掩为己有”,粮食得不到有效贮存等问题;或者官吏营私舞弊,管理混乱,使本该得到救助的对象得不到救助,本该偿还粮食的人却不去偿还,即所谓“凭为奸利,给散之际,饥民不必予,予者不必饥。收敛之时,偿者非所受,受者不必偿”,造成粮食补给不足,仓储有名无实。二是因为官办仓储兴废无常,管理不善,粮源无着,“预备无粒米”,导致官办仓储粮食的筹集不得不大量地依赖于民间的捐助,不得不依靠民办仓储来缓解官方救荒的困境。面对官办仓储不能有效发挥灾荒赈济作用的情况,真正由民间自筹、自营、自管、自救的“义仓”就得到了大力提倡和推广。如道光初年安徽巡抚陶澍在“劝设义仓章程疏”中就指出:“惟有于州县中每乡每村,各设一仓,秋收后听民间量力捐输,积存仓内,遇岁歉则以本境所积之谷,即散给本境之人。一切出纳,听民间自择殷实老成管理,不经官吏之手。以冀图匮于丰,积少成多,众擎易举,所以图便于民也。”
(二)各种民间社会救助组织的兴建
在中国悠久的民间救助活动中,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历朝历代都创建过一些民间社会救助组织。但它们的大规模出现,则是宋以后尤其是前近代时期。梁其姿就指出:“俗世的慈善机构,普遍地出现在宋代以后,明末以来,又是另一段变化激烈时期,而此时出现的民间慈善机构也就更盛况空前。”
前近代时期,官府层面的社会救助因为政策的失效、政府的无力监督、官僚的贪污舞弊等问题,对解决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困难已没有太多实际上的保障。相反,各种社会力量从稳定地方秩序、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目的出发,纷纷兴建救助机构或团体,种类繁多,针对不同的施救对象设立有不同的专门救助机构,在诸如赈饥救荒、扶弱解困、济贫恤穷、养老慈幼、优待抚恤等方面都十分活跃,在一定范围内为社会上的困难群体提供帮助,从而推动中国传统社会救助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有组织的社会救助机构,以各种善堂、善会最具代表性。善会是以推行善举为目的的自由结社,而善堂则是善会办事机构的所在以及具体实施善举的设施。善会、善堂从明末开始出现,此后一直存在于各地的城市或市镇之中。梁其姿利用两千多种方志对整个清代的慈善组织作过一个统计:育婴组织先后共成立了至少973 个,普济堂399 个,清节堂类216 个,以施棺为主的善会善堂589 个,综合性的善会善堂338 个,其他难以分类的743 个,这些慈善组织遍布全国。对贫者给食,寒者给衣,孤者给养,老者给留,饥者施粥,寡者施援,病者施药,死者施棺,同时施以道德教化,教人为善。还特别设义塾代教贫苦子弟。《苏州俞问樵捐松筠家庵于轮香局用作殡舍碑》中有载:“吾苏全盛时,城内外善堂可偻指数者不下数十。生有养,死有葬,老者、废疾者、孤寡者、婴者,部分类叙,日饩月给,旁逮惜字、义塾、放生之属,靡弗周也。”可见其功能多样,所涉及的救助对象和范围较广。“这些善堂有官办的,有民办的,也有官倡民办或民办官助的……从实际情况看,官办善堂虽然创建时间早,延续时间长,但大多时建时毁,管理不善,效果不佳……民办善堂的规模要小得多,但数量繁多,种类齐全,遍布城乡各地。”从而对基层民众的生、老、病、死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社会救助。
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竞争的加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生存压力的加大,对此深有感触的富裕工商业者往往会依托会馆、公所,积极为同业或同业的外地同乡中的破产者、失业者、贫穷潦倒者、疾病缠身者、无家可归者等举办各种社会救助活动,这同样是前近代民间社会救助活动中比较重要的方面。其救助的内容也相当广泛,有对贫困失业者的生活补助问题。如绸缎业七襄公所规定:“有异乡远客贫困不能归里者,由各肆报之公局,令司月者核实,于公费中量为资助。”有解决年老孤苦者的赡养问题,如圆金业兴复公所规定:“至年老无依,仍照旧章,公所养赡。”有处理同业人员逝世的善后问题,如创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的陕西会馆“建普济堂,以妥旅榇。”有为失业人员创造就业机会的,如兴复公所规定,“经同业公议,停收学徒,俾使失业各伙,即可设法安插,不致有流离失所之苦。”有为同业子弟提供就学机会的,如石业公所“设知新蒙小学堂一所”,“延师教授同业子弟。”它们所发挥的救助职能,学者早有评论:“苏州的许多行会都把举办慈善作为第一要务,甚至有的行会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互助。”当然,这主要发生在一些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因为那里财富力量集中,有实力进行救助。会馆、公所借此可以沉着应对突发状况,缓解社会矛盾,还可以强化同乡和同业的凝聚力,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
(三)地方宗族组织所发挥的特殊救助作用
“患难相恤”,在讲究血缘、社会组织不发达的传统乡村社会,宗族组织的救助功能更为显著。当族人因天灾人祸家庭面临生活的窘境时,宗族就会通过各种手段积极开展族内救助活动。
自范仲淹创范氏义庄对族人实施救济以来,设立义庄便成为宗族内部互助互济的一个典范。前近代时期,宗族义庄的设立有明显的扩大趋势,数量多,规模大,清代更有“义庄设普天下”的说法。义庄在社会救助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宗族内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族人实施救助的对象相当广泛,内容相当全面,涉及救灾、济贫、收恤、养老、助学、助残、恤病、送葬、婚嫁等各方面。在地方志中,有大量这方面内容的记载,如:汪氏诵芬义庄“同族繁衍,或贫乏不能自存也,将使寒者衣之,饥者食之,婚丧赈助之,才优而秀达者又奖励而裁议之。”又如《济阳义庄规条》中规定下列情况者受到不同程度的抚恤:一是“贫老无依,不能自养者”;二是“族之贫乏无依,三十以内苦志守节者”;三是“族之贫乏幼孤男女者”;四是“族之贫乏废疾,无人养恤者”;五是“间或势处极贫,因病失业,人尚安分,子女多而命运不济者”;六是“族中无力成殓者”;七是“族中无力婚嫁者”;八是“族中生育,极贫苦之家。”在“睦族敬宗”的旗号下,这些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宗族很自然地联系起来,要么提供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援助,要么收恤孤老独幼,要么资助婚丧嫁娶,要么资助贫困族人的日常教育,要么资助参加科举考试,他们互助互济,共同抵御自然灾害或社会变故带来的困窘。所以,有学者指出:“前近代时期,义庄作为宗族组织的经济实体,已经超越了偶发的、单纯的济贫性质,而具备了初级形态的社会救助性质。”
在乡村社会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下,以血缘认同为基础的地方宗族社会救助活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同族贫者、困者的物质生活条件,缓和了同族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成为宗族团结、救济、控制族人的重要手段,在民间社会救助活动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二、民间社会救助活动兴盛的原因
前近代民间社会救助活动如此兴盛,是与前近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富民阶层的发展壮大桴鼓相应的。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许多事情政府无力直接插手,不得不依赖民间的社会力量。而经济发展导致的民间财力增加,也为其插手民间社会救助事业提供了可能性。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客观背景。
商品经济在唐宋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持续的发展,形成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农业方面,耕地面积大增,土地被尽量利用,经济作物种植专门化,为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农业经营方式发生改变,商品性农业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手工业方面,生产技术较前代有了更大的提高。尤其是江南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手工业脱离农业,走向独立发展道路的情况更为明显,出现了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家庭,形成了新型手工业工场。商业方面,出现了不少工商业发达的城镇,白银货币化过程完成,商品的交换地域也从地方市场走向跨区域市场以至海外,商业资本空前活跃起来。商品经济极大地增长,社会整体趋向商业化,无论在城在乡,社会各阶层基本都与商品生产和商业交换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以不同的方式投入到商品活动之中。
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财富的增加,与前近代民间社会救助事业数量多,规模大,经费充足,救助功能齐全这样的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当时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民间社会救助活动越兴盛,因为其背后必须有强大的社会财富力量作支撑。商品经济发达的事实,就成为民间社会救助活动坚实的物质基础。已有研究表明:前近代时期的民间慈善事业,以江南地区最为突出。由于清代江南地区士绅势力较强,加上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各府县普遍设立了以地方士绅或有力者为主体的慈善机构和团体。江南地区的慈善机构不仅数量多,而且表现出种类齐全、财力充足、参与阶层广泛、活动经常等特点。前近代经济发展较强劲的苏松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范围和层级的“乡村救济网络”。
但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贫富分化的加剧,尤其遇到天灾人祸时,如果不对贫者、困者进行及时的救助,必须引起极大的社会动乱,从政府到民间,对此都深有认识。所以,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也是民间社会救助活动兴盛的客观背景。
前近代时期,土地买卖异常频繁,社会变动激烈,家庭贫富兴衰无常,财富不均,贫富分化不定。“人之贫富无定则田之去来无常”。对此,何良俊说得更为明确、具体:“(正德以后)诸公竞营产谋利……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然不五六年间,而田宅皆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然此十万之业,子孙纵善败,亦安能如是之速,盖若天怒而神夺之然。然一时有此数家,或者地方之气运耶,或诸公遗谋未善耶,皆不可晓也。”经营土地者如此,经营商业的也不例外。如顾炎武所说的:“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贫富差异的悬殊,历来是中国传统社会动荡的一个根源,前近代时期也不例外。当时,土地兼并加剧,社会“逐末”之风盛行,贫富差异加大,一部分人依靠自己的政治地位或才干等发财致富,更多的人则沦为家徒四壁的贫民,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对抗更加尖锐起来。当政府无足够的经济实力来调解这些矛盾时,很大程度上就需要民间社会力量利用各种社会救助手段来调和矛盾,富民、乡绅出资举办各种社会救助活动,就成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有效的缓冲剂。
第二,政府的大力提倡是民间救助活动兴盛的加速器。
利用民间社会力量实施各种救助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减轻了政府的压力,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因而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提倡、鼓励和支持,从而加速了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救助事业的发展。政府对民间社会力量参与的各种救助活动都加以劝促,尤其是灾荒发生,政府财力有限,仓储空虚废弛,亏空严重,入不敷出,赈济不及时,就会有针对性地劝谕富民之家捐、借钱谷,对穷民进行赈贷,以民救民。如洪熙元年,“直隶常州府奏武进、宜兴、江阴、无锡四县去岁水涝,田谷无收,民缺食者二万九千五百五十余户”,就“劝富民分借米麦二万九千九百九石有奇赈之”。
作为奖励,国家会予以适当的表彰,以扬其德,提高其政治、社会地位。如为酬答富民的仗义疏财,国家会采取名誉上的奖励和徭役上的优免,对他们“赐为义官”、“奖为义民”,“免本户杂泛差役”;或“给与冠带”;或给予“竖坊”、“置匾”等旌表,以此扩大他们的影响,提高他们的声誉。
国家还会采取向富户出售官职这样的有效手段。如成化二年(1466 年),为了赈救应天、凤阳的饥民,总督南京粮储都御史周瑄言:“移文江西、浙江并南直隶儒学,廪膳生能备米一百石,增广一百五石,运赴缺粮处,上纳者许充南京国子监生;民纳米一百石者,于本处司府州县充吏,三考,赴京授予冠带。”对于这样的建议,明宪宗“以所言皆救荒防患急务,悉从之”。又如在明武宗时,富民纳粟赈济在千石以上者“表其门”,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授散官,得止从六品”;世宗时,“义民”捐谷二十石者,即给冠带,多者授官正七品,达五百石的“有司立为坊”。历代清帝也屡颁诏旨,劝谕官绅富民捐输。如清政府于雍正二年制定了奖励措施:“有司劝捐,不得苛派,所捐之数,立册登注,不拘升斗,如有捐至十石以上者,给以花红,三十石以上者,给以匾额,五十石以上者递加奖励,其有年久不倦,捐至三四百石者给以八品顶戴带。”
利用义民旌表制度鼓励富民出赈能缓解粮食短缺现象,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如嘉靖时,“岁大饥,贫民竞起攘夺,里门多闭。冕倡义出赈,一境贴然。”义民旌表作为一种道德表扬,能够倡导人们急公尚义,激励时人,感召后人,持久地起到社会救济作用。清人就根据切身体验,对义民旌表的激励作用曾给以积极肯定:“有是义举,朝廷旌之,邑乘之,父老传之,后世颂之,人亦何惮而不为义哉?”
国家和政府的这些鼓励措施,既保证了富民的利益,也让一般民众得以生存,并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周文英提出:以富户为征资对象,把自愿出资和奖励结合起来,“于浙间富户内,不以(论)是何户,计劝率百十家斟酌远近,功绩巨细,照舍粮赈济饥民例,优以官禄,拟定功绩品级,令其开浚”。由富民承担工赈之费并负起督率之责,实质是动员和利用社会上大量私人资金兴修水利,由民众自行生产救灾,而无须官府出资和组织。政府广泛运用社会力量出资救困救灾,赈灾济贫,在其中加以组织、引导和奖励,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得以充分发挥在基层社会的救助作用。
第三,“以民养民”的社会普遍价值认同是民间社会救助活动兴盛的催化剂。
道德伦理中“善”的因素,贯穿于中国传统时代社会救助的一切实践活动中,它深入人心,在中国持续了数千年,在中国人心中已积淀成为日常生活习惯。前近代时期,富民阶层在基层社会的一系列社会救助活动,被认为是最具善心的举动,他们因此也被称为“善人”,从而被寄予可以承担养民重任的厚望,社会上由此兴起了“以民养民论”。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来强调的都是政府、君主对社会弱者的救助责任。但到了前近代时期,伴随着富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传统的“立君养民”观念有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势:即普通的民众基本生存除依赖于国家的保障之外,还要依赖于一部分特定的社会阶层——富民阶层,把对困者、贫者的救助看作是这部分人的责任,这就是“以民养民”论。它们为民间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提供了思想基础,成为地方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如果说财力充足是实施基层社会救助的物质前提,那么关于充分发挥富民阶层养民作用的议论则成为民间社会救助兴盛的思想催化剂。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公室日贫”、“私室日富”,在财富多集中于富民阶层的情况下,政府对地方的资助乏力,只能依赖民间自助,以民养民,以富助贫。富民阶层不仅是国家的支柱,更是基层社会“小民”之所赖,普遍的民众需要依赖富民,贫者、困者更需要依赖于富民。他们凭借占有的社会财富,充分发挥着“养民”的作用,成为稳定传统社会的基石。时人对此形成了一些共识,认为治理基层社会,就应当“使富民出粟以养平民,贫民出力以卫富民,此其常也。”因为“以官养民,其养有限;以民养民,其养无穷”,所以“富民者,贫民依以为命者也”;“富民者,贫民之母”等议论已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它被落实到实践当中,就是要求富民阶层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救助活动,完成养民的重任。
如当时的宗族就普遍认为族内富民在对灾害和社会弱者的救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效。广布于全国各地的“义门陈氏”认为,“宗族邻里贫富不同,富之济贫,古道也。贫者窘迫称贷,我当即与之,以济贫急,勿责之以相偿之期,听其自来……至于有疾病也,扶之;有死丧也,济之;有横逆祸患代之驱逐之;有冤抑莫伸者代为辨白之”。南关许余氏规定:“每遇荒年,如既无义仓又无祀租可拨,族长、祠董会计合族富户捐资以保合族贫户,断不至家家赤贫,家家无粮。务求一族之富人能保全一族之贫民,不使一人独受饥寒。富者有钱出钱,有谷出谷。倘明明有钱有谷,为富不仁。凡以上各条从中违拗,以致祖训家政徒为具文,贫民求生无路,则由本族持此谱呈官求究,以不孝不义之罪治之。”采取富户帮贫户、富者济贫者的做法实施族内救济,并对为富不仁者予以制裁。
对于基层社会的民众来说,富民如果吝啬于周济其他成员,就会受到来自乡村舆论的巨大压力,其后果自然是被孤立。例如富民若不向社仓输谷,则“即书某人名,加以‘顽吝’二字,贴社仓内”,并“罚令出粟,倍于常格”。甚至还针对不恤邻里的吝啬富人编排出一些遭报应,祸及子孙的阴德故事。所以,富人只有博施济众,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富贵地位,吕坤就说:“若能约己丰施,专务济人利物,则阴德可及子孙,福泽可以常享。”要求富民调有余以补贫民百姓的不足,做善事,得名誉,以此谋求子孙后代常享富贵,地方政府也会为其树碑立传,留名青史。
第四,以富民阶层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力量的主动积极参与是民间社会救助活动兴盛的原动力。
政府以明文诏令或具体政策积极倡导、鼓励利用民力,在推动民间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富民阶层的经济势力越来越雄厚,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从稳定地方社会、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目的出发,开始自觉、自愿、主动地参与到社会救助行动中来,无偿性地捐粮、捐钱、捐物救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在灾害救济、济贫恤穷、扶弱解困、养老慈幼等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使得民间的社会救助往往表现为一种富民事业,这不仅成为富民的义务,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他们的责任,收到的效果也比较显著,从而成为推动民间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原动力。
他们积极参与仓储系统的建设,如社仓的设立,“出之于民,而藏之社,社立正副,每月朔为会,社正率属读高皇帝教民榜申,以同盟之约,举众中善恶奖戒之,记其社米户口,上者出什之四,中什之二,下什之一,荒歉散及中下,大侵上户亦次及之,盖以有余补不足也”,越富者出粮越多。他们积极参与仓储的管理,如:明初苏松地区的大多数县份皆设预备仓“以贮官谷,多者万余石,少者四五千,仓设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饥馑,以贷贫民。”预备仓的直接管理者就是乡村里社的富民。他们积极参与灾荒赈济,如江西东乡县民吴安邦“富而好施,岁饥出粟贷乡间而不计其息。有贫不能偿者,及卒,取其券而焚之。”他们积极参与善堂、善会的创建,如苏州的育婴堂,“岁费千余金,皆士大夫助之。此一乡之善事也。”绍兴的育婴堂,“邑民刘世洙等捐赀建。柴世盛舍田三百亩。凡有淹溺弃婴,雇乳媪分养之,寒则给衣,病则疗药。”他们积极参与会馆的经费筹集,如婺源人李士葆“性慷慨赴义,芜湖建会馆,倡输千余金”。他们积极参与宗族内部的救助,如安徽黟县境内,“康熙六十一年春,富民输粟助赈,夏秋丰收。前年六月至秋,大旱八十余日,豆蔬俱无。至春,民益饥,乡之富人各周其亲族,城中大户富贾输银籴米,贮广安寺助赈。”他们积极参与助学,如南京王进德,“富而好施,出七万余缗构郡学讲堂,置一切礼器,又买宅一区,割田九百亩,创建江东书院,朝赐以额,高官掌其教。”富民或士绅利用自己的资产来救助贫者、困者,已成为乡村社会中的普遍行为。
富民主动救助民众,其思想出发点是儒家的敦亲睦族、崇仁尚义,是维持自身地位的道德考虑。对芸芸众生的关注,符合儒家“仁”学思想的精义,符合思想家的“民本”关怀,因此富民阶层致力于兴办各种社会救助事业。而面临灾荒困难时,也是考验人性的绝好机会,人们把捐资、捐助看成是完善个人道德的一种行为,受到社会主流思潮的倡导。“富室在丰年,贤否未知也。及至荒年,或恻怛而济惠,或顽忍而不恤,富室之贤否分矣。”富民仗义疏财、急一方之难后方可称为义民。义民之“义”体现的是富民“厚积而能乐施”的仁者襟怀和以庶人之微而以国事为重“轻利赴义”的忧世精神。所以说,富民的成功,“非独饶于资,且优于德也”。富民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活动,“富而好义”正在成为富民的新形象。由此观之,民间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足以说明富民阶层所发挥的积极影响。
三、民间社会救助活动兴盛的影响
总而言之,前近代时期在灾荒救济、尊老养老、抚育弃婴、救助鳏寡孤独等方面所开展的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是官府提倡,社会普遍认同,富民阶层为代表的基层社会力量推动的结果,展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势,收到的效果也比较显著。
第一,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
或者出于血缘亲情,或者出于人道主义,或者出于社会责任感,或者出于安定社会乃至于获取名誉和地位等等因素考虑,以富民阶层为核心的民间社会力量承担起民间社会救助的责任,不管他们出于何种个人目的对社会成员实施救助,都化解了社会成员的生存危机,缓和了他们的反抗情绪,这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前近代时期民间的社会救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冲社会震荡的功效。同时它还倡导了乐善好施、扶困济贫的社会风尚,显示了积极的社会意义。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有学者评价说:“中国古代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建立起的多主体投入、覆盖范围广阔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有力地矫治了社会两极分化的严峻形势,在贫富悬殊的社会成员之间粘合了一层温情的面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整合了社会资源,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从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来看,也的确如此。因为饥荒极易引发社会危机,统治者就提倡社仓的广建多设,如果突然“遇灾警少觉有备,亦足安辑人情”,有利于防止农民起义的爆发,巩固统治。清乾嘉年间的封疆大吏汪志伊也提到在救荒中,除官方政府出钱粮救助的主渠道之外,还应鼓励民间互为赈济,共渡难关,以便将灾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他说:“一家勤而富,役者百千夫;富济贫不足,贫资富有余;饥寒不相迫,盗贼自然无;又安有蚁聚,蜂屯意外虞”。所以他提倡“富济贫”来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稳定和安宁。又如宗族通过设置族田义庄赈恤族众,就可以收族睦族,维护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宗族内部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时,如果富者又极为吝啬,极易引发地方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顾炎武对此深有认识,他说:“民之所以不安者,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啬之计,于是有争心矣。”他提出:“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则“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富者发挥起养民作用,就可以缓解族众的困窘状况,从而凝聚民心,稳定地方社会秩序。
第二,富民阶层借此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如果说财力雄厚是富民社会救助活动的物质前提,仁义道德是富民社会救助活动的心理基础,那么寻求社会声望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则成为富民社会救助的目标追求。作为掌握大量社会财富、力量日益壮大的群体,富民在前近代社会救助事业中发挥主导作用,对其自身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
以富民阶层为代表的基层社会力量不吝啬钱财,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能够自觉地、独立地承担社会责任,纷纷开展大量救助活动,这不仅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还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它通过物质上的控制达到了精神上的控制,增强了基层社会的凝聚力,并为自身谋取利益。尤其是前近代时期,随着富民阶层的士绅化趋向,他们在基层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国家和民众也逐渐认可了他们在乡村社会的特殊身份,富民因此取得了中层代言人的地位。”这意味着他们在经济力量的增强和实际社会地位提高的同时,对地方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主导意识也增强了。他们的义举善行还能获得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极大信任,可以为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长久稳固,为其成为民间的“乡望”,奠定重要的基础。富民在举办社会救助事务的过程中,有效缓和了贫富间的对立与矛盾;树立了良好形象,扩大了社会知名度,获得了在地方社会的发言权,提高了自己的声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也为其自身的长期发展和经营培育了良好的社会土壤和气候,达到控制地方、稳定社会的目的,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者。富民阶层经济实力的发展与社会影响力的壮大同步展开,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地方社会救助主动权的逐渐扩大,其实也就是对基层社会控制权的逐渐扩大。正如张兆裕所说,富民“经历了从支持政府到晚明独自开展救荒的过程。这种情况反映了晚明富民势力的壮大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荒政的失败,以及社会权力的分化。”士绅化的富民在地方社会所进行的各种救助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地方权力向原来由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域进行扩张的结果,是士绅化的富民在地方社会谋取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卜正民对此评论说:“士绅主宰着地方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地方行政官的监督。他们拥有了一种公共的表现和声音。”
当然,对于富民在社会救助活动中的作用要给予客观的评判,正如清朝鄱阳人程直仞在其《荒政论》中所述“富家之好施者十中一二,悭吝者十居八九”。只是因为论文选取的角度是其正面价值的评价,故对其负面影响没有涉及。
四、结 语
前近代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既继承传统,又蕴含变革、充满活力的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最快,社会生活变化最深刻,社会流动加速,社会分化加剧。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变化的客观基础之上,从民间办理的仓储事业,到民间建立的社会救助组织,再到地方宗族组织进行的各种具体社会救助事务,民间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成为地方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民间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其中有政府层面的积极提倡,还有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更有富民阶层的主动参与,它是以富民阶层为代表的基层社会力量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政治地位的反映。民间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救助活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政府因制度不健全、落实不到位、人力物力匮乏等因素产生的诸多缺陷,也反映了民间社会的力量已发展到可自我组织的程度,基层社会自治化倾向的加强。富民阶层主动、积极兴办各种社会救助活动,“也可能被认为是地方士绅显示有效的地方领导者身份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共同承担社会责任,主导着前近代时期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社会救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客观公正地评价前近代民间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就不难发现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在强调国家责任的同时,重视和发挥民间力量在社会救助方面的重大作用,应该是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单凭国家的力量不可能把所有的困难群体都照顾到,因此,注重民间的自救与互助,让先富带动后富,增强“先富者”的社会责任,吸引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才能弥补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