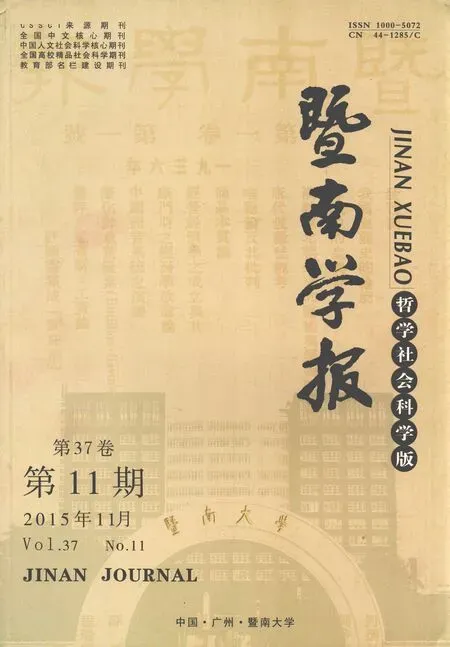地方志在区域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评《佛教与佛山文化》
黄志繁
(南昌大学 历史学系,江西 南昌 330031)
佛山因“佛”得名于唐代,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佛寺庵堂遍布佛山城乡。在已出版的佛山文史著作中对此鲜有专门论述。近日由暨南大学古籍所刘正刚教授完成《佛教与佛山文化》一书,专门论述佛山的佛教文化。这是继罗一星先生力作《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来佛山史研究的又一部厚重之作。刘教授的著作以佛教从海路传入佛山为切入点,采取纵观横览的视野,运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理论与方法,辅之于田野考察等,全面梳理了从晋到民国时期佛教在佛山社会变迁中的演变历程,以佛教传播展示佛山社会经济发展,也从佛山社会经济的发展论述了佛教传播的变化。这一学术研究视角非常独特,对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佛山宗教文化史将大有助益。
一、从不同层级的方志中搜罗史料。明清时期,编修地方志已经成为各地官府重要的文化工程之一,而且方志编纂逐渐延伸到乡镇一级机构。早在清康熙初年,佛山士人李侍问就编修了乡志,但今已散失。目前存世最早的佛山地方志为乾隆版《佛山忠义乡志》。之后,道光和民国年间又重修了《佛山忠义乡志》。佛山作为一个镇能连续不断地修纂方志,这在岭南地区独一无二,在全国也不多见。这些地方志成为后人研究佛山史的重要文献,刘教授在大作中充分利用了这批文献,从中可以管窥他对地方文献掌握的娴熟。
由于佛山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出现相对较晚,而佛教高僧传教的足迹往往也不限于一个地方。刘教授已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两点,为弥补佛山地区志书记载的不足,他把整个视角放在了珠江三角洲范围内,在书中引用了各朝代《广东通志》、《广州府志》、《南海县志》、《番禺县志》、《顺德县志》等史料。尤其对佛山曾属于南海县的事实,作者从现存的元大德《南海志》到清末宣统《南海县志》,披阅最多,从中寻找出许多与佛山佛教相关的史料线索。
当然,书中引用最多的还是三部《佛山忠义乡志》。著者在前言中指出,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地方志是《佛山忠义乡志》,这些地方志纂修年代的时间跨度较大,但对佛教在佛山地区的活动则有较详细的脉络记载。而不同时代的记载会有些许微妙变化,为研究佛教在佛山社会变迁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作者在统计明代、清前期、晚清佛山寺庙数量时,多依据三部乡志记载,向读者展示了佛教在佛山的发展趋势,其结论颇令人信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著者除了引用各种通志和府县志外,还引用了专志,如《光孝寺志》、《曹溪通志》等。可以看出,作为对地方志资料的熟悉和爬梳能力十分娴熟。
二、以方志资料佐证学术论点。佛山得名与佛教的关系,自古以来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民间流传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的说法。《佛教与佛山文化》第二章第一节专门论述佛山得名与佛教的关系,反复引用三部《佛山忠义乡志》不同卷目中的相关内容作为论据。同时,引述成化《广州志》、宣统《南海县志》论述晋唐时期珠三角地区流行茅屋建筑习俗,一直到南宋还在持续,以此证明昙摩耶舍在佛山讲经的“茅茨”,是有历史根据的。
为证明塔坡寺已经成为佛山人对地方历史记忆的一个象征性符号,著者引用《佛山忠义乡志》关于重修塔坡古庙的资料,从重修的次数、捐资名单以及文人墨客的诗句中,论证佛山人对塔坡与佛山得名的历史记忆十分深刻。塔坡寺作为佛山佛教历史文化的起源及佛山得名的历史物证,已经变成了佛山人关乎本地文化传承的历史基因。无论人世间沧桑如何变幻,对于佛山人来说,塔坡寺始终是佛山人追忆文化遗存的宝贵源泉,塔坡已经成为佛山人宗教信仰中的圣地。
一般来说,明清寺庵多建于名山之中,而在佛山这样商业发达的闹市建立如此多的寺庵,在全国并不多见。著者以方志记载的史料为依据,用表格详细分析不同时期佛山寺庵的建设情况,著者认为,佛山因佛教得名,并以禅城流芳百世,这在中国传统城市发展中独一无二。
书中还有一个观点,佛山祖庙之名应是民众亲缘与历史意识共同的产物。著者认真分析《佛山忠义乡志》记载后指出,“祖”字在大多数情况下带有血亲之意,但“祖”字也可作源头解,中国人认同的黄帝、女娲为人类“始祖”等现象就是证明。所以,著者认为,佛山的北帝庙又被称为祖庙,不能完全排除其带有始祖神灵崇拜的意思。
当然,地方志只是作者利用文献的一部分,书中还大量利用了佛教典籍、碑刻、族谱等文献,并结合地方志进行互证式的比照,使得论证更具有说服力。据笔者对脚注的粗略统计,地方志有110 多处,其他文献约150 处,而正文中直接引用的各类文献更不胜枚举。
三、不盲目相信方志资料的记述。方志作为地方士人书写的家乡文献,有时不免含有美化成分,尤其在志书传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错漏。刘教授在使用方志资料时,并没有不加辨析地采取拿来主义的做法,而是结合其他文献对方志进行了辨析和鉴别。如书中对佛山“三尊佛”、石榜、塔坡古井等出现时间、现存铁塔重铸时间的辨析和考证,都让我们对佛山历史产生新的看法。
现存《佛山忠义乡志》对“三尊佛”出土时间记载不同,乾隆志比较隐晦地说是“传说”;道光志将传说时间具体为贞观二年;民国志认为在东晋。著者通过对乡志深入辨析,并引用明清纂修的《廉州府志》、《广州志》、《广东通志》等记载,对之辨析,推论为唐代发现三尊佛像。同时对塔坡古井开凿时间和后来发掘时间也进行了合理的辨析。该书还对佛山石榜也进行了辨析,道光《佛山忠义乡志》记载石榜已遗失,民国版则有详细介绍,作者经详细辨析,认为流传至今的佛山石榜应是道光之后的作品,而非唐代一直存留的作品。
另一个体现作者对府志辨析功力的是对现存祖庙铁塔样式的最初建造时间。道光《佛山忠义乡志》记载铁塔建于雍正九年,而民国版则记载建于雍正十二年,两者相互矛盾。作者指出,如果雍正十二年重建确切的话,则合理的解释就是雍正九年倡议动工,到十二年完工,不可能在三年间又重铸铁塔。乾隆五十三年重修经堂古寺时,可能觉得铁塔与寺庙的格调不匹配,所以嘉庆四年又仿阿育王塔式建造。作者认为,这就是现在人们所看到铁塔模型的最初样式。
方志乃一地之全史,号称地方百科全书。地方志所记载的内容较全面,是研究地方历史的重要文献。按地方志种类看,目前流传下来的旧志,以省、府、州、县志为主,而作为县以下的乡镇志却不多见。从地方志入手,对开展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因为认识特定的地域,最直接的历史资料就是地方志。刘教授这部著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不仅把佛山本土的方志资料竭尽用之,而且还能从相关的方志中找寻资料,充分发挥了方志对区域史研究的作用。我们相信,刘教授这部著作能够为当代修志者提供如何收集、编纂方志的历史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