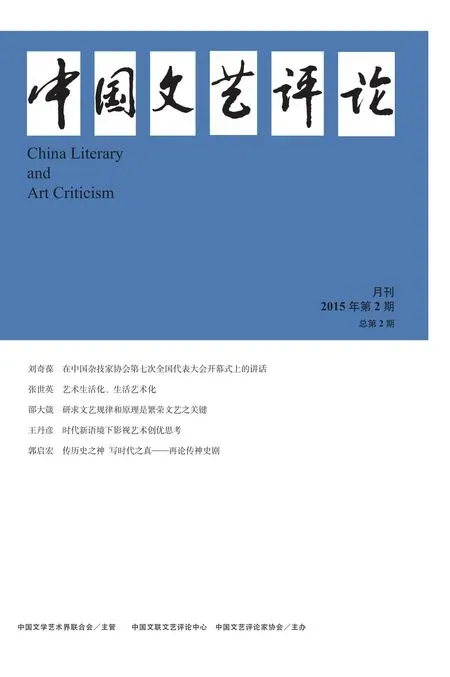电影代群耗散之后:创作流变与格局重组
陈晓云
艺象点击
电影代群耗散之后:创作流变与格局重组
陈晓云
以“代群”来研究某个特定时期的导演群体,并进而梳理电影历史的发展,是中国内地特有的现象。此种研究,在将电影导演研究清晰化为代际/块状结构并凸显其艺术/美学特征的同时,往往也会屏蔽掉某些“非典型”的导演特质,比如,作为“典型”的“第五代”的“黄土地美学”,至少忽略了或者屏蔽了吴子牛的《喋血黑谷》作为此代导演群体最早具有类型意识的存在。有意味的是,“代群”似乎在“第六代”出现之后便趋于消失,呼唤已久的“第七代”或“第八代”并没有在话语的喧闹中被催生出来。代群耗散之后,属于某一代的导演仍在创作行进之中,但与作为“代”的时候已然有了本质区别;代群的耗散,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验证着当代电影风格与样式的趋于多元,以及导演群体的趋于复杂,“代”的概念已经很难包容日渐繁复的电影现象本身;近年来新生代导演“出身”之差异,则构成了另外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传统的电影创作格局及艺术教育格局面临重组。
一、百年六代:电影代群的耗散
创作经历持续30多年的陈凯歌与张艺谋,一直被视为“第五代”的精神标杆,除了偶有作品出现的个别导演,他们是这一代导演中持续创作的硕果仅存者。人们对于两位导演的创作,普遍认同于其导演处女作《黄土地》和《红高粱》,以及被视为其艺术巅峰之作的《霸王别姬》和《活着》,同样以处女作确立了自己创作的高度,同样以20世纪中国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命运叙事完成巅峰期创作,且屡屡有意无意形成相互PK的格局(如《孩子王》与《红高粱》《和你在一起》与《英雄》《无极》与《千里走单骑》等),形构了“第五代”乃至当代中国电影历史的一个独特侧面。这两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短短几年间以《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和《霸王别姬》为中国电影赢得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大满贯,并以《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等影片数度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导演;在新世纪以来,又以《英雄》《十面埋伏》《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实践着中国电影由艺术而工业,他们自身由电影节“英雄”向票房“英雄”的转型。同时却又迅即陷入了票房与口碑的巨大悖谬之中,并由《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引发一场网民的话语狂欢。而事实上,自他们出道以来,对其创作的争议则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他们为中国电影赢得巨大国际声誉的那个年代。
在分别遭遇《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之拍案惊奇》的叙事/文化/消费困境之后,张艺谋分别以《山楂树之恋》和《归来》之表象上的“爱情”或者“家庭”伦理故事,悄悄地触摸那段与他个人生命记忆相关的“历史”,尽管银幕上的“历史”陈述因被过度消释而似乎变得不可触摸。20世纪当代中国的政治历史之于张艺谋或陈凯歌,或者说之于“第五代”,已然铭刻于他们的文化记忆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活着》和《霸王别姬》之于他们的生命意义与创作意义。历史的劫难总会在艺术中得以补偿,这至少可以解释在世界范围之内,对于“二战”的银幕书写从来没有停止过。而“第五代”的另一位导演,于这一代崛起之初堪称精神领袖的陈凯歌,却在《梅兰芳》和《赵氏孤儿》中分别完成了毫不逊色于前期创作的两个开头之后,再度迷失于《无极》开启的历史/文化/消费迷阵之中。《道士下山》与《无极》题材全然不同,而它们的叙事/文化困扰则如出一辙,以一个哲学般开始的创意与理念,最终迷失在混乱的叙事之中而遭遇自我消解,更遭遇与当下这个时代观众对话的阻断。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末《孩子王》与《红高粱》在戛纳和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全然不同的遭际,事实上标示着“第五代”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具有“先锋”以及“现代”意味的创作思潮的分化与终结,也就是说,“第五代”作为一个具有清晰可辨的艺术/美学特征的现代电影思潮的终结;如果说,《英雄》开启的“国产大片”至少还意味着建构中国电影工业上的努力及其成效,那么,作为“第五代”成员的持续创作,也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导演之一,陈凯歌在当下中国电影格局中的境遇,或许意味着,即便作为一种散在的存在,也就是说,作为“第五代”成员的个体存在,似乎也迎来了它的尾声。此处所谓“尾声”,并非单指创作数量,而是指某种精神状貌。
于导演本身,或者,于追随着“第五代”一同走来的人们,内心或许并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尽管它确确实实地发生着。相对而言,“第六代”作为“历史中间物”的存在,似乎是一个更加触目的电影现实。
关于“第六代”,网上曾经有过一种比较刻薄的评说,认为这一代还没有拍出代表作就已经结束了。话虽不免刻薄,却也包含着某种必须面对的实情。与“逆推”的“第五代”先有作品再有称谓不同,“第六代”是一个“能指”先于“所指”的创作代群,也就是说,“口号”先于实绩被预先指认。除了题材与风格上的明显差异,“第六代”遭遇的创作处境也与“第五代”全然不同。“第六代”毕业及出道之初,陈凯歌、张艺谋们已经在国际电影节上声誉鹊起,且在作为“第六代”之主体之一的85级进入电影学院就读之前,导演系连续6年没有招本科生,这客观上使得“第五代”刚出道便身处“后无来者”的境地。“第六代”出道之初,恰逢中国电影体制改革,国营片厂不再如80年代般可以为电影创新提供基地及“零拷贝”的风险,加之时代风云变幻,以及创作者自身的选择,使得这一代导演中的相当一部分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游走,其中,国际电影节依然成为其主要通道,且常常成为一种被刻意表述的“姿态”,这使得我们更多时候在关注他们的“身影”,而非他们的创作。另一方面,如果说,“第五代”的背景,除了众所周知的“78班”,黄建新等导演也与电影学院之间有着种种姻缘关系,而“第六代”的状况则更显复杂,一个显见的现象是,中戏毕业生(如张扬、施润玖、金琛等)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两大艺术院校之间的专业比较,也由表演而扩展至创作的其他领域。这种现象是意味深长的,但,当时的人们或许不会意识到,专业/创作领域的扩张,并非仅仅是艺术院校之间的竞争,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普通高校兴起的艺术教育由电影(电视)课程而至专业的变化,终于在本世纪蔓延为电影创作队伍更为显见的“跨界”现象。
与“第五代”顺利完成从国际电影节电影向市场电影的转型不同,一方面,“第六代”冲击国际电影节奖项之时,中国电影在重大国际电影节的地位,正被伊朗、韩国所取代,加之资讯及网络的发展,西方对于东方中国的异域想象,电影不再是主要更不是唯一的通道;另一方面,“第六代”的市场转型却遭遇了更多的尴尬,“艺术”与“商业”之间的游移不定,终是造成此种尴尬的原因所在。
二、跨界导演:创作格局的重组
《英雄》引发票房与口碑之间的悖谬,“不烂不看,愈烂愈看” “我想看看它到底有多烂”之类的诡异思维,成为许多观众走进影院的主要动因之一。而事实上,由观烂片而引发的吐槽快感,至少可以部分解释此种现象背后的某种引人思考的观片动机,当这种吐槽最终成为视觉化的“弹幕”的时候,其心理动因似乎便昭然若揭了。吐槽带来的巨大快乐,已经不仅仅限于电影领域。自然,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因为事实上,收获高票房的,在被视为“烂片”的影片中也仅占极少的份额。绝大多数影片,连进入院线平台的机会都不曾获得。对于它们来说,生产过程的结束,似乎同时意味着消费过程的完结。
但事实上,我们依然无法在学理上来解释类似现象,就如我们无法解释《小时代》之类的影片为中国电影市场带来的巨大悖谬。面对这样的电影现象,传统的或者现代的电影理论与批评方法,似乎都很难奏效。也因此,喜欢或讨厌的双方,通常都没有在学理层面上展开讨论,或者,争得面红耳赤,其实焦点并非落在一处。此类很难在文本意义上经得起分析的影片,却可能因其对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某种反映或者折射,而成为文化研究可以展开讨论的对象。
2015年的暑假,《大圣归来》《煎饼侠》《捉妖记》这三部影片的几乎同时出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国产电影票房与口碑之间的悖谬关系,尽管它们在叙事上并非是无可挑剔的,但至少,在大部分电影偏离关于电影的常识的时候,它们努力回到“常识”。因而,这是一个水落石出的结果,而非水涨船高的必然。这使得人们似乎相信,有品质的电影终于有了它的“春天”。当然,我指的是票房意义上的。实际情形会如何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及思考。
这几部影片所提供的另外一个重要信息是,其导演田晓鹏、董成鹏(大鹏)、许诚毅的名字,于普通观众而言,是陌生的。而他们的出身,并非经典意义上的“科班”。他们不但学的不是导演专业,而且几乎与“艺术院校”四个字不沾边。田晓鹏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具有丰富的三维动画创作经验;董成鹏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因主持脱口秀节目《大鹏嘚吧嘚》而出道,2012年起自编自导自演搜狐视频自制剧《屌丝男士》;许诚毅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早在1989年就入职美国梦工厂成为动画师,参与创作了《怪物史莱克》等影片。
电影业的“角色反串”现象并非起始于当下。仅以“78班”为例,毕业于摄影、美术等专业的张艺谋、顾长卫、侯咏、何群、冯小宁等,先后都转行成了导演;姜文、徐静蕾、徐峥等则成为明星/演员转行的经典个案。但是,这些所谓的“角色反串”,通常还是在行业内部的不同专业之间展开的。如今我们似乎更多用“跨界”来形容“角色”之间的各种复杂景观。老板、作家、IT业人士,各色人等都在“跨行”成为导演,且票房不俗。
由此反观中国的电影教育,如果说,普通大学开设电影课程/专业,最初动因还是偏于鉴赏与研究,那么,随着数字与网络时代的到来,制作设备的轻便化与低廉化成为主导趋势,它在客观上降低了进入制作这个行业的门槛,全民影像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可能。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去欧美学电影及传播类专业的学生有明显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电影人才的培养,有可能形成国内艺术院校、普通大学及海外大学三足鼎立的新的格局。此种格局的雏形,在近年来国内外举行的各类短片/微电影比赛中可见一斑,艺术院校一枝独秀的局面,正被创作主体的多元化格局所代替。短片/微电影比赛/评奖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褒奖一些优秀的作品及其创作者,而是为未来的电影艺术/工业提供人才储备。而事实上,它们也成为青年导演走向常规长片创作的一个主要通道。今日短片/微电影创作者队伍的多元化,客观上或许决定着若干年后中国电影创作主体的新的格局。
与之相关,类型意识及工业意识的觉醒,成为近年来电影创作之流变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以“娱乐片”这一内涵并不严格的概念来指陈实际上的类型片的时候,其对电影功能拓展的意图跃然纸上,它是对国产电影长期拘泥于教化功能的一种反拨,或许也是针对“第五代”早期影片票房惨淡的一种矫枉过正。教化与娱乐的双重变奏,这一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母题,在那个年代再次发出它的声响。之后及迄今为止仍然在使用的“商业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艺术片”概念,仍然是在学理上很难界定的,虽然我们约定俗成地心领神会它们之间的分野。
类型片概念的被广泛认同,以及专业院校教学由此产生的教学重心的位移,是建构电影工业不可或缺的。这个夏天受到票房与口碑共同赞誉的几部影片,几乎都有着清晰可辨的类型意识。近年来,诸如《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泰囧》这样的喜剧片,《画皮》这样的魔幻片,《孤岛惊魂》这样的恐怖片,《失恋33天》《北京遇上西雅图》这样的爱情片,《后会无期》《心花路放》这样的公路片,中国电影以某些类型为突破口,类型意识的渐次觉醒,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于明星策略、工业意识的强调,《大圣归来》《煎饼侠》《捉妖记》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三、强化叙事:电影突围的路径
陈凯歌与吴宇森,《道士下山》与《太平轮》,或票房或口碑,在这个暑期档的折戟沉沙,或许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导演年岁意义上的“老”,或者说,是某种“代”的“过时”。究其实,本质上乃是与当下社会、现实、受众之“对话”能力的丧失,当然,此种丧失存在于绝大部分国产片之中。多数时候沉迷于“历史”叙事的陈凯歌,曾一度以《和你在一起》和《搜索》试图以表现题材与触及问题的现实性,来重构此种“对话”关系,但艺术创作的诡异之处恰恰在于,他的“历史”叙事却更有意味地对应着“当下”,触及着当下受众的观影心理,这再一次有力地支持了“重要的不是故事叙述的年代,而是叙述故事的年代”这样的观点。题材的“现实性”,并不必然决定着与现实中的人们的对话关系的达成。
“对话”,实际上至少意味着“双方”,即作为创作者的导演和作为接受者的观众的某种对等关系。就如中国电影工业仍处于未完成时态,中国电影观众同样是一个指向较为暧昧的群体。暧昧,指的是它的不确定性,它的变量。据说,近年来国产电影的票房突进,便与“小镇青年看电影”这样的新的观影时尚相关,这个庞大的尚未充分开发的观影群体,其文化趣味显然与“都市”里的观众形成群体差异。不确定性还有一重意思,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类型电影创作尚未形成规模化创作/制作,与此相对应的是,指向某些电影类型或明星的相对稳定的观影人群,也没有完全形成,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观影行为的相对随意与松散。从生产到消费的一个完整链条,形构了一个关于电影的生态系统,尚处于无序的正在建构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近年来的多数卖座片可以视为“黑马”,或者说“意外”,而并非基于工业层面的精心策划的结果。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大圣归来》《煎饼侠》《捉妖记》等影片回归“常识”的努力。相比较于那些虽有票房却备受诟病的“综艺电影”或者“PPT电影”,它们在类型意识的清晰与坚持、影像质感和叙事能力的提升方面,都做出了可见的努力。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些具有良好的票房与口碑的影片中,剧作/叙事问题,亦即中国电影最大的软肋,同样也是清晰可见的。回到“常识”,是中国电影趋向良性变化的开端,而并非结果。
韩延执导的《滚蛋吧,肿瘤君》当是这个暑期档带给我们的另一份惊喜。这位科班出身(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80后”导演,在一个极易狗血与煽情的故事形态里,显现出与其年龄与经历并不相称的对于叙事的节制与控制力。这个有着现实原型的故事和人物构架,指涉着一个被叙述过不计其数的“母题”,但与同类故事不一样的是,它以一个表象闹腾的喜剧,来呈现一种催人泪下的悲情效果。原来,在国产电影中缺失已久的“情怀”并非是多么宏大的概念,对于普通人生命的尊严与美好的尊重与表达,这就是最好的“情怀”。
有意味的是,影片对于此种“情怀”的表达,是深植于一个“古老”的故事模式,一个在艺术创作中不断被“复现”的母题,一种更偏于类型的结构形态与人物塑造,而非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在理性上陷入其间的所谓“艺术电影”。在“类型”中寻求“艺术”的表达,在此前的《浮城谜事》《白日焰火》等影片中都可以见到端倪。
如前所述,剧作/叙事问题已然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即便是在让·雅克-阿诺执导的《狼图腾》中,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叙事的无逻辑、悖常理,在国产影片,以及准备投拍的剧本中比比皆是。如果说,“第五代”的前期作品主要是以凸显影像造型来对传统电影实施某种反拨的话,当他们进入被称为“国产大片”的运作的时候,叙事的硬伤便暴露无遗了。一个颇为吊诡的现象是,“第五代”的早期影片多改编自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而他们恰恰在改编中呈现出某种“作者电影”的风范;当他们进入更具工业/商业意义的“国产大片”的领域之时,恰恰却开始追求“原创”了,陈凯歌、张艺谋在继《英雄》之后的一系列影片中,都担任了“故事原创”或者“编剧”的工作。此种表述无涉他们自身的剧作能力,重点在于,商业化的类型片所要求的,恰是工业意义上的分工合作,而非追求所谓的导演个人“原创”。《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到经典戏剧作品中寻求创作素材与灵感,以及此后的《金陵十三钗》《归来》《道士下山》等影片又到小说中寻求创作素材与灵感,或许可以视为对此现象的一种反拨,所惜结果并非理想。
也因此,在国产电影票房连年递增的同时,提升中国电影的剧作/叙事能力,尤其是类型片的剧作/叙事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可以将文字剧作演化影像作品(产品)的现代工业生产能力,是寻求本土电影在好莱坞以及其他流行文化的挤压之下突围的一个重要而必须的路径。所谓“口碑”,首先基于影片作为一个“合格”的叙事产品的存在。也许,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们首先需要期待的并不是诞生多少“杰作”,而是先让作为市场主流的类型片的影像/叙事回到“常识”。首先必须是一个符合“常识”与“常理”的工业/文化产品,其次才能谈到价值观与情怀,而不是倒过来。
注释
[1] 人们在多数时候所讨论的“烂片”,主要都是以院线放映的影片为对象,而数量更为庞大的无缘院线、甚至无缘电影频道的影片,它们的资金来源与创作状况,它们的投资与创作主体的诉求,是另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
陈晓云: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影像研究中心主任、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