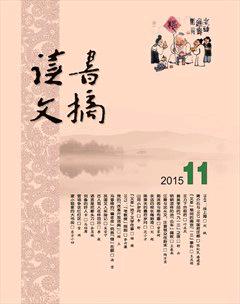官场争议红灯区
雪珥
1905年,中国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前往西方考察宪政,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五位考察大臣之一的尚其亨,被御史赵炳麟弹劾,理由是居然参与“性消费”,此事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因为,新成立的巡警部,已经在首都率先开设红灯区,按月抽收妓捐。
清朝大约是对性产业打击力度最大的。首先是中央率先垂范,废除官妓。顺治年间,裁撤有着悠久历史的教坊女乐,改用太监替代。针对各省仍保留的文工团,康熙十二年重申禁令,省府州县严行禁止提取伶人娼妇。但是,官方后续安置政策的匮乏,令乐户妓女这个群体只好重操旧业,无非从官妓转为私娼。
对于官员嫖娼,《大清律》 延续了明代的规定:“凡 (文武) 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款,惩罚嫖客、拉皮条者,不针对卖淫者。涉案官员还要有行政处分,那就是“永不叙用”。这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等于是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对于“卖良为娼”者,也给予重拳打击。同时,这一禁令,还延伸到体制内的知识精英,“监生生员”。
惩处嫖客,这是从市场需求的角度下手;惩处妓院经营者,这是从市场供应的角度下手,如此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对于延续千年的性产业是相当强大的打击。清代中期之前,性产业转入低潮。乾隆甚至将嫖娼与盗贼、赌博、打架,归为“四恶”,“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
刑律、政纪之外,清帝国也没有忽略文化领域的扫黄打非。这既是净化社会环境的需求,也是通过文字狱钳制思想的需要。
对于官方的洁癖,不少官员和士大夫都相当不满。掌握实权的地方官员,对扫黄阳奉阴违的,大有人在。雍正朝的名臣李卫,是皇帝的亲信,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开放力度就非常大,尤其是南京和扬州,相当“娼”盛。
在将嫖娼列为“四恶”的乾隆时代,广州知府赵翼就曾对上级部署的扫黄工作公开提出意见。第一个理由是就业问题。第二个理由是,性产业其实是也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吊诡的是,他居然说服了上级,“事遂已”。他的上司,一是广东巡抚德保,一是两广总督李侍尧,都是乾隆皇帝相当信任的干部。尤其广东的一把手李侍尧,非循规蹈矩之人,思想比较开放、胆子比较大、步子比较快。有这两位上司,赵翼才敢于用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作为理由,阻止扫黄。
对于广州的性产业,赵翼还是用心做了一番调查:“广州珠江疍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疍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挺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疍也。”所谓“疍户”,就是粤闽一带渔户,户口在水上,不得上岸定居,向属贱民。主业收入微薄,其中一些兼营皮肉生意,也是历来常例,政府向来睁只眼闭只眼。因此,不少专业性产业经营户,亦托名“疍户”,减少麻烦,时间久了,居然在珠江上建起了规模不小的水上红灯区。
赵翼是科举正途出身,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江右三大家”的另一人袁枚,也公然抨击政府的扫黄:“僧尼欺人以求食,娼妓媚人以求食。今之虐娼优者,犹北魏之灭沙门毁佛像也,徒为胥吏生财。”这话虽然有很大的情绪性,不过,“徒为胥吏生财”一句,还是说在了要害上。这与鸦片战争前,官方禁烟的每道禁令,都成为官吏们提高寻租价码的工具,是一样的。
若干年后,被后世俨然当作道德楷模的曾国藩,率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此时的南京,“六朝金粉之遗,只剩秦淮一湾水。”战争之后,“画船箫鼓,渐次萌芽”,六安县的县令却在境内严厉扫黄。曾国藩笑道:“闻淮河灯船,尚落落如曙星,吾昔计偕过此,千艘梭织,笙歌彻宵,洵承平乐事也。”次日,曾国藩就带着自己的幕僚们,乘船游览,大宴宾客,“一时士女欢声”。曾国藩的这一行动,就是无声的表态,超常规恢复经济,成为战后重建的关键,扫黄实在有点不合时宜,不讲大局。时人因此感慨,曾国藩真是一个讲政治的高手:“公真知政体哉!”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