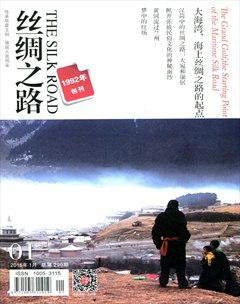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十一)
【法】伯希和著+耿昇译
1906年11月3日
该通道另一侧的遗址,始终使我感到困惑不解。我于是便决定带领五个人前往那里发掘。我们很快就在努埃特曾拾捡到一块装饰有手镯的手腕造像残片处,又发现了佛像的其他残余。其本身的价值都不大,但其头、臂和底座等造像,却都充分证明,在山口的这一侧曾存在着一个古代僧伽蓝(其大致布局省略——编者)。
正当我在这些遗址发掘时,俄罗斯驻玛喇尔巴什的领事官也出现在大道上了。他告诉我说,那匹于腹沟被一根芦苇刺伤的马,曾被我们留在克拉库尔津(克拉特勤),现在却到达了玛喇尔巴什。但它却处于一种如此严重的状态,其伤口如此吓人,以至于甚至不能把它送到肉铺里去了。这是我们的一匹驮马,它死去了。它是由于那些哥萨克人的疏忽才死去的。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运气。
那位领事官还告诉我说,后来在村子里又有人向我证实,在通道北侧中,有一个更具体的名称“九间房”(托古孜—萨莱),而图木舒克一名比它更为适宜我所在的位于南侧的遗址。我们坚持使用这个地名,正是由于它,我才最终搞清楚了,本处的古城在土著传统中叫作哈拉拜勒。哈依拜勒是另一座城市的名称,对于它的记忆,有时也与前者相联系,但它位于柯坪与乌什—吐鲁番之间,地处山中最神圣的一个麻扎的旁边。最后,我询问了巴尔楚克一名的起源,它已出现在18世纪的汉文舆地书《西域图志》中了,系指玛喇尔巴什地区,而现今的“巴楚州”一名(玛喇尔巴什)可能是它的一个派生词。原籍为浩罕的俄国领事官,已在中国新疆生活了20年,非常清楚地了解阿勒迪古城的传说。据他认为,该地名应为博依楚克,而不是巴尔楚克,是一个指从南部麦盖提直到北部的启浪之间的广袤地区。
1906年11月4日
努埃特告诉我说,“九间房”(托古孜—萨莱)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我当然必须坚持亲自前往那里勘察,同时也想看一下那些新出土的佛像。努埃特向我指出,它们处在山中我已经知道的那座佛像的旁边。我仅仅带了两个人前去,而瓦阳于此期间和马车夫法济勒一起测绘平面图去了。在M遗址上的发掘,出土了一批意义不大的佛像碎片。但我觉得B号大土丘远未被彻底清理,我将自己的人安排在那里。在白天很早的时候,我看到露出了一块墙角,其外部装饰以陶土浅浮雕。这是一种室内祭坛,我觉得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图木舒克A号寺庙l-m-o-n号的小四边形建筑物颇为相似。第一个浅浮雕一旦被发掘出土之后,便向我们显示了一身站立的瘦骨清风型的佛像,虽然它残损严重,其右部却有一尊相当于出身门第很高的婆罗门僧,扎着绶带,坐在一面很高的铃鼓法台上,佛陀的左部有四名女子。这块浅浮雕位于中心建筑物一侧。该角落东侧的浅浮雕残损甚重,只能仅仅显示出人物像大腿的外形来。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去彻底清理整个祭坛,我们将于明天再返回来。我还发现了一两件颇有价值的头像,以及装饰这座B号寺庙的真大佛像那损坏严重的巨块。
1906年11月5日
我必须用刀子去清理我们的浅浮雕,而且还必须由我亲自动手。因此,直到下述新的工作命令之前,我们尚没有使用大量民工的劳动。我带来了其中的五名民工。其中两人被用于在F号遗址最后发掘,那里有几个生石膏的线脚。经发掘只出土了几块被绘成红色和蓝色的线脚、两块带绘画的织物、一把制作得颇具艺术性的扫帚,这一切都可能应断代为穆斯林时代。
带蜂窝般小房间结构的房子确为穆斯林时代的,因为在东侧还有一处可能是用以环绕门的阿拉伯式的外部装饰框。这可能就是已经导致斯文·赫定声称其门在东面的原因。那些小房子一行接一行地变小,但未显示出一个可能是圆拱顶的起点。在每个角落里和角落的每侧,首先是一行有八间小房,然后是七间,接着是六间,直到每行一间为止。在任何地方,都未发现只有一间房的层次,而带有两间房的层次保存在东北角。
我从这幢F号房子处,派出了两名民工,前往J号以西和J号遗址。在J号遗址以西,已经由努埃特发掘出土了与A垂直的几条平行走廊,同时还有几个很大的卵形或馒头形装饰,酷似I号小寺庙中的那些装饰。我让人主要是重新发掘了J号遗址,但并未取得重大成果。我们发现了一批灰堆、一条壁炉烟道、一小段红色丝绸碎片、一小片带有三四个汉字片断的纸头。直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获得的唯一“写本”,我犹豫不决地认为确实与寺庙是同时代的。
最后,我将民工们带到了浅浮雕处。我们发现,它们的轮廓线条,似乎从两侧向更远的方向延伸。但我们必须做更大规模的清理,才能使努埃特得以拍摄。这种土方工程将会占据明天一整天的大部分时间,而且还是雇佣了五名民工。
1906年11月6日
我们在最接近中心建筑的西南侧,共发掘出土四块明显是破碎的浅浮雕,其保存状态还足以使人物塑像具有一种很优雅的姿态。但没有必要过分翻动周围的土地,因为震动会使塑像上所有脱落的碎块都掉下来。我们要搬走这些浅浮雕片吗?我自己考虑这个问题已有两天了。把它们继续抛留在那里,那就等于宣判它们会于短期内消失,而又没有科学用途。当地人很可能会取走这些头像,以把它们奉献给喀什人。无论如何,大风与冰冻也可能会于今冬毁掉这一切。但我们怎样才能以最小的损失带走这一切呢?我们没有可用于模塑的生石膏,沙子又支撑不住其负重,等等。此外,在从事任何尝试之前,努埃特还必须拍照。唯一的办法是今天要做充分的准备,以便能够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拍摄。这都是一些清风瘦骨型佛像与婆罗门僧供像。第二块浅浮雕代表着坐佛,而两个飞天或东天(这些都是天神、女神和仙女)则于其头上飞翔。这幅画面与我们教堂中的多种顶饰的姿态很相似。第三块浮雕基本上被保存下来了,代表着带光轮的佛陀像,其左部是一个带光环的年轻妇人像,右部是一个同样也带光轮的老妪像(可能是佛母摩耶)。老妪像右边是一个肩负难以分辨清楚的重物(可能为一只羔羊)的人物像。在此人脚下,又有一名年轻女婢像端坐在那里。
在从大寺庙中清理出的杂物中,我们发现了两个佛头小像,其中之一用红色陶土制成。第三个佛头像的体积很小,尚带有蓝色绘画的痕迹,其上面贴了一层金箔。出于一种令人遗憾的坏运气,这个头像被我们的哥萨克人在从遗址往住所中搬运时丢失了。
1906年11月7日
我们继续清理工作。到处都有打穿和推倒浅浮雕的穆斯林墓葬,给我们留下了令人不快的惊奇。此外,东侧的一场大火非常严重地把地面烧成了陶土,也可能是腐烂物体的分解作用而成。总而言之,那些人物造像都如此脆弱,以至于人们无法将其粗糙的外表附着杂质剔除出去。此外,在一个特定时刻,无论是在东侧还是在南侧,浅浮雕和支撑墙(挡土墙)都消失了,穆斯林墓葬似乎应对这种现象负责。然而,在南侧,我们发现墙壁内陷;与外部浅浮雕平行的地方,还有一道低矮的斜坡。其上面供有许多小体积的塑像,其中一个底座的下半部依然保留在原地。墓葬内部地面铺有一种水泥,现在已经极其易碎了。此外,庙中还保留有一尊巨大的供像,至少三倍于真大,我们已经发掘到其右脚的前半部。
我们重新带上了努埃特的18×24的照相机。我们昨天对它略有损坏,以至于今天仍然不能用它来拍照。
1906年11月8日
这个白天的收获确实不算太丰厚,我们在大土丘的东北角共发掘到一颗死人头颅、四个带有皱褶和经烧焦的圆形饰品。我们至少发现了这个东南角,还有昨天于南侧发现的内壁凹陷处的末尾,但今天尚不能复原其大致的平面图。努埃特至少拍摄了所残存的浅浮雕。我们还试图在K号遗址中心建筑物的前部和左部进行发掘,共出土一只相当大的手臂造像、无法考证出其具体内容的壁画残片,尤其是我们未找到其底座的瓦砾残余。
1906年11月9日,星期五
瓦阳于今夜进行了两次对掩星的观察,并且尚有待于对时间进行观测。努埃特对发掘物绘制了图版。我独自带领10名民工赴发掘作业面。在大土丘上,我们发现了北部的一组浅浮雕,残损甚重,但一只大象的造像却显得几乎完整无损。大约到了这一天之末,我清理了北侧的西角,发现了一个凹曲的栏杆,与另一侧的栏杆颇为相似,现在只有待于去彻底清理它了。在对这一北侧的发掘中,我们已经在那里找到了瓦阳所说的圆形饰品、两个分别为小型和中等规模的死人头颅。此外,我们还发掘到了另外一颗中型的死人头颅、某些做鬼脸的造像之残余。最后是一颗小丑的头像,其风格既不属于印度,也不属于希腊。尽管我经验很少,但它似乎更会使我联想到古代伊朗艺术。
就在同时,我继续按照上述模式而发掘K号遗址(发掘细节省略——编者)。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发现的钱币又重新提起了该寺庙被毁的时代问题。小寺庙雕像的风格,以及大土丘上某些造像的衣服皱褶(由努埃特首先拍摄的造像代表着一个女子,其衣服皱褶在呈传统姿态的胯部被系住了)。它们都明确标志着一个相对古老的时代,我更愿意相信它们是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寺庙建筑。我同时也承认,它们后来又被重新做了装饰和扩展,也可能是加入了B号大土丘上印度风格的浅浮雕,并且由此而一直维持到穆斯林时代,穆斯林们可能最终把它们烧毁了。但是,如果可以肯定,该地区在穆斯林时代之前和整个中世纪都有人居住,而且穆斯林们于此也拥有他们的宗教崇拜圣地,那么这些毁于火灾的寺庙就很可能是在此之前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本处发现的所有钱币,都是属于汉代的,其毁灭很可能要早于唐代。
1906年11月10日,星期六
今天,我共带领15个民工,以便清理K号遗址的凹陷形房间。此外,我们还带去了一个箱子盖,以将那里的浅浮雕之一取下来。这种操作并未获得完全成功,但我们也无法做得更好了。整块画面被分成几个小块剥落下来了,因为它是由数块组成的。我们尚需要包裹,并对全部物品作编号和修复。
在K号遗址一侧,我们发掘出了相当数量的僧房,还有某些小护坡道,我尚不知道其用途。在一个堆满垃圾的过道中,我们又发现了许多编织的绳子和一把旧扫帚,完全如同出自F号遗址中的那种编织绳头与扫帚头。在K2号遗址中,当发掘到其他严重腐蚀的铁块后,我们最终触及到了坚硬地面,其中的一块铁片似乎曾是一把锁头。在K1号和K3号遗址之间,一间僧房中隐藏着一躯大像的大腿部位造像;还有一种以陶土塑成并绘有红白相间颜色的大树,我们几乎掌握了其完整图案。在那里也有几种涂成白色和红色的残片,包括一件狗头像。在这个小僧房中,于一种烟道之下,有许多杏核。此外,那里还有未做重大艺术加工的一段象牙。最后,K1号遗址继续向我们提供壁画残片,其中包括一条胳膊的造像,穿有青色织物,加工精细,保存状态完好。就在同一地点,还出土了几块墙壁残片,上面有用婆罗谜字母写成的恶刹罗字。我们也可能会通过古文字,而掌握有关寺院的这部分区域被烧毁的某些征兆。我的理解是,如果那些文字均属于相当晚的时代,那么从在同一地点存在五铢钱的事实中,我们便不会得出任何结论了。
那名护送我们的中国兵卒(他事实上是土著人)今天来到了发掘现场,他的出现使我们的发掘者劲头倍增。他变得与我们的那些哥萨克人一样喜形于色。他还经过与伊利亚佐夫的一次赛马之后,互相称兄道弟。此人于晚上又叙述说,他于某一天,曾听到瓦阳为之医眼疾的那名老领事官,对那个出发为我去石窟作向导的人说:不要向他们展示石窟。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人佯装不知道石窟的方位,而整个村庄又似乎都知道其具体位置。由于民工们另外还抱怨说,那一天,当他们的报酬转到老领事官手中时,他过多地为自己而截留了。所以,我决定利用他明天的即将到来的机会,而对他做出微惩。
1906年11月11日,星期日
今天共有12名民工出发赴遗址。当瓦阳提前出发时,我与正患坐骨神经痛的努埃特为整理我们的搜集品而工作。我牺牲了几件太沉重而又没有多少价值的物品,把它们留在“图木舒克博物馆”中了。在此期间,我召来了那名老领事官,他事实上是一名“十户长”(突厥人的地方小官吏)。他向其大神们发誓,保证他从未发表过应受责备的言词。我对此并不非常坚信不疑,但我也仅满足于做出威胁,特别是由于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秘密争执,会促使我们的护卫骑兵向我们揭示那位患甲状腺病的肥胖“十户长”的欺骗行为。至于民工们的工资,他自称由于无法兑换货币,所以均未得以向他们支付。我们坚信,“十户长”在一名欧洲人眼中看来是罪犯,但他的行为就如同所有地方官府的行为一样。事实上,我不知道未能看到“石洞”,损失是否很大。因为,据新的信息资料来看,这里是指山上的一个石洞,人们于白天也如同黑夜一样,在那里都能见到“光亮”。由此而产生了许多有关宝石的传说,与勒亚依里塔格山(意为被称为“拉力”的宝石山)。但为了前往那里,至少需要去程一天和返程一天。尽管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个新向导,但我始终怀疑自己是否能重新开始这次远足。
我们完成了对K号遗址瓦砾的清理工作。我们从其中的K2号遗址中,还清理出了几块壁画(马蹄和一只手臂的造像等)。在重新研究出自I号小寺庙的物品时,我又发现了两块相当大的残片,各自代表着半身人像的残片。其上面残存着带镯子的手臂,手镯上的黄金已变成赭红色,使这条带镯子的裸臂如同穿紧身衣一般。我同样也令人清理了O处介于K和B之间遗址上的古建筑。我们另外还发现了走廊、方形小房间中提供的几块没有多大价值的残片。数面墙壁上都绘有壁画。我们还捡拾到一枚无法解读并已破碎的中国铜钱,还有一种带有一枚奇怪圆形装饰的把手。这次发掘还获得了一块经加工过的骨头,与昨天发现的那块很相似。在P号遗址处,我们又发现了一排小板凳,由其底座分开,转向内院。
1906年11月12日,星期一
由于今天是巴扎日(赶集日),所以有多名民工缺勤。但喀什人对于在图木舒克举办的每周一次闲谈的吸引力,不及多浪人(系指突厥牧民。李默德认为,他们是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混血后裔。操突厥语,形成了某些特殊的社团——译者)那样热情。多亏了这些人,我才依然获得12个人去工作。身体不适的努埃特留在了家中。
其中的一名民工,还几乎是一个孩子。他向我讲到了一尊佛像,地处山中很近的距离。他还自告奋勇地带我前往那里。我与他同去了,但我们在他所指出的地点,却什么也未能发现。他于是便向我承认,他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曾见过这尊佛像。但至少是我们向西北行进的这3.5公里的路程,并非完全是白白浪费。那里有一片沉降的山坳,整个通道过去都由一道山石形成的大墙封闭了。这是从喀什噶尔河沼泽地到恰尔巴格古城防御线上的一个新的据点,这条防御线因大山而划了一个大弧形。事实上,在距我前往地点勉强有1公里的地方,山脉向西和西南拐了一个弯。
K2号遗址的房子已被清理,它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了。我让人主攻对面一侧的Q号遗址。我们发掘出了一个土台护坡和底座,酷似另一侧的那一排,其中一个底座上带有供像的组成部分。那里的墙壁上也有绘画。最后,I号小寺庙确实提供了其广泛的雕像内容,但先前清理得很糟糕,我又让人对它做了一次彻底清空。这第2次发掘只能提供某些碎片了,唯有一个颇有价值的长小胡子男人的头像、一身带衣服褶裥的菩萨小像、一个长鸟喙人物的奇怪头像(可能为一尊歌乐神或音乐天歌神)。我们在I号遗址的墙沿下,发现了一处外貌相同的生石膏小薄像的存放处,现已完全粉碎了。它原来是在一根弯铁棍上塑成的,其外表覆盖了一层金箔。最后,清理工作使我们得以沿一行信徒像前进,其中的两躯供像在我们发掘的前几天就已经出土,明天也可能还会有新的发现。
在R号遗址的I处另一侧,我们在一个小房间中发现了一种中心祭坛。其墙壁上绘有壁画,但在令人遗憾的严重残损的小房间中,其背屏的墙壁也带有两个底座。在其中之一的对面,有一身小彩像被推翻和打碎。该尊像的装饰并不是浮雕状的,而是由绘画提供的。几块陶土碎片证实了我已经形成的一种假设。根据这种假设来看,主要是手脚之间那明显的偏差及其变形,应该是出自人们观察它们的视角不同的原因。我们确实主要是在浅浮雕上,于I号遗址的坍塌物中,发现了不是属于完整的造像,而肯定是属于浅浮雕的残片。
总而言之,其整体布局逐渐清晰了。尽管穆斯林墓葬造成了某些损坏,但它们可能还会使我们重新找到部分遗存,这是由于该古庙已经变成从未被铲平过的穆斯林大公墓了。事实上,那里从未由穆斯林们居住过。“九僧房”或托古孜—萨莱一名,于其最狭隘的意义上,便是指山北的房屋以及同一侧的防御工事。本处是特指穆斯林墓葬,也就是麻扎。中心建筑的本身也应为一处墓地,更可能是带洞穴的住宅。如果釉砖都位于佛教遗址中央,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均出自那些过去比较富丽堂皇,而今已破败不堪的穆斯林墓。如果某些穆斯林可能在佛寺后部建起来了住宅,那么他们就只能是管理中心麻扎的几位谢赫(指年长的人和以其知识而受尊重的人——译者)。
1906年11月13日,星期二
我们过早地放弃发掘,肯定是一个大错误,这一天收获了一大批发现物。在继续清理K号遗址的平坡时,使我们几乎推进到I号寺庙的高度。我们找到了一块被烧焦的木板,上面雕刻了一个人物的站像,是一种菩萨像。另外两块木板同样也被烧焦了,带有菱形装饰。
R号遗址已被做了彻底清理,它由一套矩形房间组成,而该房间又带有一间同样亦为矩形的小内间,此外还有一条从Q号护坡向下行的坡道。
我们的工作同样在I号遗址持续。它证明了该寺庙两侧现有的一行供养人像,绘在背屏内侧,由残损严重的其他雕刻图案所连接。寺庙的前部已塌到了山下。在I号寺庙的外墙一线,我们还发现了几个颇有价值的头像:一身梳高发髻的女子像,一个马头像、一个呈佛罗伦萨学派气度的人头像、一个秃头的老人像。最后,在这一堆清理出的废物中,还有一页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页纸的一角,两侧均写有婆罗谜文字母。它们逃脱了大火之劫。这是我们于此所获得的第一件此类文物。
但这一天的最大意义,也可能集中于S号房间了,这个带有壁画的房间,就如同其他许多房间一样,已经部分坍塌,与混凝土的断裂处相吻合。我们从中清理出了下部的一个房间,那里落下了几个漂亮的人头像。房间里主要由装满骨灰的骨灰瓮占据。这些骨灰瓮的形状相当多样化。我们带回了一种骨灰罐,火烧使它产生了一种相当漂亮的绿色。所有这些罐子都装有骨灰,而不仅仅是“贵族的”骨骸。在这一方面,我们尚有工作需要去做。我们将要看一下,在我们已经清理出的某些房间之下,是否还会有其他下层的房间。
那些土著人非常乐意与我们共同工作,每天25个戈比(2.5个天罡)。但他们都相当萎靡不振。无论如何,我们对于自己所获得的成果,还是感到相当吃惊。数日之前,我们无意中听到了一场颇具启示意义的对话,它是在一名前往阿克苏经商的肥胖中原人,与另一名毫无成功希望地前往于阗淘四个月黄金和玉石的人之间展开的对话。那名肥胖商人说:“这些欧洲人怎么能够知道地下有文物呢?”那名淘金工说:“这是由于他们有大镜子,他们以此从很远的地方发现一切。如果他们于其家中未能看到本处的地下,那么他们为什么为做一次从他们那里赶到我们这里的如此漫长旅行呢?”这种论调未受到反驳,那名阿克苏的胖商贾,蓄有一副用红丝线扎起来的胡须,只以缄口不言为乐。
1906年11月14日,星期三
骨灰的存放处已被清空,但我们却未发现任何新东西。我们从中还仅仅发现一个出自上一层的佛头像,还有一种带有四个活动小环的金属容器。I号小寺庙已被我们做了彻底清理,我们于东北方发现了一道门,也就是该门朝大土台护坡开放的地方。在两侧是五身巨大的人物立像,脚蹬靴子和身穿拖到膝盖的长内衣(在人们进入寺庙的方向,三身像位于大门的左侧,两身位于右侧)。此外,两侧的祈愿者像至今尚清晰可见,进口方向左侧的祈愿者像均为女子,右部的像则全部是男子。这种原料物质已变得极其易脆。保存得最完好者,便是形成中心支架的麦秸束。在进门处的左角落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很薄的金币,没有明显可见的标志,并且已经部分地被氧化。
对于骨灰存放处的情况,我忘记指出了,人们可以通过一种翻板活门而进入那里。可能是有人从那里垂放下了一架梯子,从而可以使人到达一扇今天已被火烧毁的木门。从骨灰存放处可以向内打开该门,从而进入那里。这一侧的土台护坡的界限尚未被彻底澄清。我们发掘出了新的建筑物,但我们只能在稍晚时才能对此做出决断。
在继续清理大土丘一侧的土台护坡后,我们便到达了一处阶梯,我们还必须于此之外继续进行寻找。在清理该土台护坡时,我们出于一种极好的运气,发现了用婆罗谜字母写的一小卷写本,其中很可能包括发愿文。因此,这是于此地在两天中发现的两种印度文字的样本之一。
我今天还携归了一颗头颅,带有下颌。废墟中始终都有丰富的遗骸,有一名穆斯林恰恰让人埋葬在横穿I号寺庙大门的地方。
努埃特自数日以来,一直受坐骨神经痛之苦。瓦阳也很不舒服,自我们到达这里以来,我们就自认为肯定是在玉代克里克和玛喇尔巴什之间染上了疟疾。这一切再加上我们已经长期于此停留,从而促使我们出发,以直接赴库车,我们的皮大衣和日用食品都在那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