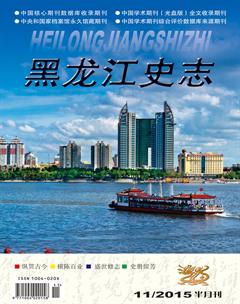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受害者
柔石的代表作《为奴隶的母亲》,主要讲述了20世纪20、30年代浙东某地乡下盛行的“典妻”制度下一个受迫害女性的生活轨迹,从而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萧红曾经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可以想象得出旧时代女性的尴尬境遇。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春宝娘的悲惨遭遇常常会引起读者的共鸣,激起读者对典妻这一陋习的痛恨。但细读文本之后,小说中春宝娘以外的另一个女性,秀才的原配妻子,实际上作为一个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的另类受害者,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历史上,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始终从属于男性,她们地位卑微,多数是名副其实的附庸。柔石笔下的秀才妻子从本质上说也不例外,但她在普遍性中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就性格上而言,她是一位在封建宗法社会中令丈夫“闻风丧胆”的悍妇。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宗法文化,宗法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无我”。学贯中西却又顽固保守的文化怪杰辜鸿铭甚至说中国存在一种“无我宗教”。[1]秀才妻子是生活在这样大环境下的小人物,自然深受这种“无我”性的影响。她受惠于封建思想得以巩固“正妻”地位,自然从内心深处去维护这种思想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同时,这种思想又反过来使她精神上更加孤立。一方面,她过着体面的生活,不会为衣食住行而忧虑;另一方面,她的内心是失意的,却还要用假面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她很不幸地在这种“无我”社会中成为一个失去自我的可恨又可怜的悲剧人物。
一、妻子的权威
作为秀才的妻子,她拥有正妻的地位和较优裕的物质生活,这个富足的家庭事事皆由她来做主,看似要比春宝娘幸福、风光得多,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因为,她没有属于自己的子女。在封建社会中,子嗣对于大家庭中的女人而言,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关系着姓氏血脉的延续,也是家族兴旺发达的标志。如果一个女人在封建大家族中没有子嗣,就意味着没有地位。表面上,秀才的妻子好像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她在家中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在这所谓的权威背后却时时潜伏着危机——她现有的地位和一切都随时可能因为没有履行传宗接代的义务而被剥夺。于是,她主动找到沈家婆要求为自己的丈夫典一个妻子,以繁衍子嗣。为此,她极力装出一副宽容大量的样子,实际内心中则充满了怨恨。她认为自己是秀才明媒正娶的妻子,在家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她竭力表现出的知书达礼,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当被典来的女人初入这个家庭的时候,她温和的态度让人一度以为她是很好相处的,但是随着对话的继续,会慢慢发现她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软中带硬的言辞向春宝娘宣示了她在家中的权威,尤其言语间不时还炫耀她与秀才之间美满而幸福的生活,言谈中,我们知道,他们也曾生育过一个孩子,只可惜早早的夭折了,并指出她也曾劝秀才纳妾,但是秀才出于对她的爱,不曾有这样的打算。精明而富有心计的举动背后,却更多的是苍白的、无可奈何的掩饰。而在春宝娘住进来以后,指桑骂槐的事件更是多次上演,她表面上的温和已荡然无存,内心的脆弱让她变本加厉地在精神上折磨春宝娘,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压抑得以宣泄。进而,她又通过教训秀才来离间他与春宝娘的关系,虽然这一举措并没有如她所愿达到预定效果。随着秋宝的诞生,她“借腹生子”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更加紧了驱赶春宝娘的脚步,以致于利用嫡庶有别的封建伦理道德欲强迫秋宝叫自己“妈妈”,叫自己的亲生母亲“婶婶”,最终她用行动上的隔离取代了形式上的隔离,将秋宝与他的生身母亲彻底地拆开,从而达到了捍卫自己家庭地位的目的。
二、妻子的悲苦
秀才的妻子既是“无我”文化的维护者,又是宗法文化的受害者。她不得不亲自为丈夫安排典妻,不得不痛苦地眼看着自己的丈夫与典来的女人同房。她通过责骂来宣泄情绪,但是,她无法理解所谓的宗法制度,更不可能从中找到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根源。她不甘心和别人分享丈夫的爱,可是,她不能为丈夫生儿育女,她犯了“七出”之条,能够保留妻子的名分已经很幸运了,这种情况下,丈夫要求典妻,她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在宗族利益面前,她只能委屈求全。因为在宗法社会里“婚约不是那个女子和男人之间的事,而是那个女子同她丈夫家庭的事,她不是同他本人结婚,而是进入他的家庭”,“她不仅在对丈夫本人负责,还对他的家庭负有责任”,“一位真正的中国妇人是没有自我的”。[2]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妻子同时也在毫不含糊地用宗法文化剥夺别人做人的权利,要求别人“无我”。她迫使秋宝娘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也剥夺了秋宝享受母爱的权利。[3]因为她没有经历抚育孩子的完整过程,她体会不到孩子与母亲之间那难以割断的亲缘关系。她无法意识到这样的举动对两位母亲来说都是一种身心上的巨大伤害,最终凭借着家中的地位,用她残存的优越感来压制比她更可怜的春宝娘,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可怜。做为封建大家庭的一员,她默默地隐藏起自己的真性情,将情感寄托在“南无阿弥陀佛”上。她既怕没有子嗣无以面对列祖列宗以及族人的指责,又怕丈夫移情别恋,可以说宗法制大家族里女人的辛酸在她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秀才眼中的“她”
她是秀才的结发妻子,不需多加交待,两人是包办婚姻的结合,没有爱情的基础,只能说互相依赖生活多年,虽然没有爱情的存在,但还有亲情的融合,只是两人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硬伤——她未能为丈夫生下延续香火的子嗣。封建社会最讲究的便是家族的繁衍,这是整个家族势力得以发展的基础。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日渐衰老的容颜时刻提醒着丈夫,两人之间是注定没有孩子的。这一切,她的丈夫又何尝不清楚。也许她年轻时的容颜曾令他怦然心动过,可时间总是无情的,它没能为她留住容颜和他们珍贵的孩子。丈夫虽然表面没有言语,但并不代表他内心没有想法,于是,她“大度”地提出为丈夫典妻,丈夫欣然的同意了。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她很能干,将家里的一切大小事物打理的井井有条,不需要秀才额外的操心,但却不是一个好母亲,因为她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她也曾努力做好,但终归失败,她“善解人意”的提出为他典置一个女人来传递香火,可以肯定秀才很高兴,毕竟这能让秀才在同族面前抬起头,不会落得个没有后代的结局。她也很体贴,亲自交待下去去寻找可以典来的女人,或许此时的秀才会发自内心的感激妻子。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春宝娘的到来,一切都在悄然改变,妻子会经常地莫名大骂,她到如今怎么变得这样不可理喻,原来自己的妻子也是个善妒的女人。她怎么会这般的贪得无厌,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该拥有的她都拥有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何必和一个典来的女人争宠呢,这太不符合自己的身份了。她应该安静些才好,无论如何将来的孩子都会尊称她一声母亲的,她有什么可焦躁的,难道她还不相信几十年的夫妻之情,她怎么就不明白呢,看来是太过尊重她了。秀才哪里会体会到妻子内心的真实想法呢,他的妻子只不过是在用她仅有的一点权力和地位来反抗这不公的待遇罢了。
四、小结
秀才的妻子在气势上看起来咄咄逼人,实际上她很脆弱,仅仅只是徒有其表。她名义上是秀才的正妻,但她何尝不是封建体制下的牺牲品呢,何尝不被封建礼教压得无法喘息呢?我们不能因为她的强悍就对其全盘否定,要辩证地来看待她的处境,既有为妻的一面,又有被欺的一面。总体说来她又何尝不是一个弱者呢?
参考文献:
[1]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
[2]王兴泉《典妻:中国封建社会“无我”文化的怪胎——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文化解读》宁波职业学院学报2002
作者简介:武林楠,女,1990年出生,籍贯黑龙江省宾县,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