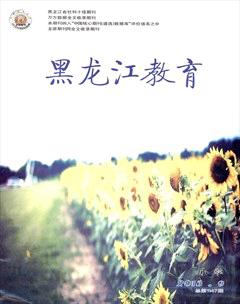我的恩师庞继轩先生
孙彦俊
有人说,遇到一位好老师乃人生之大幸,我深以为然。回首求学路,虽然念的都是极普通的平民学校,但幸运的是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使我的学生时代充满了温暖和光明。在众多恩师中,最令我景仰的一位是庞继轩先生。
先生属兔,今年77岁。他中等身材,已略显发福,但腰杆一如年轻人一样挺拔。一头浓发夹杂着少许银丝,一副银边近视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依然明亮而有神采。他走起路来脚步扎实、平稳,如果碰上紧要的事,小跑一段也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的。不相识的人无论如何也猜不到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
先生退休前是一所职业高中的语文教师。我上初中二年级时,跟先生学过一段时间作文(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课外辅导班)。现在回想起来,先生当时都教了些什么,已全然不记得了,只有那本珍藏至今的作文本上刚劲的朱红小楷和细细密密的圈改符号记录着先生治学的严谨。初中毕业后,我上了师范,同列先生门墙的刘勇考上了令人称羡的省重点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因为我们从小就过从甚密,又都对先生尊敬有加,所以从那时起,我们就时常结伴到先生府上闲坐。当初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只是感觉和先生交流,自己的知识又丰富了一些,仿佛自己又长大了一些。细算起来,与先生相识已经整整24个年头了,我们的这种交往从未间断过,而且历久弥深。每次去拜望先生,几乎都是彻夜长谈,不知不觉间,深夜已至,似乎还总有说不完的话。与先生围炉夜话很自由惬意,我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即使说得不正确或失之偏颇,也总能听到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套用“读书无禁区”这句话,我们是交谈无禁区——谈论时事,钩沉历史,月旦人物,说工作,谈教育,聊家事,畅所欲言。我喜欢这样的闲谈,它比严肃的课堂更能增广见闻,启人心智。也正是在这样的闲谈中,先生广博精深的学识、恭谨严肃的教学风范、豁达坦然的人生态度和刚正不阿的风骨都给我以深远影响。
先生好学且博学。其实先生的学历并不高,先生曾幽默地和我说:咱爷俩还是“半个校友”呢。他是“大跃进”时期读的师范学校。跃进的年代,各行各业都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连教育也如此,恨不得十天半月就建几所哈佛、剑桥。先生上师范三年级时正值1959年秋季,由于哈尔滨缺少中学教师,当时的教育部门决定让那届师范生到师专去接受大专教育,一年后速成为中学教师。被时代裹挟着的先生虽然也有一腔献身教育事业的热情,但并未被跃进的风潮蒙昧理智。他深知自己的学识浅陋,必须刻苦学习,发愤读书,以适应中学教育的需要。先生年轻时有个作家梦,他从书架上取出霍松林编著的《文艺学概论》给我们看。这本书是1958年出版的,书脊处已有些残破,书页已经泛黄。先生说,这本书他不知读过多少遍,开始读不懂,就是靠勤奋一点一点硬啃明白的,也因此积累了一些文艺理论常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工作以后,先生又攻读古诗文,每晚灯下苦读不辍,从中国文学的发轫《诗经》读起,再读“四书五经”,读中国文学史中的名家名篇。先生说,因为是自学,只能是囫囵吞枣,理解不深,不过也因此打下了一些古文的底子。这样的苦读通常都是偷偷进行的,因为当时在知识界中有一顶“白专道路”的帽子,一旦被戴上,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生从年轻时就喜逛书店,尤其是古旧书店,虽然当时囊中羞涩,但还是将心爱的书攒了满满两大书柜。先生买书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去年到台湾旅游,还背回几本古典文学。先生说,他喜欢那些竖版繁体字印刷的书。
先生文采斐然,笔墨传情,诗书文俱佳。写诗,偏爱近体。花花草草、鸟兽鱼虫,生活琐事、国家大事,凡能触动情思的人事景物,皆信手拈来,妙笔生花。随便举两例。去年,先生76岁高龄,方遂登泰山之愿,作七律一首以抒怀。诗云:“古稀尚有凌云志,拄杖躬行上泰山。玉陛冲霄升渐紧,琼岩夹道莽还闲。仰观遗墨明今古,俯看群峰叹宇寰。夫子登临天下小,向贤岂惧路途艰。”我儿子不满周岁时,一日,裸身俯卧床榻,脸下放了一本书,看似作读书状,妻为他照了一张照片,发到网上。当时只觉得好玩,心里还暗笑这小子冒充斯文。先生看后赞不绝口,赋诗一首曰《孺子观书图》:“孙家孺子性锺书,目驻神凝百事无。堪笑赤身浑不觉,只缘心有大鹏图。”书法,也是先生的雅好。铁画银勾,笔笔不苟,亦如先生之为人。先生自谦,说自己的字没有师承,没有功底,涂鸦而已,因此先生的墨迹从不肯轻易示人。我于书法是门外汉,不敢妄下断语,只是看着先生的字感觉很舒服。先生从年轻时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惜在动荡年代,都付之一炬了。到了晚年,先生仍勤于笔耕,为母亲写传记,曰《萱堂生死录》,已定稿四卷,近三十万字,还有两卷尚未完成。我和刘勇先睹为快,折服于先生惊人的记忆和朴拙的文风,更慨叹先生秉笔直书的勇气——即使对已仙逝多年仍深爱着的母亲也是功过分明,毫不讳言。先生常说,写人写事,必须用史学家的态度。
先生在教学上也是出乎其类的。先生教我作文时,我年龄尚小,还品咂不出多少味道,只感觉先生出语不凡,口才极佳,很喜欢听他讲课。如今已为人师多年的我才深深体悟到,能让学生真正喜欢上自己的教学谈何容易!我只是先生的课外辅导班弟子,没能幸运地走进先生的正规课堂接受教育,因此谈先生的教学水平多是隔靴搔痒,只能从我知道的一些小事情中找到些旁证。先生在曾经待过的几所学校里,多是担任语文组教学组长。青年教师作公开教学都常常向先生求教,先生则有求必应,尽心指导。经先生指导的公开课总能获得好评。我们去先生家做客,用的是一套古色古香的茶具,这是先生在荣退之时,那些曾受教于先生的青年教师送给先生留念的。在先生的众多学生中,我属于小字辈儿的,那些40后、50后、60后的师兄师姐中有多人现在仍与先生保持着联系,甚至陪着他饱览祖国的名山大川。他们中有的喜欢写写诗词,常拿去请教先生。先生和他们切磋砥砺,此唱彼和,悠然怡然。
先生早年命运多舛,但从不失文人的风骨。因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又是“臭老九”,再加上耿介求真的性格,命运之坎坷是可想而知的。1964年,“四清”运动波及校园。先生为了班级中入团积极分子的利益与一个“根正苗红”的团干部起了争执。此事被逐级上报,差一点就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先生谈起这段人生经历颇为感慨,讲到动情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也唏嘘长叹。是的,往事并不如烟。人生中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终难释怀!
先生说自己一生性愚,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愚堂”,自号“愚堂主人”。我请书法家韩荣吉老师题写斋号,并做成匾额送给先生。先生又赋诗一首:“一生坎坷只缘愚,愚孝愚忠百事疏。多少伤情摧肺腑,老来常恨死观书。”先生用这样的诗句总结自己的人生,未免过于悲观,但倒也是先生命运的真实写照。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中,先生都不阿谀、不媚俗,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刚直不阿的性格。这一点说一说容易,能做到的又有几人!
值得庆幸的是,先生晚年适逢改革开放,生活有了改观,衣食无忧,儿孙满堂。退休后,先生去老年大学学习电脑。从入门课开始,了解鼠标,熟悉键盘,学习打字,认识常用软件的功能,处处一丝不苟,如同一个认真的小学生。现在,先生已经成了忠实的网民,上网,写博客,聊QQ,发微信,看电影,甚至“偷菜,抢车位,打麻将”也偶尔为之。上文提到的近三十万字的《萱堂生死录》,就是在电脑上撰写的。
先生好客,师母善良贤惠。我们每次去,师母都忙前忙后,烟、茶、水果、干果、小点,样样不少;每次走,无论冬夏,也无论时间早晚,即使是深夜一两点钟,先生都执意下楼远送,看着我们上车,目送我们远去。我有时带上淘儿子去拜见师爷师奶,他们总是买上一大堆好吃的好玩的。儿子也不拘束,上蹿下跳,翻箱倒柜,喷壶浇花,饼干喂鱼,倏忽间,客厅像遭了打劫一般。师爷师奶看着不但不生气,还满面春风地说,“这就叫含饴弄孙”。
最近几年,先生又爱上了旅游,几乎每年都要走上几个地方,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观,都喜欢转上一转。很难想象,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还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在山东曲阜,先生照的一张相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先生站在孔子墓碑前神情肃穆,鞠躬致敬。那时那刻,先生会想什么呢?我猜,先生大概会感慨自己喜忧参半的教育人生吧!也许他会想:孔老夫子啊,我这一辈子追随您,前半生悲也由您,后半生喜也由您……
看着这张照片,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我想,先生年轻时虽饱经沧桑,但“晚景弥秀,晴江转春”,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又是一年教师节。我写下这些文字,献给我的先生,祝愿先生长寿安康,祈盼来日方长,慢慢叙写我们的师生情缘!
(作者单位:哈尔滨市南马路学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