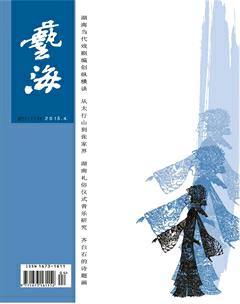亚格博和他的牦牛博物馆
佘学先
[摘要]数千年来,牦牛和藏族人民相伴相随,尽其所有提供了藏族人民衣、食、住、行、运、烧、耕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牦牛的存在和使用,涉及到青藏高原的政治、战争、教育、商业、医学、娱乐、物质用品等,深刻地影响了藏族人民的精神性格,也影响了藏族人民物质生活。十世班禅大师曾经说过:“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
[关键词]亚格博 吴雨初 青藏高原 牦牛博物馆 藏族
牦牛礼赞
八思巴·洛追坚赞
体形犹如大云朵 腾飞凌驾行空间 鼻孔嘴中喷黑雾 舌头摆动如电击
吼声似雷传四方 蹄色恍若蓝宝石 双蹄撞击震大地 角尖摆动破山峰
双目炯炯如日月 恍惚来往云端间 尾巴摇曳似树苗 随风甩散朵朵云
摆尾之声传四方 此物繁衍大雪域 四蹄物中最奇妙 调服内心能镇定
耐力超过四方众 无情敌人举刀时 心中应存怜悯意
八思巴·洛追坚赞(公元1235-1280),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位祖师,元代著名的宗教领袖、
政治家和学者。本文摘自德格版《八思巴文集》第三卷。
“亚格博”是藏语,读起来很响亮,其实翻译成汉语,就是“牦牛老头”的意思。
五年前的秋天,亚格博还是北京出版集团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在这之前,是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这时的他还不知道,后来藏族兄弟赠予他的藏族名字“亚格博”会成为他的名片,“亚格博”会成为一个拉萨街头巷尾热议的人。那时,他的名字叫吴雨初。
那段时间,亚格博总觉得有点不爽,脑子里总是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开始是模糊的、个体的,后来清晰了,是牦牛,成群结队汹涌而来撞击于胸。他心灵深处的一根弦被重重的拨响,牦牛,是西藏的牦牛在召唤呢。离开西藏十多年了,京城优裕的生活环境、繁重的事务工作、渐渐平复的西藏情结,并没有模糊亚格博对牦牛的记忆,在那曲工作十多年的日子里,牦牛堪比兄弟、救命恩人、衣食父母和知己。
牦牛,属于牛属牦牛亚属的大型哺乳类动物,也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大型哺乳类动物,主要分布在以青藏高原为中心的高海拔地区,是高寒地区的特有牛种,草食性反刍动物。
数千年来,牦牛和藏族人民相伴相随,尽其所有提供了藏族人民衣、食、住、行、运、烧、耕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牦牛的存在和使用,涉及到青藏高原的政治、战争、教育、商业、医学、娱乐、物质用品等,深刻地影响了藏族人民的精神性格,也影响了藏族人民物质生活。十世班禅大师曾经说过:“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
牦牛是藏族历史上重要的图腾崇拜物,在藏族先民描述开天辟地的古歌里,他们运用非凡的想象力,将高山大地和牦牛融为一体。有一首叫《斯巴宰牛歌》的古歌传唱至今,歌中唱到:
斯巴宰牛儿时,砍下牛头放哪里?
剥下牛皮铺哪里?割下牛尾扔哪里?
斯巴宰牛儿时,
砍下牛头放高处,所以山峰高高耸;
剥下牛皮铺平地,所以大地平坦坦;
割下牛尾扔山阴,所以山林郁葱葱。
从这首古歌中不难看出,牦牛从藏民族原始的崇拜物,伴随着神话、传说、宗教等元素,形成了一种古老的牦牛文化。
“憨厚、忠诚、悲悯、坚韧、勇悍、尽命”,亚格博归纳着“高原之舟”的特性,这不正是祖祖辈辈生活在世界屋脊上的、勤劳勇敢的藏民族的特性吗?从那以后,亚格博常常陷入彻夜难眠的境地。后来他告诉我,那时他正在北京市委党校学习,“整天都在打瞌睡,满脑子的牦牛。”
亚格博对牦牛的深厚感情,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生死经历开始的。那时他在那曲地区嘉黎县T作。那年,嘉黎县遭遇百年难遇的特大雪灾,亚格博随运送救灾物资的车队从那曲出发赶往嘉黎。在距那曲和嘉黎县都有一百多公里的阿伊拉山,一场超级暴风雪困住了车队。
“五天四夜,没有食物,不能取暖,积雪高达四米,生存的希望极为渺茫。”谈起那次经历,事隔三十多年亚格博还心有余悸。
车队用随行携带的发报机求援。地区和县里同时行动。嘉黎县委组织人员连夜敲锣通知各户烙饼。浩浩荡荡的救援队伍出发了,车队陷住了,换成马队,马队困住了,改用牦牛群。五天四夜之后,当在茫茫雪原中看见那群牦牛时,亚格博热泪盈眶。
“建一座牦牛博物馆。”亚格博豁然开朗,心结顿开。为什么建?怎么建?通过牦牛这个符号要传递什么?亚格博一条条梳理着,构思着。构思成熟后,亚格博向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副市长蔡赴朝征求意见;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号,时任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听取汇报,得到肯定和支持;二零一一年四月七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听取汇报,并于当日批示:“设想有创意,丰富了支援拉萨的T作内涵。”要求“研究给予支持的措施。”
国家机器运转起来是强大而快捷的,二零一一年六月五日,国家六个部门的省部级领导联席听取牦牛馆创意汇报,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当即表示:牦牛馆的建成,将是“国内填补空白,世界独一无二。”
2011年8月31日,牦牛博物馆在拉萨破土奠基。
有了国家的支持,故事似乎有了结局,其实远不是如此。故事才刚刚开始呢。
牦牛博物馆的馆址、地基、基础设施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援建,馆内藏品征集、牦牛群种调查、分布地域、参与筹建人员开支等等,都得白行解决。
亚格博,这个敏于思,捷于行的江西汉子作出了一个让许多人瞠目结舌的举动:辞去北京出版集团董事长职务,只身进藏筹备“西藏牦牛博物馆”。
2011年6月7日,亚格博怀揣一个ppt文件,只身来到拉萨,在仙足岛租下一间民居,开始了他的漫漫求索之路。
要建牦牛馆,首先得真正懂牦牛,它的历史渊源、种群差异、分布地域、特别是牦牛和藏族人民难以割舍的纠结交集等,都要翔实准确,让将来的参观者一目了然。
亚格博开始行动了,他和陆续加入他的团队的伙伴们历时四个月,行程一万二千多公里,足迹踏遍西藏、青海、四川、甘肃藏区,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此后,他们又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和展品征集,总行程达三万公里。
牦牛是牛属动物中最能适应高寒气候而延续至今的物种,属珍奇稀有的畜种资源,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6000米,自然条件极度艰苦的高原地区。世界上现存的牦牛总头数约1500万头,分布在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蒙古等国。其中,中国有牦牛1400万头,占世界牦牛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二以上。中国的牦牛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包括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四川、甘肃、云南等高山原野。
藏语称牦牛为“yag”,据专家研究并认定,现在的家养牦牛,是距今五千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由我国藏族的先民古羌人在藏北羌塘等地区,将捕获的野牦牛驯养而来的。据历史学家任乃强考证:“羌人把野牦牛驯养成牦牛,当比他们驯养成功绵羊的时间要晚得多……羌族在中原的殷、周之前,已经把野牛驯养成乳、肉、毛、役兼用的主要家畜……”
牦牛在青藏高原被我国古羌人驯养之后,随着古羌人的游牧、迁徙,以及劳动手段的改进,生产水平的提高,商业贸易的发展而向其四周适应生存的地区扩展。其东,从巴颜喀那山脉进入松潘草地(现四川阿坝、若尔盖、红原等县草地)而至大巴山区;其南,翻过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些山口,进入喜马拉雅南坡高山草地;其西,通过阿里草原进入克什米尔及其临近地区;其北,越过昆仑山脉和经由克什米尔而进入帕米尔及其以北和天山南北、阿尔泰地区。在以后的年代里,逐步形成现今牦牛的分布地域。
说起第一次万里跋涉,亚格博感慨万千,他说牦牛博物馆奠基的那一天,他开通了白己的博客。
“你知道我的博客现在有多少粉丝吗?”他表情有些神秘地看着我,希望我说出一个数字,我没有概念,只好沉默。
“八十三万。”他有点得意,然后又补充说:“网络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亚格博如数家珍地讲述他的考察之旅。
西藏好办,那曲是我工作过的地方,没问题。阿里没熟人,有位热心的区领导给我开了一个单子,我按图索骥,一路绿灯。出了西藏,就得靠自己了。在青海,想去一个县考察,但一个人都不认识,就去博客上找,还真找到一位。电话拨过去,是个女的,对方说不巧,正在西宁开会,不过没事,你去县政府,会有人接待。到了县里,安排很周到,考察很顺利,一打听,她是这儿的县长。在四川,要去藏区一个偏远的县考察,还是在博客上找到一位实名的粉丝,是那个县的县委书记,接待很热情,在饭桌上时,他附在我耳边悄悄问:“亚格博,能不能把牦牛博物馆办在我们县?”当然,也有波折的时候。在甘肃,我在甘肃省博物馆看见一件展品“青铜牦牛”,看标签,原件收藏在天祝县博物馆。回到房间查博客,上面有人介绍说天祝县博物馆有一个“牦牛迷”。我索来电话打过去,对方一看是北京的号,毫不客气地说:“我遇到你这种骗子太多了。”电话挂了。第二天,到了天祝县博物馆,馆员说“牦牛迷”在楼上。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外地。第三天,我又去了,“牦牛迷”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摸清了我的底细,我们见面了。交杯换盏坦荡畅谈后,居然变成朋友。在后来的“牦牛博物馆捐赠日”的捐赠仪式上,牦牛迷把他亲白设计的、矗立在甘肃广场上的、重达九百六十吨的世界最大牦牛雕像的原型小样,捐赠给了牦牛博物馆。那次考察像一次火炬传递,一站接一站,站站相连,畅快淋漓。感谢网友,感谢网络。
“四个月,一万二千公里,全程仅仅只爆过一次胎,奇迹呀。”亚格博摇摇头,沉思片刻,语气凝重地强调:“人行公益,天必助之。”
回到拉萨,馆藏物件的征集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没有钱,又要买最好的物件,你是怎么做到的?”我问。
“砍价,往最低价砍。”
“行么?”
“当然,商人重利,普通是谈不拢的。但我告诉对方,你卖给我的东西,我一件也不会私藏,你都会在将来牦牛博物馆的展柜里看到。所有人都会看到曾经属于你的藏品。藏族人是忠厚的,十有八九能谈成。”
亚格博向我隆重介绍了一位名叫次仁扎西的尼泊尔籍藏族老人。
次仁扎西六十多岁了,在拉萨做地毯生意。最初听人说有个汉人要在拉萨办牦牛博物馆,他不相信。后来说的人多了,他就去找亚格博。聊了一会,老人走了。过了几天,老人托亚格博的一位朋友请亚格博去家里吃晚饭。席间言谈甚欢,但谁也没谈博物馆,更没谈藏品。吃完饭喝茶,老人突然起身从里屋拿出四件藏品。亚格博顿时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珍品!绝对是年代久远的真品!这得要多少钱啊?”亚格博欣喜中有忧虑,忧虑中有一丝无望,以目前的经济实力,他没有支付能力。
“我的藏品不卖。”老人一开口,亚格博几乎陷入绝望。
“不过,我决定捐给牦牛博物馆。”老人大喘气的说话方式让亚格博喘不过气来。
欣喜若狂的亚格博抱起老人捐赠的藏品准备告辞,老人拦住他说:“别急。”然后又从里屋提出一个编织袋,打开,桌面上出现了七件精美的藏品。
“这些也是捐给牦牛博取馆的。”
更令亚格博惊喜的事发生在第二天。
一大早,亚格博的房门被敲开了。是次仁扎西老人的儿子,怀里抱着一台电脑。一进门,他就插上电源,打开电脑。亚格博目瞪口呆,画面上一一呈现出七十五件品像精美的藏品。
“阿爸啦说了,这些全部捐给牦牛博物馆。”
这些藏品当时分放在香港、尼泊尔等地,次仁扎西老人和他的儿子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整理打包运回拉萨,在二零一三年“5.18牦牛博物馆捐赠日”上,一次性全部捐出。事后,有记者采访次仁扎西老人,为什么一次捐出这么多的珍贵藏品,老人语重心长地说:
“西藏牦牛博物馆是藏族人的家,也是这些藏品的家。”
2014年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西藏牦牛博物馆”开馆运行。这一天,博物馆只送了三百份请柬,来馆人数将近两千。许多慕名前来者随身都带着自己珍藏的物件,要求当场捐赠。
走进“西藏牦牛博物馆”,四大展厅处处令人震撼:浓郁的西藏氛围、气势磅礴的牦牛群阵、原始古朴的历史遗件、形象翔实的牦牛知识、精美绝伦的唐卡壁画、优美动听的西藏音乐,无不彰显出不屈的牦牛精神和“人间天堂,天上西藏”的美妙境界。
亚格博领着我参观展厅,亲自担任讲解员。
“这个牦牛头是牧民捐赠的,北京大学实验室进行了碳14探测,距今已有四万五千年。这个是则介拉捐赠的牦牛皮制作的天珠,有许多人出高价购买,他选择捐给牦牛博物馆。这个绿松石牦牛雕像,是赵焕植先生捐赠的,仅材料价值就超过五十万……
在“感恩牦牛厅”,每一位参观者都会驻足凝神。大厅中央是高高堆砌的,由牦牛头骨构成的玛尼堆,整个弧形的穹庐,镶嵌了一百零八个牦牛头,气势磅礴,夺人魂魄。
藏族人民崇拜牦牛,也崇拜牦牛角,那一对粗壮的犄角,白打被古羌人驯养后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先是早期人类最原始的容器,用于饮水、挤奶,或存放剩余食物等,后来成为牧区牧民挤奶的专用器具,被称为“阿汝”。据长者介绍,阿汝之名来自古老的牧区,是早期的牧人在他们还没有学会制造铁木容器之前的常用器皿。牦牛角实用性非常强,结实耐用,携带方便,不变形,不生锈。
藏族人民使用牦牛角,但更多的是崇拜。这是一种对牦牛图腾崇拜的变异。崇拜牦牛的某种器官,将它作为神器,是牦牛被神话以后,人们借助牦牛图腾的神力,达到禳除灾魔的作用。在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里,格萨尔用神兵收服红铜解野牦牛后,“拿野牦牛的头和角,作了霍尔黑魔姜国门的招魂物,把它们放在奔木惹山(阿尼玛卿山)的北方向毒蛇奔跑的地方,以降服四方妖魔,降服十八大城。”现在穿行在藏族人民居住的地区,很多山岭、房屋门槛上,都摆置着牦牛头角,或在玛尼堆上供奉牦牛头角,表示对牦牛的崇拜。
亚格博且行且解说,在一个展厅他驻足停下,指着展厅上方两幅织着牦牛图案的哈达说:“这是清代的哈达,价值超过百万。”
“花了多少钱?”我问。他一笑:“反正这个价格我买不起。
亚格博特地将我引到一个展厅左侧的一间小屋,有点眼熟,想起来了,像寺庙大殿旁供奉守护神的侧殿。
小屋没有门,进去的正中央摆放着一个牦牛头,三面墙和顶上画着黑底金线描绘的牦牛群像,抽象而又传神。
“这是加查县昂洛村的牧民曲扎画的。仅用了三天时间。因为第四天他要赶回去挖虫草。他来时,就是钢筋水泥,他自己搭脚手架,自己调颜料画,一气呵成,简直是个天才!”
我在资料室看到了一份采访资料,其中有一段曲扎的话,他说:“牦牛馆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个事情我们藏族人没有想到要做,吴老师做成了,我对吴老师非常佩服,您做的事情和活佛做的方向基本上是一样的。活佛是好的,但做的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教育引导,吴老师对藏文化理解很深并用实际行动来保护传承藏文化,我觉得您甚至比活佛还高一点。”看完这段话,我感触很深:牧民是朴实真诚的,只要你一心一意干实事,他们会领情,更不会吝惜自己发白内心的赞美之辞。
亚格博将我领到他借用的一间办公室里,是十一楼,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可以俯瞰牦牛博物馆全貌,博物馆后面是连绵起伏的山脊和山谷。
他和我并肩站在窗前远眺博物馆。良久,他问我:“你怎么看?”
我去过许多博物馆,就说:“这里毗邻拉萨火车站,将来到博物馆来参观的游客一定很多。博物馆里应该设一些商柜,专门出售与牦牛有关的纪念品,博物馆后面的山谷里可以建一个牦牛牧场,游客参观完博物馆后,可以零距离接触牦牛,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是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但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想更多地收集藏品,更好的充实博物馆,让牦牛家乡的人来到这里后,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我想起了牧民曲扎的另一段话:“在寺庙我们能拿到加持过的甘露丸,但我们能在牦牛博物馆看到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回味曲扎的这段话,回想刚才在牦牛博物馆看到的藏族民众扶老携幼留连往返的情景,我为自己的铜臭味惭愧,并由此相信:亚格博的传奇肯定还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