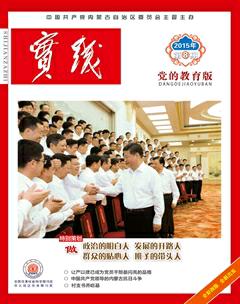维和女警在利比里亚
塔娜
内蒙古公安边防总队组建的第二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140名队员返程回国,仅有的4名女队员宛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利比里亚这片特殊的维和战场上,她们就像一朵朵绽放的玫瑰,散发着无比的芬芳。
直面埃博拉疫情
莎日娜是维和警察防暴队后勤分队医疗防疫组成员,也是4名女队员中年龄最大的。
2014年6月底 , 防暴队进驻任务区,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8月份大规模爆发。8月20日,防暴队驻地格林维尔市确认出现埃博拉确诊死亡病例,成为感染埃博拉病毒疫区。“死者距离防暴队驻勤哨位不到100米。”回忆起当地人处理尸体的过程,莎日娜依然心有余悸。
当晚,防暴队立即提升响应等级,连夜启动应对埃博拉疫情二级防控响应,全面升级防控措施,莎日娜随即投入防疫战斗。
防控埃博拉病毒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实行封闭管理,避免与外界接触。面对疫情,8人组成的医疗防疫组成为全体队员的重要保障。
从那天开始,一日3次对营区的洗化消毒,营区门口防疫室的值班加哨,以及对进出营区的人员车辆登记备案、体温检测、医学排查、适时洗消……为莎日娜的日常工作平添了繁重的一笔。
在病毒肆虐时期,执行任务时,队员们常常能看到埃博拉感染者横尸街头。队员们在这样高压、高危环境下执行任务,难免会产生恐惧心理和紧张情绪。为此,莎日娜每周都会进行两次心理巡诊,看看大家的身体是否健康、情绪是否稳定,聊聊家常,讲讲趣事,引导战友们敞开心扉。
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
苏梅娅是内蒙古边防总队医院检验科主任,她在防暴队一级医院从事化验工作。由于自然条件、卫生条件差,疟疾在利比里亚十分流行,发病率高,防疟疾成为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
8月的一天,防暴队的一名队员突感身体发热,苏梅娅第一时间赶到,一量体温,42度。
疟疾是热带传染病,没有临床经验、试纸有误差、参考资料不是很典型、没见过镜检下的疟原虫等多种因素,为治疗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苏梅娅抽取血清反复化验,在显微镜下仔细推敲,摸索中初步诊断疑似疟疾。经多方会诊后,实施针对性治疗,4天后,防暴队的第一例疟疾患者退烧痊愈。
一次晚饭前,隔壁乌克兰飞行队队医慌张地搀着一名病号朝医院方向奔来。乌克兰飞行队营区没有医院,防暴队一级医院早已成为他们最近的救治点。
这名飞行队员在做晚饭时用刀割了手,右手掌心自上而下的贯通伤足有10公分长、1公分深,解开绷带,瞬时鲜血直流。当日值班的苏梅娅迅速帮助伤员坐下摆好体位,一边给予口服高糖防止休克,一边开始清创缝合,半个多小时后伤口包扎完毕。临走时,那名飞行队员激动地用刚刚包扎好的手与所有医务人员握手致谢。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平日里,苏梅娅经常为男防暴队员们缝缝补补,帮厨做饭。“无论是对战友还是对国际友人,同在艰苦的环境中朝夕相处,给予别人帮助收获笑容,那种被人需要的价值感,是何等地幸福。”苏梅娅说。
遇见就别错过
在防暴队指挥中心执勤官戴高煜的手机相册里,有一张两瓶订制版“可口可乐”的照片。瓶身上的两行字加了特效格外耀眼,“戴高煜,遇见就别错过!”“戴高煜,我们永远在一起!”这两瓶可乐是戴高煜去年过生日时,在国内的男友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戴高煜8个月的精神食粮。
2011年6月,戴高煜从廊坊武警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呼伦贝尔市边防支队的一个基层边防派出所,在那里遇见了现在的男友何剑。经过3年的相处,这段感情在两个人的悉心呵护下,正要开花结果,戴高煜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择却不得不让他们分隔两地。
“上学时,每次路过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我总向往着当一名维和警察,终于有机会可以实现梦想了,机会难得,我不想错过。”顺利通过维和甄选后,戴高煜向何剑坦言。
纵使何剑有多么不舍、多么不高兴,面对女友的倔强、要强和不服输的韧劲,还是同意了她的选择。
出发那天,何剑穿着军装去车站为戴高煜送行。火车开动的瞬间,站台上,一个标准的军礼,何剑满含深情地目送女友,他在心里默许:“好好保重,平安凯旋!我会一直等着你。”车厢里,戴高煜郑重地回礼,待男友的身影离开视线,泪水夺眶而出。
最让戴高煜感动的是,在她离开家的这一年里,何剑逢年过节便去看她的父母。两家不在同一个城市,往返1200多公里的路程,何剑驱车跑了6次。戴高煜是家里的独生女,一向独立自主。去利比里亚维和是女儿的梦想,父母支持她的选择。埃博拉疫情大规模爆发后,他们只能偶尔通过电视新闻了解维和警察防暴队的消息。女儿到底过得怎么样?他们无从得知。
每次去看望戴高煜的父母,何剑总是把她通过微信传来的照片一一拿给他们看,给他们讲述她在维和期间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放心。
去年底,因工作成绩突出,何剑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三等功奖章。当时,他调侃道:“等戴高煜回来了,跟我显摆她的和平勋章,我也能有个荣誉跟她媲美吧。”
在历练中成长
“90后”乖乖女陶琳,是防暴队指挥中心执勤官。
2013年底,总队遴选维和警察防暴队员的通知一下,英语专业的陶琳义无反顾地报了名。初选、初训、集训、甄选,她顺利地踏上了前往利比里亚的征程。
进驻任务区的前两个月,靠着前一支队伍剩下的食品和联合国供应的给养维持生计,食物基本够吃。但原计划一个多月就能到达的海运补给物资,因西非地区持续蔓延埃博拉疫情整整推迟了两个月。
“后来只剩下银耳、木耳这两样干菜,凉拌、爆炒、炖汤,那段日子队员们戏称这道菜是‘黑白双煞。”陶琳说。
“I beg your pardon?”(请您再说一遍好吗?)第一次外出执行勤务时,陶琳担任翻译,需要与当地的维和警队对接。可他们的地方口音很重,说的英语陶琳一句都听不懂。陶琳只能将对方的话用手机录下来,逐字逐句拼写,最终完成了信息交换任务。
随后,陶琳把所有的谈话内容整理成听力资料,每天听,培养语感。后来,她已能熟练地与各国维和人员沟通交流。
此次维和之行,使陶琳感受最深的还是这个国家的贫穷。虽然利比里亚内战已结束了10年,但战争带来的阴影仍然清晰可见。
在利比里亚,市民的居住环境、卫生条件都很差,房子往往只是用木头和泥土搭个架子,四周围上草席,屋顶用铝或锡铁皮盖住,居民直接在地上睡觉。路边经常见到扎堆的孩子,看维和车辆来了,就上前伸手要吃的。他们常常饿得捡垃圾吃,有些甚至无家可归。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一个国家千疮百孔,人民连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得不到保证的时候,哪里还会有什么尊严可谈?我们的祖国是伟大的,能够让十几亿人吃饱穿暖,有国才有家,稳定的国家才是人民最大的福祉。每当我爬上集装箱眺望北大西洋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向东方望一眼,在海的那头有我的祖国,我的家。正如艾青诗中所写: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陶琳在《维和这一年》中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