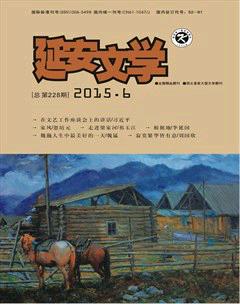迁房记

胡烟,女,文学硕士,80后。山东烟台人,现居北京。中国新闻奖获得者,鲁迅文学院第27届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光明日报》《中国作家》等。
我家住的房子,经历了几次变迁。虽说没往远处迁,可每次搬家,用我爸的话说,都叫人褪了一层皮。虽说新房条件好,可总想回到旧房子溜达溜达,去找点记忆的碎片,回来珍藏着。可惜的是,旧房子没在原地等我们。
最早,我家住幼儿园隔壁。幼儿园不叫幼儿园,叫育红班。我妈嫌育红班的小孩动静特别大,一会儿这个哭了,一会儿那个哭了,按下了葫芦起了瓢,挨个扯着嗓子喊老师,闹得慌。我不嫌闹,因为我上育红班时特招老师喜欢。老师衣服脏了,喊我,回家拿点洗衣粉吧?老师要洗头,叫我回家拿点洗头膏。老师家里来客了,就把钥匙交给我,下午上学,叫我开大铁门。拿着老师的钥匙,很有脸面。小朋友们都围在大铁门底下,唯独在当间儿给我让出一条路来。我把钥匙举得高高的,开门啦!我清楚地记得,胡晓梅老师的钥匙链上,拴着一个淡黄的钥匙扣,透明的,里面关了只小螃蟹。小螃蟹一辈子呆在里边,出不来。我常拿着它冲着太阳看,编织着关于小螃蟹被囚禁的故事。
我家住在胡同南头,门朝东,正对着的是一面旧土墙。土墙上有字:“打倒胡本干”。字是红色的,潦草,往一边倒,像是被风刮了。但凡认字的人都能看得出,这写字的人准是给气坏了,冒着一股子火气。我家原来的房主叫胡本干,爸妈要结婚,爷爷就从胡本干手里买下了这三间房。我问我爸,这胡本干是坏人吧?我爸说,是好人。好人为啥要把他打倒呢?谁要打倒他?我爸没理会。
三间房,爸妈住西屋,我住东屋,中间是灶台。我住的东屋,窗外头是个厢房,装了一屋子的渔网。厢房地上撒着红麦粒的老鼠药,因为老鼠经常拿聚乙烯的网线磨牙使。厢房把我屋的整扇窗户都挡住了,阳光照不进来。海风一来,夹杂着潮汐的颗粒,横竖都是湿。夏天潮得更厉害,招来好几种虫子。记得有一晚,睡到后半夜,后背针扎似的疼。早起,见炕上平躺了只大蜈蚣,不动弹了,拎起来一瞧,已经被我压扁了。除了虫子的记忆,我童年的很多书,也是在这个潮湿的大炕上读的。家里没什么书可读,爸妈忙着海上的事儿,没工夫给我买书看。我就借书,从同学家借《童话大王》《故事大王》《民间故事》读,就着潮湿的光阴。我爱读那些浅显的书,《民间故事》对我影响最大,让我尤其喜欢老百姓讲的白话故事。晚上一闭眼,脑子里,深山老林的精怪故事就都上演了。
院子的西南角里养狗。再往南,是个园子,我们叫它南园。园子里种西红柿、茄子、辣椒,还有一棵大梧桐。梧桐底下是猪圈。我家没养过猪,猪圈拿来当厕所用。白天的南园是好的,我妈炒着菜,就喊我去摘个辣椒给我爸拌生鱼吃,我高兴地去摘,东挑西拣。一会摘个辣椒,一会摘个西红柿,那南园里的菜,稀稀拉拉的,却永远没有摘完的时候。说起那棵梧桐,我爸曾在那上头掰过螳螂卵,硬硬的,浅绿色的一条,像冻僵的毛毛虫,用火烧了给我吃。脆脆的,香得流油,据说可以治小孩尿床。
到了晚上,南园突然变脸了,变得叫我害怕。上厕非要上南园不可,这是我最发愁的事儿。外头伸手不见五指,南园的门旧得快腐烂了,一推,吱呀——,像是推开了聊斋里的鬼故事。静时可怕,闹时也可怕。各种虫子叫,东一声西一声,神神秘秘的。更有猫头鹰上了梧桐树,冷不丁一声鹤唳,叫人吓破了胆。我不敢去,常常是憋着尿,实在憋不住了,快哭了,才壮壮胆子上南园去了。小解完了,我提着裤子就往回跑,顾不上关门。起风了,北风刮得两扇门咣当咣当响,把我妈惊醒了,在西屋吼我,起来关门!
我家最北边还有个夹道子,窄长条,墙根儿下摆了一排的咸菜缸子,总有一个缸子腌的是咸蟹子。腌咸蟹子得用鱼肝油,兑着白酒,把小花盖蟹子放在里头泡着。吃时就是生的,蟹黄稀溜溜的,往外流黄汁水。打渔回来,我爸倒上大半杯的老白干,喊我给他捞个咸蟹子。我跟弟弟馋了,他分给我们一人一条细蟹子腿儿咂摸着。
夹道的西南角种了两棵香椿树,树叶长得旺盛,我们却一回也没吃过。每年吃香椿都上菜市场去买。我妈说我家的是臭椿。明明跟香椿长得一模一样,怎么会是臭椿呢?奇怪。
在这个旧房子里,最深的娱乐项目,是夏天的晚上,观看纱窗上的壁虎捉飞蛾。像皮影戏一样的,黢黑的纱窗,先是冷不丁出现一只灰白蛾子扑腾着翅膀,接着是壁虎的雪白肚皮从纱窗的一角入画,潜伏,扭动,靠近,伏击。我爸激动地讲解,教我和我弟看现场版的《动物世界》。半岛人都爱看动物世界,全国人民看《新闻联播》的功夫,我们就看《动物世界》。什么国际新闻,俄罗斯访华,日本首相等等的,跟我们统统没关系,国内的大事儿也跟我们不相干。我妈对我爸说,你就打好你的渔就行了,外头的事儿用不着瞎操心。
爸妈住的西屋,满墙贴了我的奖状。一年一年的三好学生,过年都舍不得摘,只把上头的灰扫一扫。虽然爸妈不太重视我念书好坏,但来家里串门子的乡亲看了奖状,多少能给两句夸奖。
胡同口还有个小园子,是我家北邻居的。北邻居住的是一对老两口。老头的背是驼的,驼到了90度,我叫他弓背爷爷。我爸不许我这么叫,但爷爷也不生气,我也就没改口。大清早,弓背爷爷一摇一晃拿个镰刀,到小园里割草喂兔子。园子里的草长得飞快,割了还长,再割了还继续长,硬是把十几只兔子养得胖胖的。弓背奶奶是裹了小脚的,常常顺着墙根儿扶着墙,摇着蒲扇走到胡同口。我妈补网,她就在一旁帮忙缠梭子。这老两口,像是从民间故事里走出来的。半岛人都打鱼,他们俩却养兔子,跟谁都不相干。这是哪跟哪呢?可不是民间故事里的人物么?
闲时,我到弓背爷爷家看兔子,看兔子吃草,有时也赶上弓背爷爷给兔子剃毛,一只一只捉着剃,十分有趣。
这就是早先的房子。爸妈在里头结婚,自然,我家的根,也生在这里头。
90年代,大队盖了大批的新房。宽敞明亮的大瓦房,很多人家都住上了。没我家的份儿。一天放学,我到同学家,她说她家是装潢过的,叫我去参观。我不知啥叫装潢。进门一看就惊呆了,门框都包了边,天花板是彩色的,分好几层,还有水晶灯。家具是黑的,亮亮的闪光,地板也闪着亮光,像电视里的上海滩。回到家,饭桌上,我兴奋地向我爸汇报,宣传“装潢”这个新词儿。我爸刚开始不言语,最后扔出一句,咱家也装潢!
我爸不是随便说说的。没过几天,家里果然来了装潢队。那年代,我爸打渔顺风顺水,半岛谁都竖大拇指。走哪都威风的人,自然住房不能低人一等。
这一折腾,真是个大工程。我爸先是把弓背爷爷的园子给买了,又把南园填平了,连成了一大片,盖起了大平房,跟后头连成了前后院。新房是前院。前院里铺了花瓷砖,装了三层的天花板,装了水晶大吊灯,买了高档的新家具和皮沙发。新房不生炉子了,一水的暖气片。新房装了三层的窗帘,带花边的,一直垂到快要拖地了。折腾了半年多。
谁在新房住呢?爸妈旧房住惯了,我爸打渔回来,身上常常往下掉沙粒子,洗也洗不干净。偶尔躺在炕席上抽袋烟,炕头上抖落着烟灰,我妈嫌我爸把新房住可惜了,不叫他住。我弟胆子小,一直就跟着爸妈睡。我也不爱在新房住,新房宽敞,一人住着瘆得慌。
新房没人住。
新房供参观。一波一波的叔叔婶子大爷,来我家参观。这个天篷好啊,谁给吊的?这个灯好啊,哪家买的?这个沙发颜色正啊,花了多少钱?我妈天天领人来家参观,各种夸奖的词,听了一个遍。
新房还有一个作用,我爸妈吵架,一个住新房,一个住旧房,互不干涉。以前三天能和好,分开住以后,半个月还不见好。所以,我对这新房,并不稀罕。虽说能到屋里上厕所了,可我突然想念起我的南园子来了。
再后来,大队在半岛东边辟出了大片地,盖起了两层的独门独院的小楼。我爸居然又买了一栋小楼。我纳闷儿,咱家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呢?住得过来吗?我爸的理由叫我吃了一惊。我爸说,谁都知道咱家有钱,亲戚们买楼,都来借钱,不好意思回绝。这下好了,就说钱都买楼了。我问,那不是你挣的钱吗?你直接说不借,不行吗?我爸说,不行。你不懂。
小楼买好了,又是装潢。两层房子,装潢废了大劲。本来四口人,连一层都住不过来,非要把两层都装潢了。二楼装了粉色的大窗帘,我妈说,从外头看,好看。装潢好了,就闲在那儿。我妈说,不用住,看着就舒坦。
住哪呢?我爸妈住在小楼照壁底下挨着门口的小平房里。按照设计,那间本来当厢房使,他们在里头垒了一通大炕。睡惯了炕的人,睡不惯床。小楼里的暖气也闲着,冬天在小平房里生个大炉子,烤一炉子海蛎子,有时也烤咸鱼干。冬天晚上,小姨姨父表姐表姐夫上家里唠嗑,进门就脱鞋,全都盘腿挤在大炕上,一个挨一个,屁股叫炕烘得热热的,磕着瓜子,捧着大茶缸子,东家长西家短,唠个没完。人一散,瓜子皮叫扫帚扫出一大簸箕,往炉子里一填,轰地就着烧起来了。
这要是在小楼里能行么?新沙发,新地板,新床单,怎么动弹都不方便,那新窗帘,万一抽烟叫火星子着个窟窿,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小楼没人住。
有个插曲。搬到小楼后,前后院的平房,闲着也是闲着,叫我爸租给了在岛上打工的伙计,两口子住。租房归租房,连着我家的老狗也租给人家了。人搬了,把狗留在原地了,小楼里没给狗准备新窝。
那天,我妈正拿大铁盆在小楼门口洗衣裳,打老远就看见我家老狗,摇摇晃晃地跑过来了,跑到我妈跟前,满眼都是泪。我妈放下手里的衣裳,拿手去摸它,它竟摇着尾巴呜呜哭起来了。我妈受了感动,叫我爸在小楼门口赶紧给搭个窝,横竖不能叫它再回去了。
吃饭时,一家人合计着,这老狗是怎么找来的呢?小楼离平房远着呢,过了育红班,穿过卫生所,沿着南北大道一直往南,在第三排的胡同口还要拐两个弯,最东头,才是我家小楼。连我奶奶都经常含糊着,得一路打听着才能找见。老狗在平房院子的墙角里绑着,居然把铁链子挣脱了,跑来找我们。它是闻着气味儿来的么?那么远怎么闻见呢?想不通。反正是叫人感动。我爸也检讨了,觉得自己不够意思,租房不能连狗租。后来,那老狗,就老死在小楼里了。
小楼还有个便利,离海近,二楼能看见海。出了门走两分钟,就是南海岩。那年过年,出海的船都歇了,暖冬,我成天坐在南海岩边上的旧船梆上,耷拉着腿,看海水。海水里浮着冰,在太阳底一浪一浪拍打着船底,亮闪闪的,像是唱着什么歌。我爸找不见我,就上南海岩儿找我。我爸说,从小就看海,现在还有个什么看头呢?跟个外地人似的,显得生分。
幸亏那会儿多看了两眼。没两年,半岛搬迁了,海滩没了。
我家的小楼,统共住了三年。
半岛搬迁,是把600多户人家整个地移出海岛,搬到油田的一个小区里。负责拆迁的人挨家挨户量面积,按照室内面积,给单元楼住。半岛家家户户忙着搞建设,要么在院子里盖个棚子,要么在门口盖个工具房,恨不得连狗窝都算上面积。
年轻人都高兴着,要住小区了,集体给供暖了,可比自己生炉子强百倍,终于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了。
可叫老人们发了愁。我爷爷成天守着葡萄架子,舍不得那两颗葡萄树。还有满院子的塑料球。
塑料球是赶海赶来的。凌晨三四点钟,海里漂来塑料球。塑料球是黑的,比篮球大一圈,是渔网上散落下来的,趁着天黑往岸上漂,谁捡着是谁的。一个塑料球能卖两块钱。我爷爷觉少,天天早上去捡塑料球。天蒙蒙亮,背上驮了一长串的塑料球回来了。他跟我奶奶两个人,年吃年用都够了,就靠捡这塑料球卖。搬迁以后,海滩筑了大坝,上哪捡塑料球呢?住这老房子,烧火也不花钱,都靠捡柴火,搬了家,只能烧煤气。
那几个月,半岛上,满街溜达着长吁短叹的老人。
搬家以后,半岛就拆了。拆房的时候,全家在一旁,守着我家小楼。大铲车一铲子下去,小楼的房顶就破了一个大洞。大铲车脑袋甩几个回合,小楼只剩下半个身子。我看见我妈在一旁抹眼泪儿。
为什么哭呢?不是赔给你们新房子了么?
搬到小区,在楼底下,我爷爷在花坛里的两棵树上绑了绳子,晒衣裳。管理员给摘了,说影响绿化。我爷爷懂,树是绿化用的,不像半岛的山上,随便长在哪的。我奶奶把咸鱼酱缸子搁在门口了,又有管理员找来了,说咸鱼酱味儿太大,邻居都有意见了。以前不都搁在房门口么?这味儿散不去,可怎么好呢?
老人们对管理员说,俺不会住楼,叫俺搬回去吧?
搬回去?房子都填平了,上哪住去?山都挖平了,岛都没了,想回哪去呢?哪也回不去。
真的哪也去不了。我爷爷奶奶,就是在那个一楼的单元楼里,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