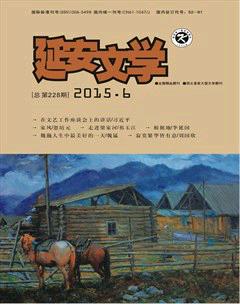我们的名字

刘浪,黑龙江鹤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5期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飞天》《四川文学》《文学界》《山花》《作品》《北方文学》等,多个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等转载并入选选本。
1
更多的时候,日子和日子之间的差异,在我看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眼下,这个猴年也可能是鸡年的春节,对我来说就只是几个平常的日子而已。
让我心情不错的,是一场中雪,已经下了两天了,这会儿还在窗外飘零。昨晚,涧河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采访了一位农业专家,是个有些谢顶的男子,看上去有50岁左右吧。这人攥着拳头,信心满满地说,这场雪百分之百预兆丰年。而我不敢确定。老天爷的事情,只有老天爷自己说了算。
不管怎么说吧,北方的冬天,只有下了雪,才像那么一回事,感觉才对路。半个小时之前,我的老婆出门了,去找她的闺蜜打麻将。我呢,沏了一杯红茶,坐在窗前,有一搭无一搭地构思一个男人的故事。过日子嘛,总要做一点事情的,一直混着不是办法,是吧?
老实说,对于这个男人的故事,我觉得无从写起。眼下,我只能确定它将是一篇短篇小说。至于这个男人姓什么,我暂且不提,但必须要说到他的名字:槐树。由此,我想这个短篇小说的题目,就叫《男人槐树》吧。
雪下得慢条斯理,像个绅士。我长久地看着窗外,看着看着,我突然就想,坐在那列火车上的男人槐树,他也一定是长久地盯着窗外吧。所不同的是,我看到的是一片清冷而缠绵的白,他看到的却是一个盛夏的午后。
那个午后闷热异常,让人透不过气来。天空诡秘地白亮着,继而又变成了阴森森的铁灰色。男人槐树斜倚在座位上,看到窗外的天空越来越低了,像一口巨大的铁锅,倒扣着,不由分说地压了下来。这辆哈尔滨开往涧河的列车,正在匀速前行,远处的山脊和近处的树冠,也就匀速地向列车后方撤退。而雷声说来就来了,轰隆隆、咔嚓嚓,不遗余力、不可一世。闪电这条抽搐着的鞭子,被雷声肆意地挥动着,天地之间就被劈出一道紧接一道的伤口,腥红并且诡异。紧跟着,雨兜头而来,跟个泼妇似的,一点过渡也没有,直接就下疯了。大地在瞬息之间就被一团浊白所笼罩,而风也开始趁火打劫了,撒着欢、打着旋,恨不得要把这个它所不满意的世界,连根带梢地吹走一样。
雷声、风声和雨声纠缠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一股脑地灌进男人槐树的耳朵里时,一定是我出现了错觉吧,我也听到窗外传来了一阵噼噼啪啪的声响。猛地愣怔了一下,我清醒了过来——春节了嘛,有人在放鞭炮,这再正常不过了。鞭炮炸开的声响,急促、固执,一气呵成,是那种没有起伏的抒情,让人听起来觉得累。
接下来,我的手机就响了。我就不由得长叹了口气。真的,我特别讨厌构思小说的时候,有人打扰我。而且,我感觉电话一定会是总编打来了,让我去报道相关领导顶风冒雪给穷困市民送温暖什么的,过去的几年,每一年的春节,我都会遭遇这类的事情,想躲都躲不开。
我就咬着牙,接听了电话。还好,不是总编打来的,而是一个女士。
我又叹了口气,当然是放松的那种叹气了,就听女士说,过年好啊刘编辑,我是张萌。
我愣了一下,随即想起这个张萌女士,是我曾经的一个采访对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她应该是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名字好像是叫《我的我的我》,也或者是《你的你的你》,反正听起来很是拧巴。张萌通过文联的一个编辑找到了我,要我在我所供职的《涧河广播电视报》上,给她发个消息。这年月,文学的日子不好过,诗歌似乎就更难,我就给她发了个半长不短的通讯,什么出身书香门第啊,在某县文联主办的全国性征文中荣获佳作奖数次啊,等等,好像还配了诗集封面照片和她本人的一张艺术照。哦,对了,应该还附了她一组或者一首诗歌吧,我真的有些记不准了。
我说,谢谢你,你过年也好啊。
张女士说,祝你新年万事如意,发财、健康、走运,包括桃花运。
我说,好啊,你也一样。
我是真的没心思跟她聊天,就要挂断电话。就是这个时候,张女士说,刘编辑,前几天我听广播,是交通台还是生活台了?反正我听见你点歌了。
我就笑了。我是三十多岁的人了,点歌?我竟然还有点播歌曲的兴致?我就告诉张女士,没有,我没有点歌。
张女士说,撒谎的孩子被狼吃!就是你点播的,点的歌是刀郎的《情人》,献给一个叫独孤蝴蝶的女子。
我的老天!这怎么可能呢?我要是真的闲得难受,我挠墙玩好不好?我怎么会去点播《情人》,而且明目张胆地送给什么蝴蝶、苍蝇?这事要是属实,而且又让我老婆知道的话,我老婆不拆了我那才叫怪呢。但我不好跟张女士发作,我就耐着性子说,一定是你听错了,我从来就没有点播过歌曲,从来没有。
张女士似乎有了些不耐烦。她说她没有听错,她说我所在的广播电视报社,跟她提到的交广、生广同属广播电视局,我点歌是有便利条件的。
我说,是,你说的没错。如果我想点歌,不用把电话打到导播间,早上上班时,在通勤车上告诉主持人我想听什么什么歌,就行了。但是……
张女士抢着说,这不就得了。
我说,关键是我确实没点歌,你以为我脑袋让傻子摸过还是被驴踢了?
张女士说,刘编辑,你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想点歌,电话还打不进去呢。你说吧,除了你,涧河还有别人敢叫刘浪吗?我借他个胆子。
我就一下子沉默了,因为张女士的话提醒了我。据我所知,在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除了我,至少还有三个人叫刘浪——这跟张女士说的敢或不敢,当然没有任何关系。我听说其中一位刘浪是个老者,六十几岁了,退休之前在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好像是内分泌科的主任吧。另一位,听声音应该是个20岁出头的男孩子,他给我打过电话,开板就说“我是刘浪”,正经吓了我一哆嗦啊。这个跟我同名,也或者说是我跟他同名的男孩子,当时是要给我提供一条新闻线索,忘了是由于我忙没去采访,还是他的线索新闻价值不大,反正我们再没有了联系。至于第三位刘浪,是个犯罪分子,5年前被执行了死刑。
我就想告诉张女士,也许是哪个跟我同名的人,在广播里点播歌曲了。可电话那头呢,张女士一定是认为我理屈词穷了,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长叹一口气,小声骂了一句,妈的。
2
老实说,张女士的电话扰乱了我的思路。我不知道这篇《男人槐树》,接下来将怎样展开。放下电话,我喝掉那杯红茶,打开了电脑,又打开了Word2003空白文档。再之后,我耷拉着头在屋子里转圈,客厅到卧室、卧室到客厅,转了七八个来回,谢天谢地,我总算想起男人槐树乘坐的那列火车,这会儿该在涧河站停下来了。
涧河站很小,一栋黄色的平房而已,不足两百平米。槐树和另外十几个人走出了列车,一串惊雷刚好在他们头顶滚过。雨倾盆而下,又霸道又天真,又放肆又单纯。那十几个人缩着脖,撒腿向票房狂奔,槐树却停下了脚步。
一眨眼的功夫,雨就将槐树整个浇透了。雨肆意地打在他的脸上,我们看不清他正在流泪。是他声嘶力竭的一声惨叫,暴露了他脸上湿湿的东西,不光是雨水。
槐树叫喊着的是这样三个字:绿叶呀!绿叶呀!紧接着,他就扑通一声跪在了站台上,仍旧叫喊:绿叶呀!绿叶呀!
槐树的叫喊,竟然没有被风雨完全稀释掉。向票房跑的人中,有两个男子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其中一个男子停顿了一下,又向票房跑去了;另外那个男子却回过身来,跑到了槐树身旁。这人大约30岁左右,穿了一件猩红色的衬衫,经雨一淋,就像浑身在冒血似的,有些恐怖,也有些滑稽。
咋的了哥们儿?跪这干啥呀?红衬衫男子问槐树。“干啥”这两个字,在红衬衫男子嘴里的发音是“尬蛤”。这样的口音,表明这个男子应该是东北籍的。
槐树根本没有理他,而是继续用两只手掌轮番击打站台的水泥地面,边击打边喊:绿叶呀!绿叶呀!开始时,槐树是左手击打一下,右手击打一下,再左手,再右手。但这种有序的节奏转眼就紊乱了,他时而用左手连击两下,时而用右手连击三下,间或还用前额去叩击。手乱了,嘴却章法依旧:绿叶呀!绿叶呀!
哥们儿你别整这出行啵?我心里毛个愣的。红衬衫男子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他一边说着,一边倒退着往票房走。
槐树仍旧没有理他,仍旧绿叶绿叶地喊着,只是声音似乎不再那么尖锐和抽搐。
这时候,列车一声长鸣,缓缓启动。倒退着的红衬衫男子猛然看到,槐树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向列车快步跑去,很明显,他是要用自己的头颅去撞击列车。
还好,就在槐树前倾的头颅,距离开始加速的列车只有不足10厘米左右的时候,红衬衫男子快步追赶了过来,一把拽住了槐树的后脖领子。又一声惊雷在他们的头顶炸响,槐树的身子被红衬衫男子扭转了过来。红衬衫男子一手抓着槐树的衣领,另一只手狠狠地抡了起来,啪!扇了槐树一个大耳光。这个耳光实在太响,连倾盆而下的雨水都似乎在瞬间停顿了一下。
你他妈的跟我装啥犊子!红衬衫男子大骂。“啥”这个字,在他嘴里的发音,仍是蛤蟆的“蛤”。
槐树被打得浑身一抖,似乎清醒了一些。他想拿开红衬衫男子的手,但红衬衫男子仍旧牢牢地抓着。
槐树说,兄弟,谢谢了,松开我。接着,槐树用手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和泪水,说,说心里话,我真不想活了。
红衬衫男子看到火车开远了,就放开了槐树。他说,哥们儿,你他妈的都要吓死我了,我还是先蹽杆子吧我。红衬衫男子说的“蹽杆子”,是个东北土语,大致是快速跑、逃跑的意思。说完这句话,红衬衫男子就快步走开了。
可是,走出没几步,他又返回来了。
你刚才喊的是绿叶,还是莉叶?红衬衫男子问。
槐树反问,你说什么?
你刚才喊的是绿叶,还是莉叶?红衬衫男子重复了一遍。
槐树的左嘴角微微有一点上扬,算是笑吧。他说,绿叶。可能是怕红衬衫男子听不清,槐树就解释了一下,他说,就是绿色的叶子。
我操,吓我一跳。红衬衫男子说了这么一句,就嘿嘿一笑,接着他就出了出站口,向火车站斜对面的一幢高楼走去了。
而我知道,这幢十六层高的大楼,它鹅黄的外表在这个冬季来临之前,已被涂刷成了浅粉色。它是北岸宾馆,涧河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3
在电脑上敲完上面这些,我就停了下来,点了根烟。真的,我不知道接下来,我该怎么叙述男人槐树的故事。这个男人的命运,在我看来真是倒霉又无辜,可我该怎样尽可能平静和有条理地记录下来?我正没有思路,我的手机又响了。
这一瞬间里,我是真有摔碎手机的冲动。我好像在前面没有交代过,我们报社其实没有专职记者,记者都由编辑兼着。新闻随时可能发生,记者的手机相应地就得随时保持畅通,这是我们报社的制度之一。摔碎手机的后果,只能是我马上再买一部新的,所以这样犯傻的冲动,我只能是动一下念头而已。
稳了稳呼吸,我接了电话。
这次给我打来电话的,是一位李姓先生。就在春节前不久,我们报社举办了一次规模还算说得过去的征文赛事,李先生是这次赛事的冠名赞助商。
过年好,刘编辑。李先生说。
我也说,过年好。
李先生说,前几天我听见你点歌了。
我浑身激灵抖了一下,真是他妈的活见鬼,刚刚张女士说我点歌,这会儿李先生又这么说。我说,那不是我,我没点歌。
李先生说,啊。
我说,嗯。
李先生说,你现在在哪个网吧呢?
我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打翻了烟灰缸。我说,网吧?我在家呢。
李先生笑了,说,刘编辑你真幽默,我在Q上都跟你聊十多分钟了。啊,我知道了,你家电脑安上宽带了啊,上次见面你还说你家电脑没上网。
我说,我家电脑一直就没安宽带。
李先生说,兄弟,这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其实吧,我就是想告诉你,坏事人人有,不漏是高手。
我说,你什么意思?
李先生说,兄弟,那我就直说了。你犯不上把场面铺那么大,点歌给那个啥啥蝴蝶,没有必要,直接拿下她就是了。一看你就是没经验啊。
我脑子里就嗡的一声,起码十几根神经短路了。我说,我,我。
李先生说,兄弟,我也是为你好。好了,咱们还是在网上聊吧。说完,李先生就挂断了电话。
我使劲拍了一下桌子,大骂一声,妈的,之后又骂了一声。难道在QQ上跟李先生聊天的人,又跟我同名?难道我的QQ被盗了,盗号的人冒充我,在跟李先生聊天?我该怎样才能让李先生相信我?或者说,我有必要让李先生相信我吗?我根本就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怕什么鬼敲门!
不过转念一想,我还是有些担心我的QQ被盗,这将指不定给我和我的QQ好友,带来多少不必要的麻烦。我就给我老婆打了电话,她的手机可以上网,我让她登录我的QQ,看看我的QQ是否真的被盗了。
我老婆那边的麻将局还在继续。她似乎手风很顺,声音里面满是活蹦乱跳的欢喜。按照我告诉她的密码,她登录了我的QQ,没问题,根本没用被盗。末了,老婆叮嘱我别光顾着写稿子,连饭也不吃。
接下来,我就将手机在手里掂了掂,然后关机,打算尽快把《男人槐树》的初稿突击出来。我已经想好了,万一总编想要通知我去采访,却联系不上我,我就说手机没电了。
可是,收拾完打翻的烟灰缸,重新坐回电脑前,我发现我的思路完全乱了。我本来是打算以槐树的叙述视角,来完成这篇小说,但现在看来,好像是不大可能了。
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办呢?
也许,我现在该让绿叶马上出场了。
4
像槐树不是一种落叶乔木,而是一个男人的名字一样,绿叶也不是植物的营养器官之一,而是一个女子的名字。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现偏差的话,数月之前,也就是槐树在涧河火车站差点寻了短见之前的四五天吧,绿叶也出现在了这里。这个22岁的女子,长到这么大都没有离开过涧河一步的女子,终于要出远门了。她要到哈尔滨去。更确切一点说,绿叶是要去哈尔滨南岗区学府路的一个建筑工地,去找她的未婚夫。
是的,没错,她的未婚夫就是槐树。
绿叶就登上了涧河驶往哈尔滨的列车。坐在靠窗一侧的硬座上,绿叶时常感觉得到腹中的胎儿在轻轻蠕动。绿叶就低下头来,抿嘴笑了,同时她还用手指捻揉着自己的辫梢。
按照槐树来信中所说的地址,绿叶并没有费太大的周折,在天色刚刚黑下来的时候,她找到了那个建筑工地。当时工人刚好开始收工,绿叶不敢向男人打听,就问了一个女工。我必须老实承认,我不知道这个女工的名字,但为了讲起来方便,我就叫她王丽吧。
绿叶说,俺想找俺家槐树。
王丽一愣,说,谁?你找谁?
绿叶又捻自己的辫梢了,脸也红得发烫,她说,俺找赵槐树。
王丽说,你是叫朱莉叶吗?
绿叶就急忙点头,说,嗯哪,俺叫朱绿叶。按我事后的推想,绿叶当时也许是这样想的:看来槐树在工地经常提起她,否则这个女的怎么会一下子就叫出她的名字呢?
王丽说,你跟我来吧。
王丽就把绿叶领回了集体宿舍,让绿叶坐在一把快要散架的木椅上。王丽说她这就去喊槐树,让绿叶等着。
王丽离开宿舍大约15分钟之后,一个男子来了。
男子没有敲门,而是哐啷一脚把门踢开。绿叶吓得噌一下站了起来,心都窜到嗓子眼了,双手也下意识地紧紧按住自己的胸口。
男子看了绿叶一眼,说,净他妈的扯淡。
之后,男子就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这个男人,就是这个建筑工地的承包人。而我要说的是,我们其实已经认识这个男人了。他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红衬衫男子,操一口东北方言,把“干啥”说成“尬蛤”,在涧河火车站救了槐树的那位老兄。
5
现在,我似乎还不可以挑明,王丽为什么会把红衬衫男子当成了绿叶的未婚夫槐树。我只能是再重复一遍王丽和绿叶的对话。王丽问绿叶,你是叫朱莉叶吗?绿叶的回答是,嗯哪,俺叫朱绿叶。
王丽把绿叶安排在了宿舍,就去找了红衬衫男子。她告诉红衬衫男子,你媳妇来找你,在我宿舍等你。之后,她就和另外一个女工,名字叫张华的女工,她们两个到超市去买哈尔滨红肠了。
红衬衫男子见到绿叶,撂下那句“净他妈的扯淡”,就走了。绿叶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只好是在这间宿舍里焦急地走来走去,还不时地推开房门向外张望。等候的过程中,绿叶一直在捻揉自己的辫梢,辫梢就要捻断了,谢天谢地,王丽和张华回来了。
王丽很惊讶绿叶还留到她的房间,她问,你家槐树呢?你怎么自己在这里?
绿叶就哭了。我想,绿叶本来应该是要说,你不是说去帮俺找槐树了,你怎么没帮俺找?或者是要说别的什么抱怨一类的话语,张华却接过了话头。
张华叹了口气,问绿叶,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绿叶的脸红了,说,没,还没结婚呢。
张华一拍大腿,说,好啊!好啊!没结婚就好。妹子,我说话你保准不爱听,但我还是得说。槐树这小子太不是个物,他也太色了,挣两个半吊钱,他麻溜领个三陪回来过夜,老丢人了。
绿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王丽扯了扯张华的衣襟,示意她不要讲下去。张华却抬手打开王丽的手,接着对绿叶说,男人有钱就学坏,这话说得一点没错。老妹,你想开点吧。
绿叶瞪大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张华。
王丽又扯了一把张华的胳膊,说,你别瞎说。
张华说,什么我瞎说?我哪瞎说了?你忘前天他把你堵屋里了?要不是我赶巧回来取东西,你就被他祸害了!
张华边说边走上前来,扶起绿叶。
绿叶扑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撕扯自己的头发。
当然了,还是根据我事后的猜想,绿叶当时的伤心,是出于她想不明白,槐树怎么这么快就学坏了呢?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啊?她的槐树离开涧河,满打满算也就半年时间,怎么就能找三陪女呢?怎么就能打祸害女同事的坏主意呢?槐树来哈尔滨打工之前,绿叶就怕他变心,所以就把自己给了他。可现在,现在,叫俺咋个活哟?
6
故事磕磕绊绊地讲到这里,我想,有些事情就已经比较显然了。尽管我们还不是全面知晓具体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王丽和张华,她俩都把红衬衫男子当成了槐树。而有意无意之间,她们又让绿叶知道,她的未婚夫已经变了心,变得不可救药。
那么,真正的槐树在哪里呢?
我也是在事情发生很久之后才知道,真正的槐树,绿叶的未婚夫,他只在红衬衫男子承包的建筑工地工作了三天,之后就去别的工地了。这个工地的人,槐树只认识一个瓦匠,这人的乳名也可能是绰号叫二孬。槐树和二孬曾经是初中同学,比较要好的朋友。除了二孬之外,这个工地的其他人,谁都不认识槐树,包括二孬的妻子,也就是女工张华。
就在绿叶在女工宿舍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槐树的另一封挂号信,其实已经寄到了绿叶的家里。槐树在信中说,他已经基本攒够结婚需要的钱了,他每天不分黑白地盼望结婚这天,盼望得都要疯掉了。
可惜,这封信,绿叶没有机会看到。
第二天,天色刚刚朦朦亮,一宿没睡的绿叶给槐树写了封绝交信。绿叶在信中说自己真是瞎了眼啊,没能看清槐树这个披着人皮的狼。绿叶让王丽和张华把信转交给槐树,之后她就哭哭泣泣地踏上了返回涧河的列车。
按照我后来的推测,应该就是在绿叶乘坐的列车启动的时候,张华板着脸,将绿叶的信交到了红衬衫男子的手里。
红衬衫男子还没看完信,就破口大骂,你们他妈的没事闲得总逗我干啥?
张华翻了个白眼,又撇了撇嘴,就转身走了。
红衬衫男子接下来的一句话,一定会让我们吃惊的。他指着张华的背影大喊,我告诉你们,我叫肇怀恕,肇东的肇、胸怀的怀、宽恕的恕,不是木鬼那个槐,不是木又寸那个树。
呸!张华向地上吐了一口,头也不回地干活去了。
这天下午,王丽和张华的工作,是给瓦匠二孬送灰递泥。两个女人一边干活,一边开始数落肇怀恕的不是。她们骂肇怀恕是陈世美,她们骂肇怀恕不得好死。张华是那种敞开的咒骂,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王丽呢,是小声附和,还不是左右观察,怕被肇怀恕听到。因为她们只是称呼肇怀恕为“他”,瓦匠二孬也就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而听到昨晚绿叶来过时,二孬停下了工作。二孬恍惚记得,槐树说过自己的未婚妻名叫什么绿叶。二孬就急忙扔下抹子和托板,跑到了包工头肇怀恕那里,把绿叶写给槐树的绝交信要了回来。
这天傍晚,二孬把信送到槐树手里的时候,绿叶乘坐的那列火车,刚好在涧河站停了下来。
走下列车,绿叶的眼泪又流下来了。腹中胎儿的蠕动,应该不是没有唤起她的母性,但她想得更多的却是,俺没脸活了,俺没脸活了。绿叶就在列车重又启动前的一瞬间,把自己的整个上半身,趴在了铁轨上。血,放肆地喷溅着……
而二孬把信送到槐树手里之后,就匆忙回到了工地。他没跟槐树讲更多,只是说昨晚绿叶来过。二孬之所以匆忙赶回工地,一是因为他要赶回去工作,二是因为他此时并不知道包工头的名字,他一直称呼肇怀恕为肇老板,他一直以为肇老板姓赵。
槐树看完绿叶的信后,也是搞不清到底因为什么。他就向领导请假,但没有请下来。两天之后,槐树终于请下来假了,他也就得知了绿叶卧轨的噩耗,家里人没谁说得清绿叶为什么要自杀。
就这样,槐树赶回了涧河。槐树也打算卧轨自杀的时候,被偶然来涧河购买建筑原料的肇怀恕救了。具体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赵槐树不认识肇怀恕,肇怀恕也不认识赵槐树。但鬼使神差,他们在涧河火车站相遇了。相遇之后,赵槐树仍旧不认识肇怀恕,肇怀恕也仍旧不认识赵槐树。我们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7
现在,我开始回想这篇《男人槐树》,是否存在什么明显的漏洞。我没有发现漏洞,就随手把手机开机了。
几乎在我开机的同时,我的手机来电话了。而与此同时,我还真发现这稿子里面,我遗漏了一个很关键的细节,这就是我忘了交待肇怀恕的妻子叫什么名字了。
肇怀恕的妻子,名叫朱莉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在前面其实是提到过她一二次的。而我亲耳听到这个名字,是在这个春节前的半个月,是瓦匠二孬告诉我的。
事实上,我原本不认得二孬,是北岸区人民法院的一个法官,介绍我和二孬相识的。法官在电话中告诉我,刘编辑,我这有个离婚案,挺波折的,你最近要是有空,过来采访一下怎么样?
我就见到了二孬,他就给我讲了赵槐树的遭遇。他说他得知绿叶死去之后,总是抱怨张华当初没有把赵槐树/肇怀恕、朱绿叶/朱莉叶给他讲明白,两口子争来吵去的,就发展到了执意离婚的地步。
他们的名字本来不一样,听起来咋就又一样,这是为啥啊?你说这是为啥啊?二孬反复追问我,也或者说是在追问他自己。而我,除了叹气,没法回答。
好了,有关男人槐树,我暂且就讲这么多吧。因为这会儿,我手机的来电乐曲再次响起,有些执着和揪心。
我一看来电显示,是老婆来的电话,就急忙接听。
我说,老婆,麻将输了还是赢了?
老婆说,你行啊!以前我怎么就没发现你呢,到广播里给你情人蝴蝶点歌,你真行!得了,我什么也不说了,离婚!
不给我说哪怕只一个字的机会,老婆就挂断了电话。
我向窗外看了一眼,发现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随机,我隐约发觉出了,日子和日子之间,有时还是会有显著的差异的。比如此刻,窗外的夜色就深重得不怎么靠谱。
责任编辑: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