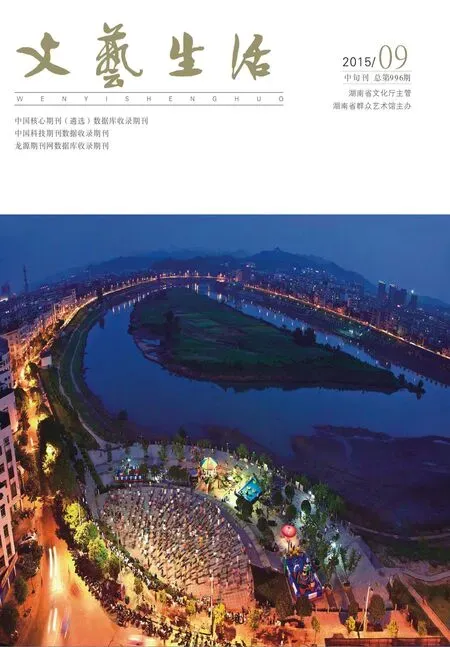浅析沈从文湘西世界作品中的爱情书写
李旭星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浅析沈从文湘西世界作品中的爱情书写
李旭星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文学中不可缺乏对于情感的书写,而爱情书写更是体现两性之间微妙关系的极为特别的描绘方式,同时也是透过这种生命存在状态探寻人的存在与人性终极的方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爱情书写独树一帜,本文结合沈从文的具体作品,分析沈从文对于湘西世界爱情描写的“原生态”角度以及其透过爱情之窗对生命之美与生命之力的极致书写。
湘西世界爱情书写原生态神性生命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幅奇景,沈从文的作品经历了近九十年的文艺风雨洗礼仍闪耀着其独特的光芒。不同于依附于宏大历史叙述之上的左翼文学,不与灯红酒绿的海派文学相谋,沈从文始终简直从自己的“希腊小庙”中眺望至美至善的纯净景色。文学评论界中向来复杂的爱情书写,也在沈从文的笔下有了特殊的沈氏风格。
一、以爱情为本体的“原生态”角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周作人从西方思想家霭理斯的性学思想处向中国知识分子引述了性心理学的部分观点,同时,周作人自己也提出“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是人性”,“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应在理性对人类本能的适当抑制与调节下达到“灵肉一致”①。周作人对于自然人性尤其是性心理的自由观念,影响了沈从文对于人性的进一步认识——人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更有着对于感性与理性、人性与神性、本能与道德相互统一和谐的不懈追求。在沈从文笔下,爱情也是人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需刻意的压抑克制,是一种美的表现形式。爱情主题或者与爱情相关的描写在文学创作和评论中常被赋予着复杂的目的性和功用化的理解,相较之下,沈从文从一个崭新的,或者说,从一个五四启蒙后早就应该出现的本体角度出发去看待爱情以及这一人类日常行为的表达。
首先,沈从文将爱情书写从社会历史的大角度中萃取出来,使之成为真正的关注对象。中国现代文学中对于爱情的描写并非乏善可陈,但以主流宏大叙事为代表的许多文学创作中,爱情书写被蒙上了一层羞于言说的意味,正如吴荪甫之于王妈、林道静之于她的三个恋人——一方面,爱情描写被视为略显负性的因素而隐去;另一方面,性别甚至爱情成为每每涉及到社会阶级、政治话语时的附庸成分——恋爱与爱情是关乎阶级或政治话语的暗示与演绎,而社会阶层与政治取向又反过来影响和干预两性之间的情感关系。这种在历史洪流中沉浮的两性关系正与沈从文所提倡的自然人性所违背。因此,沈从文在以表现湘西生命为主的作品中,刻意将社会历史的背景淡化甚至略去,只保留湘西本地最为淳朴的风俗习惯,驱动男男女女之间相互吸引、相互深爱的是单纯的个体情感的悸动。如《神巫之爱》中的神巫与哑女,《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同豹子。作为背景陪伴着故事中一对对恋人的,只有同样纯净的湘西的水与月。
相应的,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叙述的同时,沈从文也将自己的湘西梦带离了现代文明——现代化的都市逻辑、恋爱与婚姻、道德伦理等等过度规束都为健康奔放的自然爱情做了让步。在难以为现代文明触角所顾及的物质贫瘠的湘西社会,现代都市的灯红酒绿和消费逻辑全不适用。没有应酬自如、甘愿沉沦的交际花,有的只是《丈夫》中迫于生计卖身养家的船中妓女;没有欲壑难填、空虚无聊的行尸走肉,有的只是如花狗般淳朴健美的湘西的灵与肉;没有离婚、出轨等繁杂的情感和伦理纠纷,有的只是诸如《萧萧》中萧萧与花狗、媚金与豹子间极度的热爱所产生的迷恋与结合。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纯粹的,其对于自然人性与“神性”相和谐统一的追求亦表现在摆脱现代文明对于人性的过度压抑和约束。沈从文淡化社会组织、有意的忽视体制带来的所谓的社会“进步”,将男男女女们重新归入理想中的伊甸园,发乎情,不止于礼。
二、关乎生命的极致表达
沈从文将个体存在分为“生活”与“生命”两个层次,“生活”代表着人生存下去所必须达到的物质层次,而“生命”则“惟对现世光影疯狂而已”,其自身就“有光热”②。爱情作为一种自然人性的表达与追求,必然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沈从文对于爱情的书写,也表现了他内心对于供奉在“希腊小庙”中的生命之火所体现的美与力的追求。
爱情关乎生命之美。沈从文向来不吝啬对于笔下人物之美的塑造,他只愿将爱情赠与那些“相貌极美又顶有一切美德”③的湘西生灵。生命之美意味着两性之间关系的平等与和谐,也即以相互爱恋为前提,庄重而专情,爱情本身可以肆意奔放,然而爱情本身是严肃且圣洁的道德律。如《萧萧》中,萧萧作为童养媳接受了无爱的婚姻,性意识觉醒的她并未因童养媳的封建身份束缚自己的情欲,而是和健康强壮的湘西汉子花狗体验了爱情的美好。甚至是湘西水域船屋中的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同时,产生爱情的诱因也是“顶美”的,神巫爱上花帕族哑女是因为女子秀媚通灵的眼睛;媚金与豹子因歌结缘便私定终身……不为金钱,无关权势,当爱情退去传统道德审视下的丑陋外衣时,沈从文赋予了它极度的自然气质和神圣的纯洁性。在《阿黑小史》、《夫妇》、《雨后》等作品中,爱情还与自然合为一体,两性的结合与自然万物相互顺应、交融,如《月下小景》中的一段描写:“悬在树上的果子落了地,谷米上了仓,秋鸡伏了卵,大自然为点缀了这大地一年来的忙碌,还在天空中涂抹华丽的色泽,使溪涧澄清,空气温暖而香甜,且装饰了遍地的黄花,以及在草木枝叶间傅上与云霞同样眩目颜色。一切皆布置妥当以后,便应轮到人的事情了。”自然仿佛在启迪凡人的“神性”,为同样具有生命力的可爱男女准备着新房和婚床,自然果实与爱情同时成熟、收获,恋人们在自然中得到关于“神性”的最高体悟。诸如此类关乎自然及生命的原始之美、道德淳朴之美的意象群也使得其区别于其他商业化的情色描写,成为表现沈从文理想之光的一颗星火。
爱情体现生命之力。沈从文曾表示,爱情是“身心健全的年轻人”“尽种族义务”、“生理上求发展”④的生命之源。沈从文的笔下,湘西的男子强壮有力,血性耿直;湘西的女子柔情似河水,热情似篝火。湘西男女的爱情随性、洒脱,只随原始的生命冲动而生,不可抑制,不可拖延,同时也成为湘西男女互诉衷肠,沟通生命灵性的方式,是代表健康生命、响应自然及神性召唤的行动。与表现湘西世界奔放情欲相对的,是沈从文对于城市人的爱情书写。《八骏图》中衣冠楚楚的教授们因为违背自然本性的禁欲纷纷“害了点小病”,甚至病态的“想从那大理石胴体上凹下处凸出处寻觅些什么,发现些什么”⑤。爱情的缺失和对于本性的畸形压抑使得人的生命之力萎缩,变得萎缩、怯懦,甚至失去了真诚、质朴的品质,变得谎言连篇,虚伪不已。而真正体现沈从文对于爱情崇高感的理解,在于沈从文对于爱情与死亡之间的联系。“一个人生命之火虽有时必熄灭,然而情感所注,在有生命处却可以永不熄灭。”⑥整日将性命交予河流山川的水手和从事着并不安定工作的妓女相恋,将爱情的野蛮与随性发扬到了极致。翠翠的父母也选择以先后殉情来求得爱情的专注。《巧秀与冬生》中巧秀母亲与打铁匠相爱,最终面临族人非难时并未苟且偷生,选择以“沉潭”表达对自由追逐爱情的忠贞信仰。《月下小景》中的女孩情愿与傩佑在歌声中双双死去,也不愿忍受土司王的野蛮苟活。为爱抗争、为爱殉情,沈从文常以最为壮烈的求爱来表现人追求自然发展的本能——“爱能使人暗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⑦。
三、结语
总而言之,沈从文向来不吝啬于展示湘西世界的原生之美和生命的魔力,爱情书写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为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史无前例的圣洁果实——作为一名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他能够巧妙的掌握爱情书写的尺度和价值,力求写尽爱情的美好与伟大而并非其猥琐与色情。囿于中国现代历史的诸多原因,文学界鱼龙混杂的爱情书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难以为主流叙述做更为细致和理性的区分,然而沈从文的真挚和自始至终对于神性的追求赋予了这类书写超脱世俗的审美体验,成为经典。
注释:
①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1918(05).
②③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95,209.
④沈从文.给一个中学教员.沈从文全集(17)[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25
⑤沈从文.八骏图.沈从文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116
⑥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326.
⑦沈从文.生命.沈从文文集第七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1982-1984:295.
I207.42
A
1005-5312(2015)26-0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