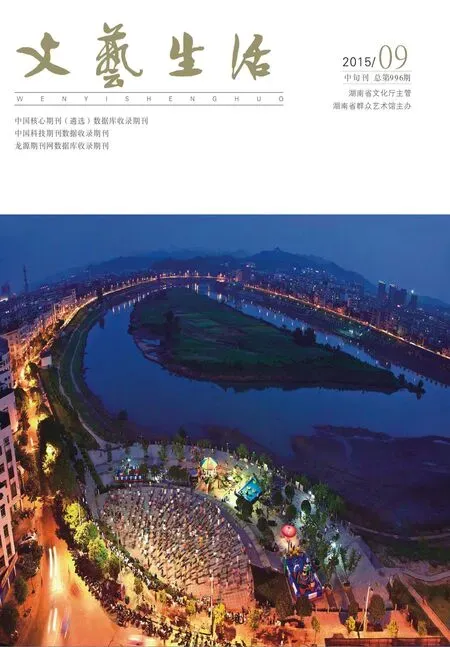论反乌托邦文学中的社会设定
——以生态批评文学为例
李诗意苏姗王鑫熊彦莹张子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100029)
论反乌托邦文学中的社会设定
——以生态批评文学为例
李诗意苏姗王鑫熊彦莹张子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100029)
“乌托邦”是人类在心中构建的理想社会,而“反乌托邦”是人类在追求乌托邦时失败的畸形产物。反乌托邦文学对可能的畸形产物作了大量丰富的构想。事实上,这些构想无不是基于对现世社会问题的探讨与反思。通过使用生态批评对所选取的具有代表性的反乌托邦文学进行分析,从精神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三个角度,可以挖掘出人类对现有社会构建的疑虑、困惑与洞见。
生态批评;反乌托邦;精神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
一、自然生态
反乌托邦小说中对于自然与人关系的描写可以分为两种,有诸如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的抽离式表现,即不正面进行描写,仅能从情节等侧面推测;也有诸如考麦克麦卡锡的《末日危途》中的详细、大量的描绘。前者小说中不突出自然与人关系的变化,默认在构想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世界中,自然仍然处于被人类利用、控制的地位,从某些角度来说,人类内部的关系与这种状态处于对等的状态,表现出在虚构世界中“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思想”(耿超:5),如小说《美丽新世界》。后者则有所不同,在对自然的描绘中,突出其毁坏程度及非常性,表现人类在失去对自然控制后,反受自然因素所限制的状态,如《羚羊与秧鸡》。
例如,小说《饥饿游戏》三部曲中的环境描写,在描绘第一区凯比特时大量采用对奢华场景的描绘,现代化及娱乐业发展的程度很高,而表现其他各区,尤其是主角凯特尼斯生活的第十二区时,则突出由于偏重发展煤矿业造成的过度开发、生态原始,“令人不安的是林中有毒蛇,还有凶残的动物,林子里也没什么路”居民的生存环境恶劣,甚至食不果腹;至于隐藏的十三区更是完全被覆盖在原始自然环境之中。而在最终的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也并没有对这样的生存状态进行改变,而只是改变了社会内部人的关系。尽管这并非小说的突出主题,但这样的描绘似乎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和谐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而《美丽新世界》所展现的以科技理性为原则建立的世界,前六章对新世界环境的描写突出其秩序与规律,甚至连自然的美丽都是为人类所利用控制其他人的工具,“培养孩子们见了玫瑰花就尖叫是为了节约”,或是将对舒适安逸的环境描写与严格控制的手段结合,形成鲜明的对比,构造出一种诡异反自然的气氛,如这一段“玫瑰开得正艳,两只夜莺各自在密林里呢喃,一只杜鹃在菩提树梢开始唱得走了调。蜜蜂和直升飞机的嗡嗡声使空气里充满了睡意”,在描写惬意童真的环境后,却很快描写另一部分的环境严苛以对比,使“新世界”的森严等级更令人信服。
而在反乌托邦小说《羚羊与秧鸡》中,有大量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根据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小说中广泛而又细致的自然环境的描述,书中的世界中的自然生态已经完全被颠覆。在本书中,我们随处可见人类对大自然的践踏,而疯狂的人类也失去了对自然的掌控权。作者想通过这些描写来提醒世人“如果人们尚不悬崖勒马,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人类与自然一同走向灭亡”(陈磊:2)。而在麦卡锡的《末日危途》中,小说中的世界是“一片黑暗和寒冷的废墟之地”,末日来的令人毫无准备。时间定格在某个凌晨的一点十七分,“一长束细长的光……一阵轻微震动”,没有任何原因和任何预兆,世界陷入了一片黯淡。麦卡锡所描绘的末日中的自然环境,是破败、萧索的,仿佛是“黑色大幕下的一座巨大的游乐场废墟”(麦卡锡:24)。作者通过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多角度,多方面地描绘末日自然生态,放大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表现了人类在大灾难中的无助和渺小,让“民众去正视现实、思考未来的出路”(方凡:73)
反乌托邦式的小说中,作者这两种不同的描写方式展示了他们在其建构的虚拟世界中对自然的定位。在《饥饿游戏》中,尽管作者有对环境的直接展现,但她并未正视自然生态问题在人类社会中的影响;而《末日危途》中大段对生态遭破坏后恶劣环境的描写,虽然直面了自然的因素,却采取悲观被动的态度,没有对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究其原因,前者认为自然在反乌托邦小说中对情节推动的力度并不大,因此并不多着笔墨表现。后者则可能是因为现下的科技状况及研究对自然问题并无突破性进展,所以认为未来可解决人类与环境冲突的希望渺茫,采取顺应的态度。
二、社会生态
从社会生态的角度来看,反乌托邦文学主要表现在专制社会以及极权统治,不和谐的人际关系,科技与欲望的肆虐三个方面。
在反乌托邦文学中,统治阶层通过控制人们行动和思想的自由来达到专制的目的——人对物品的依赖,专制集团对人无处不在的计划监控。《美丽新世界》中有一种叫做索麻的药品,它具有麻痹作用,能让人忘记烦恼进入极乐世界,书中的人有很喜欢吸食索麻,琳坦甚至因为吸食索麻过量而死亡。同样在《一九八四》中有着类似的药品类的东西叫做杜松子酒,书主人公温斯顿喝完杜松子酒之后就再也迷恋甚至成瘾。除此之外,《我们》中的人严格按照“火车运行表”作息,在《我们》社会里,数百万人每天在同一时间同一分钟开始和结束工作,同一时间进入泰勒基本功训练大厅……而《一九八四》中描述了伦敦在极权统治下的恐怖情景。
统治阶层通过这些成瘾的药物和其他手段控制人们的人身自由进而控制人们的思想。真理部的主要任务是“为了保证正确无误,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而实际上,真理部的作用是伪造、改写历史,并使其呈现出从未被改动的样子。真理部展现了党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即“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伪造,是党控制的主要手段,它抹杀真实的存在,借助语言来重造事实。在语言的极权下,过去不但改变了,而且被毁掉了。党控制了全部的记录和记忆,就控制了过去。而老大哥思想控制最成功的案例应该是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对党的政策提出了怀疑和不满,经过折磨,洗脑,最终失去了自我意识和鉴别能力,心甘情愿的爱上“老大哥”。
诚然,“文学是与政治相关的。无论从文学原理还是创作实践的角度来说,思想性-政治性都是文学生命之魂魄”(李媛:29)《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奥威尔认为:“有人认为书应该脱离政治,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我在一九三九年以后写的每一篇的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反应了极权统治和民主社会主义,当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动物农场是我在充分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努力将我的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融为一体的第一本书。”毫无疑问,继《动物农场》之后的《一九八四》是奥威尔表达其政治观点的重要载体。侯维瑞在他的《现代英国小说史》中指出:“在奥威尔写作之初,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成为了重要的主题……1934年出版的《在缅甸的日子》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奥威尔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谴责态度。”(侯维瑞:366)反乌托邦的文本往往反映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这些小说往往建立一个全新的真实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作者通过极端的手段与科技来表达对现实政治世界的不满。
另一方面,“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反乌托邦小说中。例如:《一九八四》中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人与人间禁止存在爱情与性,鲜少真诚地交流。主人公生活的每分每秒都在被监视着,“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作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因而每分每秒主人公都在克制自己,掩饰自己,表演自己。这样的社会里几乎不存在正常的人际交流,和谐的人际关系更无从谈起。《美丽新世界》刚展示了另一种社会人际交往状态。在这里,欲望被鼓励及时地释放。人不是孤独的个体,但是大部分只与同一阶级的人们打交道,并且人们之间性关系糜乱:当主人公与其暗恋的列宁娜一起走进电梯时,竟发现拥挤的电梯中的所有人都与列宁娜发生过性关系。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张冬梅:72)中人际关系也同样畸形。等级森严的不平等社会,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充斥着整本小说。这些反乌托邦作品里通过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假想与设定,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人际关系问题的强调或放大,借此对问题进行探讨,对现世具有启发意义。
自从1765年第一次工业革命起,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一直在科技的齿轮的驱动下飞速发展。人类的欲望催生着新的科技,另一方面科技也放任了欲望的滋长。反乌托邦小说对此有一个很好的描写:无论是在叶夫根尼?扎米亚京《我们》、艾萨克?阿西莫的《钢窟》,还是艾拉?莱文的《这完美的一天》、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科技都发展直至泛滥的地步。因此,人类社会高度依赖科技。科技在支撑着整个社会的运转,把人们从劳动、思考中解放,最大程度地满足着人类的欲望。放弃了劳动与思考的人类已经不是完整的人类,尽情纵欲的同时,人类也失去称之为人的宝贵的东西。
三、从“荒原”到“家园”的精神生态
从“荒野”到“家园”,实际上是“自然”一步一步被驯化的过程。
谈起对“家园”的印象,人们脑中浮现的通常是“田园诗”式的景致:水车、带有特殊记忆的房间、盛开的花丛……可能是“自然”的景物(花,树,河流),也可能是“人造”之景(花园、房子)。但可以注意到的是,即使是“自然之景”,也是经过人类“筛选”的那部分“有益”的自然。因此从这方面而言,“家园”是个文化概念,一个能让人“诗意栖居”的环境。
“荒野”指的是未经人类开化、无法为人类所利用的土地。“荒野”的意象通常与“不祥”、“磨难”联系在一起。《圣经》中,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摩西率领人民在荒野跋涉了四十多年才到达了上帝应许的流着奶与蜜之地,这些都塑造了“荒野”意象在西方主流文化里的象征义,即控制、约束以及规则的缺失。之所以“荒原”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因为所有考量标准都以“人”的立场出发、以是否能为人类所利用作为判断标准。
与“荒野”挂钩的人类“文明”,也往往被认为是“蛮荒”的、“原始”的,因为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地理环境的边缘,也常常暗示着人类道德的边缘。如《蝇王》中,杰克和拉尔夫在荒岛两端所建立的“政权”的对比——后者试图将人类文明的火种带到荒岛,建立民主制度,塑造一个“乌托邦”式栖居之所,而前者则妥协于象征“原罪”的荒岛环境,精神状态也渐渐被同化,最终退化成茹毛饮血的“野蛮人”。
作为一种“生态”,个体的精神生态难以把握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作为一种动态的、独立的、不断变化的体系,外部难以对个体精神生态加以控制,这便与乌托邦所崇尚的“绝对的人造秩序”相悖了。第二,当物质的发展超越了精神的发展,这一生态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人类将以“创造”来填补这一“空虚”,可是一旦自然无法继续承受人类的深度改造、环境持续恶化,那么人类将面临的会是更可怕的精神荒原。
反乌托邦小说通常将背景设定为末世,即饱受人类工业文明摧残、灾难过后无法复原的自然。过度的文明最终却摧毁了文明本身,也摧毁了文明的创造者。典型的是小说《路》的设定,世界经过核灾难的洗劫,只剩下一片荒芜、尸横遍野、了无生机。此时“道德”范畴早已不复存在,没有食物,大地上到处都是谋杀,幸存的流亡者冒着被食人者捕杀的危险。小说在这样极端环境、极端精神危机的背景下展开,叙述一对父子为了生存而逃离人造荒原的故事,其中不断穿插父亲有色彩的、昔日生活的回忆片段,也即是乌托邦式的乡愁。父与子同样站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着生存,却在一路上不断地进行着“高于生活”的对话,谈论道德,谈论信仰,谈论“心中的火种”,为小说黑暗可怕的基调注入了一点人性的光明。
人类有毁灭自然生态的力量,但是最终毁灭、击垮人类的,一定不是自然,而是人类自己。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者互相关联,但精神生态相对于前两者又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它不依赖实体表现、更加“虚幻”,也因此充满无限可能性。死亡还是生存,决定权在人类手里。孩子的母亲因为无法忍受生存的压力而选择自尽,孩子成了父亲唯一活下去的支柱,他用信仰和亲情让孩子看到残酷现实表象下,精神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他支撑到孩子足够接下“心中的火种”的时候,才安心地倒下。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生态批评解构下反乌托邦小说的终极意义——通过虚构的末世、荒原激起读者心中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是激励性的,鼓励现实中的人们追寻道德认同感,从而防止生态毁灭。
四、结论
反乌托邦文学,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探讨与反思了在人类历史进步过程中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以及精神生态的状况。当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研读后,可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自然生态方面,反乌托邦文学通过构想突出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恶化,自然仍然处于被人类利用、控制的地位,从某些角度来说,人类内部的关系与这种状态处于对等的状态,表现出在虚构世界中“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思想”(耿超:5),同时部分反乌托邦文学作品在对自然的描绘中,突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程度以及严重性,当人类对自然失去控制之后,反受自然因素所限制的状态;其次,从社会生态的角度来看,反乌托邦文学主要描述了在专制社会以及极权统治下,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在科技的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类的欲望的肆虐和膨胀。而精神生态相对于前两者又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它不依赖实体表现、更加“虚幻”,也因此充满无限可能性。人类有毁灭自然生态的力量,但是最终毁灭、击垮人类的,一定不是自然,而是人类自己。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在反乌托邦小说中互相关联,又相互影响,共同展现了自近代以来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1]耿超.生态主义视域下《美丽新世界》主题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
[2]陈磊.阿特伍德小说《羚羊与秧鸡》的生态批评解读[D].沈阳: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
[3]方凡.绝望与希望:麦卡锡小说《路》中的末日世界[J].外国文学,2012 (02).
[4]李媛.反叛与延续——从“反乌托邦三部曲”看反乌托邦小说[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9.
[5]侯维瑞.英国现代史小说[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6]张冬梅.《使女的故事》的生态批评解读[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08.
I06
A
1005-5312(2015)26-0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