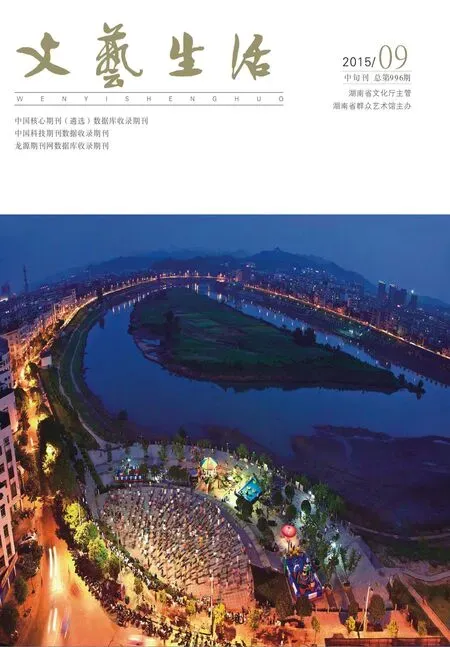警、觉、幻
——以《大劈棺》为例浅析汪曾祺后期作品中的女性观
杨晓烨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警、觉、幻
——以《大劈棺》为例浅析汪曾祺后期作品中的女性观
杨晓烨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本文以剧本《大劈棺》为例,分析汪曾祺晚期作品中的情爱观,并进一步阐释隐藏在其女性观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并试图从其作品中爱欲和生死的辩证主题下,儒道交叉的文化思想之下进行有序的阐释和理解,重构晚期汪曾祺的立体形象。
女性观生死儒道后期
汪曾祺的文字,平淡充实,安定而有市井气,有着温厚和悲悯的底子,他以善意抵抗世俗,以包容精摩世界,还原的是生活的原态和人性的本真,在他笔下,一花一草、一衣一蔬,皆有灵气和情致,饮食男女,人间百态都有其自然的天性和自由。即使是情欲纠缠也写的纯真和美好,剔除了粗鄙和肮脏,承袭的是明清之后的古典主义与新时期现代主义交融的女性观,这种对于两性关系的大胆姿态,让其作品尤其是后期作品的风格愈发游刃有余,诙谐潇洒。
一、“衰变中年”下的反叛与突破
汪曾祺曾经自题绝句一首,“衰年变法谈何易,唱罢梨花又一春”①,其后期作品在延续着其一贯的恬静平实的写作风格的同时,也与之前呈现出了较大的反差性,表现出了更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把关注点更多的放在了突破日常伦理和道德束缚,反常规、反传统的故事上,而越过道德界限的女人则成为了主要刻画重点。1989年汪曾祺创作的剧本《大劈棺》便能集中代表其在后期创作中思想和主旨的转型。这部七场戏剧歌舞剧改编自传统京剧剧目《大劈棺》,庄周得道,路遇新孀扇坟使干,以便改嫁;庄周因此回家试探己妻田氏,伪病死,成殓,幻化楚王孙,携一家僮来家。田氏见王孙,顿生爱慕,拟嫁之,洞房中王孙忽患头痛,谓死人脑髓可治。田氏乃劈棺取庄周之脑,庄周突然跃起,责骂田氏。田氏羞愧自杀,庄周弃家而走,汪曾祺用诙谐幽默的笔调改写了原剧中对女性的道德批判,而借由庄子之口,对庄妻的自主追求幸福的勇气加以肯定和鼓励,并对其看似离经叛道的荒唐行为加以“赦免”。在整个剧本中一共出现了三个女性角色,首先是“未亡人”少妇,在丈夫尸骨未寒的新坟上用扇子扇风,期望能够早点解脱道德束缚,另觅新欢。少妇这一形象正是千百年来苦守忠贞戒律的中国妇女的心理投影,所谓的三纲五常的沉重枷锁正使得其沦为命运的最终牺牲者。而与此相比,田氏则更加大胆勇敢的多,尽管之前在与庄子争论时,以及与少妇的言谈对话里表明自己忠贞的决心,但当对楚王孙一见钟情之后,立马亲手推掉自己建造的“贞洁牌坊”,表现出对爱情的炙热追求。其中,看来无足轻重的一个细节极能表现出田氏的性情特点,即在其差使春云去买丧葬用的货品时,春云曾这样转述田氏的要求,“春云:‘这口吧。你这棺材是凉的还是热的?’棺材匠:‘凉的热的?’春云:‘我们师娘让我买什么都要热的。包子、花卷、烧饼、油条,都得是刚出锅的,热的。”从春云之口,我们了解到田氏对“热”的东西这一要求。在这里“热”所传达的并不单单是物品的体感温度,似乎也能解释到是对人性的温度的传达,田氏对于“热”的要求,来源的是内心的涌动和欲望,是对鲜活生命的希冀和要求,与无数个选择在丈夫去世后守寡一生凄苦过日,自愿选择了“凉薄一生”的女人相比,在冰冷不近人情的封建礼教之下,田氏对“热”的选择,正是其真实人性的传递,同时也对其后来打破世俗礼教的不逾矩行为作了很好的心理来源和铺垫。所以,其后的故事发展中,无论是自荐保媒,还是劈棺取脑,田氏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人性应有的温度和需求,即使中间有犹豫和纠结,但在其身上我们能看到人欲的正常释放以及个性的合理舒展。而另一个不起眼的配角春云,正如传统剧目里的其他小丫鬟一样,扮演的是插科打诨,穿针引线的角色,她的旁白趋于口语化,幽默诙谐,却又别有深意。在田氏与楚王孙初次相见时,她在一旁对注视良久的二人插话道,“嗨嗨嗨,看两眼就够了!哪有这么死气白赖的!”让田氏不禁羞愧。可以看出,春云这个小丫头所占的立场,正是“世俗”的立场,她基于世情之上对于田氏大胆举动的评论,正是基于封建常情之上的道德批判以及人情反讽。所以此时汪曾祺在这部剧目中的三个女性的角色的设置显得别有深意,从春云到少妇再至田氏,从站在道德立场的小丫头到矛盾挣扎的年轻未亡人再到具有反叛精神的大胆女性,三个女人的性格特点是循序渐进的,对于世俗的态度也是遵循从服从到忤逆的逻辑顺序。而在故事的最后,汪曾祺也借由庄子之口的唱段,“倒不如松开枷锁,各顾各。”则表现出了对妻子“出轨”的理解和释怀。
从《大劈棺》我们可以看出,在汪曾祺后期的作品中,女性的地位一跃而上,改变了先前的依附顺从地位,开始主动谋求个人的幸福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汪曾祺的小说真正的实现了从五四便开始延续下来的“女性解放主题”。这类女性并不是自甘堕落,放荡形骸的,而是充满了自主性和自觉意识,她敢于们对自己的命运抉择负起责任并承担后果,与印象里懦弱愚钝的女性不同,她们更加独立,更加具有尊严,也更具有现代意识。而正是透过以这类女性为主角的全知叙事来看,汪曾祺的作品中革命性的通过性欲和道德的双重角度建立了一个反传统反概念化的全新女性观。
二、儒道理想下的“文化重构”
中国的文化延续着双重线索,一是代表官方的儒家文化,其扮演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影响着官僚士大夫的一举一动,二是民间文化线索,以数术方技为代表的实用文化,上承原始思维,下启阴阳家和道家,以及道教文化。②而对身体的叙述也因这双重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多面性的特点。首先儒家文化对身体的态度代表着传统文化中身体观的主流。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重视人伦道德,提倡个体应融入社会/集体/国家/天下之中,它注重的是社会文化的身体,是身体的道德性,君子儒士的形象也就成了儒家理想的身体形象,他试图以“修身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强调身体的道德性和与文化的一统性。而非主流文化像道家文化、道教文化等则较少像儒家那样重视家国天下,他们把关注的焦点更多的投向了个体本身。道家认识到个体生命的短暂性,而身体又是“道”之载体,故要“体道”必须“保身”、“全生”。庄子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③抛弃了大语境话语,道家对身体的重视更倾向于对自我个体的爱护和珍重。因此,在这两种文化话语之下,中国文化对身体的表述呈现出了差异性存在,而对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开辟了新时期“寻根文化”先例的汪曾祺来说,其截然不同的女性观点正是这两种文化线索的交叉性表述。
首先,正如《大劈棺》中庄周人物的设置,汪曾祺的开放,自由大胆,具有极强的突破性的两性观点,深受道家中“道法自然”的影响,不要为了人工而毁灭天然,不要为了世故去毁灭性命,保存人性的天真纯粹,用平等自然的观点去看待人欲追求,反对儒家的强权话语,对于儒家文化中对于身体的压制和规范进行摒弃和排斥。因此在这样的观点下,《大劈棺》中庄周最后的唱段,“我这就打点行囊包裹,浪迹天涯,神游六合。你也解脱,我也解脱。”以及开头和结尾的两段歌词,“宇宙洪荒,开天辟地。或为圣贤,或为蝼蚁。”其所还原的是道家意境,达成的也是一种逍遥于世,还原世俗的生存哲学。
其次,汪曾祺的性爱表述看似是以道家思想占据核心地位,但是其话语表达以及最终追求确带有明显的儒家思想。一方面,在八十年代文化寻源的风潮之下,作为其领军文人,汪曾祺对于性爱的大胆表达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传递的是特定时代的文化潮流和风向,而这种话语表达也自然带有明显的“文化领袖”色彩,是掌握一定话语权及话语空间的主流文人的特有优势。汪曾祺的“士大夫”气质,让其文字即使“异端”色彩浓厚,但仍然是依靠于主流规范之下的。另一方面,汪曾祺试图通过性爱描写建立一片和谐天地,包容、理解、兼爱,是其想要达成的理想境界。汪曾祺将不为人所理解的人性从生命的暗影下打捞起来,使其有光,发亮,充盈,其所还原的正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极乐天地,并最终达成万物的大和谐。
三、结语
而除此之外,新时期现代主义的思想也容纳在汪曾祺的情爱描写之中。《大劈棺》中对存在主义的追寻,其中的荒诞感、宿命感、悲剧意识都体现出现代主义文学的大致特征。所以汪曾祺寻求的正是传统文化和现代主义的接轨和兼容,以其严肃的态度、平等视角和心态对待两性关系,写出了复杂的人性、独立的人格、自主的意识及美之所在,表达出对人性的欣赏和尊重,起到了瓦解权利话语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汪曾祺性爱故事具有“文化重构”的意义。正如题目所言,汪曾祺的女性观正如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之际,所见众女子的命运判词之后,在一响贪欢之后,留存下来的,是警,是觉,更是幻。
注释:
①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八其他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3.
②李零.中国方术正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
③庄子.孙海通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53.
I207.42
A
1005-5312(2015)26-0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