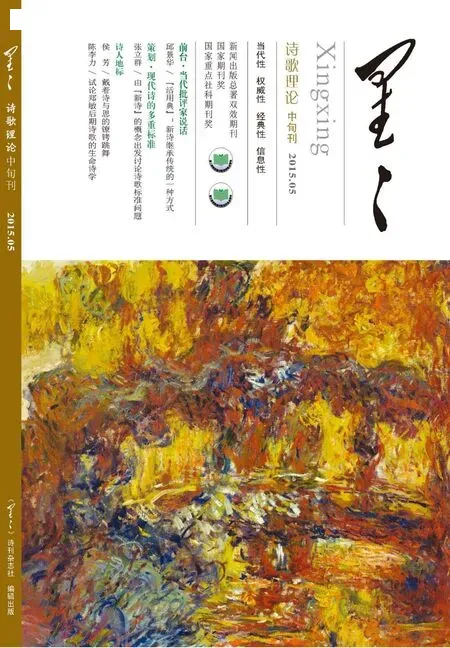黄昏的十五度角:在现实与虚构之间
——章闻哲散文诗《黄昏的处境》文本初探[1]
[前沿话题]
黄昏的十五度角:在现实与虚构之间
——章闻哲散文诗《黄昏的处境》文本初探[1]
李仕淦
正如我无法把黄昏归入白昼还是夜晚一样,我无法告诉你黄昏对于我来讲究竟是什么。也许,它是时间的另一种形态,也许它根本就不是时间。
它的可疑在于:世界因其抵达或降临而成为一种无限扩长而柔软的气体,我们深陷其间,只是一些气泡,连同我们所触及的苍茫、深渊以及其余。[2]
这是我的黄昏,当然,黄昏对于你肯定是另一回事。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黄昏,每个人的黄昏都各不相同。而章闻哲似乎在说:黄昏或许就是每个人各自的处境。
在这个意义上讲,进入另一个人的黄昏,就是进入另一个人的处境。这是一种冒险的越境行为。尽管这个以“文本”方式貌似敞开一切的“处境”(个体经验世界),欢迎一切“窜入者”的进入,但由于敞开者,即言说主体的言说方式与策略不同,加之不可避免地携带着言说主体极具个体隐私的一面,它显得机关
重重,进而也显然遮蔽着主体许多无法让“窜入者”感知、觉察、经验的盲点、禁区,甚至就是黑洞。章闻哲的“黄昏的处境”充满迷津和陷阱。因此,我们不得不倍加小心,更何况章闻哲在敞开她的黄昏处境的起初,连她自己也是小心翼翼地只“把房子打开十五度角的小口”。
这个小口打开的时候,“黄昏的色调已经迅速加深,并被一场大雪所调和”,打开的一刻,“雪花正在恣意走笔”。而在此之前,“两个褐色的鸟巢是整个冬天的纪念碑”——来自于主体内视境遇的“一个暴政者的眼色”已经击中我们,“凝重而偏执”。而后,顺着这个十五度角的小口望出去,我们看到了昏色浮动的大地与“太阳沦落”的整个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难以言说的意味,它是章闻哲的,也是我们的。她的策略在于通过“文本”的建造,通过“文本言说主体”内外视域的呈现,在“敞开与遮蔽”之间,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把自己(写者、打开者)和我们(读者、窜入者)一同拖入万物凋敝以“褐色”为中心语的“处境”深渊,在时间潜伏、不动声色的巨大寂静与虚无中,怀抱着太阳与太阳一同沉沦陷落。而在我们与她一同陷入的时候,也许只是转身的瞬间,章闻哲又让我们看见了“六角花絮带来的冥王星的光亮”——我们所触及的这个“世界”并不止于太阳沦落的苍茫大地,而是我们藐如沧海一粟存在其间的整个浩渺宇宙。
但是,这显然还不是章闻哲“黄昏处境”的全部,它还只是“外在世界”的描述,是主体存在整体“处境”的宏观背景,尽管这一背景图式的展开仅仅给出一个“十五度小口”的观测视角,已经足够让我们晕眩和迷失。至此,章闻哲的“黄昏的处
境”仅仅拉开序幕,整个“处境”的“内在世界”还处于遮蔽状态,在“寒风”到达之前还在“冬眠”。
而紧接着,我们仿佛象被谁推了一把,推出了“黄昏”之外,我们站在了这个“黄昏处境”的对面,保持着一种可疑的距离或是某种难以穿透的“隔绝”,我们成为局外人,成为将要上演的一出舞台剧的看客——
戏剧的舞台当然是这座房子的室内,可以想象是很日常的起居空间,而背景就是上述房子打开十五度角小口我们与主体一同所经验到的整个宇宙大时空——在雪花飘舞太阳沦陷的苍茫大地与冥王星光亮撕裂、洞开的浩渺天体之间,光影交替变幻来回不停地转换、交叠、回旋。
“寒风”如期造访,“左拥夜色右拥雪花,或一身黑衣,肩上佩戴几许银羽”,这个最先出场的角色,“或许是一个不拘小节的诗人”,在两分钟内被谋杀——“寒风连同它的体温一起消失”,不见“踪影”,留下一个“非常邪门而刺激的新闻现场”。
被杀者是“寒风”,而谋杀者是谁?主角出场,信誓旦旦坦陈“在两分钟内我将成为谋杀者”,并很愿意有人把她的身份猜想成“巫师、种盅者、恶鬼、梦游者、妖精”,因为“这些角色都有足够的力量把生命杀死而不留痕迹。就像蛇类一样,把整个吞下去,连皮屑和骨头渣都不剩下。”然而,在舞台光影变幻中,主角经过大段、大段的独白、对话与潜对话(关于工程师、种盅者、巫师、魔鬼的“知识”与“智慧”及其相互关系,关于“友爱/仇恨”、“幸福/痛苦”,“生存/杀戮”、“欲望/理智”、 “险恶/纯真”、 “昧良/正义”等等)激昂而不无偏执
的“雄辩”之后,彻底干净地推翻了自己“谋杀者”的身份,并理直气壮地声称:“寒风因为夜色而死,因为雪花而死。这是我给出的最正直的理由。”
这的确是个邪门而刺激的“新闻现场”,一宗匪夷所思的“谋杀案”。“寒风之死”,无论是死于“谋杀”(人为的?),还是死于“夜色和雪花”(自然的?),这个虚构事件,或者说这个事件的“舞台戏剧”演绎,在言说主体带着某种“恶毒惬意”陈述事件和复制事件现象,一同把我们卷入“现场”并见识她“魔鬼派头”尖刻的冷嘲讽里,多少让我们感受到某种“黑色幽默”或是卡夫卡式的忍俊不禁。在这里,“谋杀对象”是虚拟的,甚至就是“虚无”(因为它是“风”),尽管文本中有“来客”或是“诗人”的暗示性对象所指,但可以“看不见”或“不看见”(“如果不看被害者是谁”)。然而,“谋杀”却是真实发生了,被害者可以是任何具体的“生命”。我们不排除文本陈述的事件是对我们日常现实几乎无时不刻都在发生的“谋杀”现象的映射(这或许已经具有了某种世俗化存在所关注的很高的“现实意义”?),但显而易见,这不是章闻哲的真正意图。章闻哲(写者)把这个事件现场界定为邪门而刺激的“新闻现场”,在案情的末了,“言说主体”从“角色”游离而出,她一面让我们(看客——读者)勘察“现场”,“查看证据”,并要求感激她让我们认清了“那些巫师、种盅者、梦游者、妖精等,不过是魔鬼的宠臣或游戏的工具”,一面双臂抱胸,倚于门侧,吹着肖邦《小夜曲》口哨,看着我们“一本正经地消费正义感和仇恨”。如果这是“新闻现场”或整个事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那么,它(即主体与角色游离)所刻意留下的这
一“线索”,旨在引发我们注意:在这一宗简单、甚至“破绽百出”而又布满“蛛丝马迹”疑惑重重的“谋杀案”中,必须关注的并非事件所指涉的“虚拟现实”或“日常现实”的真实与否,而是由“日常现实”提取通过“虚拟现实”建构起来的整个“文本现实”的真实性——在现实与虚构之间,被文本“虚拟现实”(即表象)所遮蔽的内心真实(本质)恰恰因被“遮蔽”而“去蔽”——它将直接导入“黄昏处境”的“内在世界”。
这是第一幕,“黄昏处境”的“第一种境遇”。
第二幕,“在另一种处境里”。这起承转合的一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舞台背景上打出的“字幕”。前一幕过渡到后一幕,整体大时空背景依然延续,但随“剧情”进展,背景图式变化中出现了阳光明媚、惠风和煦“花好柳不败”的南国景色和春天梦幻。而“剧情”较之第一幕匪夷所思的“谋杀”似乎要简明得多,“言说主体”作为“主角”出场,依然以独白、对话与潜对话推进“剧情”的发展。然而,这个“似乎简明”的剧目也并非真的简明,无论是背景的变化,还是角色的变化,尤其是事境陈述和情境渲染与第一幕风马牛不相及而大相径庭的差异,一时间,还是让我们感到云里雾里。尽管一开始章闻哲(写者)就安民告示指出这是“在另一种处境里”,尽管我们已在第一幕里几经折腾而有所心理准备。
“言说主体”作为“主角”刚一出场就说:“我对房子里的另一个人说”。这个所谓的“另一个人”,是谁?在哪里?事实上,作为“角色”,这个“另一个人”始终没有出场,然而又始终都“在场”。这或许正是章闻哲(写者)精心设置的一个“陷阱”——“虚拟对象”。这个“虚拟对象”可能是“人”,
也可能是“物”。如果是“人”,“他”可能是“你”(或“我们”)——看客、听者、读者,也可能是“我”(或主体)——角色、言说者、写者,可能是“活人”(包括虽生犹死者),也可能是“死人”(包括虽死犹生者);如果是“物”,“它”可能是那一轮沉落的太阳,或遥远的冥王星,也可能是房子外那棵树上的鸟巢,或室内任意一种物件;当然,不可缺漏的还有巫师、魔鬼、妖精等一类的鬼怪精灵。一句话,上述一切对象都可以是这“另一个人”,一切“言说”所针对的是主体存在的“整个世界”,尽管章闻哲作为“言说者”还是作为“写者”总是保持着一种“真理在握”,“你爱听不听、爱读不读”,不无“傲慢”与“挑衅”的姿态。
那么,“主角”对“另一个人”说了些什么?开宗明义:“鉴于我已成为一个世界的敌人,我愿意把它看成世界的友人”。前半句,显然是对第一幕的慨括总结,亦即对“言说主体”作为“角色”或者说就是主体形象的存在价值判断。“世界的敌人”,当然站在“世界”对立的一面,对“世界”抱有警觉而深刻的“敌意”,从第一幕的言说内容与言说姿态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些直观的感觉:叛逆、反抗、斗争、决裂或是“他”与世界存在关系的中心词,讥讽、冷嘲、揭露、批判、辩驳则是对抗这个世界的有力武器,而悲剧、痛苦、绝望、孤独、“黑色幽默”、虚无、荒诞或是其存在于世界的刻骨感受与经验。——但这仅仅是这个主体形象的一面。而它的另一面,或许就是几近结论判断的这后半句:“世界的友人”。
在文本的“虚拟现实”中,这个“世界的友人”所指是房子外那棵树上鸟巢的“主人”。“也许鸟巢已空”,也就是说这
个“主人”可能在,也可能不在。如果还在,它也许“也象我一样用十五度的视角窥视雪花”,它“天真烂漫,对着亲吻它额头的雪花说着嗯嗯的话”;如果不在,它离开,“或许已迁徙至南国,在暖水和熏风的环境中,它抬起头眺望北方时,眼中的光同样是温热而美丽的”。——一切仿佛只是“也许”,但一切皆可能,我们再次陷入章闻哲所设下的陷阱或迷津:鸟巢的“主人”究竟离开还是没有离开?它是否只是“言说”的表象,亦即它仅仅只是“语言或词语字面含义”所确定的“世界的友人”?但很快,我们便逃离了这一陷阱或迷津。在这个“虚拟现实”的事境中,鸟巢的“主人”——鸟,它在或不在鸟巢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也和我一样用十五度的视角窥视雪花”, 它天真烂漫,“在它情人的眼中,它是身段和话音都带着温婉和柔媚的小妇人”。换一种说法,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鸟”在这一事境中就是一个“喻体”,它的“本体”就是“言说主体”(或“形象主体”)本身,也就是说,“言说主体”(或“形象主体”)才是真正的“世界的友人”。“喻体”的存在或可表征了“本体”存在的生命自然属性,但“言说”的本质内涵以及“写者”的真正意图则在这个“言说表象”的背后与深处:“言说主体”作为“世界的友人”它具有着与“世界的敌人”完全不同或相反的德性与品行,这在事境陈述与情境渲染烘托的交叠转向中,尤其是在“写者”于“剧情”推进过程一再“站出来”针对“读者”进行暗示与提示性旁白的指涉中。
事实上,“剧情”演绎至此,我们已可明确前后两幕出场的“主角”是同一个“角色”,即“言说主体”或“形象主体”,所谓“世界的敌人”与“世界的友人”则是这个主角“角色”的
“一体两面”。在第一种“境遇”里,这个“角色”如果可以用“尖酸、刻薄、狡猾、霸道,甚至恶毒、阴险、残忍、暴力等等“词汇”为其性格特征贴上“反面”标签的话,那么,也可以用这些“词汇”的“反词”,比如温和、友善、正直、纯真、本分、非暴力等等来为第二幕“另一种境遇”里出场的这个“角色”贴上“正面”的标签。进而,还可以用“光明/黑暗”、“绝望/希望”、“高尚/卑鄙”、“积极/颓废”等等一组“词”与“反词”来为前后两幕两种使“角色”发生裂变的“境遇”情形或形态打上烙印。但是,这样做是及其危险的,我们将即刻滑入“二元对立”机械辩证的泥潭显得浅薄而自讨无趣。尽管在这一幕往后的“剧情”进展中,确乎还出现了有关“南方”(光亮)与“北方”(灰暗)、“白昼”与“黑夜”、“母性”与“父性”等的情境描述和独白、对话与潜对话“言说”,而使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这种“二元对立”强制性力量的压迫。在这一幕里,与第一幕一样,“角色”的“二元对立”显然是存在的,但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绝对对立,而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亦即在“角色”或“言说主体”这里,对立两个向度的力量或“势力”共同集聚于一身,同时发生作用。因此,“言说主体”以“角色”的口吻如是说到:“没有一个时代不需要母性的安抚,毫无疑问,在母性的形式里,囚禁着无数父性的内容”,而“囚禁中的父性看上去始终统治着母性”,甚而这个“角色”分化出“A、B、C”等几个角色同时登台亮相,从不同向度展示出“角色”的性格特征,从而直接指向“言说主体”或“形象主体”灵肉精神内里,达成与“外在世界”描述相对应而互为表里的“黄昏处境”里“内在世界”的揭示与呈现。
对照与统观前后两幕,“言说主体”作为“角色”的“一体两面”,就像文本所写“母性与父性”的合体,在一个具体“角色”或者说在一个具体的“人”(无论是谁)多重性格,多种品行、德性的混合,无法简单以“好或坏”、“贵或贱”,“神或鬼”、“圣或怪”等简单做出界定与评判。“一体两面”,更确切地说是“一体多面”,“多质与多值”混合在一起无法分割、游离、靛青,犹如“黄昏”交合、搅和了“昼”与“夜”,难以界定它的界线和归属。章闻哲在她“黄昏处境”的前后两种“境遇”里,呈现了“人”存在的这种本质特性和存在的现实。如果说,这个“黄昏的处境”不仅仅只是章闻哲一个人的,也是我们所共有的,那么,在这里,即“文本现实”的“境遇”里,作为“人”存在的本质特性和存在现实被揭示与呈现出来,显然其指向不是单一的一个角色(一个人)或几个角色(一群人),而是现代生存的人类“整体” ,用一句过时的话说也是“大写的人”。 生存于“世界”中的“人”如是,“世界”本身的存在亦如是,我们同样无从以“好或坏”、“光明或黑暗”、“神圣或卑劣”等简单地对历史任何时代“人”所生存其间的“世界”进行评判,更无从简单地从我们正生存其间的“当下世界”中获得明了的答案。“人”与“世界”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正因这种“混合性”与“不可分割性”显得愈加复杂、晦暗而难以理喻。
然而,这种“混合性”与“不可分割性”,恰恰又是由于“分裂性”所导致,那就是人与世界、人与自我的分裂。在上述第一种“境遇”里,“言说主体”以“角色”出场,几乎是下意识并充满快意地愿意有人把他的身份猜想为巫师、种盅者、恶鬼、梦游者、妖精。这多种角色集于一身,一面是“混合”无须
也无从“分割”,而另一面却恰恰又是“割裂”——主体性存在之撕裂与被撕裂、分离与被分离,主体的多重身份恰恰意味着没有身份。这种自我分裂,使存在主体迷失,深感被其所生存其间的“世界”放逐、遗弃而自我消失,其极致状态与情形足以使主体疯狂、崩溃,由此导致与世界的分裂成为必然。事实上,人与自我的分裂和人与世界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在“另一种境遇”里,“鸟”作为喻体出现,表征本体(主体、人)存在的生命自然属性,这是一个向度的意旨;如果我们结合第一种“境遇”里有关巫师、魔鬼“这些恐怖工程师”的“辉煌历史”与“荣誉”的言说内容,和此一“境遇”里“母性与父性”的相关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意旨的另一个向度,即“人”作为自然生命物种与作为文明生成“物种”,在其漫长的历史存在中始终伴随着自然基因与文化基因的冲突与融合,而在当下(现代)其“冲突”则成为人与自我、与世界分裂潜在而直接的动因。
当然,导致分裂的原因远远不止于此,要更为复杂、诡异、尖锐得多。因此,文本中“言说主体”一再从“角色”游离而出作为“写者”三番两次“站出来”说:“我急于找出这样的镜子来,“我必须要找出这样的镜子来”。而最终,就是这个“站出来”的“写者”也难以预料地被推出了“境遇”之外,与“我们”——读者、听着或看客——站在了一起,完全是一副“看客”的姿态,冷静到几近冷酷而又不无惊讶地自言自语:“就在这黄昏的第一种境遇里,镜子内外的杂耍者,忽然惺惺相惜起来。”“剧情”至此嘎然而止——在“黄昏”这面镜子的内外,被彻底分裂的“主体”——是“角色”、“言说主体”、“写者”,也是“看客”、“听者”、“读者”——成为“世界的杂
耍者”只余下相互间的“惺惺相惜”,惨淡、无奈、孤独、“自慰”、唏嘘……
“剧情”结束,而这最后一幕的定格,仿佛永远也不肯拉下帷幕——我们依然陷在章闻哲“黄昏的处境”里而难以脱身,象被这个“黄昏”漫天飞舞的雪花所笼罩围困一样,我们忽然感到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命运感所捆绑捕获。
也许我们的阅读是误读,尤其是这最后的一幕,它的内涵指向或许未必如此“消极”。站在“写者”的角度来考虑,文本结束句的“客观冷静”,或许正是面对存在“境遇”不可理喻现实的一把“解剖刀”或“匕首”,内敛集聚着理智的寒光。“惺惺相惜”或许正是超越了 “孤独”、“无奈”,“自慰”、“可怜”存在状态之后,激发潜在生命能量抗衡整个存在现实的肇始,亦即鲁迅所说的“绝望之希望”。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这个“舞台剧”是典型的现代剧,前后两幕所展开演绎的“境遇”,是现代人的存在“境遇”,“黄昏的处境”,即现代人的“存在处境”。我们陷入这个“黄昏的处境”, “世界”令我们充满疑惧,它的苍茫、虚无、孤独、痛苦,挣扎、无奈、可怜的绝望气息,或许就是存在主义者们所称的“地狱”(萨特)或“荒诞”(加缪),而我们所感受与意识到的难以言说的“命运感”,这“命运”,既是个体的,也是整体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当下的,按敬文东的说法就是——“我把这种隐匿、不动、抽象而又无条件地高居人类天宇的命运称作本体命运;本体命运恐怕正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问题”。[3]
章闻哲“黄昏的处境”呈现了这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问题,它所传达出的人在本体命运层次上的疑惧、茫然,并由此而
产生的人与自我、与世界分裂的虚无感、迷失感、可怜感,揭示了现代人存在“荒诞”的本质内涵。也就是说,在这一章散文诗里章闻哲(写者)通过文本的“虚拟现实”对现实存在或当下世界进行了解构和重新命名,文本“境遇”或整个“黄昏的处境”所传达出的荒诞感与对荒诞感的态度,显现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实质。但这个“黄昏的处境”,之于章闻哲散文诗整体文本对“世界”的解构、重构与命名而言,还仅仅只是开端(本文后面的章节将进一步探讨,再此按下不表)。就它对现代与现代本质的揭示、反思与批判而言,也还只是一个常识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与认识,对于章闻哲“黄昏的处境”,也许“镜子”才是关键词,才是文本超越常识性和普遍性问题与认识的秘密所在。
在文本呈现的“另一种境遇”中,前后出现三次关于“镜子”的陈述。上文已经提到这是“写者”从舞台剧“剧情角色”或文本“言说主体”游离而出的“陈述”,之所以用“陈述”,而不是“言说”或“演绎”,原因就在于这三次关于镜子内涵的文本表达是“写者”的旁白,是“写者”站出来“说话”,不是“角色”所说,也不是“言说主体”所说,至多是“言说主体”的一种“变声”或“变奏”。这三次的出现,从“急于”找出镜子到“必须”找出镜子再到最后找出镜子的超客观“冷静”,“陈述”的语气和语调前后明显有一个变化过程。语气和语调的变化显然意味着“主体”(言说者、写者)的内心变化,也就是说语气和语调的变化过程意味着就是内心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在文本阅读中或许及其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然而就是这个“变化过程”,章闻哲(写者)于文本中为我们留下了擦去“书写”之后依稀可辨的“痕迹”——“镜子”可以照亮“世界”,
它是隐匿存在的,寻找它是必须而刻不容缓的。
在章闻哲这里,“镜子”或许就是“房子打开十五度小口”所看到的半明半暗的幽冥“黄昏”,也或许就是为“看清”这个“黄昏的处境”而打开的“十五度的观测视角”。当然,也还可以是其它。如上文所述,“黄昏”的镜子,不仅让章闻哲(言说者、写者),也让我们(听着、读者)“看清”了一同生存其间的现实“世界”,人与自我、与世界分裂而深感“荒诞”的现代存在本质。但章闻哲的“镜子”,更确切地说是章闻哲所要寻找的“镜子”不止于这一层涵义。“看清”现实存在“处境”及其本质,这只是前提,换一句话说,就是已被“看清”的“世界”只是章闻哲(写者)要“解构”与“超越”的“世界”,而“找出镜子”,除了要于“分裂”的现实境遇中找到“缝合”的“自我”,即确定与确立“自我身份”之外,进而就是要找出“解构旧的世界”与“重构新的世界”的理由与办法,达成“新的世界”的“重构”与“创建”——这一点,其企图与愿望只要我们对章闻哲的散文诗整体文本稍作“观察”就不难发现。对于章闻哲(写者)在这一章散文诗,即《黄昏的处境》里的“镜子”,我们或可进一步做如下的文本解读:
“镜子”,“虚”与“实”的对应与对立,由此我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有关“事物”和“世界”的对应与对立——“现象/本质”、“物质/精神”、“肉体/灵魂”,“现实/虚构”、“遮蔽/敞开”、“说/听”、“写/读”等等。这个“镜子”,就像我们日常所使用的实物镜子一样,通过它我们看到了“自己”和“自己的另一面”,它是我们认识与把握“事物”与“世界”的一把“钥匙”。不过,作为认识的“道具”与认识方法它还只是通常
的一种比喻。在《黄昏的处境》这里,除了这一层意思外,更主要的是“镜子”作为“事物”与“世界”的“中介”,尤其是“主体”与“客体”发生关联的“中介”而存在的谕旨。
首先,体现于文本的“虚构”。文本的“虚拟现实”经由对“日常现实”的“提取”(提炼)而成为“文本现实”,这就是“虚构”,这个“虚构”就是找到“镜子”的办法,或者就是要找到的“镜子”本身——作为“中介”,经由“虚拟现实”联通“日常现实”与“文本现实”,打开“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联而实现“文本现实”的真实性。显然,作为“文本现实”,“言说主体”也经由“言说”此一“虚拟现实”(事境、情境)的过程,使“自我”与“世界”,即“主体”(人)与“客体”(世界)发生关联,同时,在此一过程中, “言说者”的“言说真实内涵”也正由于“虚拟现实”的“遮蔽”而恰恰“去蔽”,“言说”的真正涵义被豁然“敞开”,从“写”的角度而言,或许就如欧阳江河所指出的一样:“写,就是物在词中的涌现,持留,消失。写,在某处写着它自己根深蒂固的空白和无迹可寻,它擦去的刚好是它正在呈现的”[4]。
艺术创造的“魔镜”所指或许就是此一境况。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在“遮蔽”与“敞开”之间,“黄昏的处境”里确有一面这样的“魔镜”在其间隐匿与闪现,我们必须也只能和章闻哲(言说者、写者)一样把它“找出”。作为中介事物,“镜子”在这里显然还具备“通过”的能量,具有一种“桥梁”的性质与功能。这个“镜子”,之于哲学,或许就是从现象抵达本质的“桥梁”,之于宗教或信仰,或许就是从此岸到彼岸的“船度”,而于诗歌(包括所有艺术)就是想象的“翅膀”。虚构与
想象,成为诗歌艺术与诗人存在的唯一“法宝”或“魔杖”所言或许就是这个意思,而在章闻哲的散文诗文本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上述哲学、宗教、艺术三者“集于一体”的迹象,“镜子”对于章闻哲显然更为重要,正如上述其企图与愿望是要通过文本的创建而达成对“旧世界”的超越与“新世界”的重建。此其二。事实上,在这个文本中,章闻哲(写者)寻找的“镜子”还可以指向“写的”策略与技法,亦即她——“站在虚构的一边”与“不用思想而用物来说话”[5]这两个相互背离的诗学方案的合并之运用,以及语言象“灯”一样打开文本的“词与物”、“说与听”、“读与写”的闪烁光芒。“镜子”,成为章闻哲,也成为我们超越“黄昏的处境”从现实通往未来的飞行“魔毯,成为存在的全部理由。
行文至此,我们仅仅读了章闻哲的一章散文诗,正如企图从她为我们打开的这个“十五度角的小口”就看清“世界”全貌是不可能的一样,我们只在这一章作品中就指望洞悉其整体文本的奥秘也是不可能的,进而现在就要对其文本做出怎样的结论显然也为时过早。尽管这个“十五度的视角”确乎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某种景象,也体验和感受到了我们生存其间的当下现实的“现代”本质,并多少领略到了文本因其源起于现代主义实质与背景而所具有的散文诗的“现代性” 品质,同时,也见识了她的“镜子”所涵有的关于“现实与虚构——虚构与真实——存在与诗(艺术)”的“魔法”力量。因此,我们还只能小心翼翼地从这个“十五度角的小口”深入,以“窥探”章闻哲散文诗文本整座“房子”的堂奥秘密, 如果不被“谋杀”或掉入她布下的重重“陷阱”与“迷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