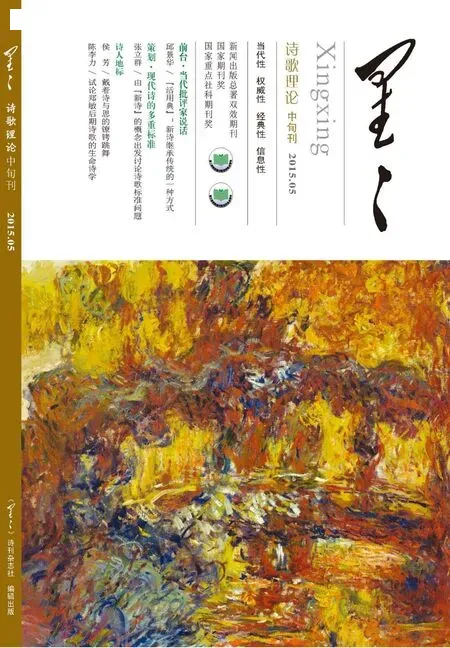试论郑敏后期诗歌的生命诗学
试论郑敏后期诗歌的生命诗学
陈李力
郑敏的《郑敏诗集1942-1947》是继冯至的《十四行集》之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又一部从不同角度展开对生活与生命沉思的诗集,它是一部生命的雕刻者之歌。无论是《灌足》中灵动的少女在浸着双足开始了她的梦,还是《村落的早春》中人们在经历过寒冬的坚忍、春天的迷惘、夏季的风雨后,村落终于恢复了往日的欢欣,并期待着更多“绿色希望的旗帜”[1];还是《荷花(观张大千氏画》中“承受了更多的生,这严肃的负担”[2]的荷花象征,我们都可以看到郑敏毫不吝惜对生命力的赞美,感受不同的生命形态之美以更好地关照生命的存在。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有若干对郑敏早期诗歌作生命角度进行论述的专论,如蒋登科《论郑敏早期诗歌中关于生命状态的思考》,从生与死、爱与恨、苦与乐、梦想与现实等几组矛盾为切入口解读郑敏的生命诗学;孙良好《不老的生命之歌——有关郑敏生存境况和研究现状的描述和梳理》,以一种新范式的综述角度对郑敏诗歌创作与生存境况结合起来考察郑敏生命之歌的由来与走向;孙其香《论郑敏的生命诗学》,从感悟生命、牵手死亡、领受寂寞与爱的乐章这四个主题全面勾勒郑敏诗歌的生
命诗学的体现,但惜对郑敏早期与后期的诗歌作品与诗歌理念的转变没有足够的重视。
诚如伍明春在《诗与思比邻而居——论郑敏1979年后的诗歌与诗论》中指出,“1979无疑可以作为一个确切的分解线”[3],这一年之后的郑敏沉积了三十年的时间,再出版了《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中采花》和《郑敏诗集》等诗集,在九叶诗人中创作年龄跨度最大,甚至这在整个中国诗坛都是不可多见,确可谓“常青藤”之称号。而对其这后期诗歌的研究除了上述伍明春外,还有谭桂林《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让郑敏以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张玉玲等从“不在之在”角度分析郑敏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里尔克、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后对人性、潜意识、欲望等的抒写;钱晓宇等以意象、艺术追求、忧世情怀等分析郑敏诗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而关于其后期诗歌的生命诗学之延续则尚未有专门的论述,笔者在此文中勉力一试。
一、对生命再度诗意的表达
郑敏后期写的第一首诗,《诗呵,我又找到了你》[4],虽说是在与九叶诗人唐祈等碰面受到他们的鼓励,再重新拿起放下了三十年时间的笔,但更多的恐怕是她又找到了用诗来表达生命的感觉。真正的诗人,只有触碰到了生命的旋律的时候,他才会写诗。西人华兹华斯说“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我国传统文论也有诗是“发乎情”而用以“言志”的论述,但若只是偶尔的感情的宣泄,比如一个热恋中的人用诗来表达一下他对恋人的爱慕
之情或者一个失恋中的人用诗来宣泄一下他的痛苦,而没有持久的捕捉关于自身生命的领悟继而坚持用诗的形式来表达,那恐怕与诗人这个身份还是相去甚远。世人都以为写诗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但实质上诗人的写诗是一件相当寂寞、煎熬的事情,是在对生命的生与死、爱与恨等各种领悟中的反复的煎熬,直至最后的解脱、升华,凝练成为一行一行有意味的文字。郑敏在西南联大刚接触写诗领域时,其导师冯至便告诫她,写诗是一件十分寂寞的事情。但她欣然前往,颠沛沉寂三十年后她再一次的欣然前往,她写道:
呵,我又找到你,我的爱人,泪珠满面,
……
我吻着你坟头的泥土,充满了欢喜。
让我的心变绿吧,我又找到了你,
哪里有绿色的春天,
哪儿就有你,
就在我们心里,你永远在我心里。
如有你在我身边,我将幸福地前去……
《诗呵,我又找到了你》
郑敏把诗比作她的爱人,她又再一次的找到了她的爱人,激动得泪珠满面。她的“爱人”是从坟头里刚爬出来的,但是却带有“绿色春天”这样充满生命力的象征,诗人有了她又将可以勇敢的幸福的前行,如其诗说,“没有水手依恋平静,/安全的平静是最危险的死亡,/充满危险的波涛才是生命,/我们离开海上的
蓬莱还很远,/可珍惜的不是静止,/而是季风中的波浪,好送我们到第二个童年,/历史的又一个黎明。”[5]309这里“常青藤”开出了她的第二春,找到了她的第二个童年,但却要去海面波涛上冲浪,只为那里有她所要追求的生命。她对生命表现出了使命般的执着,直到1995年还说,“对于生命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希望做一个强者。我觉得最可惜的,像冯至和卞之琳,实际上他们是很了不起的诗人,可是都在生命这个方面就自己封住了,所以再也写不出……我觉得做一个生命的强者对诗人是很重要的。在任何时候,如果你自己不同意,没有任何人能扼杀你的生命。”[6]
而在新时期郑敏关于生命的思考有几个母题是对她前期作品中所体现的延续,比如依然钟情描述死亡的《死亡第二次浪漫歌唱着》、《在死亡面前》、《在一个追悼会上》等,就直接以死亡为主题,通过描写死亡的形象、写死亡与生的抗争与转换,去抒发对生的渴求、对生命的珍惜。“死亡,一个美丽而忧郁的少女”、“她感到无限的宁静”、“她的奉献/像秋天的麦束在田野列队/欢送一个单纯的灵魂归去”,[7]死在诗人的笔下不是可怕的,甚至是一个温馨可人的形象,或者是一个“我比他要大的”“孪生兄弟”[8],又如她说,“在死的火里曾找到生,在生的火里遇见了死”[9]等等。这与前期的《死》、《人力车夫》中描述的生与死的两种生命状态的对抗,在主题上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意象的营造与感悟的方式上有所突破。郑敏对死亡描述的钟情,应是因其接受里尔克与海德格尔的西方哲学背景有关,与我国传统的“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同,与佛教追求来生的世界也不一样,西方传统文化对待生命而是一种
“向死而生”的态度。“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以向死存在的方式活着”,亦即以“有死”活或者“能死”的方式活着,人们不是一步步走向还在远处尚未到场的死亡,而是在我们的“走向”本身中死亡已经在场,因而面对人生,即是面对死亡,此死亡是带有触发人对生存的“尽责”的积极意义的。郑敏大概正是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在其作品中才出现这样大量的对死亡的描述,而这也正是她对生的思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又比如依然有对母爱的超越性的认识,郑敏在诗集序中说到很多新生代女作家“往往只倾向于女性在爱情、性、婚姻方面的自我解放,和‘女性个性’的挖掘充分表达,母爱这一主题却几乎被摒弃”[10],以为母爱几乎都带有缺乏反抗、缺乏觉醒的意味,但是“女性写作如果能再关心解除性禁锢、自由发挥女性者青春魅力之外还能探索像诺贝尔和平奖得者修女特丽莎那爱人类的境界和精神,和生活里一些默默无闻的单身母亲的母爱,就会达到更高层次。”[11]早在其早期诗歌如《金黄的稻束》中郑敏就表现出与一般女性主义者重视维权意识不一样,而是基于对对生命的自觉关注,站在生命的高度,讴歌母爱是仁爱、慈爱、宽恕,是人类思想之源头。新时期她又写到“孩子,我们是迁徙的像群,/走着,吃着,回想着,一条/没有尽头的路/默默中/寻找希望和平衡”[12],母亲对孩儿关爱是一辈子的忧戚与共;“你的耳里有新格兰的浪涛/我的耳里有北方白杨的呼啸/各自走向生或死的召唤”[13],母亲的胸脯不仅能把孩儿养育长大,也能任由他们鸟飞鱼跃;“在另一个云飞雨急的下午/我也曾在站在那黑色的海岸上/想像那远古的海盗帆船/时间曾将你这不幸的一代/劫走,迷失在昨天的雾里……也许梵高的彩舟在此浮现在雾中/载着
你和你的一代从绝望里航来”[14],是母亲对下一代的怜悯和期待。若果说郑敏在早期写到“自己的,和敌人的尸体/比邻地卧在地上/搭着手臂,压着肩膀”[15],所体现出的是超越敌我的、浓郁的人性光辉,那么这里所体现的则是超越男女的、具有人类共同母亲般的大爱,这也正显现出了郑敏对生命所思考的深度,不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诸如政治、身份等各种因素的羁虑,而是真正的回归本真之我。
二、对生命介入的沉思与体验
郑敏新时期的第一部诗集《寻觅集》里,可以明显看出她在刚开始重新写诗时的一段寻找的过程,“诗停止了,像一条僵蚕,/当它不再有透明的唾液/在它的体内呼喊,呼喊/要求你吐丝、写、写、写”[16],但是郑敏很快就找到了她的突破的方法。如果说郑敏早期诗歌对生与死的思考更多是从哲理上的思考,那走过半世纪风风雨雨的诗人,在后期则是以一种介入的沉思与体验进行。
其一,她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与及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不在之在”的接受,化为自己的“不再存在的存在”,她说,“诗,我追求/哲学,我在寻觅”[17]认为诗与哲学并非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是“在一个中有另一个的厚味”[18],从而更加明晰了其诗歌的哲学思考倾向。但她”不再存在的存在”该当作怎样的理解?于“存在”一词,海德格尔由始至终也并没有下过一个明晰的定义,其意义是在对“存在者”与“此在”的区分中凸显出来,可大体解读为人的生存状态及其意义;从海氏又把人
的生存区分为本真的生存和非本真的生存也可看出“存在”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的内涵。海氏所谓非本真的存在就是沉溺于日常生活中,遗忘了存在,遗忘了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与意义的反思与追问;而本真的生存就是站出来生存,不忘存在,牢牢记住存在,时时刻刻去存在,即走向存在、回归本真的生存。此正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郑敏虽把自己关于这一部分的诗歌标题为“不再存在的存在”,实际上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并不违背,郑敏正是要去追寻这“不再存在的存在”,其在观察西方人文价值的丧失后及我国80年代朦胧诗后的新生代对终极意义的抛弃,自感这关于生命意义的存在不再存在了,继而要以自己的方式去追寻回来,去呼吁人们再去关注这曾经存在过的存在。她在诗集序中说“不少荒诞先锋作品意识到人类在机会的戏弄前的无能的窘境,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接受荒诞。但一旦人们保持和已逝的存在联系,和它们的踪迹对话,这些不再存在的存在能使你充满无形的能,走出机遇、环境的灰暗,使荒诞如魔法破灭,而生活在新的维度中,变成拥有光亮的新空间的人,精神因而获得自由。”[19]因而她写道:
无限是无法看到的,然而
你意识到它的存在
它的光和引力是一张
看不见的网
一切都在其中
(《当你看到和想到》)
“不再存在的存在”,无法看到,也无以言说,但是却可以意识到,郑敏后期的诗作正是这样,通过沉思与体验,去捕捉这一张蕴含一切的网。
其二,郑敏在研究二战后美国的诗歌过程时开始了对潜意识的关注,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她“1985年后我的诗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我在重访美国以后,受到了那个国家的年轻的国民的气质的启发,意识到自己的原始的生命力受到超我的过分压制,已逃到无意识里去,于是我开始和它联系、交谈,因为原始的生命力是丰富的创造源泉,这样我就写了《心象组诗》,我竭力避免理性逻辑的干扰,而让积淀在我的无意识中的力量自己活跃起来,形成图象和幻象出现在我的心象。”[20]因而诗人在描写人的生命、人的欲望等时,所依赖的并非是行走的吟唱,通过不断的走访、体验而得,所描绘的也很少是人的行为、事件,乃是于生活中寻常的各种事物,加入敏锐的捕捉,继而通过沉思,由自己的潜意识去驱使语言的自动组织,开出一组一组烙下自己生命烙印的意象。其写《诗人与死》大型组诗时,每天两首,几乎都是不假思索而成,计划写二十首,但在准备写第二十首时“潜意识”不合作了,始终都写不出来,那诗人也不刻意苛求,即由其以十九首的面目面世。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郑敏在早期对生与死的追问还带有悲愤的情绪特征,那么在后期诗歌中则转化为成熟的沉思。如“走在冬天下午的林园里/枯枝用有力的黑色线条/将蓝空划碎/看到那遗忘了夏季鸟声的树林/想到的却是婆娑的林影/在看到和想到之间/人类延续着生的欲望”[21],甚至在《成熟的寂寞》中把这种沉思的寂寞直接宣布为只有寂寞才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
其三是与中国传统象数思维的结合,摸索出类似“体验”的方法。郑敏接受的解构主义其核心内容就在于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不同于结构主义寻找一个能够解读文本最终意义的恒定模式,而更关心可感的、外在的空间的符号所繁衍出的永无止境的意义。这样就给她在反思我国传统诗学时,与“天人合一”的象数思维结合的契机,得以用感性化直觉和感悟以把握世界,将日常的感性经验融入她理性的哲学思索中。此与狄尔泰论及诗与体验的关系说,即认为个体对自己的生存、对象世界和自然的关系的体验出发,把它转化为诗的创作的内在核心,所有这一切体验的主要内容是诗人对自己生命意义的反思,很切近,故而笔者在此用“体验”这一并不甚精确的词概括郑敏所逐渐摸索出来的创作倾向。这种体验的形式,让诗人得以“客我合一”,真正的实现了她诗与哲学的并驱, “在我的身体里有一张张得大大的嘴/它像一只在吼叫的雄狮”[22],然而诗人捕捉到的“不是光滑的鱼身/是变幻不定的心态”,[23]“寂静填满着空虚……生命的汇流,外在的、内在的/你,我,宇宙”[24],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在它的体内/被包围/抚爱/消化/吸收/她终于找到生命的燃点”[25],在沉思与体验中,自己的生命融于万物的生命,自己的心象化作自然的物象,又转化成为她笔下的意象。
三、对群体生命的历史反思
伟大的诗人总是能将自己的思考与领悟置于时代与历史的潮流之中,与整个生他养他的民族血浓于水,郑敏在前期作品中描
写的贫穷、困难、战争便是当时动荡不安的形势的写照,而在后期的作品中,诗人在经过“闷葫芦”的日子过后,应当是对当时的时代怀有期待和信心的,“只要山风一天吹过五岳,/我就在那里,陪伴着你……我的骨骼是石林,/我的心是天池,/我的思想是/武夷深处的浓雾”,[26]甚至模仿艾青说“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对历史的关注也有如:“曾经被雷鸣电闪照亮/用生命的十年读完/一部很荒诞的悲喜剧/所有错误都打击在/无知的空想的伤口/从此走上反思之旅。”[27]
但若说与生命的反思相关的,则是对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关注,首先有《骆驼的脚印——至一个不知疲倦的知识分子》,“驼铃断断续续/沙堆重重叠叠/正午的酷热燃烧着棕红的毛发/深夜的严寒让四肢抽疼”[28],中国知识分子最压抑最苦闷的时期大抵就是在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了,但是诗人还是从这严寒酷热中发现了他们的坚持,“淡漠的哲人,坚韧的学者/在那高尚的驼峰里,装满对困难的藐视,傲岸,自足,忠诚……脚印、脚印、脚印/地球不足月球/风沙终会将脚印淹没/但他相信/会有更多年轻的脚印、脚印、脚印”。[29]这里满溢了诗人对那时代还在坚韧的知识分子的崇敬。继而在影响很大的组诗《诗人与死》[30]中,诗人又对那时充满幻想、天真而又执着、忠诚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同情,并又开始与死对话。“我们焚烧了你的残余/然而那远远还不足/几千年的债务/倾家荡产,也许/还要烧去你的诗束/填满贪婪的焚尸炉”,被压抑着的人,同样还要被索取个不完;“那双疑虑的眼睛/总不愿承认黑暗”,“对春天信仰、虔诚而盲目”,充满热情但却太过于天真;终于“让一片仍装满生意的绿叶/被无意中顺手摘下丢进/路边的乱草水沟而消灭”;“人
间原来只是一条鸡肠/绕绕曲曲臭臭烘烘/塞满泥沙和掠来的不消化”,所谓理想也仅是不能消化的杂乱和粗糙;“我们都是火烈鸟/终生踩着赤色的火焰/穿过地狱,烧断了天桥/没有发出失去身份的呻吟”,悲哀的是“我们”整整的一代人。
虽然郑敏诗歌创作曾经沉寂了三十年,但不并不影响郑敏对生命本质的探索与追问,她的生命史也是一部诗歌史。在其诗歌创作生涯中,郑敏执著地追求生命与哲学的融合,这使她的诗歌充满了形而上的思辨色彩,可以看做是一曲深沉的生命冥思曲。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
[1] [2][4][5][9][15][16][22][23][24][25][26][28][29] 郑敏:《郑敏文集·诗歌卷(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第64页,第150页,第309页,第191页,第33页,第153页,第174页,第173页,第177页,第183页,第102页,第104页,第105页,
[3] 伍明春:《诗与思比邻而居——论郑敏1979年后的诗歌与诗论》,《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6] 徐丽松:《读郑敏的组诗〈诗人与死〉》,《诗探索》1996年第3期。
[7][8][10][11][12][13][14][17][18][19][21][27][30] 郑敏:《郑敏文集·诗歌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53页,第536页,第405页,第406页,第464页,第461,第465,第512页,第512页,第407页,第35页9,第621页,第387-399页。
[20] 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