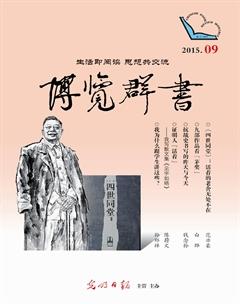证明人“活着”
陈蔚文
可以肯定,证明人“活着”这事的指标绝不仅是肉体的新陈代谢。在新陈代谢中,有知觉和灵息的参与,才可称为“活着”,否则只是生物性的一个过程,无异于稗草、蟾蜍或鼠类。
每个意识到自己“活着”的人,大概都有其自身的证明方式。有轰烈的,有安静的,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
看见或看不见,都是“存在”。尽管,看不见,往往不被承认。
总是有些强硬的标准横贯整个时代,比如我那一代的父母,或说“中国式父母”,有明确划一的养育观,说白了,考高分,进好大学,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人生,除此外是下角料的生活。我这种走神走得厉害的人,自然属“废料”。好处就是索性一意走神,丧志到底,在父母称作“闲书”的纸页里越走越远,迷途不返。
由此,发现一种标配外的“存在”。和具体参数无关,通向无垠,通向一次艰难的的目地论演变,通向不可穷尽。
“当我们呼吸正常时,并不认识到这是多么重要,而急促的呼吸降临身上,才想到呼吸是我们的命根,是所有正常生活的决定因素,将一种曾经认为是恒定的力量因而被永远忽略的东西忽然推到眼前,这就是所谓的存在。”
写,就是寻找“恒定因而被永远忽略的东西”的过程。它囊括世间的蝇营狗苟,生老病死,囊括了自我,成为探索自我并与自我互证的历程。
此前虽有无数雄椽巨笔录下过这些,可我的亲朋及邻居二大妈刘胖子没被录下;某条青春期的郊外公路没被录下;某次雾失楼台、某家消失的小食店、某块老厂区黑板上的手写告示没被录下;某个腊月凌晨,在上海东安路270号肿瘤医院的排队没被录下……
我的写,于是成立。
像穿过开往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神奇站台——在九号站牌与十号站牌间,看去两者中间什么也没有。有个胖女人告诉新生哈利波特,“别停下来,别害怕,照直往里冲,这很重要”,哈利弯腰趴在手推车上,向前猛冲,眼看离两站台之间的检票口栏杆越来越近——他已无法停步——手推车也失去了控制,他闭上眼睛准备撞上去——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继续朝前跑,睁开眼睛。一辆深红色蒸汽机车停靠在挤满旅客的站台旁。列车上挂的标牌写着:霍格沃茨特快,十一时。哈利回头一看,原来检票口的地方现在竟成了一条锻铁拱道,上边写着: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他成功了。
罗琳的这段描写,着实精彩!它打破了一道重要的隐形界限,将现实与魔幻结合,创造了和人类世界的列车并驾齐驱的另个世界。
那个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也可视作生活与文学间的镜子。当写作者受激情驱使,不停下,照直往里冲时,就冲进了生活的另个维度,与生活平行但更加深邃的内部。
人间万相,汤汤浊流,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个世间永是一个纷杳的实体。经由文学棱镜的映射,周尔复始的线性生活有了廓影、深度、体量和质感。
此外,文学的“晶化”使世俗有了另一向度的价值。即便最贫穷低贱者,如福楼拜《三故事》中的主人公费丽西蒂,一个虔笃的贫苦女佣,在文学里却有了属神的可能。这动人的庄严,惟有在物质客体世界以外的空间得以实现。
它还是时间本身。
“每一本书是所有的时间,所有的道路。它们排列,叠加,缠绕,交通,把你围拢在以书为墙的那间书房里,你在其中的命运无非是不知所云”,在图书馆连排的书架中,如入时间的迷宫。惶惑及疑问同时敲响:这世上,还缺你的这一份写吗?
同类的问题是:这世上的人够多了,数量比最宏大的图书馆的藏书还要多上许多,你还有必要活吗?你活着对人类会提供什么新意义?为什么你不怀疑这个呢?连闪念都不会,因为你从不是为世界与人类而活。你为自己,为需要你的人而活。
写亦然。我,可以是我们。我们,不一定是我。
文学将一粒米从米仓中辨认出。
尼采说,“你的真正的本质并非深藏在你里面,而是无比地高于你,至少高于你一向看作你的自我的那种东西。”
大概这就是写的理由,写,使你一次次地高过自我,翻过此前以为不能的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