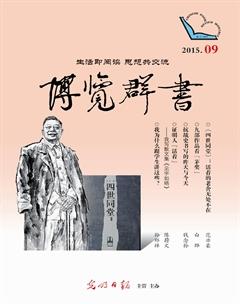1945年:老舍的奔走与奔忙
史宁
1945年,时年46岁的老舍依旧居住在重庆西北的小镇北碚。尽管当时身上还肩负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工作,但自1943年起,除特别重要的会议前往重庆外,老舍常年在此居住。
北碚虽距重庆不远,但相比重庆更加清净,适宜写作,老舍十分喜欢这里,于是从1943年一直住到抗战结束。此时的老舍,正在全力创作他的宏篇巨制《四世同堂》。
这部作品自1944年初开始写作,至当年11月10日,前34段以《惶惑》为名在《扫荡报》上开始连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希望此书“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进入1945年,他开始《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的写作。至当年的5月,第35段开始在重庆《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连载。然而,彼时的写作并非总是伴着安适平静的环境,时常被诸事所打扰。1月10日,“文协”作家骆宾基、江村二人因从事进步活动在酆都被国民党特务抓捕。重庆文艺界人士闻讯异常激愤,纷纷谴责当局的专制行为,“在高唱人身自由的时候,竟有如此事件发生,实使各界人士对中国民主政治大表遗憾。”“文协”总会除即电酆都县县长查明真相外,并积极设法营救。“文协”理事会特策议营救办法,决定推孙伏园等人向参政会、卫戍总部机关交涉,根据保障人身条例,使早日恢复自由。郭沫若、冯雪峰迅即联系邵力子,老舍则求助冯玉祥将军,跟有关当局拍案要人。最终在多方努力下,骆江二人在一个月后被释放。类似的营救,以往发生过多次,作为“文协”的总负责人,老舍每次总是在积极奔走,不是亲自去当局交涉,便是向政府高层的朋友求助。他视之为自己的工作职责,因而每每总是挺身而出,绝无退缩。
2月1日,老舍在《南风》杂志上发表了《今年的希望》一文。每年在公历新年或农历新年之际,老舍大都会写出类似“新年试笔”的文章,俨然成了他个人一种特有的习惯。在这篇文章中老舍写道:“去年写成的三十多万字,有三十万是《四世同堂》的,其余的是一些短文的。本来想把《四世同堂》写到五十万字,可是因为打摆子与头昏和心境欠佳,就打了个很大的折扣。今年,我希望能再继续写下去,而且要比去年写得多。”三天后,老舍的小女儿在北碚出生,这天刚好是立春节气,于是老舍为她取名为舒立。小女舒立出生在老舍生活最为贫苦困顿的时期,在喜悦之余,也为全家的生计又增添了负担。老舍后来在《八方风雨》的长文中写道:
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年初,因为生了个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头晕。春初,又打摆子。以前,头晕总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这病。
同一时期,老舍给好友王冶秋的信中写道:
年前立春日生一女娃,数夜未能安睡,故除夕前二日又患头晕。一歇又歇了一个月,近数日才勉强执笔,续写《四世同堂》。服了四剂中药(为省钱),头昏见好,只是药有轻泻之品,日来老拉肚子。
身体如此羸弱,缘于经济拮据造成的营养不良。老舍自1940年开始因贫血而导致头晕症,几乎每年都要犯一两次。一旦病倒,便只能静养不能继续写作。因此抗战时期的创作可谓是在贫病交加之下的苦写。然而如果仅仅是贫病造成的苦痛,自小生于贫民家庭的老舍早已习惯于此。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精神方面的困扰令其蒙垢。这就是1945年春天发生在重庆颇为轰动的黄金案丑闻。
3月底,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指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信托局以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从3月30日起把黄金价格由原来的每两2万元,提高为每两3.5万元。此政策的出台,无形中将当时流通的法币币值贬值了75%。孰料有人提前泄露了黄金涨价的消息,在28日当天,黄金出售的数目就猛增了1万多两。重庆的各大银行也事先得到了加价的消息,通宵办理起黄金储蓄业务。许多官僚、豪商和银行职员彼此心照不宣,大量抢购。次日,有报纸披露了黄金储蓄提价75%的消息后,舆论及各界人士纷纷指责财政部事前泄露消息,丑闻迅速轰动了整个重庆,并传遍了各地。4月19日,重庆一些报纸因“黄金案”发,登载了一批私购黄金者的名单,其中有“舒舍予等五户共一百五十两”云云。因而引起一些人对老舍的误解,甚而有人乘机中伤。其实,“黄金案”中的这个“舒舍予”与老舍无涉,而是另有其人。4月20日,我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首发专讯辟谣:“黄金案中的‘舒舍予’与老舍先生无关”,“老舍仍然在乡下过着穷作家的生活,靠着卖心血及衣服杂物维持全家衣食,与黄金案中之舒舍予其人,毫无关联之处。”尽管如此,因未能将报载舒舍予所系何人查证,始终无法打消人们对老舍的质疑。直到一年之后,这个所谓的舒舍予才终于浮出水面,乃是孔祥熙的二女儿为购买黄金而假冒的名字。但那时老舍已远离故土,假若他知道这个消息后,或许也只能报以一声苦笑。
5月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文化会堂举行会议,纪念“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文艺节。老舍与邵力子、郭沫若、茅盾、孙伏园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邵力子为主席。老舍在会上报告了会务,并且借机对恶意污蔑买黄金之事做了澄清,他说作家救济费宁可存在银行贬成不值一个钱,也决不买黄金。
8月15日,侵华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山城民众接连几天都在欢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然而老舍对此却并未发表任何文字。不过在稍后的重阳节,老舍曾与于右任、程潜等人一同到重庆上清寺登高赏花,归来后赋诗二首,从这两首颇具杜诗手笔的五律中人们似乎可以窥探抗战结束之际老舍复杂的内心:
干戈余痛在,菊酒不胜情。
风雨八年晦,贞邪一念明。
双江秋水阔,万树远烟平。
缓缓移帆影,思归白发生。
劫后逢重九,登高倍有情。
黄花连影瘦,霜叶入云明。
蜀道知艰苦,乡思系太平。
文章能换酒,笑傲遣余生。
(《乙酉重阳于程两诗翁招饮赋此述志并以致谢》)
几乎与此同时,老舍又一次被病痛压垮,同时患了痔疮和痢疾。在给王冶秋的信中他说:“前些日头昏,发痔,痾痢,倒好像要完蛋的样子。后来,痢先止,痔仍未全好,头昏依然,直到如今。我也是那样感觉——惨胜或无异于惨败也。”老舍另一位好友吴组缃在9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菽园带来老舍、李紫翔兄及盛光勤函。老舍贫血复发,又患痔病痢,有‘深盼死在这里免得再受罪’之语,竟阅,使人万分难过。”
抗战八年已将老舍的身体折磨消耗得虚弱不堪,且身心俱疲。获得抗战胜利的消息后,他很快给在山东的好友王统照写了封信,希望能在青岛替自己物色一所小房。老舍久想重新恢复战前自己在山东时期悠然有序的日子,远离政治生活与各种文艺论争,专心做职业写家。不过他的希望又一次落空。“按我的心意,‘文协’既是抗敌协会,理当以抗战始,以胜利终。进城,我想结束会务,宣布解散。朋友们可是一致的不肯使它关门。他们都愿意把‘抗敌’取销,成为永久的文艺协会。”(《八方风雨》)10月14日下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开理监事联席会,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自本月10日起,正式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会上通过了老舍起草的新会章,并且决定继续由他担任总务部主任,领导“文协”的日常工作。老舍对此也欣然接受,只要他人有需要,他总是最大可能地牺牲自我,毫无怨言,一如他为自己取的表字“舍予”一样。
11月12日,重庆《扫荡报》自孙中山八十寿辰日起更名为《和平日报》,老舍特为此撰《和平》一文。文中说:
为预防大的灾变,人与人之间需要和平。……和平应当是人与人之间的永久契约。……有了和平,人类的眼才会看到更远的地方,而且设法安然的走到那里去。……他的最大过错是打了几十年的内战,没有工夫去想更远大的问题。最近,他又打了八年的仗——这回,他没有过错,可是大大的伤了元气。现在,他的敌人已经失败,也比任何人更需要和平。和平会恢复他的健康,也会使他痛定思痛,去为自己与全人类想一想将来的问题,尽一点他对全人类应尽的责任。
尽管这只是为报纸改刊而作的应景文章,但其时正值国共两党重新对峙,内战一触即发的大背景下,老舍写此文的用意则十分明显。其后他在《在复旦大学“国父八十诞辰纪念晚会”上的讲演》《我说》等文章中都一再申明了类似的观点。
恰在此时,老舍接到来自美国国务院的信函,邀请他赴美讲学,为期一年。实际上,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费正清博士在此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老舍赴美讲学属于美国“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肇始于1940年。在1946年-1947年这批赴美知识分子的候选者中,除了已经入选的张孝骞、侯宝璋、赵九章等五位学者外还特意增加了三位文艺家,首先选定的便是老舍,除了《骆驼祥子》英译本在美国成为畅销书,作家本人在美国声名远播之外,还因为他是当时战后中国文艺界中间派的著名代表。11月28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女士亲自前往北碚拜访老舍并具体商讨落实赴美讲学一事。老舍经过权衡认为应邀赴美有几点益处。第一,可借此机会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抗战以来文艺活动取得的成就;第二,可以领略和学习美国先进的文化与技术,开阔视野;第三,有可能的条件下休养身心并腾出时间安心写作。于是老舍慨然应允,并开始着手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在出国前夕,老舍写了一组抗战回忆录《八方风雨》,全面回顾了自七七事变直到抗战胜利这八年来自己的生活与写作情况。在最后一节“望北平”的结尾,老舍做了一首名为《乡思》的七律诗。似乎是对自己亲历八年抗战的况味做了一番感慨和总结。
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
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
西风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羚角斜。
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
尽管思乡情重,但老舍毅然再次踏出了国门。1946年3月5日下午,老舍登上一艘名为“史各脱将军号”的美国运输船驶离上海港口,船上载运1650名美军士兵,另有美侨200余人,向地球另一半的大陆缓缓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