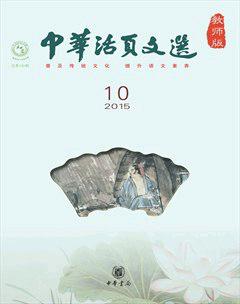唐诗中的重阳节
孙国锋
一、 重阳节
重阳节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据《西京杂记》中贾佩兰讲述九日习俗的记载来看,西汉初年即有此俗。曹丕《与钟繇九日送菊书》曰:“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见三国时的重阳会已颇有声势了。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桓景登高避难的传说,既确证也丰富了重阳节俗。
至于定名为重阳节,则是在唐代(之前只是泛称作九日,唐及以后各代,则重阳与九日并用,现代的九日已无专指之意)。宰相李泌提请确定上巳、中和、重阳为一年之三大节庆,获准。再加上唐皇室的亲自加入(九日游曲江),使得重阳节活动在唐及以后的时间里盛况空前。这一点,从王维“遍插茱萸”的诗句中可以得到佐证。
重阳节主要的活动是登高,这一活动的来源自然是桓景避难故事。而后来人们登高主要为赏秋。重阳的节俗还有野游、骑射(此活动唐代依然盛行)、放风筝、迎出嫁女归宁、食蓬饵、吃重阳糕、饮菊花酒、赏菊、插茱萸等。文人显贵还有“享宴高会”、相属赋诗的风雅。茱萸最初是切碎囊佩的,魏晋以后便演化为插了。先是“插茱萸于臂”,而后干脆插在发间鬓角。
唐宋以后,茱萸日少提起,只剩下簪菊了。起初只是文人显贵的风雅(如范成大《重阳不见菊》:“可怜短发空欹帽,欠了黄花一两枝”),明清时代的簪菊赏菊,几乎成了全民性的风尚。清代的《辇下岁时记》载:“九月宫掖间争插菊花,民俗尤甚。”
二、唐诗中的重阳节
如果把唐诗比作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大百科书,那么“重阳节”就是其中一个不菲的辞条。我们从古代节俗描写的角度来观照传统的“重阳节”。
登高。这是重阳节活动的重头戏,也是诗人们描写重阳之侧重。如李白《九日登巴陵望洞水景》:“九月天气清,登高无秋云”;刘禹锡《九日登高》:“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杜甫《九日》:“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以及《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登高的习俗起于醒桓景避难,而登高诗中用典最多的,是“孟嘉落帽”。孟嘉是陶渊明的外祖父,随桓温征西时,在龙山重九登高欢会,风落帽而不自知,后作“落帽赋”反倒获得在场文人及桓温的称赞。于是,《岁华纪丽》便把重阳节称作“授衣之节,落帽之辰”。后来人们更是不拘礼法,视“重阳落帽”为风雅之举,甚至有意模仿。诗中的表现如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明何孟春《送菊涯翁》:“多情不用防吹帽,短发犹禁插满头”。而能把菊花插满头的杜牧和梅尧臣,帽子自然是早就除去了的。
另一个文人津津乐道的典故来自孟嘉的外孙陶渊明。南朝宋檀道济《续晋阳秋》中记载,某年重阳日,幽居的陶渊明菊下独坐,无酒为伴 ,正惆怅间 ,忽见一白衣人自花间飘然至,原来是江州刺史王泓派人送酒来。陶渊明大喜,与白衣使畅饮而醉,作《九日闲居》一首。此即“白衣送酒”之典。
唐代的诗人们对“白衣送酒”这一富有浪漫色彩的故事情有独钟,直用、曲用,各尽机杼。李郢《重阳日》“愁里又闻清笛怨,望中难见白衣来”,李白也“因招白衣人,笑酌黄金菊”(《九日登山》),岑参在《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中叹息道:“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皇甫冉《重阳酬李观》更是毫不遮掩:“不见白衣送酒来,但令黄花自在开”。其他,如孟浩然的“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秋登蓝山寄张五》),崔国辅“九日陶家虽载酒,三年楚客已沾裳”(《九日》),崔曙“且欲近寻陶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无不飘溢着“白衣送酒”的芳菲。
且不管酒是送来的,还是家酿的,总之饮酒,特别是饮菊花酒,乃重阳节里不可缺少的内容。席间赋诗,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或许跟孟嘉祖孙的两篇诗文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簪菊、赏菊。这同诗中用上“白衣送酒”典故一样,簪菊赏菊似乎也使重阳活动充满了高雅意味。郑谷说:“王孙莫把比蓬蒿,九日枝枝近鬓毛”。重阳被称为菊花节、茱萸节,也证明了菊花在这节庆中的重要位置。
不过唐时茱萸也还在重阳节庆活动中风光着:王维告诉我们,那时的茱萸是深入人心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多愁善感的杜甫叹息道:“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李白、孟浩然也各自作出证明:“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宣州九日寄崔侍御》)、“茱萸正可佩,折取寄情亲”(《九日得新字》)。至于清代顾祖的“茱萸黄菊寻常事,此日催人易白头”(《甲辰九日感怀》),只能算作是对茱萸往日风采的一种缅怀了。
而真正长期活跃在重阳节庆活动中的是菊花。《仙书》云:“茱萸避邪,菊花延寿”。延寿比避邪更为实在,于是这“融融冶冶”的黄金花受到诗人们由衷的称颂。
杜牧:“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齐安登高》)。
郑谷:“更待金英发,凭君插一枝”(《恩门小谏雨中乞菊戴》)。
公乘亿:“带香飘绿绮,和酒上乌纠”(《赋得秋菊有佳色》)。
……
这些是簪菊诗(顺带在此一提:宋人杨万里有“嚼香”“蕊浮杯”的爱好),赏菊之诗更是不胜枚举。杜甫有“九日”诗十数首。写菊如:“庭前甘菊移时晚,青蕊重阳不堪摘”(《叹庭前甘菊花》),“采采黄金花,何由满衣袖”(《九日寄岑参》),“晚来高兴尽,摇荡菊花期”(《九日曲江》),于写菊之外,多有人世之叹、家国之忧。郑谷之爱菊,几乎可以和陶令相比了:“日日池边载酒行,黄昏犹自绕黄英。重阳过后频来此,甚觉多情胜无情”。杜牧对菊也别有深致:“雨中衣半湿,拥鼻自知心”。王勃因“开门有菊花”,而自翊“是陶家”(《九日》),可见他也是陶令的崇拜者、菊花的有情人。元稹及黄巢对重阳菊也各怀深情(详见下述)。
值得一提的是,重阳节不仅仅限于九月九日这一天,九月八日已算开始,而九月十日更被称作“小重阳”。李白《九月十日即事》就写道:“昨日登高罢,今朝又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三、唐重阳诗的内容与特色
重阳节诗人们喜咏菊,然而其表达方式和意义却有很大差别。
“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菊》)李义山通过菊的绚丽的颜色和幽香,又搬来陶罗二位助阵,为菊花唱了一首赞美诗。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菊花》)元稹好像在说:“是花都爱,不是偏爱菊”,但“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这满园的黄英、整日赏菊的举动,又实实在在地表明了元稹对菊的喜好。
“篱东菊径深,折得自孤吟。雨中衣半湿,拥鼻自知心。”(《折菊》)这折来的菊花简直成了杜牧倾诉衷肠的恋人了。“雨中衣半湿”,真是有了“爱相随”,“风雨我都不后悔”。“拥鼻自知心”,难道只是一种爱的表白吗?看来除了对菊花形态美的热爱,更有其精神方面的因素。
“王孙莫把比蓬蒿,九日枝枝近鬓毛。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菊》)郑谷则不仅限于对菊形态的赞美——先是通过“九日”里人们的普遍行为,暗示出菊花在人们心目中特殊而又崇高的地位,而后又以“不羡瓦松高”的拟人手法,更加体现出菊花“甘于平凡,执着奉献”的高贵品质。这大概就是作者之所以如此爱菊的根本原因吧。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第后赋菊》),“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于桃花一处开”(《咏菊花》),黄巢咏起菊来也透着一股冲劲,居然为“独立寒秋”的菊花抱起不平来,真是“爱菊爱得他心痛”!
我们不妨将这些诗与屈大夫的“夕餐秋菊之落英”、陶元亮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西风中”作一比较,不难看出,唐以前的咏菊诗,重在对孤傲清高(或说是孤芳自赏)品格的一种欣赏。表现了文人们不慕名利、淡泊宁静的心态,重视内心的自我认识。而唐代的咏菊诗,在积极用世的风气下,更多地体现了诗人们在功名的追逐中几番扑腾之后的复杂心境:有的顿悟离开旋涡;有的喘息未定又再度投入;有的欲进欲退彷徨不定。唐以后的咏菊诗,一方面体现了对屈、陶理想的向往,另一方面也因时代的动荡,菊花“独傲寒风,不畏强暴”的精神得到更多的宣扬。从以上的分析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管窥到咏菊传统在内容上的流变。
在文人喜欢四处流浪的唐代,重九望乡思乡也是重阳诗里的一大主题。这在唐以前似乎不很突出,唐以后的那些只懂得因循的文人们也不过有一些仿制品罢了。
“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这是初唐的人们在登高望乡,格调似乎明朗些,虽然也道出些“悲”“苦”,读来却不甚悲苦;倒是后来孤独的杜甫抱病登台,举杯望乡,让人不见“悲苦”字,却自有一番悲苦在心头。中晚唐的登高思乡缺少撼人之作,这或许也跟时代有关系。
不过唐代望乡思乡的经典之作,还得算少年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作者先以一个“独”字、两个“异”字,定下思乡的基调,而后又迂回一层,以一个“遥”字,既写出了远距离的相思之苦,又显示了以彼地写此地的独特视角(这一视角让我们想起李商隐《夜雨寄北》“巴山夜雨涨秋池”、杜甫《月夜》“遥怜小儿女”以及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想得家中夜深坐”),再通过“遍插”与“少一”的鲜明比照,尽现了“忆”的主题。怪不得人们在“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晚上,总要一年又一年不倦地唱起这首“倍思亲”的歌。
描写节令,借以抒怀,在古典诗歌中极为常见。本文只是对唐诗中的重阳节作了一些粗略的轮廓描摹,至于把重阳放在思想史、文化史的大范围中去观照,并且更加深切地探究其本质内涵与价值体现,则需另外论述了。
(选自《铁道师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