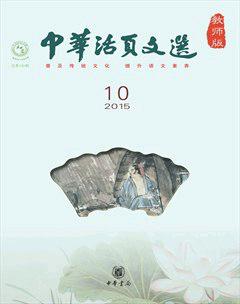书声灯影里的大师气韵
周庆安+谢志浩
没有人怀疑过,一百年来的清华园群星璀璨。人们在仰望百年群星的时候,常常只注意他们的光芒,而忽略他们的轨迹。其实光芒总会起自东方,而落于西天。只是他们在清华园里的日子,已经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永恒可见的轨道。
这里有四大导师徜徉于国学院,更有陈岱孙教经济,潘光旦讲社会,金岳霖、梁思成走马河山,悠游哲思与建筑,在教学之余做邻居,讲故事。教授们把小数点点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让天平左右均匀而美妙。正是在他们并不伟岸的身影下,有曹禺做剧于图书馆、钱钟书读史在课堂。有百年大师的厚德载物,才有雏凤亮清声,从此不一般。
杜威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所以清华园里道德的养成,师德的垂范,知识体系的形成,也都仰仗于这些耕读教书的长者。我们一直都说,中国的高等教育要脚踏实地,其实大师们就是高等教育的实地。他们就像清华园的土壤,酸碱适度,经风耐雨,长出中国现代化的从业者和实践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从基础学科开始,术业精深,成就斐然。但他们最大的成就,其实是他们留在清华园里的书声灯影。这里就是他们的生活,也就是教育的社会。在他们这里,伟大之路并非遥不可及,只不过你是否愿意付出和他们一样多。
拥有璀璨星光的,并非只有清华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上,大师成为一种无与伦比的财富。因为他们在教育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的人数并不算多,但是作品多、学生多,故事多。他们的历史价值,往往大于他们的当下境遇。这与我们头顶的星空何其相似。当我们看到光芒的时候,他们已悄然隐去。
招贤纳才
1924年,曹云祥校长大刀阔斧向“改大”迈进,而国学研究院的设立,在这位哈佛工商管理硕士看来,是“改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按照曹云祥的设计,有朝一日,清华“改大”成功,那么,国学研究院必然转型成为现代分科的研究所。这样,清华国学院,从一出生,便注定是“短寿”的,这也更增添了它自身的传奇色彩。
胡适作为清华“改大”的筹备顾问,曾被邀请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胡适十分谦虚地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胡适的建议,奠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态格局。遗憾的是,特立独行、具有魏晋风度的章太炎先生,哪怕自己开设国学学校,也断然不会担任导师。
谁是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合适人选呢?曹云祥校长也是动了一番心思的。最好是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理念,对梁任公、王国维具有理解和敬意的年轻学人。这样,主持《学衡》的吴宓,历史性地成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最佳人选。1924年尚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吴宓,得悉可以回到母校清华,自然是梦寐以求。于1925年2月5日抵达北京,当晚拜访老友袁同礼,次日上午便到了水木清华。
八年了,吴宓眼前的一切,竟是那样亲切。甜蜜之中也有一丝忧伤,见到马约翰先生,难免尴尬。1916年,原本应该与洪深、陈达一起赴美的吴宓,因为体育和体检不合格,推迟“放洋”。经过一年体育锻炼和配合治疗,1917年得以与挚友汤用彤一起“放洋”。
1918年从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转学至哈佛大学的吴宓,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吴宓与汤用彤共居一室,关系友善。1919年初,陈寅恪由欧洲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习巴利文、梵文。吴宓与陈寅恪特别投缘,课余时间彻夜长谈,乐而忘倦。陈寅恪见解精辟,妙语解颐,令吴宓佩服不已。1919年3月26日,两人结识不久,吴宓便在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吴宓来到清华,校方已经决定礼聘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而陈寅恪,则得益于吴宓的鼎力推荐。若吴宓与陈寅恪的人生轨迹未在哈佛交汇,国学研究院的历史,自是另一番景象。
鸿儒相聚
时光流转,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文化更新的速率加快了,思想界时刻添加着新鲜的血液。很有一帮“中国少年”,厌弃中国文化和传统,对于“国故”,既没有兴趣进行同情的了解,更欠缺温情的敬意。
中国的文艺复兴,具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创造新文化为中心,以解释中国何以为中国、欧美之所以为欧美作为两个基本点。也就是说,新文化的创造,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就要求,对待中国文化,应当具有理性和温情。
吴宓1921年回国之后,和朋友们一起创办《学衡》杂志,而王国维先生,是《学衡》有影响力的作者。吴宓在见王国维先生之前,就已经心意相通。如果没有这点因缘,1925年2月13日,吴宓持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到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寓所,就是给王国维跪下来,也未必能打动老先生。
话说回来,吴宓并没给王国维下跪,而是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王国维老先生,这位末代皇帝的南书房行走,后来心情愉快地来到清华园,并于4月18日搬到清华园,居住在西院十八号。清华曾有意聘请王国维担任国学研究院院长,老先生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坚决不肯。
梁启超与清华,也有着殊胜的因缘。1914年,老先生倦游政界,曾在清华工字厅赁屋著述,名曰“还读轩”。当年11月5日,梁启超应邀发表题为《君子》的演讲,勉励清华学子作中流砥柱,出膺大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能够成为清华校训,得益于梁任公的这次演讲。任公与清华的渊源实在深厚,他的两个儿子梁思成、梁思永,都是清华毕业生。吴宓在拜谒王国维十天之后,1925年2月22日,前往天津饮冰室,拜访梁启超。任公愉快地接受了礼聘,并在北院二号居住。
赵元任是第三位报到的导师。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哈佛大学具有深厚渊源,吴宓、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都是哈佛大学校友。赵元任属于最具有文艺复兴风味的人物。1910年,赵元任作为游美学务处第二届幼年生,与竺可桢、胡适赴美游学,可谓清华“史前期”的学友。1920年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回到清华任教,曾任罗素翻译。“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新娘是杨步伟医生,好友胡适乃证婚人之一,这对“新人物之新式婚姻”,轰动一时。1925年6月8日,赵元任到京,次日,梅贻琦、张彭春接赵元任一家到清华园,住在南院一号。
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第四位报到的导师,直到1926年8月,这位夫子才姗姗来迟,寓所与好友赵元任挨着——南院二号。8月28日,赵元任夫妇陪同陈寅恪进城,购置家具。赵夫人古道热肠,陈寅恪多在赵元任家吃饭,而陈寅恪则把自己住房的一半出让给赵元任搁书。陈氏1928年结婚之后,两家形成通家之好。
清华主事者对国学的理解很是开阔,否则,不会聘请赵元任这位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更不会聘任李济这位哈佛人类学博士担任国学研究院的特约讲师。
大幕已经拉开,国学研究院的先生和学友们,元气淋漓、大气磅礴地演绎着一出绝唱。
名师高徒
蓝文徵曰:国学研究院,自成立至结束,历时仅四年,虽似昙花一现,但其逸事佳话,却最耐人回忆。
1925年3月,国学研究院刊出招生广告。4月23日,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商定招生试题。8月1日,公布新生录取名单。9月9日,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
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发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的演讲,指出研究院的性质为,“研究高深学术”“注重个人指导”。与此相匹配,研究院导师的工作,分为“专门指导”和“普通演讲”。
王国维指导经学、小学、上古史和中国文学,梁启超指导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陈寅恪指导年代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等,赵元任指导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李济指导中国人种考。
清华园花木扶疏,宛如世外桃源,国学研究院,让人不自觉地联想起古代的书院。梁启超在1925年9月9日下午的茶话会上,热情奔放地做了“旧日书院之情形”的演讲,引起学友强烈共鸣。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第一级学友,共计三十三名,刘盼遂、杨鸿烈等十位学友,考取研究院之前,已经有著述;学友多属于性情温厚、酷嗜学问之辈。国学研究院有着师生的良好互动,浓厚的学术氛围,学友之间,情同兄弟,亲如手足。可以想见,经过耆学硕儒的点拨,名师出高徒,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研究院1929届毕业生蓝文徵,在《清华校友通讯》发表《谈陈寅恪》,深有感触地说:“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
国学研究院仅存四年,四届只有74名毕业生,绝大多数没有辜负导师的良苦用心,成长为文史大家。
师生情深
国学研究院学友,除了接受专门指导,还要听先生进行普通演讲。1925年9月14日,王国维开讲《古史新证》,是为普通演讲的第一课。老先生言辞恳切,“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1926年,姜亮夫经过补录考试,进入国学研究院,一丝不苟,刻苦用功。除了李济的课听不进去,其它课程,姜亮夫都听得津津有味,难以忘怀。王国维讲课,非常细腻,也不大看同学们。冷静的头脑、平和的性格、浓厚的感情,是先生所独具的风格。
梁启超讲课,姜亮夫觉得最受益。梁启超讲解,从多角度打量先秦典籍,并且给予总结。
陈寅恪广博深邃的学问,一度让姜亮夫异常苦恼,无论如何追赶,陈先生的学问也是望尘莫及。陈先生最大的特点,是每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
赵元任讲课的材料,往往都是生活中的方言,这让姜亮夫知晓描写语言学和声韵考古学的区别与联系。赵元任引起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兴趣,使他最终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当时,清华每周都有一个同乐会,师生一起联欢。唱戏、唱歌、背书、讲笑话,都是国学研究院师生的业余消遣。
梁启超和王国维两位先生讲课都很严肃,但是,同乐会的即兴表演,令学友们耳目一新。有一回,任公先生背诵一段《桃花扇》,而静安先生则背诵《两京赋》。
最能解颐的则是赵元任,把大家的茶杯收去,调正音调,用茶杯演奏一曲,四座皆惊。有一回赵元任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出发,然后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广州、上海,各地方言惟妙惟肖。1938年先生去国外,用纯正的英语讲课,竟有人打探,是否伦敦人?
陈寅恪在同乐会这种场合,从不肯为大家说笑。其实私下谈话中,别具一种幽默。先生曾给国学研究院学友们说,你们太厉害了,“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令人拍案叫绝。
留下传奇
国学研究院学友们,多有国学根底,大多数人是冲着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先生去的。真正理解和体悟赵元任和李济两位先生学问的,并不多见。那时,在一般人心目中,赵元任的描写语言学和李济的考古学,与传统“国学”不大搭界。这样两位先生的学生,其实寥寥无几。
王力的导师是梁启超、赵元任。梁任公对王力的毕业论文评价很高,但是,赵元任却很严厉,并指出“言有易,言无难”,这令王力非常受用。王力日后赴法国留学,并进行语言学研究。而李济只有一位弟子———吴金鼎,就是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者。
赵元任和李济,学问的作业方式,与梁启超、王国维迥然不同。他们一学期上课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奔走于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回到北京,赵元任不是和刘半农、钱玄同等朋友聚谈,就是进行歌曲创作。《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这时期的杰作。
1926年2月至3月,李济在山西汾河流域做田野调查,染上伤寒。李家老爷子听信庸医,病情危殆,侠义心肠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自作主张”将李济紧急送往协和医院,可以说挽救了李济的性命。从此,赵元任和李济成为通家之好。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自沉;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1928年底,李济在广州晤傅斯年,答应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兼考古组主任,赵元任担任语言组主任,两位先生从此离开了清华园;而陈寅恪则留在清华担任历史系与中文系合聘教授。
1929年,风云际会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落下帷幕。
1929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国学研究院师生集资,在工字厅东南土坡下,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梁思成设计碑式,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
纪念碑文开头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之句,既是对王国维先生的褒扬,也是对清华国学研究院“院格”的真实写照。
(选自《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