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感性与历史理性的超验呈现
——莫言《丰乳肥臀》的现代性气质
赵蕾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0000)
身体感性与历史理性的超验呈现
——莫言《丰乳肥臀》的现代性气质
赵蕾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0000)
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实现了两方面的共同书写,一方面是身体感性,将女性“身体”作为现代性文化隐喻,呈现出现实性与永恒性交织共存的“现代性”文化网络;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历史、文化等人类共同的经验关照和生命承当意识,追问社会变革时期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困境,钩沉历史的存在图景,并实现了女性主体由内在性向超越性的转变。两方面的书写体现出一种同时具备身体感性与历史理性的现代性气质,并以男性视角下的“超验话语”超越日常生活表象,反观男性经验世界,复归性别本体。
《丰乳肥臀》;身体感性;历史理性;现代性
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囊括了北方大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与人间百态。其重要突破在于它实现了两个方面的共同书写,一方面是身体感性,将“身体”作为民族社会中具有现代性的文化隐喻;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历史、文化等人类共同的经验关照和生命承当意识,并通过书写女性实现了女性主体由内在性向超越性的转变。整部小说以男性视角下的超验话语为其主要的语言形式,既强调情感、肉身的感性质感,又实现了向至高理念世界的升华,呈现出文学作品的现代性气质。
一、“身体”作为现代性文化隐喻
乔以钢借鉴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身体”与“主体”互换理论,认为“身体是一种在基本物质形式(肉体)下具有自我感知、体验和思考能力,同时以某种自性(identity)触摸现实、感悟历史、凝视未来,表达内在与外在、表象与本质、自我和他者多维关系的集合体”[1]62-63。在这里,“身体”与外部世界的内在同构关系使它被高度抽象化,纳入了逻各斯二元对立的传统,进而成为文化的塑造物和衍生体。
在《丰乳肥臀》中,丰乳肥臀是上官家女人的光荣传统,以母亲上官鲁氏为代表的女性身体,成为上官金童一生中感知自我和认识世界的媒介和方式。“丰乳”和“肥臀”是生命得以生成、呵护和滋养的象征,是纯净无私的母爱的象征,母亲的一对乳房是时刻召唤金童去占有的强大力量,是他幸福快乐的源泉,是他的一切精神寄托与情感归宿。同时,上官金童对母亲乳房的过度贪恋使之成为一种母性崇拜,女性乳房被高度神圣化,成了庄严、神秘、不可侵犯的权威,“我渴望着跪在全世界的美丽乳房面前,做他们最忠实的儿子”[2]126。在上官金童心里,乳房是爱,是诗,是高远的天空和丰厚的大地,是骚动的生命和澎湃的激情,是倾注于他所有情感并甘愿在它面前低到尘埃里的精神载体。乳房就是他圣洁的爱人。
女性乳房不单单作为描写对象,它更多是作为连接整个物质世界的媒介、成为文化的塑造物和衍生体而存在,贯穿于文本所反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动荡风云。在人物所经历的人生各个时期,乳房都是一种独特而意义深远的存在。对尚在襁褓中的金童来说,母亲的乳房是“丰满的宝葫芦”,是“两只欢快的白鸽”,使他爱不释手,那是和平年代女性身体的温润与柔美;抗日战争来临,母亲遭遇轮奸,双乳惨遭蹂躏,金童认为“真正的好乳房是永远毁坏不了的,它们像某种人永远年轻,它们像大松树郁郁葱葱”[3]54,乳房被寄予了战争年代永不衰竭的品质与力量;母亲倾注于全部身心的儿女长大后却回报给母亲伤害与痛苦,因为大姐的私奔,母亲的衰老从乳房开始,出现了难以消却的皱纹,金童从此改变对母亲乳房肆无忌惮的态度,开始珍惜和养护它们,岁月和经历终究会在母亲身上留下痕迹,但也赋予母亲最朴实无华的睿智;金童长大后,母亲尝试给他断奶,金童把对母亲乳房的依恋转移到其他女人身上,逐渐地乳房对他而言已不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更重要的是寻求心灵归宿;经历过十五年劳改后,金童更是把对乳房的执念向纵深处延展,在他眼里整个天地万物都成了由乳房连接起的存在,“把一切都归结到乳房上,用乳房把整个物质世界串连起来,这就是精神病患者上官金童最自由也是最偏执的精神”[4]326;80年代,金童成了乳罩店的老板,乳房在现代文明的畸形趋势下被推上了无以复加的至尊地位,成为世界的本原,对乳房的关爱程度更是成为衡量一个时期内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现代文明的盲目推进给乳房罩上了虚伪做作的物质性外衣,泯灭了女性身体原本的纯净美好;在小说结尾,金童躺在母亲的坟墓前,眼前飘来飘去着一个个宛如精灵般的乳房,美好至极,他放弃了一生中都在试图捕捉它们的努力,只是幸福地注视,“天上有宝,日月星辰;人间有宝,丰乳肥臀”[5]400,也许这时金童才明白,星空只能仰望,触不可及,他应该做的只是落脚于大地而已。
约翰·奥尼尔认为:“人类首先是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以此出发,他们由身体的结构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会以及动物的种属类别。”“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6]17。在《丰乳肥臀》中,以乳房为代表的女性身体作为符号,象征着近一个世纪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并最终指向一个有关身体的文化隐喻结构——在身体“肉身性”的背后,是现实性与永恒性、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共存的“现代性”文化网络,是一种新的思考和感受历史价值的方式。在从文化的角度去反思和批判历史时,把女性身体作为文化发展与历史转折的重要契机,从而实现对文化传统和历史规律的顺从或叛逆。永恒不变的是富于润泽的乳房,变化的是历史岁月中每一个转瞬即逝的现时独特性打在乳房上的烙印,从而反射出一个个充实的现时存在图景。
二、钩沉历史的存在图景
作为新历史小说,《丰乳肥臀》试图还原历史的原生态。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人物不是对一个活人的模拟,他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7]42,32。在这个意义上,叙述者上官金童荒诞病态的一生和上官一家的生活境遇呈现了自1938年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土改、“反右”斗争、“文革”直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对人类内在生存情状的洞幽烛微,由此对社会变革时期人类的生存意义、生存困境等问题进行思索。以上官一家作为现代性空间的一个延展,上升为历史理性。
上官金童是上官鲁氏与马洛亚牧师所生的中西混血儿,他的出生伴随着日军入侵高密东北乡,小说主要以他的视角展现了动荡的社会变革中上官一家经历的逃难、饥荒、批斗、劳改等艰难的生存境遇。上官金童空有俊俏的外表和清醒的头脑,却无做事的能力和气魄,一辈子掉在女人的奶头上,窝囊胆怯,碌碌无为。“反右”运动中金童因“奸尸罪”被判刑十五年,改革开放后刑满释放,新时代的社会大潮仍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因懦弱的本性一次次被女人欺骗和利用,最后只得装疯卖傻,毫无尊严地活着。小说对人物的无意识心理和对人物欲望真挚而做作的袒露,使上官金童的一生展现了动荡变革的历史岁月赋予每一个经历着它的人内心中一个不愿面对的自我——反射出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眼前是令人迷惘又振奋的当下,骚动不安却无路可走,明辨是非却无力反驳,想确立自身的存在却到头来毫无归属感,最终只能沦为被社会和时代所抛弃的行动上的瘸子,精神上的侏儒,生与死、光与暗、爱与苦,都是如此接近。在这个意义上,动荡的社会现实中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上官金童。
上官鲁氏的其他女儿后代贯穿于中国20世纪的民间势力和权力高层,展现了社会变革时期不同阶层人的生存困境。上官家女儿的命运多以悲剧告终,四姐想弟回乡后遭到反右分子丧失人性的“展览式”批斗,精神失常、旧病复发而死;五姐盼弟在文革中被一辈子追随的革命所捉弄,不堪重负地自杀;七姐求弟在反右斗争中的农场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劳动改造,用性换取食物,因饥饿暴食而死;八姐玉女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忍母亲在农场用自己的胃袋储存食物、回家再倾吐出来以给儿女喂食的艰辛,为减轻母亲负担投河自尽。上官家女儿的命运影射出时代的风貌,建国后相继而来的土改、“反右”斗争和“文革”并没有帮助人民逃脱战争的苦难,而是带来离自己更近的身心折磨,带给这些无辜的民间女性不堪的命运和结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也不是吹遍人间的各个角落,普通百姓没有洗雪掉宿命般的苦难,权力高层也没有享受到精神上的幸福。来弟之子鹦鹉韩借助改革的浪潮与妻子开办东方鸟类中心,借贷政府巨额财产却最终破产,后被判刑;盼弟之女鲁胜利改革开放后担任大栏市市长,权力的喧嚣孕育出越发贪婪的人性,因贪污受贿被判死刑;司马库之子司马粮在土改运动中被迫出走,后成为巨商,改革开放后回乡投资,纸醉金迷的生活仍未带给他精神上的富足。由此隐喻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曲折与艰辛,也隐含着作者的潜在追问,社会变革时代人类的生存意义是什么?生存价值在哪里?翻天覆地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困境,社会各个阶层各色人等仍无法找到自己准确的角色定位,无法在自己存在的社会中有所作为,实现自我价值。作者由此钩沉出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图景,刻画出一个个“实验性的自我”真实的生存境遇,呈现出一个高高在上、可以任意摆布我们的历史现代性。
三、女性主体的“超越性”存在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认为一切生存都同时是超越性和内在性,男性将两者成功地综合在一起,但女性却往往被禁锢在内在性之中,丧失了超越性,“男人总是把女人看作既定的内在性”,“她不是主体、超越性、创造力,而是满载流体的客体”[8]230。而在《丰乳肥臀》中,作者笔下的女性挣脱了内在性对女性传统角色的束缚,尤其是以上官鲁氏为代表的母亲形象呈现出作为女性主体的“超越性”存在。
上官鲁氏虽不如婆婆上官吕氏以绝对霸权统治整个家庭的刚烈与硬气,却蕴蓄着更多具有“超越性”的母性本质和女性气质。婚姻剥夺了上官鲁氏的一切生理和心理满足,否认了她的自由和生育能力,所以将她导向通奸,她与除没有生育能力的丈夫之外的其他八个男人生下了八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上官鲁氏以最朴实、无私、坚韧的母爱本性在艰难的历史岁月中抚育着她的儿女,成为儿女生命的载体,忍受着世间所有强加于她的磨难,越是痛苦越是咬着牙坚持活下去。她的伟大不在于她的隐忍,而在于她以强大的内心进行抵抗,始终以积极勇敢的心态面对天灾、人祸和死亡。她的“丰乳”和“肥臀”顺从月相变化的节奏,岁月先是使之成熟,然后使之损伤,她在这肉体中感受到这种抵抗。在战争期间逃难的途中历经艰险,风餐露宿,她以羸弱的身躯拖着儿女的生命,在遍布尸体的荒芜之地尽力为儿女创造一片温暖的栖息地,透露出历经人世沧桑后的坦然与练达。她以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滋养着儿女,始终对儿女们怀抱希望,不愿他们过逆来顺受的生活,而是要经历有骨气有担当的人生,“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我要看到我的后代儿孙浮上水来那一天,你们都要给我争气!”[9]228上官鲁氏告诉儿女的每一个道理,都是最朴素的真理,她的一生虽忍辱负重,却始终在用她的“强”去爱儿女,而不是用她的“弱”,她要她的儿女子孙“活着”,而不是“不死”。在这个意义上,这位忍受了人间一切苦难的母亲,也同时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对女性自身内在性的超越。
与同时期女性文学中多以“性征话语”、“自闭话语”实现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对现实的隐性关照不同,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多使用“超验话语”,即在男性视角(有时是作为男性窥视者的视角)下超越日常生活表象,反观男性经验世界与复归性别本体的特殊表达方式,呈现出拨开现实的重重迷雾后最原始的生命感受和最本真的生存状态,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富于润泽、力量与奇异神采;一系列充溢着性征的越轨笔调和对“丰乳”、“肥臀”的露骨描写实现了对性别本体的回归以及对人真实欲望的正视与彰显。女性主义者普兰·德·拉巴尔曾说:“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而莫言的小说不护男人的短,
不藏男人的拙,呈现出的是最接近生命本真状态的男人和女人。
[1]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3][4][5][9]莫言.丰乳肥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2013.
[6](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1999.
[7](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2.
[8](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Ⅰ[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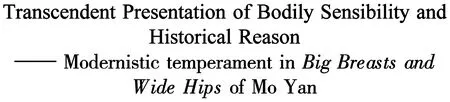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史素芬)
Zhao Lei
(Faculty of Arts,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400000)
I247
A
1673-2014(2015)06-0045-04
2015—07—26
赵蕾(1992—),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