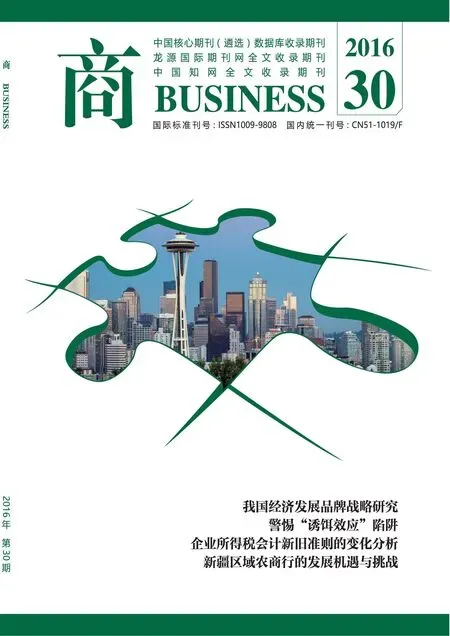亚当·斯密“自制”美德解读
郑铮
摘 要: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将审慎、仁慈、正义、自制作为人类的四大美德,并视“自制”为其他三种美德践行的保障。“自制”的本义就是抑制过度的激情,保持内心平静,情绪镇定,维护社会和谐。“自制”的主要对象有两类:一是恐惧和愤怒等;二是舒适、享乐和赞扬等。“自制”的目标是寻求合宜性。所谓合宜性就是将激情控制在一个合理且为人们所能接受的程度,以取得他人的理解和同情。“自制”是德性完美和德性合宜所必需的一种美德,是引导他人践行其他美德的保障。
关键词:美德;自制;激情;合宜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凭借在《国富论》中对自由市场理论的贡献与对重商主义的批判被人们尊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在这本书中对于人类“自利”本性的描述为日后西方经济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理性经济人假设。如果仅就此便认定斯密主张的就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利己主义,或许有些片面。因为与此同时,斯密还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他将审慎、仁慈、正义、自制作为人类的四大美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自制”这一德性尤为重视,并将其视为其他三种德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因此,对斯密“自制”德性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把握斯密的理论体系。
一、“自制”的本义及其主要对象
斯密认为“人自己的激情非常容易把他引入歧途——这些激情又是促使他、有时诱引他去违反他在清醒冷静时赞成的一切原则。”[1](P308)由此看来,人们仅仅做到审慎、仁慈、正义还不足以达到品性上的完美。在此之上,还需要做到对自身过度激情的控制,才能保证这些美德得以顺利践行。可见,斯密所强调的自我控制,其本义就是要人们在过度的激情面前,克制情绪,保持镇定,使内心达到平静与镇定,维护社会和谐以便更好的践行其他美德。
那么,什么样的激情是需要克制的呢?斯密借用前人的观点,根据抑制这些激情难易程度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那些“要求作出相当大的自我控制的努力来抑制的激情、甚至是片刻的激情”[1](P308),主要是指恐惧与愤怒等。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人类对于生存与繁衍的渴望被视为人性的起点,也是支配人类活动的自然动机。他写道:“……因而,自卫、种的繁衍就成为造物主在构造一切动物的过程中似乎已经确定的重要目的。人类被赋予一种对那两个目的的欲望和一种对同二者相反的东西的厌恶;被赋予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一种对死亡的害怕;被赋予一种对种的延续和永存的欲望和一种对种的灭绝的想法的厌恶。”[1](P95)人类之所以恐惧多数是因为对于生命可能遭受伤害的本能反应,对于恐惧的抑制也就显得极为不易,因此斯密给予对恐惧的抑制以最高的评价。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正是由于他们或是为了自己的祖国、或是为了崇高的目标与理想,能够在紧要关头克服人类本能反应的桎梏,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因而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爱戴。
相比较对恐惧的抑制,对愤怒的抑制或许显得不是那么崇高。斯密强调了对于宽容这一品质的赞扬。他认为,固然有时对于十恶不赦之人及其行为的愤恨是合理的,然而若是能将愤怒转化为宽容,似乎更能得到他人的钦佩。“在许多场合,宽恕这种高尚的品质,甚或比最合宜的愤恨更为优越。”[1](P312)此外,对于愤恨这一激情的抑制并非总源于人们主觀上有意识的自我控制,有时也可能源于恐惧。针对这一种情况,斯密认为“动机的卑微消除了这种抑制的一切高尚性质。”[1](P312),也就是说,如果因为恐惧得原本的愤怒得以消退,那么这样的行为不仅不该得到赞扬,反而应受到鄙视与嘲笑。
当对恐惧与愤恨的克制被美德所驱使,致力于正义的事业之时,这种品质无疑是伟大的。它不仅保证了其他美德得以顺利的转化为实践,而且“自制”美德其自身也显示出其独具的魅力,因而为人称道。不幸的是,斯密也注意到,“自制”这一品质有时也会被坏人利用,去行使一些不义之事。例如那些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老谋深算极具城府政客等等,这些人所具有的“自制”品质可能会使其行为变得更加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密看来,尽管“自制”如果被不当的利用会产生负面效果,当然这些负面效果会引起人们的厌恶与批判,但就这些人所具有的“自制”这一品质本身来说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自我控制仍是一种伟大和值得尊敬的力量。”[1](P13)另一类需要克制的激情,主要指的是“容易在转瞬间、甚或在较短时间内加以仰止的激情”[1](P308)如舒适、享乐、赞扬等。这一类的激情较之恐惧与愤恨要显得平淡很多,对它们的抑制也比较容易,但这丝毫不影响抑制这类激情的价值,人们对其仍然会给予较高的评价。“……这种优美和优雅,虽然不那么光彩夺目,但是,其令人喜爱的程度并不总是低于英雄、政治家、议员的显赫行为所伴有的那种优美和优雅。”[1](P315)对于此类激情的控制,由于其本身所显示出的朴素与平淡,因而也就不用担心会被用于不良的目的,所以对于这种激情的抑制总会使人感到愉悦。“对不很强烈的和狂暴的激情的抑制,似乎更不容易被滥用到任何有害目的上去。节制、庄重、谨慎和适度,总是可爱的,而且不大可能被用于任何有害目的。”[1](P314)
二、自制的目标——对合宜性的追寻
不同于理性主义对于人类激情的轻蔑与排斥,亚当·斯密作为一名情感主义者,他并不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激情,而是要将激情控制在一个合理且为人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即合宜性。他认为,“同情”是我们每个人天生所具有的天性,“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和同情……”[1](P1)我们每个人在同情他人同时,也渴望得到他人对我们的情感的赞同,并“把同伴们同自己情感的一致看作是最大的赞赏”[1](P11)。这种来自他人的同情能够使我们在情绪上感到愉悦,正因如此,为了得到他人对我们的同情,进而使彼此的情感达到一致,我们就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行为,尽可能地让他人接受我们,也正是“自制”所要达到的目标。
斯密认为,“自我控制的美德在大多数场合主要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一种原则——合宜感,对想象中的这个公正的旁观者的情感的尊重——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1](P343)由此可以推论,斯密所提出的“自制”,其实质就是使自身情感与行为达到“合宜”程度。在《道德情操论》中,“合宜”无疑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一个重要概念,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与情感达到“合宜”的标准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与同情。“在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同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情绪完全一致时,它在后者看来必然是正确而又合宜的,并且符合他们的客观对象。”[1](P14)对于一些情感来说,不足比过分更容易使人感到不快,这类的情感的合宜度一般较高;而另一些激情,人们希望的反而是不足而非过分,这类激情的合宜性一般较低。“前者是旁观者最乐于表示同情的激情,后者是旁观者最不想表示同情的激情。”[1](P315)
在斯密看来,那些由肉体产生的各种激情,即那种人类对于肉体快感毫不掩饰的自然欲望,例如过度的食欲、放纵的性欲等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合宜的。斯密明确表示:“我们对肉体所产生的各种欲望所抱有的反感;对这些欲望的一切强烈的表示都是令人恶心和讨厌的。”[1](P30)因此,对于贪图舒适享乐、追求肉体快感之行为的节制就变得非常重要,也恰恰是由于这一点,自制显现出其作为一种美德的价值。“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为节制的美德存在于对那些肉体欲望的控制之中。”[1](P30)此外,人们对于肉体可能遭受伤害所显示出的恐惧以及其他过度的反应也被斯密认定为不合宜的肉体激情,除非遇到真正关系到生命的危险,否则对于他人可能遭受的肉体痛苦,人们并不会予以同情。面对肉体的痛苦,只有做到克制与冷静才能达到合宜的标准。“我们对肉体的痛苦并不感到同情,是忍受痛苦是坚韧和忍耐克制的合宜性的基础。”[1](P33)
而对于那些愤怒、憎恨、嫉妒、怨恨等不友好的激情来说,由于旁观者所感受到的激情远远达不到当事人本身对于该激情所持有的激烈程度,因而也很难得到他人的同情,所以这类情绪也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虽然斯密也承认,憎恨与愤怒的激情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过度的软弱反而会被人视为懦弱;“但这些激情本身仍存在一些令人不快的东西,这些东西使它们在另外一些人身上的表现成为我们嫌恶的自然对象”。[1](P40)人们的想象通常根据客观对象的所产生的直接效果而非间接效果。例如,人们会为皇宫的华丽而感到愉悦,但忽视了其更为长期的效果。因此,只有在事情十分严重以致如不恼怒就会被人视为懦弱的情况下,愤恨才会被接受,这也就是不友好的激情的限度。斯密强调,“我们应当根据愤恨的合宜性的意念、根据人类期待和要求于我们的意念而愤怒,而不是因为自己感受到那种令人不快的激烈的激情而愤怒。”[1](P44)因而“宽宏大量或对自己维持社会地位和尊严的关心,是唯一能使这种令人不快的激情的表现高尚起来的动机。”[1](P44)与此相反,对于那些宽宏、人道、善良、怜悯、相互之间的友谊和尊重这类积极向上的正面情感,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博得他人的好感,拥有较高的合宜性,即使有所过度人们一般也不会介意。这是因为“旁观者对感到那些激情的人的同情,同他对成为这些激情对象的人的关心完全一致。”[1](P45)
由此可以得知,斯密之所以强调要抑制上述那两类激情,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激情的合宜度较低,很难得到他人认可与同情;但同时这些激情的产生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又是不可避免的。“自制”就是使這些激情达到合宜的程度,让他人能够广泛的接受。当然,克服人类的本能反应的这一过程是相当不易的,有时还必须需要超常的毅力与意志才能办到,也正因如此,“自制”被斯密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美德。
综上所述,自制是德性完美和德性合宜所必须的一种美德,其实质是对合宜性的准确把握和正确践行,引导人们更好地实现其他美德。
三、对曼德维尔“自私”恶德不可抑制的批判
在《道德情操论》第七卷中,斯密借对曼德维尔“自私”恶德论的批判,进一步阐述了其包括“自制”在内的美德理论,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澄清。
曼德维尔认为,人类自私的恶德最终导致了社会的繁荣。他将社会比作一群蜜蜂,其中有无数的蜜蜂都充满着贪婪与欲望,正是由于这样的激情,驱动着每只蜜蜂辛勤的劳作,整个蜂群才得以强生壮大繁荣。对于人类那些自私的激情是不能被消灭的,人类一切行为都是出于利己之心,或是受到虚荣心的驱使,对于激情的抑制,也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私利与自我满足。
斯密针对曼德维尔的观点,提出了三点不同的意见。第一,斯密对于如何定义“虚荣”,的含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那种想做出光荣和崇高行为的欲望,那种想使自己成为尊重和赞同的合宜对象的欲望,不能恰当地叫做虚荣。甚至那种对于名符其实的声望和名誉的爱好,那种想获得人们对于自己身上真正可贵的品质的尊敬的欲望,也不应该成为虚荣。”[1](P407)斯密不仅不把这两种行为定义为“虚荣”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可贵的美德。“前一种是对美德的爱好,是人类天性中最高尚和最美好的激情。后一种是对真实的荣誉的爱好,这无疑是一种比前者低一级的激情。但它的高尚程度仅次于前者。”[1](P407)而只有那种为获得自己不配得到的称赞、喝彩而哗众取宠、自吹自擂之人才能称之为虚荣。这样的激情当然是不能得到他人同情的,因此应当进行“克制”,尽力避免。
第二,斯密反对曼德维尔那种先将一切激情都视为是恶的,进而推论出人类不可能抑制自身的激情,“自制”不仅不可能反而是有害的,社会的利益依靠的是个人的劣行等错误观点。如上所述,斯密并不对激情予以完全的反对,而是主张不能将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激情混为一谈。他主张根据“合宜性”这一标准对于激情进行具体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应当对某一种激情进行抑制。“合宜的程度,即公正的旁观者所赞成的任何激情的程度,是因激情的不同而不同。”[1](P315)那些积极向上的感情容易得到旁观者普遍同情,因而合宜度较高,比如仁爱、仁慈、天伦之情、友谊、尊敬等;反之,愤怒、憎恨、嫉妒、怨恨、仇恨等这种感情则合宜度较低。我们可以看到,合宜度较高的情感往往是人们乐于见到的,对人类社会来说也是利大于弊,所以根本就不用进行抑制,有的甚至还应进行提倡;而对于那些合宜度较低的激情,则对人类社会通常是有害的,因此需要人们努力去克制。
第三,斯密认为,人们的对于过度激情的抑制、对于美德的追寻,不仅仅是为了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从而获得外界的赞扬与称赞;对于一个良知尚存的人来说,其行为除了要达到他人的认同之外,还必须接受自我内在良心的审视。我们不仅要做到让他人感到“合宜”,还必须使自我内心感到“合宜”。“合宜”在斯密这里既是他律,也是自律。对于真正美德的热爱与对荣誉的热爱虽有一些雷同,但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是十分巨大和明显的。对于后者而言,其“总是在根据人类天性所能想象的那種最崇高的和最神圣的动机采取行动。”即使他的行为可能遭受他人的误解,甚至是轻视与仇恨,但其依然不感到羞辱。因为,他的行为符合其良心的标准,他相信人们如果能真正了解他,一定会赞同他的行为。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三卷中,区分了“赞扬”与“责备”、“应当责备”与“应当赞扬”这两组概念,前一组代表了他人对我们的实际评价,而后者是我们对自身经过良心审视后的自我评价。在斯密看来,仅靠前者是不足够的,这充其量只能成为我们对自身行为评估所遵循的第一个标准。“虽然人以这种方式变为人类的直接审判员,但这只是在第一审时才有效”[1](P158),更高的一个标准则是依据我们的良心,即公正的旁观者。“最终的判决还要求助于高级法庭,求助于他们自己良心的法庭,求助于那个假设的公正的和无所不知的旁观者的法庭。”[1](P158)一个坚强且高尚的人,必定时刻以公正的旁观者的角度、运用自我内在的良心对自身行为进行审视,并根据自我控制的满意程度来界定自身行为的正误。
四、结语
我们通过解读斯密关于“自制”美德的论述,可以看到,斯密在主张自由市场学说,肯定人性自利的同时,对于社会道德的状况同样给予高度的重视。他以人类所共有的“同情”,渴望他人“情感共鸣”的本性为基础,建立了一套以“合宜”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强调道德的他律性的基础上,更为重视道德的自律性,并提出了“公正的旁观者”这一概念。我想,斯密之所以对美德如此强调,正是由于他看到一个自由的市场是离不开道德保障的,一个没有道德约束的社会是无法维持的,而谨慎、仁慈、正义、自制这些美德对于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关注亚当·斯密经济学观点的同时,不应忽视其伦理学的见解,这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忽视任何一部分都是片面的,甚至会造成曲解或误解,从而产生负面影响。(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 约瑟夫·克罗普西著.邓文正译.国体与经体:对亚当·斯密原理的进一步思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 罗卫东.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