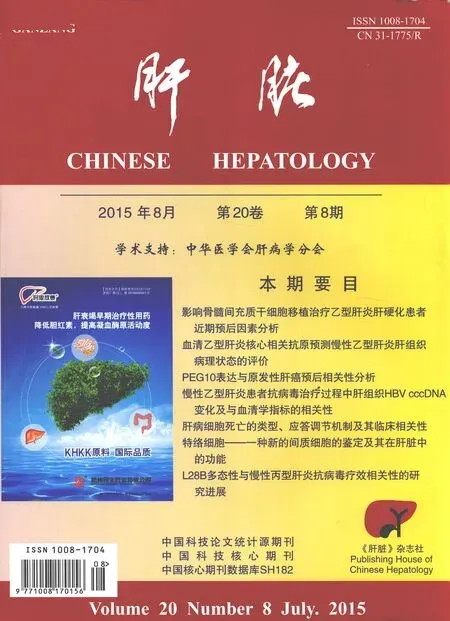肝病细胞死亡的类型、应答调节机制及其临床相关性
王英杰 于乐成
·热点论坛·
肝病细胞死亡的类型、应答调节机制及其临床相关性
王英杰 于乐成
健康肝脏的肝细胞死亡(HCD)有助于保持细胞丢失和补充之间的严密平衡,控制器官的自稳。正常肝脏绝大多数肝细胞处于 G0期,其更新率很低,任意时间内仅约0.05%的肝细胞通过凋亡被清除,且主要发生在3区。但当大量肝细胞死亡和肝功能严重受损时,肝脏可表现出快速而强大的再生能力,以避免肝脏主要功能丧失。肝脏对细胞死亡的反应,包括提供细胞外基质以保持肝脏机械结构的稳定性,触发肝细胞再生以修复功能性肝实质,其首要作用乃是保持肝脏的结构和功能。但在威胁生命的急性损伤作用下,细胞死亡反应变得不可控制,成为肝病进展的关键触发因素,促使肝纤维化、肝硬化及HCC的发生[1]。
HCD几乎见于所有类型的人类肝病,是反映病毒性肝病、中毒性肝病、代谢性肝病和自身免疫性肝病等的敏感指标。不同肝病的HCD模式有显著不同。凋亡(apoptosis)、坏死(necrosis)和坏死性凋亡(nacroptosis)等不同的细胞死亡模式可触发特定的细胞死亡应答,并通过多种不同的机制促进肝病进展[1]。本文在介绍各种细胞死亡模式、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和特定细胞死亡应答促进肝病进展的分子机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HCD对多种肝病进程的影响以及细胞死亡通路作为肝病治疗靶标的可能性。
一、肝脏细胞死亡的类型及其调节
细胞死亡的发生不仅是细胞对理化和有害因素的被动反应,也可由宿主通过程序性细胞死亡(PCD)主动诱发。PCD在发育和机体的自稳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直接参与对嗜肝病毒等病原体的防御,是阻止恶性转化的一个关键机制。
传统上公认有两种迥然不同的细胞死亡形式:其一是细胞凋亡(apoptosis),介导PCD,由特定的级联放大信号主动诱导,具有高度的可控性;其二是细胞坏死(necrosis),是细胞的意外死亡形式。新近发现PCD也可激发一种特殊的细胞坏死形式,称之为坏死性凋亡(necroptosis)[2]。多种细胞死亡模式的调控性质不仅影响人们对潜在病理生理学机制的认识,也提示对于细胞死亡不能作为经典治疗方法靶标的疾病,有可能针对细胞死亡的调控机制进行干预(图1)[1]。
(一)坏死
坏死被看做是理化应激未经调节的主要后果,以线粒体损伤、ATP耗竭和随后的ATP依赖性离子泵衰竭为特征。这将导致细胞和细胞器迅速肿胀,伴膜泡形成,最终出现细胞破裂,此即所谓细胞胀亡(oncosis)[3]。细胞内成分随后溢出至细胞外环境,诱发明显的炎症反应,导致坏死,这是一种免疫原性细胞死亡形式[3,4](图1)。
新近发现坏死也涉及调节性因素,包括线粒体事件。线粒体通透性转换(MPT)导致线粒体微孔开放,渗透压力改变,触发线粒体肿胀和氧化磷酸化解偶联。坏死通路的调节(调节性坏死,regulatednecrosis)与细胞死亡的相关性可由能抑制肝细胞坏死的药物得到显示:靶向于MPT主要促发因子的亲环素(cyclophilin),或靶向于c-Jun-N末端激酶(JNK)等线粒体下游介质的药物。此外,缺乏ATP可能会使凋亡转变为继发性坏死,这种情况被称为“坏死样凋亡(necraptosis)”或“凋亡样坏死(aponecrosis)”[5],以区别于“坏死性凋亡(necroptosis)”。因此,在ALD和NAFLD等相关肝病,坏死、凋亡和坏死性凋亡等多种细胞死亡形式普遍存在,且很可能是同时存在[1]。新近有关肾脏缺血/再灌注的研究显示,调节性坏死(regulatednecrosis)和坏死性凋亡(nercoptosis)的抑制剂具有叠加效应,显示了上述发现与治疗的相关性。
伴有细胞死亡过程的疾病,例如对乙酰氨基酚(APAP)诱导的肝损伤和缺血/再灌注损伤,以往认为其细胞死亡主要是非调节性坏死(unregulatednecrosis),但现在发现该过程可被MPT抑制剂(环孢霉素A)或JNK抑制剂所调控,提示调节性坏死在这些疾病状态下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坏死调节通路数据的增多,新的问题是单纯细胞坏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使肝病进展。
(二)凋亡
与坏死相比,凋亡是一个高度可控的生化过程。这个过程由一系列被称为半胱天冬酶(caspases)的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的协调活动来实现,将细胞及其组分最终分解为碎片(图1)。因此,凋亡在形态学上与坏死明显不同,典型特征是细胞固缩、核浓缩和碎裂。凋亡是病毒性、胆汁淤积性、脂肪性及酒精性肝病的一个常见特征。在病毒性肝炎肝组织切片中,凋亡表现为易见的特征性嗜酸性小体(councilman body)。
由于凋亡细胞迅速被清除,通常认为凋亡不引起炎症或仅引起轻度炎症。这是因为凋亡可激活表达于凋亡小体的磷脂酰丝氨酸等吞噬信号,促进吞噬细胞对凋亡细胞的吞噬作用,从而阻止细胞内容物外漏。而凋亡细胞泄漏的少量促炎介质,如趋化因子、ATP、三磷酸尿苷及鞘氨醇磷酸酯介质等,可能是吞噬细胞能有效侦测到凋亡细胞所需的重要信号;被激活的Caspases也能处理细胞内容物,减轻其引起炎症的能力[6]。

图1 肝病时的细胞死亡形式
在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者,由于凋亡是肝细胞死亡的主要形式,因此其血清 ALT水平正常或轻微升高,尽管肝炎仍在持续进展[1]。另一方面,当有更多肝细胞凋亡时,血清ALT水平将会升高。这支持如下假设,要么是因为吞噬细胞对凋亡肝细胞的吞噬已经饱和或吞噬速度不够导致凋亡肝细胞漏出一些较高水平的细胞内容物,要么是一部分肝细胞并不因单纯凋亡而死亡。因此,肝细胞凋亡可能并非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惰性过程,而是有可能促成肝炎、肝纤维化和HCC。
根据触发事件是细胞内在性还是细胞外在性,凋亡通路可分为各自独立的内在性和外在性通路(图1)。内在性通路一般通过B细胞淋巴瘤2(Bcl2)家族触发凋亡,而该家族可控制线粒体外膜的透化作用、细胞色素C的释放及随后的Caspases激活。内质网应激(ERS)和p53活化等数种细胞内凋亡触发因素能激活这一通路。ERS通常是内质网中非折叠和错误折叠蛋白堆积的结果,导致所谓的非折叠蛋白反应(UPS)。轻度ERS具有细胞保护作用,而严重或持久的ERS将通过激活JNK和HOP以促进细胞死亡。例如,在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ERS增强可诱导细胞死亡和疾病进展。病毒感染通常也会诱导ERS,例如HCV在体外培养和感染者体内均可触发ERS。游离脂肪酸在体内外均可诱导肝细胞发生ERS,并触发一种称为脂性凋亡(lipoapoptosis)的内在性细胞死亡通路[7];但这种脂性凋亡一般主要经由JNK活化介导,呈ERS非依赖性模式[1]。p53是内在性细胞内死亡通路的另一重要调节因子,也是持续运转的细胞命运程序的中心组分,这种程序决定了细胞是选择启动DNA损伤的修复还是由凋亡介导其死亡。作为对癌基因激活、DNA损伤和衰老的应答,p53被活化,并且主要是通过Bax等特定靶基因的转录调节来诱发凋亡。当损伤不太严重时,p53通过p21等靶标诱导细胞周期停滞,从而允许进行细胞修复。p53的功能也因此被喻为“基因组卫士”,可防止肝细胞发生恶性转化。HCC一般是通过获得p53基因突变来逃避这种控制机制。
外在性细胞死亡通路一般是由肿瘤坏死因子(TNF)家族成员的死亡受体配体所触发,包括TNF自身、Fas配体(Fas L)和TNF相关性凋亡诱导性配体(TRAIL)。肝细胞表达高水平的死亡受体,可能是为了能有效清除被嗜肝病毒感染的肝细胞。死亡受体介导的细胞凋亡是多种肝病的一个主要特征。拮抗Fas的抗体既能迅速触发鼠类和人类肝细胞的凋亡,也能导致小鼠发生急性肝衰竭(ALF)和死亡,这突出表明肝细胞对死亡受体诱导的细胞死亡具有高度敏感性。在肝脏,外在性和内在性信号通路是关联的,因为肝细胞作为“2型细胞”,需要通过线粒体扩增来执行细胞死亡,而线粒体扩增需要借助由细胞色素C释放所介导的Caspase-3的活化(图2)。
TNF和Fas L介导的细胞死亡共享信号转导通路中的许多组分,例如在受体寡聚化诱导的Caspase-8募集之后形成的死亡诱导性信号复合物(death-inducing signalingcomplex,DISC),可导致执行死亡的Caspases活化(图2)。但Fas活化的结果是肝细胞死亡,而TNFR的活化可影响多种细胞应答,不仅包括细胞死亡,也包括细胞存活、炎症和增殖[1]。核因子κB(NF-κB)是一种重要的细胞保护通路,可上调Bclxl和c-FLIP等抗凋亡基因,阻断JNK持续活化,而JNK是TNF诱导细胞死亡的一个重要通路。持续的JNK活化可被NF-κB依赖性抗氧化蛋白,如铁蛋白和超氧化物歧化酶2(SOD2)的上调所阻断。抑制NF-κB可揭示由TNF所诱导的、由活化的JNK和一种被称为Sab(SH3BP5)的线粒体外膜蛋白相互作用所介导的线粒体氧化应激自我放大通路。这一通路支持着JNK的活化,从而导致cFLIP降解,抗凋亡的Bcl-2家族成员的抑制,以及促凋亡Bcl-2家族成员的活化(图2)。因此,TNF介导的细胞死亡需要对NF-κB或其靶基因的抑制,并可被JNK的抑制所阻断。JNK也可促进保护性应答,例如肝细胞增殖和肝脏再生。

图2 死亡受体所介导的细胞毒性和细胞保护性通路的活化
TNF信号的双重特性,以及抗凋亡和促炎信号相对于诱导细胞死亡的优势性已在多种疾病模型中得到证明。单独注射TNF或脂多糖(LPS)并不引起显著肝损伤。但条件性删除肝细胞的Nemo、Tak1、Caspase-8抑制剂c-Flip(NF-κB靶基因),或IKKα和IKKβ,从而阻断NF-κB的作用,或以D-氨基半乳糖抑制肝细胞转录,均可促使肝细胞对TNF诱导的凋亡敏感和发生肝衰竭。
(三)坏死性凋亡
凋亡的概念及其能够被NF-κB所阻断,似足可解释TNF如何介导肝脏细胞死亡。但近年有证据显示存在第三种细胞死亡形式,即整合了坏死(necrosis)和凋亡(apoptosis)双重特点的坏死性凋亡(necroptosis),这一重要认知的转变对上述传统概念提出了重大挑战。坏死性凋亡和凋亡的上游分子机制是相同的(图2)[8],这支持如下假说:在凋亡被抑制的情况下(例如被表达抗凋亡基因的病毒所抑制),坏死性凋亡是一个能保证细胞死亡的备用通路[1]。虽然坏死性凋亡与凋亡共用上游介质,但其最终结果却是细胞和细胞器肿胀引起的细胞渗漏(图1)。坏死性凋亡在TNF介导的细胞死亡中最为典型,而TNF介导的细胞死亡不仅与多种类型的肝病高度相关,而且也可见于缺血再灌注损伤等其他的情况。
死亡受体的活化究竟是诱导凋亡还是坏死性凋亡,这取决于2种激酶:受体相互作用蛋白(RIP)1和3。活化的caspase-8可裂解RIP1和 RIP3,促使平衡偏向凋亡;而抑制caspase-8则有利于RIP1和RIP3复合物组装,形成“坏死体(necrosome)”,成为坏死性凋亡信号的关键转导子[2]。坏死体活化导致坏死性凋亡的具体分子机制尚存在争议。混合谱系激酶结构域样蛋白(mixed lineage kinase domain-like protein,MLKL)是坏死性凋亡的一个关键介质。有证据显示,MLKL可通过线粒体靶点增加线粒体活性氧基团(ROS)的产生。新近研究表明,MLKL可触发细胞毒性钙离子和钠离子内流,而这需要MLKL易位至胞浆膜。
侦测坏死性凋亡以便判断其在人类疾病中的作用的方法刚刚开始发展;在动物模型和药物诱导性肝损伤(DILI)患者中,磷酸化MLKL可能是坏死性凋亡的一个潜在标志物[9]。迄今为止,关于坏死性凋亡在肝病的作用及对其机制的了解,大多数资料乃是来自小鼠研究。有趣的是,相对于肺脏和脾脏,RIP3在健康小鼠的肝脏仅有微弱表达;但在对坏死性凋亡敏感的细胞(例如敲除caspase-8),RIP3的水平是上调的。以牛痘病毒感染小鼠,可诱导其肝脏组装RIP1/RIP3复合物,提示坏死性凋亡是抗病毒应答的一个组分[10]。在APAP中毒和长期喂饲酒精后,RIP3缺乏的小鼠其肝细胞死亡是减少的,提示坏死性凋亡参与了这些疾病的发病过程。虽然RIP3的缺乏可抑制坏死性凋亡,但在早期阶段应用坏死抑制素1(necrostatin-1)阻断RIP1,或MLKL缺乏,均可减少细胞死亡;而RIP3的缺乏并不能在24h内取消APAP诱导的肝损伤。因此,可能有其他通路促使细胞死亡或弥补了RIP3的缺乏[1]。最后,应用肝脏特异性Tak1缺失的小鼠模型(一种慢性肝损伤模型)研究显示,RIP3介导的坏死性凋亡和Caspase-8介导的凋亡作用相左。在这一模型中,Tak1和Caspase-8联合缺失的小鼠的坏死性凋亡与肝细胞和胆管上皮细胞的低增殖相关,这减少了HCC和胆汁淤积的发生。相反,凋亡与肝细胞高度增殖和HCC发生相关,而与胆汁淤积无关[11]。肝细胞中坏死性凋亡和凋亡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与在其他器官中所见是类似的;肝细胞缺失Caspase-8的小鼠所发生的由RIP3介导的自发性肝损伤进一步突出显示了这种关系[1,11]。
(四)自噬和细胞死亡
自噬(autophagy)是细胞通过溶酶体对细胞内不同成分进行的分解代谢,既是清除细胞内无功能组分的一大机制,也是能量的来源[12]。自噬被认为是一种细胞保护性通路,可防止酒精性肝病(ALD)、TNF诱导的肝损伤、APAP诱导的肝损伤、缺血再灌注损伤以及高脂饮食诱导的脂质堆积[1]。在特定情况下,自噬可以和细胞死亡发生关联,但其促进细胞死亡的功能有待进一步认识,尤其是在肝脏疾病时[1]。
二、肝内细胞死亡调节的几个特殊问题
(一)胆汁淤积和胆汁酸诱导的细胞死亡
胆汁淤积是急慢性肝病的一个共同特征,毒性胆汁酸的蓄积促使肝细胞死亡。在培养细胞中,胆汁酸诱导的细胞死亡大多数是凋亡,由死亡受体(包括Fas受体)配体非依赖性活化所介导。胆汁淤积性肝病也常触发细胞坏死,这从胆管结扎引起“胆道梗阻”的表现、Mdr2ko小鼠以及胆汁淤积性肝病患者中可以得到反映。尚不清楚这是由胆汁酸引起还是由其他机制引起。
(二)非肝细胞群的细胞死亡
非肝细胞群的细胞死亡也是慢性肝病的一个基本特征。不论是从机制还是从所致肝病来看,胆管细胞的死亡都不似肝细胞死亡那样具有特征性。TNF受体(TNFR)家族介导的凋亡,由Fas、TRAIL受体2或CD40活化所介导,似为最常见的胆管上皮细胞死亡形式[1]。胆管细胞凋亡见于免疫介导和药物诱导的胆管疾病,并可促进疾病进展和胆管缺失。相对于肝细胞死亡是创伤愈合和纤维化的共同触发因素,据信乃是胆管细胞增殖而非胆管细胞死亡促进疾病进展,例如在胆管相关病变中可促进胆道周围纤维化[13]。
肝星状细胞(HSC)的死亡是清除活化的肌成纤维细胞和消除肝纤维化的一种机制,一般认为其在慢性肝病是有利的。肝窦内皮细胞死亡可见于缺血再灌注损伤(例如肝移植)之后,但其对器官功能障碍的相关影响仍有争议。目前对肝脏巨噬细胞死亡的调节及其对肝病的影响亦不十分清楚。肝脏也是能导致肝脏高度免疫耐受的活化CD8+T细胞等特定免疫细胞亚群的“墓地”。
可见,细胞死亡对肝病的影响具有细胞特异性、阶段特异性和环境(病种等)特异性[1]。
三、细胞死亡的应答通路
虽然急性或慢加急性肝病时大量肝细胞死亡会损害肝功能,但在大多数慢性肝病仅有少部分肝细胞在同一时间死亡,这种情况下细胞死亡对肝脏功能并无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而肝脏对细胞死亡产生的应答可持续数十年,决定了长期后果和临床结局的发展方向(图3)[1]。
(一)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是慢性肝病时细胞死亡和炎症之间的桥梁
模式识别是固有免疫的基础。异常的分子模式不仅在宿主识别病原体的过程中起作用,也在识别与组织损伤相关的危险因素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在组织损伤后,濒死细胞释放的DAMPs可引发无菌性炎症。DAMPs的释放主要发生在坏死和坏死性凋亡后,因为这两种死亡使细胞膜丧失了完整性,由此解释了这些细胞死亡模式的炎症性质[4]。某些DAMPs,例如高迁移率族蛋白B1(high-mobilitygroupbox1,HMGB1),在细胞凋亡时甚至能主动保留下来。在急性肝病,例如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和APAP中毒,肝内数种DAMPs和DAMP受体,包括HMGB1(通过晚期糖化终产物受体或TLR4)、甲酰肽(通过甲酰肽受体1,FPR1)或ATP(通过P2X7)等,可触发炎症细胞募集,促使炎症形成和损伤加重。DAMPs诱导的无菌性炎症对慢性肝病进程的影响目前知之甚少。新近报道,卵圆细胞的增殖和HCC的发生需要RAGE(HMGB1的受体之一)的参与,提示慢性肝病时RAGE可能在DAMPs和HCC发生之间提供了一种机制上的关联。倘若DAMPs是参与驱动慢性肝损伤诸多并发症的一类潜在高度相关的治疗新靶点,则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凋亡细胞释放的低水平DAMPs是否促进病毒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和酒精性肝病(ALD)等相关慢性肝病的炎症[1]。此外,应激细胞分泌的介质可能会额外介导肝脏对损伤的反应。例如,应激性肝细胞释放的IL-33可通过固有淋巴细胞促进纤维增生和胆管增殖。

图3 特定细胞死亡模式和其后的细胞死亡应答对肝病进展的影响
(二)细胞死亡应答和肝纤维化
肝纤维化是临床上与慢性肝病最为相关的后果之一,并与各类肝病时ALT的升高相关[1],也与Caspase活化的标志物--被裂解的细胞角蛋白18(keratin18,K18)水平升高相关。HSC是引起肝纤维化的主要因素,但对HSC活化和HCD之间的分子关联仍知之甚少。虽然DAMPs为HCD和HSC活化之间提供了直接关联这一假说很有吸引力,但并未得到严格检验,也无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DAMPs可直接活化HSC[1]。另一种假说是,DAMPs可作用于其他类型细胞,进而释放导致肝脏纤维增生的介质来活化HSC,例如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和血小板衍生的生长因子(PDGF)。在这些可能的中介细胞中,目前了解最多的是肝巨噬细胞与HSC之间的相互作用,能促进HSC产生纤维成分。此外应当考虑到,在病毒性肝炎等许多非胆汁淤积性肝病,细胞死亡的形式主要是凋亡,这些情况下所释放的DAMP水平可能是较低的[1]。
足够的证据证明凋亡可以触发纤维增生。通过敲除小鼠肝特异性Nemo、Mcl-1或Bcl-xl基因,可选择性增加这种小鼠模型的肝细胞凋亡[14],为凋亡和纤维增生之间提供了一种关联。但由于这些小鼠模型通常伴随ALT水平升高,因此尚不确定这究竟是单纯凋亡还是包括坏死性细胞死亡。泛Caspase抑制剂IDN-6556可减少胆管结扎诱发的肝纤维化,而泛Caspase抑制剂VX-166对抑制NASH诱导的肝纤维化却收效甚微,尽管可以改善肝脏损伤和炎症。相较而言,剔除RIP3可抑制坏死性凋亡,保护小鼠不发生NASH诱导的肝纤维化,这突显了如下假说,亦即是坏死性凋亡而不是凋亡控制着代谢性损伤的肝纤维化[1]。
凋亡或坏死性凋亡与HSC活化之间的关联尚未得到充分认识。数项研究提出,HSC对凋亡小体的吞噬作用将细胞死亡和HSC的活化联系了起来;一些体外实验表明,HSC在吞噬凋亡小体后,其活化、迁移和存活均增加。多种促纤维化介质的增加提示凋亡可通过职业性吞噬细胞等间接机制来刺激HSC的活化和纤维化形成。
(三)细胞死亡和代偿性增殖
部分肝脏切除术常被用来研究患者在外科手术后的肝脏再生及其模型。而人类疾病时的肝脏再生可能是对急性肝细胞死亡(例如APAP中毒后)或慢性肝病时持续性细胞死亡的直接反应,而不是大块肝脏解剖结构或功能丧失的直接后果。因此尚不清楚细胞毒性肝细胞丧失后的代偿性再生与部分肝脏切除后的肝再生是否存在机制上的不同。通过动物模型已经很好地构建了HCC发生与肝细胞代偿性增殖之间的相关性[11]。尤其是上文提及的特异性敲除肝脏Tak1和Nemo基因的小鼠表现出了大量的代偿性增殖,被认为有助于HCC的自发性发生发展。在这两个模型中,凋亡似均为驱动增殖的力量[11],但尚不清楚哪些介质和细胞类型与这些过程有机制上的关联。
(四)细胞死亡和HCC发生
HCC发生与细胞死亡密切相关,但需仔细区分发生于非转化肝细胞的细胞死亡和发生于转化肝细胞的细胞死亡,因为这两者具有相反的功能效应。在非转化肝细胞,细胞死亡是一种肿瘤促进机制,由增强的代偿性增殖、纤维增殖和炎症所介导。敲除肝脏特异性抗凋亡蛋白Mcl-1或Bcl-xl,不仅可提高肝细胞的凋亡率,还能导致HCC的自发性发生发展,清晰显示了肝细胞凋亡的肿瘤促进作用[1]。在敲除肝脏Bcl-xl的模型中,若进一步敲除Bak,可抑制HCC发生,为肝细胞凋亡和HCC之间提供了一种直接关联。条件性敲除肝细胞的Nemo基因以抑制NF-κB,可导致细胞死亡大量增加和HCC自发性发生发展,也证明了肝细胞死亡和HCC之间的相关性。敲除肝脏特异性IKKβ可增加致癌物诱导的细胞凋亡和代偿性增生,促进HCC的形成;而敲除由Bcl-2家族成员p53上调的凋亡调节因子(PUMA),可减少HCC的发生。在近来的一些模型中,共敲除(codeletion)促凋亡基因Fadd或Caspase-8,可阻止HCC的发展,凸显了细胞凋亡的关键作用[11,15]。同样地,抗体介导的FasL中和作用不仅可阻止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转基因HCC小鼠模型的肝细胞凋亡,还能阻止其肝癌发生。
与非转化肝细胞死亡的促肿瘤作用相反,转化肝细胞死亡则能限制HCC发展。因此,肿瘤细胞常常要经受一种选择过程(例如p53基因突变),以便使其能成功地避免凋亡。下调促凋亡的Bax和Bcl-XS,以及上调抗凋亡蛋白Bcl-XL、Mcl-1、存活素(survivin)和X连锁的凋亡蛋白抑制物(XIAP),可赋予转化肝细胞更强的生存能力[1]。在慢性细胞死亡,以及通过筛选生存和增殖能力最强的克隆以试图获得高度细胞更新等情况下,细胞死亡遗传耐受性的开发是有利的。除了那些已被详细描述的机制外,嗜肝病毒感染也可导致对凋亡的耐受性的增大[16]。外加的生存信号可能是细胞外来源性的,例如肝脏微环境的改变或能增强肝内TLR信号的肠道渗漏。Mdr2敲除的小鼠可表达一种IκB超级阻遏物,能抑制NF-κB,使小鼠的肿瘤发展降低;这表明NF-κB作为一种关键的抗凋亡通路,能促进转化肝细胞的生存[17]。
不同的细胞死亡模式对肝脏癌变有着不同的影响。尽管普遍认为凋亡是一种惰性细胞死亡形式,但前述小鼠模型提供的证据显示,增强和减少肝细胞凋亡的干预措施均强烈提示凋亡是HCC发展的主要动力[1]。在TAK-1敲除的小鼠中进行的共删除(co-deletion)实验显示,是凋亡而不是坏死性凋亡促进了该模型的肿瘤发生[11]。尚需在其他肝癌发生模型中进一步证实此发现。目前并不清楚凋亡这种经典的惰性细胞死亡形式如何导致癌症。一种可能是,与坏死或和凋亡相关的继发性坏死相比,对凋亡小体的吞噬能更有效激发可促进HCC形成的代偿性增殖或纤维化。抑或这样设想,促凋亡的“执行酶(executioner enzymes)”,包括脱氧核糖核酸酶(DNAses),可诱发临近的细胞发生并行性损伤;或某些细胞能逃脱“凋亡攻击”而幸存,但其基因发生了改变并最终导致癌症。
四、细胞死亡的生物标志物
(一)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血清ALT是诊断和监测急慢性肝病最常见、认识最成熟的生物标志物(表1)。血清ALT几乎由肝细胞特异性表达;普通人群血清ALT的水平与总病死率和肝脏特异性病死率是相关的,但与其他病因引起的病死率无关。G-谷氨酰转肽酶(GGT)和AST等其他肝脏生物标志物水平的升高与总病死率有关,但不能特异性反映肝脏相关病死率。在HBV感染者、HCV感染者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患者,ALT水平升高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临床进展相关(表1)。虽然ALT似为预测慢性肝病进展的、认识最成熟的生物标志物,但对急性肝病而言,其他一些生物标志物比ALT更加敏感,例如微小RNA(microRNA,miR)-122、HMGB1和K18[1]。与ALT相比,AST也在心肌、骨骼肌、肾脏和血液等更广泛的组织中表达。因此对肝病而言,血清AST水平升高的特异性不如ALT。较高水平的AST,特别是AST/ALT比值>2,提示重度ALD,但这并不具有特异性,AST对判断酒精摄入及ALD的敏感性是较低的。AST/ALT比值升高也与NASH患者纤维化风险增高相关。
(二)K18
K18是一种48kD中间丝蛋白,高表达于上皮细胞,释放到细胞外时可作为上皮细胞死亡的血清标志物。K18首先被Caspase裂解为44kD和4kD的两个片段,然后44kD的片段再被Caspase裂解为29kD和23kD两个片段。众多临床研究中应用的M30抗体可识别44kD和23kD片段C末端暴露在外的新表位。M65等其他抗体,则在一些研究中被用作细胞坏死的标志物,尽管M65抗体既能识别未裂解的K18,又能识别被Caspase或其他蛋白酶裂解的K18。虽然对基于抗体的分析方法能否可靠反映Caspase裂解的K18和凋亡仍存在争论,但许多研究显示K18在量化分析细胞死亡和预测临床结局方面是有价值的。
K18作为生物标志物最有力的证据来源于对NAFLD的研究,其对诊断NAFLD中的NASH患者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18],并与临床参数和组织活动度评分(HAI)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表1)。对HCV感染者的研究显示,血清氨基转移酶水平正常的患者中约有50%可出现血清K18水平升高,其中30%的患者处于肝纤维化晚期阶段。作为ALD标志物的Mallory-denk小体,主要就是由泛素化的K8和K18聚集而成[1]。因此,全长K18和K18片段与ALD患者肝内的Mallory-denk小体、肝细胞气球样变和肝纤维化是相关联的。尽管对K18作为多种肝病的生物标志物的数据令人鼓舞,但在推荐其常规应用于临床实践之前仍需进行更多的研究。
(三)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
HMGB1是一种非组蛋白DNA结合蛋白,存在于所有真核细胞中,在细胞坏死后被动地释放出来,但高乙酰化的HMGB1也可由炎症细胞主动分泌。由于受到十字形DNA的滞留,凋亡细胞仅释放少量HMGB1。HMGB1在伴有坏死性细胞死亡的肝病中得到大量研究。APAP中毒的患者,其总HMGB1和高乙酰化HMGB1水平均增高。在过量APAP引起急性肝损伤的8h内,总HMGB1水平对急性肝损伤的判断优于血清ALT水平。总HMGB1和乙酰化HMGB1水平的增高与APAP中毒后的不良预后相关,而血清ALT水平则不能反映这种情况[19]。
(四)微小RNAs(microRNAs,miR)
miR在调节基因表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miR-122是肝细胞中含量最多的微小RNA,在肝细胞损伤后释放入血。APAP中毒后,miR-122水平升高,能较血清ALT水平更早地反映肝损伤,对急性肝损伤后果的预测也优于血清ALT[20]。在慢性肝病,miR-122水平与肝纤维化严重程度呈负相关,可能反映了有功能的肝细胞的丧失,而不是肝细胞的死亡率。血清miR-29、miR-133、miR-571和miR-652水平升高反映了由于肝细胞死亡引起的HSC活化和肝纤维化[1]。

表1 细胞死亡的生物标志物及其对急慢性肝病的预测价值
(五)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1
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1(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1,CPS-1)是肝细胞线粒体中含量最丰富的蛋白质,具有比ALT更高的肝特异性。新近项研究表明,在APAP中毒、Wilson病和缺血性肝损伤引起的急性肝损伤中,CPS-1被触发。由于CPS-1半衰期非常短,所以能较ALT能更准确地预测肝损伤的终止[1,21]。
五、临床肝病中的细胞死亡
(一)药物诱导性肝损伤(DILI)
DILI是西方国家ALF的主要病因,也是临床实践中急性肝炎或胆汁淤积的重要病因。DILI最常见的原因是APAP中毒,可诱导剂量相关性肝细胞坏死,其机制包括将一部分APAP转化为活性代谢产物,耗尽谷胱甘肽(GSH)并与蛋白质共价结合,而线粒体是关键的靶细胞器,可通过持续活化JNK而促进细胞死亡。N-乙酰半胱氨酸(NAC)是APAP过量的早期特效解毒剂,能补充GSH以阻止活性代谢产物的共价结合,成功中和APAP的毒性。然而,当APAP已被代谢和GSH已被耗尽之后,NAC的疗效则十分有限。一些无对照的临床研究提示,对于正在减弱的毒性,较晚(APAP过量后48h或后来才发现的亚临床无意间中毒时)应用NAC仍可有一定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针对JNK等下游通路的其他治疗可能是有益的。虽然延迟的JNK抑制在动物模型中效果良好,但是在中毒早期NAC的效用,理论上关系到对JNK依赖性再生信号晚期保护效用的干扰;而APAP中毒患者的关键窗口无法识别,使得JNK抑制剂在临床背景下难以被应用。尽管在APAP中毒的早期阶段坏死性凋亡是重要的,但由于抑制RIP3未能阻止晚期肝损伤,这使得坏死小体(necrosome)不宜作为APAP中毒时的治疗靶点[1]。
除外APAP,大多数DILI属于特异质性DILI(idiosyncratic,IDILI),其细胞死亡是由适应性免疫系统介导。新近发现HLA和DILI之间存在关联,提示患者具有发生IDILI的遗传性风险[22]。当前认为IDILI药物可引起肝细胞应激,为遗传易感性个体的免疫系统提供危险信号。能够抑制免疫介导性细胞死亡机制的药物对IDILI的早期可能有益,但尚未得到正式研究。一旦发生ALF,这类治疗方法就已经失效了[1]。
(二)病毒性肝炎
大多数急慢性HBV或HCV感染可诱导主动抗病毒免疫应答,导致对被感染肝细胞的主动杀伤。被感染的肝细胞主要通过CD8+效应性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K)被清除。病毒未被清除的患者,其体内持续存在T细胞和NK细胞介导的肝细胞凋亡。被感染肝细胞的凋亡不足以清除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的病毒,反而成为肝病进展的重要驱动因素。T细胞和NK细胞诱导的肝细胞凋亡主要由TNFR家族成员(包括Fas和TRAIL受体2)介导,少部分可由颗粒酶B和穿孔素介导。前述小鼠研究显示,凋亡足以触发纤维化和HCC。可见,在慢性HBV和HCV感染者,因持续清除被感染的靶细胞而诱导的凋亡很可能是疾病进展的主要因素[1]。但在HCV感染者中应用Caspase抑制剂IDN-6556和GS-9450的有关研究尚未有阳性发现。由于直接抗病毒药物对慢性HCV和HBV感染的疗效良好,因此Caspase抑制剂等针对靶细胞的治疗策略不太可能在未来成为临床上治疗病毒性肝炎的一个策略[1]。甘草甜素能抑制HMGB1,改善HCV感染者肝脏的坏死性炎症和纤维化,但不能降低血清HCVRNA水平[23];这提示在病毒性肝炎等肝病患者,甘草甜素可能是通过抑制HMGB1介导的细胞死亡应答而发挥治疗作用[1]。
(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
NAFLD是西方国家最常见的慢性肝病。其中NASH是一个更具侵犯性的疾病,与单纯脂肪变性的不同点是NASH存在肝细胞死亡和随后的细胞死亡反应,病理上表现为肝细胞气球样变、炎症浸润和/或胶原沉积,并能促进肝纤维化、肝硬化和HCC发生。目前临床上并无可有效阻止NASH诱导肝纤维化和HCC的药理学对策,这凸显了鉴别NAFLD转变为NASH的信号调节通路的必要性。这种转变过程往往伴随ALT水平的升高,提示细胞死亡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1]。在所有细胞死亡通路中,凋亡是这种情况下最具特征性的细胞死亡类型[24]。因此,数个大型临床试验显示,血浆K18片段(CK-18Fr)的水平与肝细胞凋亡的强度相关,并可独立预测NASH的存在。除了推测的细胞凋亡作用外,新近还发现NASH肝脏能高表达RIP3[25],提示坏死性凋亡可能是NASH临床研究的另一个靶标[1]。
已提出多种细胞内机制可触发细胞死亡及NASH进展。例如,饱和脂肪酸较不饱和脂肪酸的肝毒性更强。肝脏脂肪酸堆积可刺激ROS产生,推测这可能是由于β-氧化增强及随之发生的线粒体电子传递链中的电子流过载所致。ROS水平增高可直接损伤DNA、蛋白质和脂质,通过活化JNK和p38丝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等应激相关信号通路而促进细胞死亡。脂肪酸诱导的JNK活化被认为可能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内质网应激反应(ERSR)的作用仍存在争议,因为敲除CHOP可加重NASH。与细胞内的凋亡通路相比,对NASH情况下外源性死亡受体介导的细胞凋亡通路知之甚少。虽然NASH患者的脂肪组织增多与TNF等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相关,但这些细胞因子对细胞死亡的促进作用及其临床相关性仍属未知。在小鼠NASH模型中,敲除TNFR可保护小鼠不发生肝脂肪变性和纤维化。此外,TRAIL受体2在肝细胞的脂性凋亡(lipoapoptosis)中也起某种作用,但其对NASH的促进作用有待测试。
减肥手术可持续改善胰岛素抵抗、肝脂肪变性、炎症、血清ALT和K18水平以及肝纤维化等。多年来认为胰岛素抵抗是NAFLD最相关的潜在病理生理学机制;应用吡格列酮和罗格列酮治疗第一年期间即可出现血清ALT水平和肝组织学改善。但由于多种原因,相关指南并不推荐将该疗法作为一线治疗。相较而言,针对细胞应激和细胞死亡通路的研究已取得有价值的发现,并已改变临床标准。基于ROS在细胞死亡和NASH病理生理学中的突出作用,PIVENS研究检验了抗氧化剂维生素E(VitE)在无糖尿病的NASH患者中的作用。结果显示,无糖尿病患者在服用VitE后出现肝脏炎症减轻,血清ALT和AST水平下降,但纤维化没有变化;该发现是新近NAFLD指南一条推荐意见的基础,亦即VitE可作为经肝活检确诊NASH的无糖尿病患者的一线治疗药物[26]。有研究以法尼酯X受体(farnesoid Xreceptor,FXR)激动剂奥贝胆酸(obeticholic acid,OCA)治疗伴有2型糖尿病的NASH患者,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轻体重,降低ALT和GGT水平,促使肝纤维化标志物水平下降;但本试验中的血清ALT和肝纤维化标志物水平的下降仅见于应用低剂量OCA进行治疗时。另一项2期研究报道,以选择性Caspase抑制剂GS-9450治疗NASH患者,约35%的患者出现了ALT水平恢复正常,但其对肝组织学的效果未知,且K18的减少并不明显。总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靶向于细胞死亡和氧化应激的治疗方法对NASH可能是有益的,但尚需更大型的试验和更长的观察期来判断相关临床后果[1]。
(四)酒精性肝病(ALD)
ALD是世界范围内与肝脏相关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酒精滥用增多和乙型肝炎及丙型肝炎流行率下降,预计ALD会进一步相对增多。酒精性脂肪性肝炎(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ASH)是一种严重的ALD,可进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和HCC。与NASH相似,ASH的特点是肝脂肪变性、细胞损伤和炎症。有证据显示ALD存在细胞凋亡和坏死。酒精的细胞毒作用至少部分是由代谢产物乙醛所致,乙醛可导致ROS产生过多,进而引起脂质过氧化、线粒体损伤和细胞死亡。因此,应用抗氧化剂可改善实验性ALD。肠道通透性增加可导致门静脉脂多糖(LPS)水平升高,增加TNF和IL-6等炎性细胞因子及ROS的产生,损伤肝脏;TLR4缺乏的小鼠和经过不吸收性抗生素清洁肠道的小鼠,其肝损伤减轻即证明了这一发现。TNF可介导酒精性肝损伤,抗TNF治疗能阻止酒精诱导的大鼠肝细胞死亡。应用RIP3缺乏的小鼠进行研究表明,在酒精性肝损伤,坏死性凋亡参与了TNF依赖性细胞死亡。上述通路应用于治疗ALD和/或防止发展为HCC的临床可能性仍待探索[1]。
持续酒精摄入是ALD进展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因此戒酒是最为有效的防治措施。药物治疗主要限于重症急性肝炎。但目前尚不清楚可能由ROS、TNF和细菌性PAMPs触发的肝细胞死亡是否为急性肝炎的主要促进因素。大多数研究显示,糖皮质激素可提高急性肝炎患者的短期生存率;因此成为基于Lille评分定义的应答者的一线治疗药物。小鼠研究揭示了TNF在介导ASH依赖性细胞死亡过程中的突出作用,这是临床上应用TNF抑制剂依那西普(etanercept)和己酮可可碱(pentoxifylline)试验性治疗ALD的基础。但新近一项大型试验未能证明联合应用糖皮质激素和己酮可可碱的疗效优于单独应用糖皮质激素,依那西普反而提高了急性肝炎患者的病死率和感染率。NAC等抗氧化剂的疗效也不确切,因为与单独应用糖皮质激素相比,联用NAC和糖皮质激素仅改善一个月的生存率,但对六个月的生存率无明显改善。
(五)肝细胞癌(HCC)
HCC是慢性肝病最常见的终末阶段,其发生是多因素的。细胞死亡在促进 CC发生中的相对作用取决于潜在肝病的性质。例如,在HBV感染者和NAFLD患者,即使缺乏慢性肝损伤和/或肝纤维化,仍可发生HCC;这表明在特定疾病背景下,非细胞死亡依赖性致癌信号可能足以触发癌症发生,例如HBV诱导的信号或代谢的改变。尽管如此,高达80%的HCC乃是发生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状态下,而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是在慢性肝细胞死亡过程中渐次发生的。此外,上述来自小鼠模型的数据强力支持肝内的慢性细胞死亡足以触发HCC。同样地,大量临床研究表明肝细胞死亡的生物标志物和癌症发生风险之间存在关联。例如,血清ALT水平持续大于45U/L的HBV和HCV感染者,其HCC发生率分别是ALT水平持续正常的肝炎患者的10和7倍。因此,指南推荐ALT水平是监测和治疗肝病的一个部分。
对肝内调控细胞死亡的通路进行干扰似为一种很有希望的HCC防治策略,但这可能需要依赖阶段、疾病和定位特异性方法。HCC的预防策略需要在早期阶段抑制细胞死亡,从而终止能引起HCC的细胞死亡/炎症/再生/纤维化级联反应。欲达此目的,除了治疗基础疾病,还可尝试采用DAMPs抑制剂如甘草酸,或采用利福昔明等不可吸收性抗生素以阻断“肠道微生物-肝脏轴”,或采用能抑制细胞死亡、炎症或纤维化的其他修饰剂。
相反地,对于已发生的HCC的治疗,要促进癌组织中的细胞死亡但又不能伤及健康肝脏[1]。目前唯一批准用于治疗HCC的这类药物是索拉非尼(sorafenib),能影响HCC的增殖和血管生成,但不影响细胞死亡。除了射频消融和经动脉化疗栓塞等选择性不高的能诱导HCC死亡的消融策略外,更具HCC特异性的治疗方法也在研发中。溶瘤病毒能选择性诱导HCC死亡;一项2期临床研究显示,具有溶瘤和免疫治疗作用的牛痘病毒JX-594能够剂量依赖性改善HCC患者的生存状况。测试JX-594和索拉非尼联合疗效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另有研究应用反义XIAP联合索拉非尼以降低癌细胞的凋亡阈值,促进肝癌病灶中的癌细胞死亡。
六、结论
细胞死亡几乎是所有急慢性肝病进展机制的中心所在。坏死性凋亡等多种新的细胞死亡模式,以及调控细胞死亡及细胞死亡反应特定通路的发现,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急慢性肝病病理生理学过程的认识。坏死性凋亡是凋亡的重要后援,这一发现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何以Caspase抑制剂未能在临床肝病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可能很有必要同时阻断多条通路,或阻断那些被认为更具反应性或毒性的通路(亦即可能是坏死性凋亡而非凋亡)。考虑到上述难题以及阻断一种细胞死亡通路可能会活化另一条通路,未来研究应关注肝脏细胞死亡应答通路的调控问题。这些通路可能隐含急慢性肝病简化治疗的重要线索。对急性肝病而言,那些能触发肝细胞增殖的通路的活化可能是有利的;而对慢性肝病而言,阻断促纤维化、促增殖及致炎性细胞死亡应答通路,则可能达到阻止疾病进展的效果[1]。细胞死亡新的生物标志物可能有助于更准确地预测肝病的结果和帮助制定治疗决策。
1 HLuedde T,Kaplowitz N,Schwabe RF.Cell death and cell death responses in liver disease:mechanisms and clinical relevance.Gastroenterology,2014,47:765-783.
2 Linkermann A,Green DR.Necroptosis.N Engl J Med,2014, 370:455-465.
3 Festjens N,Vanden Berghe T,Vandenabeele P.Necrosis,a wellorchestrated form of cell demise:signalling cascades,important mediators and concomitant immune response.Biochim Biophys Acta,2006,1757:1371-1387.
4 Kaczmarek A,Vandenabeele P,Krysko DV.Necroptosis:the release of 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and its physiological relevance.Immunity,2013,38:209-223.
5 Lemasters JJ.Dying a thousand deaths:redundant pathways from different organelles to apoptosis and necrosis.Gastroenterology,2005,129:351-360.
6 Martin SJ,Henry CM,Cullen SP.A perspective on mammalian caspases 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gulators of inflammation.Mol Cell,2012,46:387-397.
7 Cazanave SC,Gores GJ.Mechanism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hepatocyte lipoapoptosis.Clin Lipidol,2010,5:71-85.
8 Vanden Berghe T,Linkermann A,Jouan-Lanhouet S,et al.Regulated necrosis:the expanding network of nonapoptotic cell death pathways.Nat Rev Mol Cell Biol,2014,15:135-147.
9 Wang H,Sun L,Su L,et al.Mixed lineage kinase domainlike protein MLKL causes necrotic membrane disruption upon phosphorylation by RIP3.Mol Cell,2014,54:133-146.
10 Cho YS,Challa S,Moquin D,et al.Phosphorylationdriven assembly of the RIP1-RIP3 complex regulates programmed necrosis and virusinduced inflammation.Cell,2009,137:1112-1123.
11 Vucur M,Reisinger F,Gautheron J,et al.RIP3 inhibits inflammatory hepatocarcinogenesis but promotes cholestasis by controlling caspase-8-and JNK-dependent compensatory cell proliferation.Cell Rep,2013,4:776-790.
12 Choi AM,Ryter SW,Levine B.Autophagy in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N Engl J Med,2013,368:651-662.
13 Xia X,Demorrow S,Francis H,et al.Cholangiocyte injury and ductopenic syndromes.Semin Liver Dis,2007,27:401-412.
14 Luedde T,Beraza N,Kotsikoris V,et al.Deletion of NEMO/ IKKgamma in liver parenchymal cells causes steatohepatit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Cancer Cell,2007,11:119-132.
15 Liedtke C,Bangen JM,Freimuth J,et al.Loss of caspase-8 protects mice against inflammation-related hepatocarcinogenesis but induces non-apoptotic liver injury.Gastroenterology,2011,141:2176-2187.
16 Arzumanyan A,Reis HM,Feitelson MA.Pathogenic mechanisms in HBV-and HCV-associ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Nat Rev Cancer,2013,13:123-135.
17 Luedde T,Schwabe RF.NF-kappaB in the liver-linking injury,fibr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2011,8:108-118.
18 Musso G,Gambino R,Cassader M,et al.Meta-analysis:natural history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and diagnostic accuracy of non-invasive tests for liver disease severity.Ann Med,2011,43:617-649.19 Antoine DJ,Jenkins RE,Dear JW,et al.Molecular forms of HMGB1 and keratin-18 as mechanistic biomarkers for mode of cell death and prognosis during clinical acetaminophen hepatotoxicity.J Hepatol,2012,56:1070-1079.
20 Antoine DJ,Dear JW,Lewis PS,et al.Mechanistic biomarkers provide early and sensitive detection of acetaminophen-induced acute liver injury at first presentation to hospital.Hepatology,2013,58:777-787.
21 Weerasinghe SV,Jang YJ,Fontana RJ,et al.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atase-1(CPS1)is a rapid turnover biomarker in mouse and human acute liver injury.Am J Physiol Gastrointest Liver Physiol,2014,307:G355-G364.
22 Kaplowitz N,DeLeve L.Drug-induced liver injury: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In:Kaplowitz N,ed.Drug-induced liver injury.3rd ed.San Diego,CA:Elsevier,2013:3-14.
23 Manns MP,Wedemeyer H,Singer A,et al.Glycyrrhizin in patients who failed previous interferon alpha-based therapies:biochemical and histological effects after 52 weeks.J Viral Hepat,2012,19:537-546.
24 Hatting M,Zhao G,Schumacher F,et al.Hepatocyte caspase-8 is an essential modulator of steatohepatitis in rodents.Hepatology,2013,57:2189-2201.
25 Gautheron J,Vucur M,Reisinger F,et al.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between RIP3 and JNK controls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EMBO Mol Med,2014,6:1062-1074.
26 Chalasani N,Younossi Z,Lavine JE,et al.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practice guideline by the American Gastroenterological Association,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and 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enterology.Gastroenterology,2012,142:1592-1609.
2015-06-22)
(本文编辑:赖荣陶)
510282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王英杰);解放军第八一医院全军肝病中心(于乐成)
于乐成,Email:gslsyc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