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中人(五题)
岑燮钧
戏中人(五题)
岑燮钧
醋溜鱼
三十六年前外滩上的那条醋溜鱼的味道,白秀文到老都不会忘记。
那时的外滩没有现在整齐,一切都是随性的。汽笛在迷离的灯光中,一波长一波短。这进进出出的轮船,演绎着多少离合悲欢。
耳边小调的旋律,从舞厅上传来,隐隐约约。她与何生对坐着。何生脱掉了戎装,他要到舟山去,明天就动身。那时,她刚夜场结束,演的是《虞美人》。剧场后门停着一辆车,姐妹们都知趣地避开了。
外面的风声时缓时紧。就像此刻的窗外,微微飘动的窗帘仿佛虞姬的流苏。可惜你没看上,白秀文说,我们明天换戏了,这是你唯一没看的一部。何生已经三个月没有留在身边,即使回来,也是匆匆见一面,即刻就走。他有公务在身。这光怪陆离的世界,已经四面楚歌。但是,她只是个唱戏的,外面的游戏,由男人们顶着。
帘幕揭起,侍应生进来。
“先生,小姐,这是你们点的醋溜鱼,请慢用。”
何生开的第一筷,只是他夹给了白秀文。
白秀文夹筷子的样子,让何生着迷。她总是握在筷子尾上,这样显得筷子特别长,就像她穿旗袍的身姿,显得下身特别婀娜修长一样。
人说,这种腰叫水蛇腰,能毁掉男人的。
“黄鱼的味道总还是一般,我倒是喜欢吃那酸酸甜甜的醋溜糊。”
醋溜糊里有香菇、嫩笋丝,要紧的是还有韭黄,吃起来不至于空落落,让人觉得藕断丝连一般,既滑溜,又有嚼头。
三十六年后在香港,何生又点了一道醋溜鱼。
这是白秀文复出后第一次来香港。来之前,团里千叮嘱万叮嘱,一遍一遍强调纪律。她出来是向团里请的假。虽说,私下逛逛走走,也算不得什么。但是,香港毕竟不同于内地,何况何生是从台北飞来的。
第一面见到他,她怔了一下。那不是她记忆中的何生,他已是两鬓斑白,原先曲折有致的人中,在瘦挺的双颊映衬下,显得俏皮而优雅。但是,现在他一脸沧桑,那么多沟壑淹没了那一点点凹凸分明的人中。只有那鼻翼,还能看出当年模样。她抿了一下嘴唇,努力不使泪水溢出来。
窗外,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潋滟波光,被霓虹灯染得幽昧而驳杂。比起当年外滩的夜色,这里更有海的味道。那种潮潮的气味,也许台北也如此吧。
他说,他不听剡剧有三十六年了。
何生给白秀文斟酒,白秀文用手掩了一下高脚杯。我不会喝的,你知道的。白秀文说。你还是没有变,何生给自己斟满,呷了一口,看着白秀文。这是你喜欢的醋溜鱼,你尝尝。他夹了一筷,放到白秀文的碟子里。
这种姿势,白秀文熟悉而又陌生,就仿佛他的身体,如今看来,已判若两人。
白秀文拿起筷子,在盘子里夹了少许,放到嘴里。她慢慢抿着,那滋味,到底隔着太久的时光。
“还好吃吧?”
白秀文点点头。但是,她的舌头告诉她,那不是以前的味道。她用小汤匙舀了些醋溜糊,浇在鱼肉上。
“可有当年的味道?”
“还好……”
其实是,醋溜糊的甜味压过了酸味,正好与当日反了一反。少了点韭黄,味道就有点闷腻了。
“昨晚你演的《虞美人》,让我触景生情,流了不少的泪啊。”
“没有那时好看了,老了。”
“那时我错过了你的戏。好在酒是陈的香,如今演来,更有味道。当年我与你外滩一别,也是这般光景啊。兵败如山倒,从此天各一方……”
这样的天翻地覆,谁能料得到呢?老实说,当日演《虞美人》,多少有点小孩子过家家的味道。何生没看上,倒也不甚可惜。只是在这变乱中,她小产了,后来再也没有怀上过,终使她一生萧疏——到如今不说也罢。
“我原先还以为是‘春花秋月何时了’的那个‘虞美人’,其实就是京剧的《霸王别姬》。不过,若是演‘春花秋月何时了’,也是一样的……”何生像是跟白秀文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与京戏比起来,剡剧更儿女情长些。”白秀文放下筷子。
何生拿出了一张照片,“当年我们分别时,就是这般模样,还记得吗?”
白秀文一看,不由内心颤抖。她看看眼前的何生,又看看照片里的何生,不由一声长叹。为这一张照片,她受了多少苦。藏过天花板上,藏过煤炉灰里,甚至藏过马桶底下,但最终还是被搜出来了。那时,她是被作为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看待的,能挨过来,只能说是奇迹。
她用手帕擦擦眼角。
“怎么了?”
“没什么,看看照片,真像做梦……”
临别时,何生说:“我等你,说不定有一天你可以来台北演出……”
白秀文到底没有送何生去机场。她不想让人发现什么。
可惜的是,第二年何生就病殁了。
白秀文八十八岁才过世。临终时,她忽然说想吃醋溜鱼。等做来时,已闭了眼。学生们收拾遗物时,发现了那张照片,才知道老师就像那虞姬,也是一段传奇。
她们看了也动心。
葬花
早先,反串的事儿是常有的。老先生们走江湖,什么都演,男男女女是不论的。
小袁长得好,身材修长,脸蛋带着娃娃气,而又英气逼人,漂亮得像女孩子。老先生带着他,就仿佛带着个如花的少女,怎会不喜欢?与阿姨们配戏,女人们疼着他,就像疼自己的儿子。
演《雷雨》时,小袁的周冲让人眼前一亮。
为了“练兵”,团里组织了一次反串大会演。那些老戏骨,真是了得,演老生的反串成了鸨儿,演小姐的成了武将,演风流小生的竟做了“奇怪刁”……排练时,自己都笑岔气。但是,一旦化妆上台,就演啥像啥,没一个漏气的。
让小袁演的是《葬花》,演林妹妹,而原先的林妹妹演宝玉。小袁有点走不进去,演女人,搁不下脸。一个老先生看出点苗头,说演戏啊,要脸就是不要脸,不要脸就是要脸,你得把自己忘了。后来想出的办法是带妆排演,小袁渐渐进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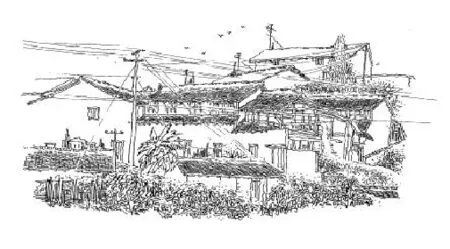
“小袁真俊啊!”张阿姨说。
“我看啊,还是反一反的好,你看,比小林更像黛玉!”李阿姨压着嗓子跟张阿姨咬耳朵。
不知小林听到没有。反正,小袁的黛玉惊艳了。
公演时,领导都来了。演出气氛很好,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戏迷们笑得泪水都出来了。领导们平时绷着的脸也舒展开来,难得放怀一笑。上台祝贺时,领导说:演龙像龙,演虎像虎,你们演绝了!
“你真的是小袁?”一个女领导说。小袁害羞地点点头。后面的大领导握住他的手,说:“祝贺你演出成功!”回头又看了他一眼,笑了笑。
小袁觉得又温暖又难为情。
一次,他们演《雷雨》招待客人,小袁依旧演周冲。他的戏不多,却博得了不少掌声。是领导先鼓的掌,领导鼓掌了,谁不跟呢?
第二晚,上面通知进“大院”演出,让他演《葬花》。
“这位是昨晚演周冲的!”
“怎么可能?”客人很是惊诧,而领导很得意。
从此,小袁成了红人,经常有机会到“大院”演出。
大家看小袁的眼神慢慢地变了,像要发现什么似的。谁也没明说,但都意会他背后有人。
但是,小袁反而变得沉默了,心事重重的样子。后来,他甚至拒绝反串演出,除非上面点将去“大院”。大家的理解是,他背靠大树好乘凉,已经今非昔比。所以,要看小袁的《葬花》,那是很不容易的。
人们对小袁最后一次反串演《葬花》记忆犹新。这是作为压轴戏推出的。出场时,落英缤纷,舞台效果极佳。以前,只是虚拟一下了事。
大家很快忘了台上的是小袁。林妹妹幽幽然出来,轻移莲步,在满地落红间自怨自叹。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黛玉如此,但小袁是重点培养对象,团里的人都眼红呢。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那声音,渐渐有了伤感,钝钝的痛,似乎是真的。他在唱“质本洁来还洁去”时,泪水溢满了眼眶。一个小后生,能反串把戏演成这样,不得不让人由衷叹服。小林是正宗嫡传的“林妹妹”,都没他演得好——难道小袁真的具有炉火纯青的演技?
可惜,花无百日红。革命的气氛越来越高涨,反串作为“封资修”被禁了。
乌云压顶,风云突变。“大院”的斗争让人目瞪口呆,你方倒台我登场,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
团里也不闲着,老先生们一个个靠边站,进牛棚的进牛棚,隔离审查的隔离审查。他们原来是老江湖,谁没个把柄落在人手呢?
大家忽然发现,小袁不见了。各“战斗组织”都在找他,可就是找不到,不知是谁先下的手。各种消息满天飞,有一种说法是,他与大院里的一个女的不清白。“难怪,他总是上大院去演出!”有人向小林打探,小林说反正每次演出,她先来了。
小袁是在一个深夜被另一派抢走的。
当大领导被押上台时,陪斗的还是小袁。小袁的嘴角、眼角都有血痕,衣服明显被撕扯过,有一处裂开着。前襟耷拉,露出胸的一边,里面的血痕更加明显。大家的目光在小袁身上搜索着,上上下下。最后,只得逡巡在胸前的“不是男人”四字上,只恨那纸牌遮挡了要紧处。
这一次批斗范围不大,有种暧昧的味道,谁也不知道两个男人是怎么弄的。
小袁的头垂得很低很低,他的身子在簌簌发抖。不久,身下湿了一摊。
反戈一击的是女领导,她成了革委会主任。
第二天,人们发现小袁真的不见了。后来,在郊外的江里发现了一具男尸,身上也有血迹。捞上来后,摊在岸边。
风吹来,落花乱飞,一些落在尸体上,一些飘到江里,随水远去。
骂贼
杨小娟的十七岁是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度过的。
之前,她一直是个快乐的孩子。母亲杨素娟既是名角,又是团长,她在团部,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很小的时候,她就喜欢上舞台,看妈妈演戏。水袖一甩一甩,她觉得特好玩。妈妈拗不过,就让她跑龙套。她起先当个站队的宫女,后来会演了,就给妈妈当丫鬟。演《桃花扇》时,她甚至当了B角。阿姨们都说她很有天分,将来定是个红角儿。
但是,现在她只能低着头走路。杨素娟被押上了台,杨小娟还能有好日子过吗?这个艺名才用了不到一年,她真希望自己不是杨小娟,而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上午,批斗大会在学校大操场举行,杨素娟在列。杨小娟深深地埋下头,耳朵嗡嗡叫,脸颊一阵烫一阵冰,一会儿血红一会儿煞白。她听到母亲在辩白,说没有……我不是……中央领导看过我的戏……这时,崔阿姨走上台去,她说:你就是特务,解放前我亲眼看见你和国民党特务在街头接头。“你,你,你血口喷人!”崔阿姨犹豫了一下,突然一个巴掌,打在母亲脸上。于是,全场高喊“打倒”。她偷偷瞟一眼,看见母亲刚想抬头,就被戴红袖章穿绿军衣的小将按下头去,随即一顿皮鞭。那声音很刺耳,一揪一揪,让人心拎起来,要尿尿似的。
崔阿姨是母亲的大弟子,解放前就跟着,见人从来是一张笑脸。
她不敢看母亲。母亲演《江姐》时,也曾遭遇这样的虐待。可那是在戏里,哪像此刻,灵魂里起革命呢?
这革命,平息,要等到母亲平反重新安葬之后。母亲死得很惨,是自杀的。
此后,她继承了母亲的衣钵,重拾艺名杨小娟。此前,她下放农村,叫刘红旗。
母亲如果能再坚强一些,也许就熬过来了。
也就这么想想。不能往深处想。杨小娟还年轻,她有她的生活。何况,演到哪里,大家都很尊重她,甚至把她看做是杨素娟——她与母亲很像的。她也知足了。
直到退休。她空了,学会了上网。无意中,她看到了“杨素娟吧”,都是母亲的戏迷发的帖,对母亲的《桃花扇》赞不绝口,称母亲是“活香君”,不但在舞台上塑造了活生生的李香君的形象,而且在生活中,也是一位性格刚烈的女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让杨小娟很欣慰,不由泗泪滂沱。她记得有一回演《桃花扇》时,李香君撞头自尽,母亲竟真流血了,她吓了一大跳。她一边拿过纸巾揩泪,一边往下点,又翻一页,忽然,“杨素娟之死”的帖子直逼眼帘。她闭了一会眼,心有不忍,怕撕开自己的伤口。多少年来,靠的就是回避,遗忘,自慰。毕竟,母亲去了很多年了。
终于,她还是点开了这个帖子。她一条一条往下看,发现,满屏都是对崔阿姨的谴责,说她忘恩负义,欺师灭祖,出卖灵魂,猪狗不如……是她,逼死了自己的老师。更有甚者,说如果自己遇到姓崔的,肯定扇她一巴掌,让她跪在杨素娟坟前,赎罪!
其实,不是这样的,她轻轻对自己说。她还能很清晰地记得,在母亲平反大会上,崔阿姨痛哭流涕,长跪不起。此后,她很少再登台,把平生所学,悉数教给杨小娟。后来,她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不久就病逝了。
“大家都这样谴责姓崔的,难道她女儿就没有一点过错吗?”
杨小娟的心拎了一下,很多年没有这样让人颤抖了。
“她曾与母亲划清界限,她母亲游街时……”她看不下去了。她站了起来,摘下眼镜,扭了一下眉心。她喝了一口水,又慢慢坐下。正像帖子所说的,她在那天的批斗大会上,继崔阿姨之后,第二个站出来,向世人宣布,与母亲一刀两断,从此恢复本名——刘红旗。她要像自己的名字一样,红旗飘飘。她说,我一定站稳立场,站在革命群众一边!
但是,那天在路上,她抱着一棵树,呜呜地哭了。
她恨自己,为什么要生在这样的家庭?这时,她看到游街队伍过来了,她有一种冲动,也想把鞋扔上去,振臂高喊:打倒特务杨素娟!但是,她没有多余的鞋子。她只能站在一边,看游行队伍过去。她发现母亲头发散乱,嘴角流血,一副疲惫极了的样子。有那么一瞬,她似乎看见自己了。她心里一惊,但队伍马上冲乱了,母亲的眼神一直在寻找什么似的。她低下了头,被冲来冲去。游行车过去后,她跟着大家,做出高呼的样子。其实,声音像蚊子,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
回到家,她颓然倒在床上。
整书包时,一张报纸倒了出来。对了,是昨天同学给她的。报纸上说,李兰芬负隅顽抗,以自杀对抗革命群众!
上星期,革命组织要她交代解放前她妈的情况。她说,那时还没我呢。让他们去找李兰芬。
李兰芬是母亲解放前的搭档。
母亲没有回来。前二天中午,上面通知她去送饭。她想告诉母亲李阿姨自杀的消息,但是她不想跟母亲搭话,怕……出门时,她回身又给母亲带了件衣服,就用那张报纸包了……
她像塞狗食一样,从门底下塞了进去,转身就跑。
“那不是启示她妈也自杀吗?”那个帖子说。
“她跟姓崔的是一个德性,只是她是女儿,她妈也会原谅她,我们又何必愤愤不平呢?”跟帖说。
她一下子傻掉了。她说不明白当时的动机——难道那张报纸真的是催命符吗?!
其实,李阿姨后来又活了,而母亲竟真的一去不返了。
她恍惚了很久,母亲的脸老在眼前晃悠,一会儿是素面朝天,一会儿淡妆浓抹。不知是灯光的缘故,还是窗帘的缘故,她老觉得母亲就在身边,耳边是挥之不去的鼓板的声音,似乎在演戏,好像是《桃花扇》,她在“骂贼”……这戏她演过多次,李香君血溅若桃花……血,哦,一摊血……母亲跳楼了……
杨小娟六十七岁那年,天天到母亲坟前唱“骂贼”……
秋千
戏开始了,李青梅坐在秋千架上。丫鬟轻轻推着,一晃一晃,让人不禁茫然起来。
四十年前演这出戏时,自己还是少女模样;没想到,一晃成了老年李清照,再演婀娜姿态,竟有些生疏,到底是老骨头老脸了。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不来香港也有三十多年了。天下大变那年,也曾来香港避居数月,虽有点落魄,毕竟是“剡剧小姐”,采访的采访,邀请的邀请,与达官贵人多有过从。如今再来,虽号称“艺术家”,却不过一老妪罢了。
昨晚的欢迎宴会,倒还有些排场。只是,腔调变了。一代风华,如今都凋谢了,无论拿叉拿盘,都硬手硬脚,举杯祝酒,也带着三十年革命的气息。
好些人都不认识了。
席间,一个穿着旗袍的贵妇走过来,说“李小姐,你还认得我吗?”李青梅总觉得面善,却一时答不上来。她说:“你当年到边疆去,我父亲还特地到火车站迎接你呢!”——原来她竟是曹司令的女儿。
多少年了?李青梅扳扳手指。她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上头找她谈话,鼓励她支援边疆,扎根边疆,说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也就是说,剧团要外迁。她一时不知所从,但还是表态:我去做动员工作,就是只剩我一人,我也会孤身前去!
“不,你要带着你的剡剧团一起去!”领导温和地说。
顿时,团里炸开了锅。她隐隐感知,是有人排挤她。犹记得那次复演《李清照》时,某人曾陪同领导坐在下面,那眼神有说不出的味道。但领导说,这是组织的决定。那时,她的《李清照》多红啊,不逊于某人的《梁红玉》。只是,自己仅仅是一个角儿,而某人已是剡剧界的代表人物。
同行三分仇,果然!
她在边疆,几度想重排《李清照》,总不如愿。结果,让她移植了《梁红玉》,仿佛她只是某人的影子而已。这使她越加相信是某人搞的鬼——司令他们是粗人,知道什么。
这一回,赴港演出,终于一了夙愿,重排了《李清照》。但是,她也有苦恼,就是无法完美再现少女李清照的情态——她太沧桑了。
焉得不沧桑?
当戏演到国破家亡,李清照孤身奔赴江南之时,李青梅的每一段唱,都声情并茂,仿佛杜鹃啼血,如泣如诉,如怨如慕。
这人的命运啊,就像秋千,晃荡来又晃荡去。
与李清照一样,李青梅同样遭遇了不幸。她一度曾是座上宾,可不久就沦为扫厕所的下等人。剧团砸烂了,有六七年时间,她一直扫大街、捅下水道。司令都被打倒了,世界翻了个个儿,她还能在舞台上闺房闲坐手捧诗书吗?就是做梁红玉、穆桂英都不行了。她的手越来越粗糙,越来越像松树皮。无人时对镜自照,做戏中情态,兰花指都像老梅枝了。
有一回,她捅了一天的下水道,起来时晕倒了。
一个裹着头巾的女同志,把她扶到树下,把围巾围到她身上,说:你受苦了,一切总会过去!她事后想想,总觉得有些蹊跷:她认得我?她是谁啊?
昨天,曹司令的女儿说“当年你扫大街时,我曾扶你起来”,让她忽然重又记起这件事。“那是你吗?是你,真的是你!”李青梅盯着看,不由激动起来。
“其实,解放前我就是你的戏迷了!”
当年,剡剧大盛,投票评选“剡剧小姐”,是娱乐界的一件大事。为此,戏迷们奔走相告,为各自的偶像拉票。据传,女子中学还有人发动全体学生,投票给李青梅呢。
“没想到,原来就是你啊!”
“那时,我是学生会干事。记得还到后台来找你签字呢,不知你还记得否?”
两人的手不由得握在一起,只是已不是当年的手。当年签字,手似玉葱,轻轻一挥,龙飞凤舞。那个“梅”字,她还特意练过,连体一笔,结尾来个大甩,就像是挥洒水袖一般。
“你可知道,当年你带团到边疆来,也是我帮父亲点的将!”
“什么,是你?”李青梅心里一沉,但脸上依旧挂着笑容。多少年来,她以为决定她命运的是某人,没想到竟是眼前的这个人。而某人跟自己一样,也曾被隔离多年,看来大家都是苦命人,更别说谁决定谁了。
如今曹司令已经调到北京,女儿定居香港,而只有自己依旧远离剡地。
李青梅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
想当年蓬莱春状元红,
酒阑歌罢玉壶空。
菊花笺上落珠玑,
锦绣文章入杯中。
……
李清照的手掠在满头白发上,唱完了她最后的戏。
李青梅演老年李清照最拿手,仿佛她就是李清照似的,一唱就让人动容。邂逅曹司令女儿,让她一夜无寐。没想到,今次来港,竟也是她牵的线搭的桥,这让她悲欣交集。人说贵人相逢,她可算得?就像荡秋千,荡来荡去,总还是秋千架下。而此刻,当老了的李清照坐在秋千架上,陷入深深的回忆之时,她感觉仿佛是在回忆自己的一辈子。
戏完了,帷幕渐合。
她依旧坐在秋千架上,久久不愿起来……
寒窑
午后的阳光,在车外跳跃。王素琴的耳边,一直围绕着孙怡香的声音。五十多年前,与她公演《评雪辨踪》的那个午后,她俩在过戏。她一时着迷,竟忘了接下句。
孙怡香的声音好听极了,清正优雅,字字送听。
与她排戏,总是要失神。有时她伏在孙怡香身上,做小女子状,因为孙怡香是演小生的。大家就笑闹一番。
但是,后来自己做了团长,就不好这样了。
车在乡间公路行进。秋后的田地,显出衰败的迹象。有的撂荒着,有的种着几行菜。王素琴一头银发,比这农田更衰老。她已经有三十年没来这里了。当年被管制劳动,整整八年,就在这里度过。与她同一组的是孙怡香,但她早三年走了,走之前,留下了她仅有的三元四角钱。
在舞台上,她们一个是小姐,一个是书生,谁曾想到会成为“做窑”人。
她记得很清楚,有一回她在窑内“出砖”,突然晕倒了。是孙怡香,又是按摩,又是掐人中,硬是把她从死神边拉了回来。其实,她当时已尿血很久了。
“妈,是这里吗?”
“应该是这一带,但是,好像一切都变了。”
正好路边的地里有一个农夫,王素琴示意停下来。农夫也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一打听,才知道干校的八一窑场早没了,转过那个村子,河边荒地里有一摊乱石头,就是当年的窑址。王素琴让儿子带她过去。他们在庄稼地里摸摸索索前进,又熟悉,又陌生。果然,乱草丛中,还有些地基,这是窑棚,这是窑基,两厢是晒泥坯的地方,再过去些,是埠头。这些年,她经常梦见自己与孙怡香在窑边,一会儿好像在演《评雪辨踪》,刘月娥走出窑洞翘首远望,吕蒙正冒雪而来;一会儿又变成自己搬着砖瓦坯子往窑洞里送,孙怡香擦着满脸的汗在里面接应……
她一直想回一趟八一窑场。戏里的刘月娥与吕蒙正,能寒窑苦守——她与孙怡香呢?
儿子要回美国了,若再不让他陪去,怕是没得机会了。一想起美国,她就感到不安,仿佛有心病似的。自从那年孙怡香滞留美国,与女儿团聚之后,她很少回来。近些年气氛和缓了,来过三次,可是三过团部而不入。孙怡香在访谈中只谈自己演的角色,搭档的戏一概不谈。王素琴看了,到底有些悲凉。做人一辈子,故人是越来越少了。
王素琴在荒地中颤颤巍巍地走着,一脚高一脚低。儿子扶着她。一棵孤零零的树,在荒草夕阳中,茕茕孑立。她扶着这棵树,感到了自己的虚弱。再怎样凌厉的个性,在岁月中都会风化成婆婆妈妈。若是廿年前,她不会这样多愁善感。
“你回不回去?”
当初她就是这样严肃地质问孙怡香的。可是,孙怡香却云淡风轻,她只想趁这次剡剧团来美国演出的机会,留下来,与孩子共享天伦之乐。反正,过不了几个月,她就可以退休了。
终于,她说出了一句严厉的话:
“那你以后就不是剡剧团的人了!”
也许是这句话伤了人心。孙怡香也是多少年的剡剧人了,她俩是同一个村子走出来的同科姐妹,一起唱戏,一起闯江湖,就是“文革”都没能让她们分开,临到老了,竟要这般决绝!
孙怡香离开时,侧了一下脸,似乎想回头,但终于还是走了。
可是,她不知道,当时的局势,多么紧张。走出寒窑才几年,过来人焉能不知这又是一个紧要关口?有消息造谣说,她们将滞留美国,这无异于叛逃。作为团长,她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回国。
“原轿去,原轿回,一个都不能少!”
她的坚定立场,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但是,毕竟少了孙怡香,仿佛她王素琴带团出了什么大事似的——外人怎么看呢?
有五六年,孙怡香的退休手续,一直搁着。很多人都在背后传,是她作的梗。
后来,据说“有人”悄悄地替孙怡香办了。
这么些年过去了,人们再也不提这件事,包括那场风波。但是,她依然觉得自己没做错。当然,孙怡香也没错,就像她如今对儿子恋恋不舍,希望他多呆些日子一样。
这个午后,她在窑场废墟边呆了很久。
回来时,她随带了一块完整的瓦片。这当然不是秦砖汉瓦,却是当年的一个见证。一路上,她黯然无语。
儿子临走的那个晚上,她把他叫到了自己的房内。打开一个匣子,里面就是那块瓦片。
“你把这个匣子带给孙阿姨,就说这是妈从八一窑场的遗址上带回的。”
那一晚,她做了个梦,梦见窑场上风云突变,她心里很急,就是迈不开步。她大喊:“阿香,阿香,要下雨了!”话音刚落,果然暴雨如注,她和孙怡香辛辛苦苦做的砖瓦坯子,化为了一摊烂泥……
半夜惊醒,但见窗外,一弯红红的下弦月。

